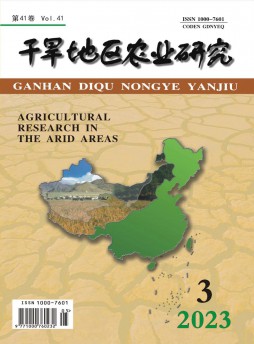地區財政管理變遷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地區財政管理變遷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財政管理與運轉問題關乎到國家興衰,遼在占有幽云十六州后,統轄部分山西地區,而遼統轄下的山西地區是其重要財賦來源之地,遼朝極為重視。遼朝以西京建立為分界點,在西京建立前,山西地區的財政問題應由南京三司統一管理。在圣宗開泰年間,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出現過一次小的變革。興宗重熙年間設立西京后,這一地區的財政運轉問題逐漸明朗起來,由西京轉運使司負責。
關鍵詞:遼代;山西地區;財政;西京
區域財政的管理與運轉關乎到國家的治理和統轄,以游牧民族契丹族為主體所建立起來的遼王朝,吞并幽云十六州后,兼治部分華北地區,山西北部區域在其治下,成為其重要財賦來源之地,對遼朝經濟至關重要。在現階段關于遼代財政問題的研究中,[1]尚未出現對山西地區財政運轉問題的專門研究。本文重點研究遼代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并探討整個遼代時期山西地區財政管理變遷及運轉狀況,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遼朝對山西地區的經略及統轄
遼代對山西地區的經略到最終實現對其統治的這一過程,早在阿保機建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史載:唐天復五年(905年),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乞盟,阿保機與李克用會于云州(今山西大同),結果拔數州,盡徙其民以還。[2](P2)此后,遼朝開始大規模頻繁地掠奪山西、河北等漢地,太祖建元神冊之后。神冊元年(916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于青冢南。”[2](P11)神冊三年(918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為大內惕隱,命攻云州及西南諸部。”[2](P12)天贊二年(973年),“夏四月癸丑,命堯骨攻幽州,迭剌部夷離堇迭烈徇山西地。”[2](P20-21)在《遼史•太宗本紀上》中也記載著,天贊元年太宗隨太祖經略各地方的情況:“及從太祖破于厥里諸部,定河壖黨項,下山西諸鎮……所向皆有功。”[2](P27)太宗時期,遼對山西地區的經略已由掠奪轉變為對其進行政治上的統治。“天顯五年(930年),春正月庚午,皇弟李胡拔寰州捷至。”[2](P33)“天顯九年(934),冬十月丁亥,略地靈丘。”[2](P36)十一年(936后)“九月丁酉,入雁門,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2](P40)會同元年(938年),是遼經略山西地區的一個新階段,后晉石敬瑭獻幽云十六州給遼,遼盡有幽云十六州之地。其中包括山西地區的朔州、應州、云州、寰州。大同元年(947年),太宗克晉入汴,對山西地區的控制進一步加強。遼代所統治的山西地區的州縣名稱詳見下表:
二、西京建立以前山西地區的財政運轉
從契丹建國前開始經略山西地區到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建立西京,這期間有130多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問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太祖到圣宗統和年間太祖時期,遼朝對中原地區僅限于掠奪、攻打階段,對于這些地區財政問題的治理辦法并沒有確立起來。至太宗會同元年(938年),遼兼制幽云十六州后,升幽州為南京后,遼代的南北面官體系中南面官系統逐漸確立起來。大同元年(947年),遼太宗克晉后,對山西地區的統治進一步穩定。但這一時期山西地區的財政是如何進行管理的,史料并沒有明確的記載。至穆宗時,在《遼史•本紀》中出現了一條關于云州地區農業情況的記載,應歷二年(952年)“九月甲寅朔,云州進嘉禾四莖,二穗。”[2](P70)另外,在穆宗應歷五年(955年)和圣宗乾亨四年(982年)分別出現了總領山西事之職。應歷五年耶律屋質“為北院大王,總山西事”。[2](P1388)乾亨四年“冬十月,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2](P1425)在圣宗統和四年(986年)“十一月辛丑,詔以北大王蒲奴寧居奉圣州,山西五州公事,并聽與節度使蒲打里共裁之。”[2](P134)三人中,耶律屋質、耶律勃古哲在遼史中有傳記記載。從二人的傳記中來看,領山西事之職應不包括山西地區的財政問題,而是以軍事職能為主,而且,圣宗統和四年正值遼宋戰爭之際。雖然耶律屋質的傳記中所記并不明顯,但在耶律勃古哲的傳記中可以看出勃古哲出任總領山西事之職的原委。傳中記載“圣宗繼位,太后稱制,會群臣議軍國事,勃古哲上書陳便宜數事,稱旨,即日兼領山西路諸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燕,勃古哲擊之甚力,賜輸忠保節致主功臣,總知山西五州。”[2](P1425)可見勃古哲兩次出任領山西諸州事,均是因為在軍事上表現突出,所以會授予其領山西事之職,以統領改地區的軍事事務。圣宗繼位后,關于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問題,似乎有跡可循。圣宗統和元年(983年)九月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之。”[2](P119)在統和四年(986年)時,北宋分三路攻打遼朝,結果“寰州”、“朔州”、“應州”、“靈丘”等地,皆叛附于宋。遼以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蒲領為南征都統,以副于耶律休哥,來應對北宋對遼的軍事行動。在北宋與遼的這次戰爭中,圣宗在同年四月,曾命南京三司發放軍資,統和四年“四月己未,休哥、蒲領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2](P130)山西地區是這次宋遼戰爭中的前沿陣地,圣宗令南京三司補給軍需,恰恰說明,山西這一地區的財政應由南京三司監管。而且在同年的六月“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2](P130)這很可能就是對四月份“給軍前夏衣布”的回復,百姓所納三司的布帛達不到軍前所需,故增之。此外,在《遼史•食貨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圣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奏言,民艱食,請馳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2](P929)說明,此時山西地區的財政由南京三司統一管理。
(二)圣宗開泰年間《遼史•本紀》圣宗開泰三年(1014)“三月戊申,南京、奉圣、平、蔚、云、應、朔等州,置轉運使。”[2](P175)相應地,在《遼史•百官志四》中,在南面財賦官轉運司職名總目條下有奉圣州轉運使司、平州轉運使司、蔚州轉運使司、應州轉運使司、朔州轉運使司的記載。圣宗在開泰年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地方行政上的改革,根據《遼史•地理志》記載,圣宗在這一時期曾大范圍的在中京置縣。在《遼史•本紀》中,圣宗對南京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開泰元年(1012)“改幽都府為析津府,薊北縣為析津縣,幽都縣為宛平縣,覃恩中外。”[2](P171)從這兩方面來看,圣宗在山西各州設置轉運使司,也是其所進行的一些改革和嘗試。而且,遼朝也有因臨時所需而設置辦事機構的習慣,設立轉運使司的州南部都瀕臨宋境,所以在這些地區設立轉運使司的原因,應與兩國之間的榷場貿易有關。圣宗開泰年間,距離遼宋戰爭已過去十年,作為整個遼代經濟的咽喉地區,山西及幽云地區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也應是其大范圍置轉運使的原因。另外,遼西京多邊防官,出于供給軍需的需要,也是其設置轉運使司的原因。圣宗太平三年(1023年)“十二月壬戌,郎玄化為西山轉運使”,[2](P214)因為《遼史》中其它處,均記為“山西轉運使”,所以認為此處“西山”應為“山西”的誤記。那么“山西轉運使”的出現遠在西京建立之前,對這一情況,我認為此時的“山西轉運使”所管轄的區域不同于西京設置之后的區域,范圍應只包括山西地區的幾個州。從各州分置轉運使司到郎玄化擔任山西轉運使,期間不足十年,這可能是由于地區財政上的過于分治,不利于對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而又將這一地區的財政統歸山西轉運使管理了。這也為西京設置后,如何處理財政問題提供了借鑒。至興宗設置西京后,西京統轄的地理范圍擴大,所需要解決的財政問題也不僅是山西地區,故而設置正式的理財機構———西京轉運使司來進行西京地區的財政管理。
三、西京設置后山西地區的財政管理
遼興宗重熙年間,鑒于山西地區經濟的發展及與西夏關系的緊張,遼朝為了更好穩定山西地區,在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為西京,設立大同府,山西地區財政,則統一有西京處理。
(一)西京設置的原因遼、北宋、西夏呈三足鼎立之勢,三者之間的關系往來影響著各政權的政策動向。西京的建立與遼、西夏、北宋之間民族關系的變化有著深程度的原因,尤其是遼與西夏之間的關系。遼與西夏的民族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太宗—圣宗時期,二者為藩屬國關系;興宗時期,西夏李元昊建號稱帝,力圖擺脫遼朝的羈絆,獨立起來。道宗—遼亡,二者又恢復為藩屬國關系。興宗設置西京,正值二者關系的第二階段,遼與西夏的關系惡化。[4](P130)其關系惡化的原因即設置西京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太平十一年(1031年),圣宗崩,興宗繼位。同年“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2](P241)七年后,重熙七年(1038年),“夏四月己巳,以興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2](P248)公主死因不明,生前與李元昊不睦,并且死于李元昊稱帝當年,這對遼與西夏之間的關系造成了影響。第二,在遼與西夏的交界處,居住有一部歸屬于遼朝的黨項族,在李元昊稱帝后時常入侵這部分黨項,《遼史•本紀》中載:重熙十二年(1043年)冬十月,“壬子,以夏人侵黨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2](P229)重熙十三年(1044年)夏四月,“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黨項等部叛附夏國”,“丙辰,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2](P231)正是出于對西夏作戰的需要,以及西部邊防的穩固,興宗著手設置西京。另外,西京南部地區,與北宋相鄰,西京的建立也有利于遼對北宋的防御。《遼史•百官志四》中記載:“遼有五京,……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也正印證了西京設置的原因。
(二)出任山西轉運使的人員情況及其職能據統計,遼一代出任山西轉運使的共有五人。另外,還有一人出任過權知轉運事一職。其民族及任職時間等詳見下表:五京計司雖然機構名稱不同,但其所履行的職能應是大同小異的。根據耶律儼傳中記載,在耶律儼出任山西轉運使后,“刮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2](P1558)其基本職能應包括征收賦稅、發放官員的俸祿,另外,西京與西夏、北宋邊境相鄰,根據《遼史•食貨志下》記載:“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有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2](P929)還應負責管理兩國邊境上的榷場貿易。此外,從其他四京計司的職能,也應包括賑濟災民、調撥軍餉,管理所轄范圍內的鹽課、坑冶、商麯等基本事務。
四、結語
遼代山西地區的財政運轉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兩個時間段:太祖至圣宗統和年間以及圣宗開泰年間;第二階段為西京建立之后與其他四京計司一樣,西京轉運使司雖然設置時間較晚,但在遼代的經濟發展中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終隨著西京的建立,財政管理問題走向了正規化和制度化。無論是西京設置之前,將山西地區的財政問題歸屬于南京三司管理,還是圣宗開泰年間在各州分置轉運使司,都為西京建立后,山西地區以及整個西京地區的財政管理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借鑒和經驗。西京的建立,使山西地區的財政問題得以解決,遼代的南面財賦官體系也得以完善。
參考文獻:
[1]關樹東.遼朝州縣制度中的“道”“路”問題探研[J].中國史研究,2003(02):129-143;
蔣金玲.遼代南面財賦機構考[J].求索,2012(03):230-232;
向南,楊若薇.遼代經濟機構試探[J].文史,1983(07):105-121;
王民信.遼代的理財機構———五京諸司使及南面財賦官[J].書目季刊,1976(02):91-102.
[2](元)脫脫等撰.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武玉環.論遼與西夏的關系[J].東北史地,2008(04):61-65.
[4](宋)葉隆禮.契丹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4.
[5]向南.遼代石刻文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向南,張國慶,李宇峰.遼代石刻文續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
作者:陳德洋 付亞洲 單位: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
- 上一篇:淺談新事業單位會計制度財政監督范文
- 下一篇:金融危機下家庭金融投資與風險規避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