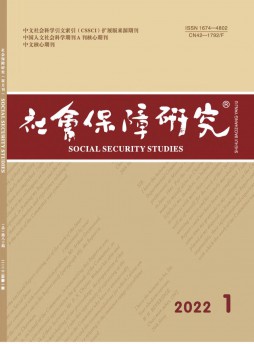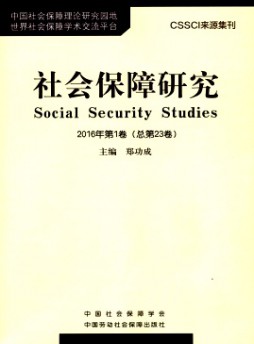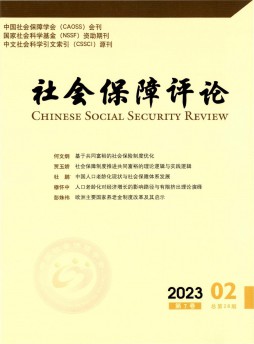社會保障稅的性別敏感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保障稅的性別敏感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背景
稅收政策中的社會性別問題,無論對于稅收學研究,還是對于婦女/性別學研究而言,都是一個頗具新穎色彩的命題。其實,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各類公共政策,對于不同的利益群體,將會產生不同的社會經濟影響,這本是常識層面的問題。而在各類群體劃分中,性別分類則是最為重要的類型分布之一。在精細化管理中,需要從跨部門的視角,考察稅收政策對男女兩性的經濟社會影響及其差異,并通過性別敏感分析與回應,提升現實稅收政策的作用效果。稅收政策的性別影響分析,源自于社會性別預算(GenderBudget)的研究。對社會性別預算的研究,最初集中于財政支出領域,之后逐漸發現預算收入環節,尤其是稅收政策的制定,同樣會對男女兩性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對稅收政策性別影響的研究,也是社會性別預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政策對不同性別的勞動者具有不同影響,國外學者多依稅種分類來考察不同稅種對男女兩性的影響,主要包括稅收政策給不同性別帶來的勞動供給變化、家庭勞動時間變化、收入變化、就業及生活水平變化等。對于稅收政策中的性別因素,目前主要是域外學者的研究,國內研究中,除馬蔡琛等(2009),馬蔡琛、劉辰涵(2011)在社會性別預算研究中,探索性地開展了稅收政策的性別影響分析外,總體上處于空白狀態。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依性別分類進行的經濟分析中,稅收政策性別影響的研究仍然相對匱乏,為數不多的研究也多為定性分析,相關定量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稅收政策性別分析的理論基礎:稅收性別歧視與無酬勞動
1.稅收性別歧視
隨著時代的進步,稅收制度也在不斷完善,并反映著社會和文化的普遍規則。而這些規則中也包含著性別歧視,這種歧視在某些稅收制度中也或隱或現地體現出來。稅收政策通常包括兩種性別歧視(Stotsky,Janet.1997a):顯性性別歧視和隱性性別歧視(explicitgenderbiasandimplicitgenderbias)。顯性的稅收性別歧視大多表現在特定的稅法條款中,這些條文對男性和女性采取區別對待的方式。顯性的稅收性別歧視,因其主要基于對稅法條文的解釋,故相對容易分辨。例如,20世紀70年代以后,加拿大政府受到供應學派稅收理論的影響①,不斷提高其失業保險稅的受益條件,規定某些重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工人(如因撫養子女停業后重返崗位的女工),無權享受失業保險[1]。但是,在現代稅制中,這類顯性的性別歧視已經相對少見。隱性的稅收性別歧視,即基于社會工作分配或經濟活動造成的對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響。如對某些女性就業比例相對較高的行業征收重稅,實際上就屬于一種隱性的稅收性別歧視。隱性性別歧視主要是因為稅收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未能充分考慮性別差異而造成的。
2.照料經濟與無酬勞動
照料經濟(CareEconomy),也稱基于照料勞動的經濟,是指對人的直接照料活動,包括涉及生育、照料他人和創造安全且具親和力的社區等所有活動[2]。由于這些照料活動發生在家庭內部,提供者也以家庭成員為主,因此往往被看作一種“愛和情感的付出”。將家庭的照料勞動和家務工作歸于私人情感與社會規則的后果之一,就是公共預算在分配資源時未能充分考慮這部分的利益訴求,現實生活中照料勞動主要由婦女以無報酬勞動的方式承擔。在現行的國民經濟賬戶(SNA)核算中,無酬勞動的價值也不計入,使得在分配公共資源的時候,往往忽視了這些女性無酬勞動者的潛在需求。照料經濟和無酬勞動在稅收政策制定中十分重要。首先,忽視照料經濟和無酬勞動往往導致隱性或顯性的稅收性別歧視。例如,在坦桑尼亞的個人所得稅收入認定上,家庭產業的收入被認定為丈夫的收入,而忽視了妻子從事家庭產業的勞動價值[3]。其次,忽視無酬勞動和照料經濟的稅收政策,事實上會加重女性勞動者的負擔(因為女性往往承擔了大量的無酬勞動),抑制了女性的市場勞動參與率,進而導致稅基的相應減少。最后,在稅收政策中,如果適當考慮照料經濟和無酬勞動的貢獻,對增加女性勞動供給具有重要影響。例如,在個人所得稅的家庭聯合申報中,給予育兒補貼,女性就可能選擇將孩子送到專業育兒所,自身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取工作報酬,以增加社會勞動力的有效供給。
社會保障問題中的性別因素,可以上溯至16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烏托邦”構想中,關于孕婦、產婦、哺乳婦女以及嬰兒對受到社會保護、享受專供飲食的美好追求。近期的研究,則包括Oppenheim和Harker(1996)對于男女之間社會保障項目不公平提出的指責[4]。其研究顯示,一些與婦女特別相關的津貼(如一般的生育獎勵)逐步被取消,其他津貼(如未成年子女津貼、單親父母津貼等)亦變得不再那么慷慨[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社會保障體系的轉型,其中社會保障稅一直是屢屢言及卻鮮有實質進展的改革動議。社會保障稅征繳效率高且成本低,體現了社會保障籌資手段優化與效率提升的制度優越性[6]。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社會保障稅實際上是一個由養老社會保障稅、醫療社會保障稅、失業社會保障稅等諸稅種組成的復合稅收體系。不同的社會保障稅制設計,也會產生相應的性別影響差異,主要體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社會保障稅與男女退休年齡之間的性別影響
根據各國人口統計數據,男女壽命存在一定差別,女性壽命較男性要長,退休后需要享受保障的時間也較長。據衛生部的統計資料,中國2009年的人口預期壽命為73.1歲[7],其中男性為72歲,女性為75歲[8]。根據美國社會保障署的《全球社會保障》統計,男女法定退休年齡不一致的國家有67個,退休年齡相同的有98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中,英國、意大利、奧地利、巴西、阿根廷、智利男女退休年齡分別為65歲、60歲;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均為60歲、55歲;東歐國家和澳大利亞男女退休年齡也不一致[9]。同時,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一般低于男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顯示,2008年各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本國的總勞動參與率相比,均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如表1所示)。并且,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女性收入與男性收入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2009年,國際勞工大會上提交的一項報告中就明確指出,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的等量工作工資平均只有男性的70%~90%。國際工會聯合會(ITUC)2009年對20個國家進行的勞動力統計分析也得出,平均性別工資差距高達22.4%,男性處于優勢地位②。經合組織(OECD)2010年的研究報告則顯示,其成員國正式職工收入存在著17.6%的性別工資差距(其中,差距較大的有韓國和日本,分別超過40%和30%)③。根據中國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2005年全國女性就業人員月均收入為465.51元,僅為男性月收入的67.75%[10]。伴隨著我國從“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向“部分積累制”或“完全積累制”的轉型,勞動者退休后領取的社會保險金,與其個人賬戶積累關系越來越大(即社會保險稅的個人積累賬戶基金越多,退休后可以享有的社會保障金就越多)。然而女性一方面收入較男性低,并且退休年齡較男性提前,實際工作時間較短,所以社會保障稅(或社會保障繳款)個人賬戶積累基金與男性相比,難免會相對較少。同時,因為女性平均壽命較男性更長,故女性退休后需要的社會保障時間段也相應更長,這進一步加劇了女性養老金水平的相對差距。此外,對一些學歷較高的女性勞動者,她們因求學導致開始工作時間較晚,而其所在技術型工作崗位,即使超過退休年齡也仍可繼續勝任。對這一高知女性群體而言,這種社會保障稅制設計就顯得更加不公平。
2.社會保障稅中再分配效應的性別影響
在稅制結構設計上,盡管社會保障稅通常具有繳款上限的規定④,但其與個人所得稅一樣,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應。也就是說,通過社會保障稅補充社會保險基金,使得一部分國民收入從高收入者轉向中低收入者。在許多國家,社會保障基金由公共財政體系承擔“兜底”責任,對于繳納社會保障稅的低收入勞動者,事實上也存在著一定的財政補貼。此外,各國社會保障稅制體系中,勞動者退休后領取社會保障數額的計算方法,對中低收入者也比較有利。如在美國的社會保障稅體系中,對社會安全金的計算,主要是設立兩個計算點:680美元和4100美元,分別分配以不同的權重。對一個月收入5000美元的勞動者來說,假定其收入保持不變,退休后可以領取的社會安全金為:680*90%+(4100-680)*32%+(5000-4100)*15%=1841.4美元⑤。單純就計算方法而言,低于兩個計算點的收入占社會安全金的權重較大,這對中低收入者是比較有利的。因此,就社會保障稅的再分配效應而言,至少在理論推演層面上,社會保障稅的性別影響表現得對女性更加有利。因為女性無論在經濟地位上還是收入水平上,通常比男性勞動者要低。單純從這一性別分析視角來看,社會保障稅的實施,應該是有利于占低收入者較大比重的貧困女性的。
3.社會保障稅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日本的案例
由于社會進步以及習俗的變化,社會保障稅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固化的社會保障稅制度,反而會對女性勞動者的就業率和就業質量,產生負面影響。日本的社會保障稅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規定,厚生養老金和共濟養老金的被保險人,其無業配偶年收入不超過130萬日元,或勞動時間不超過普通勞動者的3/4,就可視為第三類被保險人,無需繳納社會保障稅也可獲得“國民年金”。這一規定是與日本二戰后普遍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相適應的⑥。然而,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第三類被保險人制度,未能充分考慮雙職工家庭、單身職業女性等自己繳納保險費者的利益。對單一戶主家庭(尤其是單身母親家庭)、單身女性家庭等生活較困難群體,缺乏養老保障方面的特殊考量。這樣就從制度上固化了不盡合理的性別分工模式,因為只有“丈夫工作、妻子做全職主婦”的模式選擇,才更能體現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日本的社會保障稅模式所可能造成的性別歧視主要體現為雙職工家庭和“男主外女主內”家庭之間的不公平。單身職業女性工作期間需按月繳納高額的養老金(即社會保障稅),而婚后如果不選擇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則難以享受“第三類被保險人”減免養老金繳納額的優惠待遇[11]。此外,只有公司雇員的妻子,才可以享受這一福利,個體經營者、農民的妻子卻無緣享有。從社會公平的視角來看,對某一類型的女性提供額外優待,似乎有悖于就業政策的性別中立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在女性參與勞動比例越來越高的發展趨勢下,這種做法也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有工作能力和熱情的已婚女性的工作積極性。
4.社會保障稅的遺屬保障和配偶津貼
第一,遺屬保障(allowanceforthesurvivor)。由于通常女性壽命比男性長,并且在婚姻中男性往往較女性略為年長,故而喪偶女性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作為社會保障稅機制設計的單獨方面,來加以重點考察。很多女性晚年喪偶,而之前的家庭養老中,男性的社會保障金往往較多,占退休后家庭總收入比重很大。這時社會保障稅制設計中的遺屬保障金,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很多情況下,一對年老夫婦的生活費用,很大程度上依靠丈夫的社會保障金,喪偶后的老年女性生活難免會陷入窘迫。采用遺屬保障制度,通過對喪偶的女性給予一定的保障金補償,可在相當程度上保證其晚年正常生活。第二,配偶津貼(spouse’sallowance)。往往存在這樣的情況,家庭中女性僅為家庭主婦,負擔家庭勞動、照顧子女老人,未能正式就業或者僅從事臨時性兼職工作。雖然她們為家庭和社會做出了貢獻,但并沒有獲得相匹配的收入。這些無酬勞動應該得到政策上的補償,配偶津貼恰恰考慮了這一因素。家庭中的低收入者,由于從事了大量的無酬勞動,以致未能通過市場來獲得貨幣收入,其繳納的社會保障稅自然較少,所以獲取的社會保障金也相對較少。配偶津貼通過對這類家庭中的低收入一方發放額外津貼,以有效保障其家庭生活。四、中國社會保障稅政策設計中的社會性別因素由于我國尚未正式開征社會保障稅,而僅為具有一定社會保障稅功能的“五險一金”制度,其中最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在擬議的社會保障稅制度設計中,需從以下方面就性別因素加以必要考慮:第一,實行與社會保障稅相配合的高學歷女性彈性退休制度。我國各行業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頗為不同,地區發展也極不均衡。強制要求女性在55歲退休,會使得一些尚具勞動能力并愿繼續工作的女性,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僅對經濟發展不利,且因退休后養老金收入與個人賬戶相關(退休前個人賬戶積累越多、工齡越長,退休后所能獲得的收入也越多),對于那些因求學導致開始工作時間較晚的知識女性尤為不利。因此,可以考慮對高學歷女性(如博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女性)施行彈性退休制度。對于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但仍具備繼續工作能力和意愿的知識女性,并不強制退休,而是采行尊重其個人意愿的彈性退休制度。這種做法在繼續發揮知識女性社會貢獻的同時,也豐富了社會保障稅的稅收來源,合理推遲了社會保障專戶的支付啟動時點。第二,在社會保障稅制設計中,適時引入遺屬保障金和配偶津貼繳款等救濟性規定,為喪偶遺屬和夫妻一方為低收入者的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這類繳款可以納入現有的養老保障繳款體系中,也可待社會保障稅統一開征時,再行綜合考慮。注釋:①供應學派經濟學(Supply-SideEconomics),又譯為“供給經濟學”,是20世紀80年代初葉風行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理論之一,其核心理論體現為主張減稅以增加有效供給的稅收思想。供應學派經濟學家強調通過改革稅制結構,特別是降低稅率,允許自由市場經濟中的刺激因素發揮作用,進而鼓勵儲蓄和生產。進一步論述可以參閱:韋特•P•甘地等的《供應學派的稅收政策———與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性》,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②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性別平等處于體面勞動的核心位置》(報告六),第98屆國際勞工大會,日內瓦,2009年。這20個國家分別是阿根廷、巴西、智利、丹麥、芬蘭、德國、匈牙利、印度、意大利、韓國、墨西哥、荷蘭、巴拉圭、波蘭、俄羅斯、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③見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工作中的平等:不斷的挑戰》,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關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則和權利宣言》的后續措施要求編寫的綜合報告。第100屆國際勞工大會,日內瓦,2011年,21-22頁。國際勞工組織北京局網站,www.ilo.org/ilc/ILCSessions/99thSession/reports/WCMS_154784/lang--fr/index.htm。④在各國社會保障稅實踐中,通常對于超過一定數額的工資部分,不納入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范圍,這就是社會保障稅的“累退性”。⑤計算方法來自金葵花保險網,www.xiangrikui.com/yanglaobaoxian/changshi/20101119/74271.html。⑥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這一制度與男女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馳,也不符合日本政府希望男女發揮各自價值、共同參與社會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