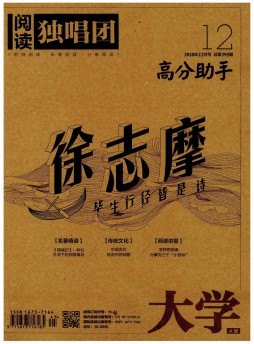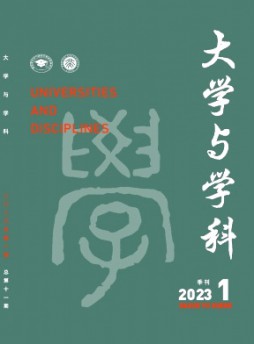大學文化視域下的院校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大學文化視域下的院校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701年,美國耶魯大學創始人對蘇格萊大學的組織結構之綜述和研究被認為是院校研究的最早發端。二戰后,由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高校管理的復雜化,院校研究在歐美高等教育界興起并迅速流行開來。1965年美國院校研究協會成立,通常被看作是這一新領域正式形成并且組織化的標志[1]。如今,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等眾多美國高校都成立了相對專業且獨立的院校研究機構。院校研究已成為美國大學管理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美國高等教育長期獨霸世界的格局。作為舶來品,由于歷史原因,院校研究在我國起步較晚,大約在20世紀70—80年代,才被引入我國,最初主要是對國外院校研究學術論著的介紹、翻譯。隨著我國對高等教育戰略的調整,在高校擴招、其辦學自主權的逐步放開以及高等教育市場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開啟了我國院校研究的中國化進程。2000年3月,華中科技大學院校研究發展研究的中心成立,標志著院校研究在我國的正式興起[2]。國內院校研究在歷經“感知階段”和“認知階段”[3]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關注并從事院校研究的專業人士,如華中科技大學的劉獻君和趙炬明、蘇州大學的周川、北京大學汪慶華、南京農業大學的劉曉光和南京師范大學的蔡國春等。
除了對國外院校研究成果進行介紹之外,學者們開始立足我國國情,探尋院校研究的本土化實踐以期解決高等教育的現實問題,從而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促進高等教育事業。尤其是2003年10月我國首屆院校研究學術研討會的順利召開標志著我國院校研究已初步形成規模。但與美國院校研究相比,中國院校研究的氛圍不濃,許多大學領導對院校研究缺乏足夠的興趣和認知,大學的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夠,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了解程度還很低,高校還普遍缺乏開展院校研究所需要的最基礎的數據系統[4]。這或許也是我國院校研究一直以來不能深入且無法充分發揮其作用以解決高校現實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大學文化與院校研究的內在性關聯
美國高等教育專家布魯貝克指出,大學確立其地位主要有兩種途徑,也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是,以認識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二是,以政治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5]。前者強調大學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功能,后者強調大學的社會適應性。大學的本質是一種功能獨特的文化組織[6]。作為大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院校研究與大學文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1.大學文化認識論取向與院校研究目標的一致性英國學者邁克爾•吉本斯指出,現代知識的生產與傳統的知識生產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現代大學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是可以實現來源于不同途徑的現代知識相互交流的最重要場所[7]。知識運動常常與問題解決過程結伴而行。大學的院校研究主要是針對單個特定高校實際運行中的問題,結合相關理論,通過相關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診斷,以試圖解決高等教育問題。同時,院校研究主要是為了提升該校領導層管理決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換句話說,院校研究追求高校管理效能,能夠營造民主、科學、有利于知識傳播的環境。院校研究過程有助于知識運用與傳播、同時又將會產生新的知識。
2.大學文化的政治論取向與院校研究的目標具有同一性自中世紀大學誕生以來,大學的職能從培養人才到發展科研,再到服務社會的發展過程,每一次都是大學適應社會的調整過程。這與潘懋元先生曾提出的“教育的外部規律是教育要與社會相適應”是一致的。大學合法性是社會需要,大學唯有適應社會才不會被社會淘汰。正是由于高等教育適應了社會發展變革的大趨勢,作為組織機構的高等教育才得以保存、延續并基業長青[8]。院校研究是結合一定的理論,針對單個高校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運用科學手段進行的研究。這些研究對象與社會需求變化有關或直接來自社會變革,基于院校研究結果的決策將更加有助于使大學適應社會得以生存、實現其服務社會的功能和使命。
3.院校研究發展與大學文化建設兩者之間相互促進就文化本身而言,是抽象、無形的,需要借助于具體的載體進行表現。實現存在的、具有不同校情的院校既是大學文化的體現者,也是大學文化的創新者、建設者。院校研究立足于特定高校進行研究,使高校領導們更理性、清醒地全面掌握本校情況,推進決策的科學性。決策改變行動,行動影響思維,思維建構文化,從而實現對大學文化建設的推動作用。再者,整個院校研究過程絕不是“文化無涉”的純客觀活動,即研究主體帶有一定的思想、以具有某些文化傾向性的理論為指導,研究對象處于特定的大學文化氛圍之中,研究結果的解釋、運用同樣處于研究者和決策者的文化影響之下。因此,先進的大學文化可以推進院校研究。
三、我國院校研究的文化審察
1.大學管理文化的行政化傾向阻礙院校研究現代大學肇始于歐洲中世紀大學。在西方,盡管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知識經濟、全球化等諸多社會變革的洗禮,但大學的精神實質,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民主管理、兼容并包等原則始終保持穩定,成為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精神內核[9]。然而,在我國,由于歷史因素,我國高等教育制度深受原蘇聯的高等教育體系的影響。自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的自上而下、高度計劃、統一集權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成為大學行政化嚴重的根源。盡管自1985年以來,國內針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政策性文件相繼出臺,但改革目標偏移、改革對象模糊、改革主體缺位以及改革路徑不明[10]等因素使大學“去行政化”舉步維艱,依然停留于理論探討。大學行政化的具體內容包括管理大學的行政化與大學管理的行政化兩個層面,前者指政府與大學的關系;后者指在大學內部的行政權力居于主導地位[11]。來自大學內外的行政權力桎梏、甚至破壞了大學文化,使其徹底失去了獨立自主性,嚴重影響了院校研究。首先,院校研究機構及其研究人員缺乏獨立性。“院校研究在高校中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工作崗位,具有身份和研究上的獨立性。”[12]國外在院校研究方面比較發達的國家,大多數高校設具有獨立性的院校研究機構,并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專業化人員。如,美國“常春藤聯盟”大學,院校研究機構人員配置的特點突出表現為“小團隊”和“專業化”兩大特征[13]。國內院校研究機構,大多隸屬高校行政部門,研究者以非學術型教師系列的行政人員為主。由于行政權力的主導,院校研究人員往往以學校行政部門說了算為榮,研究人員的研究行為只對上級分管院校領導負責,校領導則只對上級政府部門負責。如此,自下而上,向自己每一級的上級領導負責,看似秩序盡然,但實際上易迎合領導個人理念、背離院校研究的目標,院校研究成了為行政體系的政策做注腳。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缺乏科學性。數據是院校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國外的院校研究機構都有規范、可靠的數據來源。例如,美國高校院校研究數據系統的建設狀況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囊括了全校各種數據的完整規模數據庫;第二種是院校研究機構直接從學校各業務處理數據系統里定期提取數據,建立自己的數據庫;第三種是根據學校各個部門以書面或電子形式提供的數據,院校研究機構建立數據庫;第四種是院校研究機構直接使用業務數據處理庫[14]。建立于客觀數據分析基礎之上的研究科學性強、可信度高、影響力和執行力強。相比之下,我國長期以來的院校研究一直處于迎合行政權力的研究狀態。完整數據系統的建設是學校各個部門相互協作的結果,然而,在高校行政化體制下,權力形態的早熟和膨脹,就會導致對行政權力“一把手”不夠重視或欠考慮的事情無法開展研究或結果極不理想。因此,數據的缺失已成為國內院校研究客觀存在的事實。再者,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晉升機制都是其社會結構的核心[15]。由于院校領導由上級任命,早已是官僚體系的成員,他們深諳我國官僚系統的晉升條件:聽話和維穩。而披露關乎全民利益的真實信息往往會招來大眾的強烈批評,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尤其是近年來,在高等教育對社會資源的優先使用且消耗量增大、大學學費上漲、人才培養質量有下降之嫌而備受社會各界質疑的情況下,為保守起見,大學忽略真實數據已成為常態。實在不然,數據作假也成常用手段,這些假而空的數字對院校研究的分析、交流與共享毫無益處。
2.大學學術文化功利主義傾向影響院校研究一個多世紀前,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就曾指出,經濟的迅速增長打破原有的社會關系,在該情況下人們容易接受新的觀念,同時社會也容易失去發展方向[16]。19世紀下半葉,美國《莫里爾法案》的簽署打破了洪堡時代“純粹學術研究”的局面,開創了大學服務社會的先河。此后,世界范圍內各國大學先后走出象牙塔,不同程度地走進社會、邁向市場。市場的邏輯就是迎合大眾,將一切變成商品販賣以實現資本貪婪繁殖的本性。市場的本質是功利的,唯利是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功利主義的典型特征。市場規則、競爭法則被引入大學,功利主義在高等教育系統大行其道。傳統的大學學術文化曾經作為社會精英的代表,正在被功利主義嚴重侵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資源成為高校生存的基礎,資源的稀缺性必然帶來高校內部學科領域發展的不均衡。投資少、見效快、收益大的學科和領域成為重點與優先關照的對象,而那些建設周期長、經濟收益不明顯或收益速度較慢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則大大受限,大學整體的學術景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效益成為考察大學學科專業領域發展的主要指標。院校研究的目的是為院校管理提供決策支持,屬于幕后輔助性活動。到目前為止,國內這方面的研究結果主要以理論為主,處于“務虛”階段。院校研究的性質決定了它不可能在短期內立刻產生經濟效益。而且,許多大學領導對院校研究缺乏足夠的興趣和認知,大學的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夠[17]。因此,院校研究處于高校資源分配的邊緣地帶。復雜問題的解決過程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進行客觀、公正的院校研究需要研究人員堅守大學核心理念、守得住寂寞、專心治學。反觀當下的高校考核機制,重數量、重實利,功利性極強。年終考核、職稱評定等功利主義因素,無不時刻催促著研究者縮短研究周期、快速發表成果。作為社會上的高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內部的知識生產者、文化創新者,其智力本不該輕易受到外界利益的誘惑而為之打敗。但如今面對現實壓力,院校研究者們也不得不放棄學術理想進行自救。市場的力量和經濟利益消解了大學人的傳統學術文化,外在消極的功利主義因素給院校研究帶來了沉重打擊。
四、結語
“如果把一所大學比喻成一輛汽車,那么,領導是駕駛員,院校研究就是這輛車的儀表盤。”[18]信息化時代的大學要實現科學、高效、可持續性發展就離不開院校研究,院校研究已然成為現代大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外部規律表明,來自外界的政治環境、經濟結構等因素都會對院校研究的發展帶來影響。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教育的外部規律只能通過內部規律來實現[19]。大學的本質是一個功能獨特的文化組織,大學文化之于大學,正如土壤、空氣、水分、陽光之于植物的生命一樣,須臾離開不得[20]。對我國大學院校研究有著深刻作用的正是來自于內部的大學文化,大學文化對院校研究的影響隱蔽且深刻。大學文化具有價值導向、目標激勵、行為規范和情感凝練等功能,是大學人共享核心價值體系的精神家園[21],是院校研究擺脫外界負面因素的干擾、起穩固學術價值作用的“錨”,是進一步規范院校研究學術行為、激勵并引領院校研究者在時代潮流中堅守學術理念、勇往直前的內在靈魂。錢穆先生說過,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以大學文化視角審視院校研究發展成為一種應然。在劇烈變動的社會環境下,大學要實現更好的生存,迫切需要變革大學文化。院校研究立足于高校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試圖促進實際存在的不同院校發展決策的科學化,營造科學民主的大學文化氛圍。解決大學問題的過程是解決大學文化問題的過程,也是推動大學文化發展和創新的過程。
作者:繆紅燕 單位:南通大學 現代教育技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