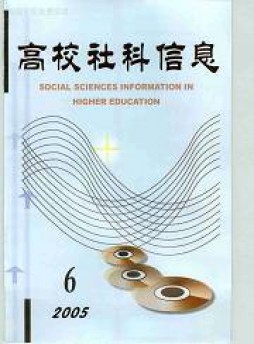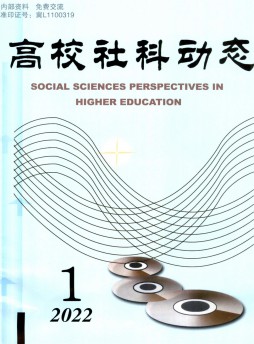論高校博物館傳承大學文化體系的構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高校博物館傳承大學文化體系的構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高校博物館的歷史和文化是大學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文章以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為例,探索了高校博物館如何傳承大學文化并構建相應的大學文化體系的內容。首先探討了高校博物館與大學文化融合的過程,從最初為教學提供實習資源和為科研提供資料的大學教育輔助機構開始,逐漸過渡到滿足和挖掘觀眾的博物館教育需求,再到以藏品為媒介傳承大學文化。其次,對大學文化進行了解構,指出高校博物館在傳承大學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構建了高校博物館傳承大學文化的體系,即立足專業,奠定高校博物館在大學中的地位;開發觀眾需求,以大學文化引領觀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消費需求;招募和培養大學生志愿者,在面對面的服務中展示、傳承和宣揚大學文化;分解大學文化層次,從博物館角度展示和傳承大學文化。
關鍵詞:高校博物館;大學文化;文化體系;構建
作為大學文化傳承和展示的最重要的場所之一———高校博物館不僅承擔著大學教學實驗室以及科研資料室的功能,也成為了大學對外的形象標識之一。高校博物館是大學對外展示的重要的名片,在一定意義上是正規的大學學校教育和非正規的社會公共文化教育的結合體。大學在育人和化人的過程中,堅守育人目標———為國家培養有德、有用、有才、有為的建設者,圍繞教育目標的達成和校園文化的建設而引發的教育理念的調整、教育與教學活動的改進都成為了大學文化的內涵和外延。
一、高校博物館與大學文化的融合
自從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高校博物館在英國牛津大學建成后,高校博物館取得了與大學學術地位相匹配的重要地位。鴉片戰爭后,清朝狀元實業家張謇面對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發現了教育救國、興國的重要意義,在1902年創辦了我國較早的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為了給學生提供教學實習機會、培養務實創新精神,在1905年建立了我國第一所高校博物館———南通博物苑。這表明,我國的高校博物館一出現就非常明了自己的目標———基于教育并服務于教育[1],并以教育目標來驅動收藏和展示功能的呈現。下面以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的發展為例,探討高校博物館與大學文化的融合過程。
(一)建館初心,輔助教學實習與科研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的前身是成都地質學院教學陳列室,是在建校之后的第四個年頭———1960年建立的,1962年,學校把現存的幾個地質陳列室合并在一起,更名為成都地質學院陳列館,包括巖石、礦物、礦產和古生物。在當時,陳列館的管理人員主要由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擔任,同時,陳列館根據學校教學目標的要求和國家對礦產大量的需求狀況,對教學計劃、內容、形式等進行了調整,創建了以教室和陳列館為主的室內教學場所和以野外地質考察和勘探為主的室外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在學校的師生共同努力下,不僅編制了1:100萬的四川大地構造圖和四川成礦預測圖,而且研究領域也擴大到了地史古生物、礦床等。陳列館與學校的教學和科研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不僅為學校師生提供理論和實物的證據,同時,師生又以自己的學識,通過野外采集和征集的途徑,為陳列館帶回大量的標本反哺陳列館藏品的數量和品種。以化石完整率較高且個體較大者著稱的合川馬門溪龍由我國恐龍之父———楊鐘健教授研究后,于1965年落戶成都地質學院博物館,成為該館最珍貴的鎮館之寶。該化石作為重要的教學標本,為學校的地質學、地史學和古生物學的教學和科研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培養了很多杰出的地質學家和恐龍專家,如邊兆祥、竺國強、何信祿、蔡開基、李奎、歐陽輝、王正新、楊春燕等。
(二)重新開館,順應改革開放的潮流陳列館在1966年至1978年之間因為的影響而閉館。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祖國的發展帶來了煥發出生命活力的春天,成都地質學院陳列館順應學校教學需要也重新開館了。學校的教師經歷了的災難后,更加地珍惜自己的青春年華,以強烈的報效祖國的信心和激情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中。1980年,陳列館更名為成都地質學院博物館,由我國著名地質學家邊兆祥教授任館長。針對當時地質學教學的改革要求,首先重新調整了教學課時的設置,即課堂教學課時占總學時70~80%,實習和實驗課時占總課時的20~30%;其次,針對實際教學中暴露出的室內教學中的一些問題,如對標本的感性認識欠佳、對理論系統的理解不足等,邊兆祥組織全校師生收集、整理資料,結合標本和書籍,設計并繪制了如巖石、礦物、礦床、古生物、生命起源與演化等普通地質學的系統教學內容。該舉措讓博物館成為了學校教學實習不可或缺的場所,同時,也為學校教師的科研提供資料,從而成為了與大學的地質學學術地位相互映襯的地位,這些舉措為博物館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2]。博物館順應時代的發展,敏銳地意識到了社會民眾對神秘的大學文化和大學博物館藏品探秘的需求,借助學校30周年校慶的機會,于1986年實施了全年360天對外開放的舉措。赫赫有名的合川馬門溪龍骨架化石成為了成都地質學院的象征和標志。博物館隨著學校的發展,在1993年更名為成都理工學院博物館,在2001年更名為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同時,隨著博物館人對博物館功能認識的深化,對博物館的公益性質中的社會教育功能進行了充分發掘。博物館既有專門為教學活動開展而專設的主題教學實習室,也有迎合觀眾需求而擴充的展廳,陳列的精美礦物、寶玉石、古生物標本、海洋標本等吸引著社會各界人士。之后,隨著藏品數量和種類的增多,以及觀眾對博物館文化消費需求的發展,又增設了觀賞石展區、仿真恐龍展區,并改建了生命起源與進化陳列廳[2]。
(三)物以載道,文以化人博物館藏品是人類歷史文化和自然文化見證的重要物件。在對藏品進行收集、整理和展示后,還需要深入發掘藏品的文化價值,通過物件的身份信息、歷史信息等的解碼和重構,以達至其文化價值引領和化人的功能。對藏品本身進行研究以及拓展的博物館教育活動,不僅讓博物館自身潛力得到挖掘,也讓博物館有了更加強大的生命力。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缺失的中侏羅世恐龍資料在四川自貢找到了,博物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從此開始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研究工作,為博物館和學校贏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省部級三等獎和地質礦產部“八五”優秀科研集體獎等,這些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迅速的轉化為學校的教學實習資源和案例,以及開展科學教育和培養人文情懷的博物館教育的物件。通過研究藏品本身在歷史中的故事以及附著在以藏品作為有效記憶物件上的人的故事,成為了大學文化中培養大學生人文情懷的有效途徑之一。如校友鄔宗岳冒著生命危險從珠穆朗瑪峰海拔8000多米以上采集并捐贈的二云母花崗巖標本,該館老師冒著鵝毛大雪在四川榮縣親自征集的大型斜層理標本,該校老師以學識、智慧和真誠感動老鄉后分文未付的情況下征集的層狀方解石標本,該館老師不懼山路崎嶇和道路的艱險,頭頂烈日甚至有的老師因為高強度勞動暈倒后繼續在山野采集的何氏通安龍標本……每每徜徉于這些故事中的時候,無論是大學生、老師還是觀眾,都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故事中的人和事與物,在博物館中立體起來了,那些具有人文情懷的故事和博物館展品融合在了一起,讓博物館的教育不再是生硬的,而充滿了人文的情懷。大學不再僅僅是知識本身的傳授者,而是大學生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或理性[3]。
二、解構大學文化傳承大學文化
(一)大學和大學文化大學的英文是“university”,其原初的意思是“大而全的宇宙”,根據原初意義的演變,大學是一個通過建立起探尋知識和智慧的學習共同體進而促進高尚人格的養成,從而成為引領社會發展的思想中心和精神家園。大學文化的內涵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豐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解讀,有的同意大學文化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環境文化的觀點,有的同意大學文化包含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觀點。綜合比較后認為:大學文化作為一個體系,由五個金字塔形狀的子系統組成。該金字塔從下往上依次為:第一層是位于基層的物質文化體系,包含景觀文化、環境文化、標識文化和文化傳播載體;第二層是制度文化體系,包括決策與執行文化、組織與人事文化、管理制度文化;第三層是學術文化體系,包括學術道德與學術風氣、學術氛圍與學術環境、學術傳統和學術聲譽;第四是行為文化體系,包括校風等大學風氣、行為規范和榜樣文化;第五層位于最頂端的精神文化體系,包括大學精神、校園價值、辦學傳統、辦學特色、辦學思想和辦學理念[4]。
(二)解構大學文化,傳承大學文化荷蘭哲學家馮•皮爾森認為:“文化是人的活動,是堅持尋求增進、變化和改革”[5]。大學文化是大學在辦學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固定下來的并成為該校傳統的文化。諸如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喬治亞大學、德國的洪堡大學、中國的北大、四川大學等不僅有世界一流的博物館,還有屬于自己特色的一流的大學文化,博物館自身發展融入了大學發展的過程中,并且相互促進和相互融合,為大學文化的豐富增加了素材和資源。1956年建校的成都理工大學是響應建國之初國家百廢待興的國情而建立起來的中國第三所地質院校。教師和干部來自重慶大學、西北大學和南京大學、北京地質學院、東北地質學院、中南地質局等30余所高校和機關。來自天南海北的文化和智慧交融在一起,互相交流交往和影響,形成了既多元又逐漸有了大學的特色“篤行、勤奮、求實”的大學文化,并逐漸成為了成都東郊片區的文化名片。改革開放后,學校因為解決了干部和職工家屬的一些具體問題,從而讓成都成為了教職工的第二故鄉,他們身上煥發出的青春活力和激情為大學文化注入了濃墨重彩,“窮究于理,成就于工”正式成為了學校的校訓。該校訓鼓勵師生在日常的工作、學習中學會學習,探究事物內在規律,并以理論為指導,通過真抓實干的實踐獲得成就和成功;同時,體現出理工大學文化的厚重與博大,蘊涵了“厚德、博學、篤行、勤奮、求實、創新”的深刻內涵。成都理工人在傳承理工文化方面不僅有繼承,而且有創新。首先是立足于大學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和豐厚的人文精神;其次,師生把文化元素通過不同的展示形式和載體融入到學習和生活中,如學校的校刊、校報、社團雜志、運動會、社團文化活動、志愿者活動、迎新晚會等。通過這些文化表現形式和載體,逐漸豐富并傳遞著大學文化的深刻內涵,讓每一個理工人都以成為理工的一員而驕傲和自豪。
三、高校博物館傳承大學文化體系的構建
大學文化對社會觀眾的吸引力越來越強,高校博物館則是邀請社會觀眾的名片之一,對作為教學輔助單位的博物館文化體系的構建其實質也是大學文化體系的構建。
(一)立足大學傳統專業,傳承大學文化高校博物館必須立足于學校傳統優勢專業,整合校內外資源,才能更好地傳承大學文化的精髓。高校博物館的建筑、景觀、藏品、展品是大學文化的濃縮和展示,只有為學校教學提供優質的教學實習資源以及為科研提供第一手資料才不會被邊緣化;同時,博物館通過對展品和展線的設計,從而充分發掘、宣傳和弘揚大學文化,不僅可以有效地擴大大學文化的影響力,而且可以通過博物館鏈接起厚重的經過時間和空間積淀下來的大學文化。更為重要的是,部分觀眾還可以通過博物館教育活動的開展解決現實生活和學習中的部分社會問題乃至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問題。成都理工大學傳統優勢專業有地質、能源、資源科學、核技術、環境科學等,對校內外相關專業的教學提供實習資料,以及為校內外的科研提供重要的一手研究資料。四川師范大學的地理系學生、西南石油大學等學校也借助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的實物標本,一方面為學生提供了教學中感性認識,從而增強了實物與理論的結合,深化了教學內容的內涵和外延;另一方面,教師提供的現場講解和演示,教師個人形象和魅力,讓學生建立起個人與教育內容的關聯性,促成學生以自己可以理解的具個體特征的全新的觀念和方法看待世界,從而內化為學生個人的知識體系和精神上的滿足感。
(二)開發觀眾需求,普及科學知識和培養人文情懷博物館觀眾的成分、層次、教育背景、文化需求及需求強度、對博物館教育認知程度存在相似性和差異性,高校博物需要向社會博物館學習,突破大學管理體制和機制的限制,在經費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開發和發掘觀眾不同層次的需求,包括學習科學文化的教育需求、休閑娛樂需求、聚會交友需求等。根據對博物館觀眾的研究,高校博物館觀眾主要是該校師生、青少年和兒童,其他的大部分觀眾是由孩子的需求而“被領進”博物館的。所以,博物館在把握科學性、真實性的基礎上,還需要增強互動性和參與性;同時,要以大學優勢傳統專業為基礎設計相應的展覽主題,以傳遞大學人文精神、校園文化價值為目標來設計有故事有意義的展線或展覽,吸引觀眾一次次走進博物館。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根據觀眾對大學文化需求的特點,設計了相應的寶玉石專題、礦物巖石專題、生命進化與演化專題、恐龍專題等不同主題的展覽以滿足觀眾的不同需求。同時,根據兒童心理和生理發育特征,設計了有意義的系列親子體驗活動,不僅讓觀眾在博物館中尋找到自己精神所需,而且也促使觀眾一次次走進博物館,把博物館當作休閑娛樂的場地和交友聚會的好去處。
(三)培養大學生志愿者,助力大學文化的傳播高校博物館中的志愿者大部分是以本校大學生志愿者為主,而大學生在對該校的校園文化的習得、理解、解讀、傳播等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大學校園的空間與環境、大學文化的情景與意境等最能為大學生所把握,并成為大學文化的天然的傳播者,而經過博物館專門訓練的來自不同院系的大學生之間的文化碰撞,更是為大學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增添了新時代的氣息。而在博物館這個小的空間里的交流和互動也促進了各院系文化之間的融合,更為重要的是為各志愿者充分深入理解自己大學的大學文化創設了有意義的場境。大學生志愿者是高校博物館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既是從屬于一個文化盛宴傳播的學生社團組織,也是一個可以培養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志愿服務組織。首先,大學生充滿了朝氣和創新意識,善于接受新知識而且傳遞新文化的能力較強,所以,一般比較受小朋友和喜歡接受新鮮事物的觀眾的喜歡;其次,身處大學校園的大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大學文化成為了大學生本人的文化營養素和文化基因,在逐漸內化為大學生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的過程中,也在形成、塑造和發展著大學生本人的人格力量和精神豐盈的高度和深度。所以,大學生具有了對該校大學文化有較強的理解力和傳播能力,帶著大學文化的氣質直接影響著面對面的觀眾。
(四)分解大學文化層次,展示和傳承大學文化大學文化作為一個系統所具有的五個層次,前兩個層次———基礎的物質文化層次和制度文化層———是師生的所見所聞,能浸潤并影響師生的言行;學術文化層次和行為文化層次則演變成大學文化的內核和精神;最高的精神文化層次則逐漸成為該大學師生所具有的集體性意識形態,包括精神層面和思想理念層面,并成為了大學文化的靈魂和精髓。高校博物館以展品、科研資料、科普、教育等不同的方式呈現出歷史的厚重和自然的神奇,成為高校和社會大眾共享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構,始終以我國的教育目標為指導,通過不同途徑和方式方法達成的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的教育活動,直接以物、事和人與觀眾的靈魂進行溝通,逐漸影響和內化為觀眾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同時,高校博物館積極響應國家對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傳播,不僅創建不同的媒體,如辦理刊物、收藏并出版書籍、營建網站等,而且開展與實施具體的活動,如參與每年固定的地球日活動、博物館日活動、科普活動周、科普活動月、以館藏特色創設教育活動等,并成為大學文化的展示、傳播和傳承載體。神秘的大學正在以高校博物館為紐帶逐步向社會觀眾揭開面紗,其中,高校博物館在傳承大學文化過程中對大學文化體系的構建起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徐堅.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J].中國博物館,2015,4:11.
[2]陸遠,王正新,胡芳,等.成都理工大學博物館三十年的歷史沿革[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2:54-55.
[3]周本貞,陳璐,羅文.形勢與政策[M].科學出版社,2011,3.
[4]王永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大學文化體系要素相關性分析[J].經濟師,2010,6:16.
[5]袁昌仁.教師文化的多元功能反應[J].遼寧教育,2012,9:53.
[6]張洪鋼.論高校博物館社會教育功能的發揮[J].高教學刊,2018(08)
作者:羅德燕;趙仕波 單位:成都理工大學
- 上一篇:外語教學中的跨文化教育實踐范文
- 下一篇:新時代大學文化軟實力提升的探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