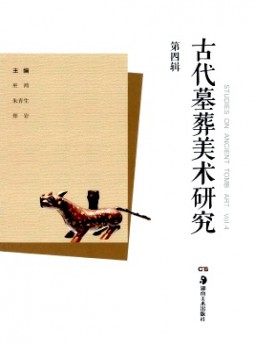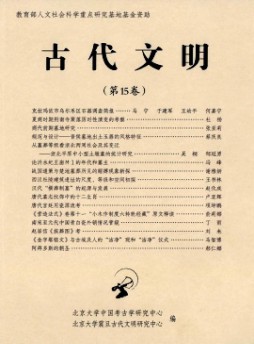古代戲曲互動接受的藝術效果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古代戲曲互動接受的藝術效果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古代戲曲的傳播接受呈現出場域形態的“多元化”與效果生成的“動態性”,其實踐主要圍繞文人曲家-藝人演員-讀者觀眾等展開,形成不同主體、不同場域、不同方式的對話互動,達到文本效果與場上效果的雙重審視,并表現為戲曲文本效果的接受評閱、場上效果的演賞互動等方面,從而發掘出戲曲效果研究的重要內蘊和時代意義。
[關鍵詞]戲曲;接受;效果;互動
古代戲曲的接受場域附著濃郁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質,同時呈現出場域形態的“多元化”與效果生成的“動態性”。“多元化”是指戲曲接受的參與主體紛呈,涉及文人曲家-藝人演員-讀者觀眾等,他們或評點切磋,或同場觀演,力求戲曲觀演的最佳效果。“動態性”則指戲曲接受不同于詩詞鑒賞停留于審美效果的靜態呈現和文本“價值”的表現,而更重視不同主體、不同場域、不同方式的“對話”,涉及文人的評點交流、舞臺本的改編傳播,場上演出時藝人之間、藝人與觀者之間的舞臺互動等,都會推動戲曲效果的直接生成,所以不同主體之間的對話互動也促使即時效果的精彩呈現。目前學界對于古代戲曲的接受研究漸成熱點,如趙山林《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總論戲曲藝術的傳播接受,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側重經典文本的接受研究等,但對接受效果的關注不多,僅有吳秀瓊《<哈姆雷特>的語體風格及其戲劇效果》等文。古代戲曲接受效果形成的豐富內涵顯然值得深入研究,這并不是簡單套用西方文論的接受理論,進行古代戲曲接受闡釋的具體實踐,而是二者存在共同對話的理論平臺。古代曲家如何面對戲曲“活”的綜合藝術,構建起豐富精彩的效果理論闡述,本文試圖梳理這一問題的重要內蘊和時代意義,從而展現古代戲曲“活”的藝術生態效果。
一、戲曲文本效果的接受解讀
傳統文學文本的接受多局限于作者-文本-讀者的單線路徑,至古代小說又增加了說書人、書坊主等角色。古代戲曲的接受形態則更為豐富,涉及戲曲文本的傳播接受與劇場舞臺的觀演反應,戲曲接受呈現出文本與場上效果的雙重表現。圍繞戲曲文本展開的效果審視,則有文人曲家自我創作的效果期待,文人讀者群體對于文本的鑒賞評點,藝人觀眾對于劇情的感應共鳴等,都是基于戲曲文本的文學元素得以鋪展,從而實現戲曲接受效果的互動演繹。一方面,古代戲曲文本承載著曲家的無限寄托,他們對此嘔心瀝血而成的文本,賦予不同程度的效果期待,希冀得到讀者觀眾的普遍認同。不少曲家意識到戲曲效果實現的艱辛與波折,故而感嘆“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期待“知音君子,這般另做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與妻賢”(《琵琶記》[副末開場])。另外,“有歡笑,有離折,無靈異,無奇絕,按父子恩情,君臣忠直,休言打動眾官人,直甚感動公侯伯”(《新刊重訂出像附釋標注趙氏孤兒記•第一出副末開場[滿江紅]》)。清醒認識到戲曲效果的直接影響。有些文人曲家甚至注意到隱含效果的實現,并在文本創作之初即已明言,如《荊釵記》“新編傳奇真奇妙,留與人間教爾曹,奉勸諸人行孝道”(《屠赤水批評荊釵記•尾聲》)。“荊釵傳奇會編巧,新舊雙全忠孝高,須勸諸人行孝道”(《新刻原本王狀元荊釵記•尾聲》)。明確提出希冀達到“勸人行孝道”的戲曲效果。另一方面,戲曲文本效果的能否實現,還需與接受群體進行互動交流,這既有文人讀者的接受評點,又有藝人觀眾的心靈感應。其一,文人曲家費盡才華而成的戲曲作品,能夠得到同行文人的擊節贊賞,可謂既是對文本效果的直接認同,又是對自我才情的高度肯定。同時作為作者的曲家也十分珍視讀者的評點反饋,孔尚任曾十分明確地說出:“讀《桃花扇》者,有題辭,有跋語,今已錄于前后。又有批評,有詩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頂,總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讀者,順筆書之,縱橫滿紙,已不記出自誰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愛。至于投詩贈歌,充盈篋司,美且不勝收矣,俟錄專集。”[1]1對于文人讀者各種方式的回饋表示出“知己之愛”的重視態度。可見,孔尚任一語道出文人讀者的效果回饋,體現為“投詩贈歌”和“評點論析”等外在形式。梁辰魚《浣紗記》曾風靡一時,王世貞有《嘲梁伯龍》:“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艷詞。”[2]625此外還有汪道昆《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胡應麟《狄明叔邀集新居命女伎奏劇凡玉簪浣紗紅拂三本即席成七言律四章》等,都直接贈詩表示觀戲之后的欣賞態度。有些文人并不滿足吟詩嘆賞,而是開始動手評點劇本,展開對戲曲文本的情緒表達和冷靜思索。評點文本體現出文人曲家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如《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第十四出《堂前巧辯》紅娘責備老夫人一段尾批:“這丫頭是個大妙人。”[3]150有時讀到情節生動或文辭美妙之處,直接簡言“好”、“妙”的欣喜之情,抑或“我欲贊一辭也不得”[3]150。有時甚至為之手舞足蹈或是悲傷流淚,如湯顯祖評《西廂記》第四折《佳期》:“讀至崔娘入來,張生捱坐,我亦狂喜雀躍。”[3]237
古代戲曲文本效果的實現,從讀者尤其是文人階層的接受內容而言,大致表現在對于戲曲主題和文筆才情的欣賞。洪昇作《長生殿》第一出《傳概》[滿江紅]即言:“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萬里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4]1所以剛問世時便有人稱“是劇乃一部鬧熱《牡丹亭》”,洪昇對此創作宗旨的評價“以為知言”[4]1。湯顯祖《牡丹亭》中杜麗娘超越生死的情感追尋,巨大的藝術魅力震撼無數青年男女,婁江俞二娘反復誦讀并再三品味,終而悲情過度斷腸而死,湯顯祖聽后也傷感不已作詩痛悼:“何自為情死?悲傷必有神,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5]710這些“天下有心人”的女性讀者,都是感于愛情的知賞共鳴。對文筆才情的肯定同樣如此,不少文人曲作極盡鋪衍藻麗之能事,如屠隆《曇花記》《彩毫記》等劇,“學問堆垛,當作一部類書觀”,而被時人稱為“才士之曲”,他們希冀的是“奇文共賞析”的審美效果。[5]20同時,多元紛呈的接受效果又逆向影響戲曲文本的再創作,身為作者的文人不僅在意讀者的評價意見,而且邀請他們直接參與戲曲文本的修訂潤色。湯顯祖早年創作《紫簫記》,好友孫如法就曾轉告:“嘗聞伯良(王驥德)艷稱公才而略短公法。”湯顯祖對此表示“良然”,并且希望日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6]171。清初洪昇創作《長生殿》經歷十六年的潤色修改,完成《沉香亭》到《舞霓裳》再到《長生殿》的轉變,前一次轉變正是接受懂詞曲的朋友毛玉斯的意見,認為與屠隆《彩毫記》近似故而“排場近熟”,“因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更名《舞霓裳》”。后一次華麗轉身則是好友兼“第一讀者”徐麟的意見反饋,并且經常一起“審音協律,無一字不慎”[5]1,所以才有“愛文者喜其詞,知音者賞其律”的文本效果。[5]228其二,文人曲家對于文本效果的主觀期待,不僅在于讀者群體的鑒賞評點,而且還有藝人觀眾的感應共鳴。孔尚任創作《桃花扇》“十載經營,三易其稿,博采遺聞,入之聲律,一句一字,抉心嘔成”,可是待他帶入京城希冀為人所識,卻是“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著眼看畢之人”,孔尚任為此“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1]2。即使如此他還是“轉思天下大矣,后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而當看到“金斗班”元宵演出時,特別贊賞“《題畫》一折,尤得神解”[1]2。后來孔尚任不斷看到自己作品得以精彩演出,并且受到觀眾的普遍認可,“群公咸集,讓予獨居上座,命諸伶更番進觴”,同時“座客嘖嘖指頤”,孔尚任也“頗有凌云之氣”[1]2。嘔心瀝血而成的作品終究獲得好的戲曲效果,也是曲家頗為欣慰之處。當然,文人曲家精心創作并且希冀的效果期待,還需演員的精彩演繹和觀眾的會心領悟,才能促使戲曲效果在此互動交流中完美實現。明末杭州女演員商小玲最擅長演《牡丹亭》傳奇,每次演到《尋夢》、《鬧殤》等出戲時,仿佛身臨其境而淚痕滿面,終于在唱到《尋夢》“待打并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個梅根相見”時,一并想起自己的相同遭際,悲痛地倒在舞臺上香消玉殞。《牡丹亭》一經演出就會招致婦女爭相觀看,為此而被詆毀為“導以淫詞,有不魂消心死者哉?”因為“熾情欲,壞風化”而一度被禁毀[7]29。這恰從另一方面透露出女性觀眾對《牡丹亭》的會心領悟,正是由于其富于強烈的藝術震撼力,才觸發觀眾的感動而引起轟動效果。
文本效果的互動交流有時也會存在某些誤解和不暢,讀者對于作品的誤讀不解,以及演員對于作者文本的妄加改動,也使得文本效果的實現形成不同層面的錯位和受阻。湯顯祖作《牡丹亭》招致當時不少文人曲家不合格律的批評,認為難以獲得較好的舞臺效果,故而他們紛紛動手改編才引起湯顯祖的不滿。洪昇《長生殿》因為“伶人苦于繁長難演,竟為傖輩妄加節改,關目都廢”。為此洪昇特意叮囑“當覓吳本教習,勿為傖悮可耳”[5]1。孔尚任作《桃花扇》一時轟動,不少文人曲家技癢難耐并動手改編曲本,“顧子天石讀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為《南桃花扇》。令生旦當場團圓,以快觀者之目;其詞華精警,追步臨川。”孔尚任也不得不表示遺憾之情,“雖補予之不逮,未免形予傖父,予敢不避席乎。”[1]1此外,演員根據舞臺演出的需要,也會對文本進行刪節改動而引起作者的不滿,“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負作者之苦心。今于長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改也。”同時,對于戲曲文本中的說白部分,“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謔,往往點金成鐵,為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字。”[1]9作為作者的文人曲家針對互動過程的錯位誤解,不得不表示出自己的明確態度。戲曲文本效果的實現還與出版流通領域的書坊主有關(明清時期不少曲家同時身為出版商,如汪廷訥等),他們主要著意外在形式的精益求精,如印刷紙張的選擇、刻工技藝的苛求、文本字體的斟酌等,試圖促使文本效果臻于完美,希冀為讀者所悅目賞心。其中戲曲文本的圖像本為輔助說明之用,使得內容表現得多樣化和形象化,正因為此,不少文人曲家與書坊主開始講究文本圖像的處理,如晚清著名的戲曲出版家劉世珩出版《暖紅室匯刻傳劇》,就是聘請當時名家為劇本增加補充精美的圖像,“舊有繡像圖畫,皆室人江寧傅曉虹(春姍)所模。無者補畫。畫者,錢塘汪待詔社耆(洛年)、長沙李貳尹仲琳、休寧吳縣尉子鼎、吳縣周布衣喬年。”[8]2戲曲文本的畫像不再僅是作為簡單的補充,而是融入戲曲文本成為效果實現的重要拼圖。古代戲曲在其發展的相當一段時間內,隨著文人群體大量介入文本創作,使得戲曲效果的實現大多停留于文本層面,與讀者交流密切的文本效果得到放大,成為案頭把玩賞讀的文學作品,而失卻戲曲場上效果的另一特性。戲曲作品一度成為文人曲家自我宣泄的載體,如屠隆感于才高背棄而作《彩毫記》以李白自況,抒嘆心中滿腹牢騷不平之氣,故而被評價為“學問堆垛,當作一部類書觀,不必以音律節奏較也”[9]20。這或許也是文本效果過于彰顯所帶來的弊端。
二、戲曲場上效果的演賞
互動戲曲效果更具特色地立體呈現還在于立足劇場舞臺,圍繞藝人-觀眾、藝人-藝人、觀眾-觀眾等主體之間的演賞互動,實現動容、動心、悅目、賞心的多元形態。不過,不同演出場所形成的演出效果也各自不一,如勾欄瓦肆、廳堂樓臺、酒樓茶肆、虎丘西湖等地,外化為觀眾的會心一笑、或鼓掌歡呼,或低眉抽泣、或吶喊震天,都是以舞臺為中心表現出的不同戲曲效果。舞臺劇場效果的精彩實現,既有藝人自身的修養熏陶、技藝精湛,又有藝人與藝人之間的心有靈犀、同臺對戲,藝人與觀眾之間的情感溝通、演賞互動,同時作者主觀的劇本設計即已關注舞臺演出的需要,冷熱場的調劑、文武戲的中和等,以及劇場布置,舞臺道具、背景、服飾、化妝等斟酌,都為舞臺效果的最佳呈現鋪墊準備,成為共同影響場上效果的諸多元素。其一,“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曲者居其半也。”故而“作曲者與唱曲者,不可不相謀也”[10]179。舞臺效果的精彩演繹與文本創作的前期鋪墊密切相關,文人曲家同樣究心于戲曲文本場上效果的實現。明末清初阮大鋮《石巢戲曲四種》、李漁《笠翁十種曲》等劇,都著意結構關目的新奇、舞臺表演的鬧熱,從創作者角度介入場上效果的多層建構,有的甚至直接參與指導戲曲表演并提出修改意見:“是書義取崇雅,情在寫真,近唱演家改換有必不可從者,如增虢國承寵、楊妃忿爭一段,作三家村婦丑態,既失蘊藉,尤不耐觀。其<哭像>折,以哭題名,如禮之兇奠,非吉奠也。今滿場皆用紅衣,則情事乖違,不但明皇鐘情不能寫出,而阿監宮娥泣涕皆不稱矣。至于舞盤及末折演舞,原名霓裳羽衣,只須白襖紅裙,便自當行本色。細繹曲中舞節,當一二自具。今有貴妃舞盤學浣紗舞,而末折仙女或舞燈、舞汗巾者,俱屬荒唐,全無是處。”[5]1洪昇分別從情節處理和舞臺表演方面指出乖違“崇雅”、“寫真”的審美標準,從而難以實現其預期設想的場上效果。其二,藝人在場上表演的精彩與否同樣關系效果期待的實現,他們或完全忠于劇作者的本意兢兢表演,或根據舞臺演出的需要動手刪改,對于戲曲場上效果實現起到較為關鍵的作用,故而元代胡祗遹從形態舉止到歌唱表演提出“九美”之說,明代潘之恒《與楊超超評劇五則》總結出“度、思、步、呼、嘆”的表演五要素,都意在探究提升藝人的表演技藝,達到最佳的舞臺形象與表演狀態。
藝人不僅要求自身技藝水平高超,而且藝人與藝人之間也須藝逢對手,才能取得較好的場上效果。《消寒新詠》記載了不少優秀的藝人搭檔,如集秀揚部小旦倪元齡與貼旦李福齡,“年歲相若,身材頡頏,即技藝亦相上下。”“元齡宜笑,福齡善哭。”“論怡情,福齡少遜元齡之風致;論感懷,元齡不如福齡之逼真。各有好處,不容沒也。”最難得的是二人“同歌合演,如《水漫》《斷橋》《思春》《撲蝶》《連廂》以及《忠義傳》之扮童男幼女,彼此爭奇,令觀者猶如挑珠選寶,兩兩皆愛于心,莫能釋手。斯誠一對麗人,可稱合璧者也”[11]64。二人之間不僅心心相惜而且藝逢對手,高手之間的心靈默契鑄就了場上經典的表演瞬間。其三,從觀者層面而言,“樓上所賞者,目挑心招、鉆穴逾墻之曲,女座尤甚;池內所賞者,則爭奪戰斗劫殺之事。”[12]254雖然來自不同的地域、階層導致關注不同的欣賞目的,但是場上效果的追求無非兩個層面:既要“看戲”又要“看藝”。“看戲”重在戲曲表現內容即情感體驗而言,如《清忠譜》《桃花扇》等反映現實的作品曾引起明末清初的觀眾強烈反響,但有些觀者對戲曲內容早已爛熟于心,所以這時更在意“看藝”即領會表演者的技藝,如“靜如處女,動若脫兔;重如泰山,輕若鴻毛”的形體美,“聲要圓熟,腔要徹滿”,還要“眼靈睛用力,面狀心中生”,“有意有情,一臉神氣兩眼靈。”潘之恒說自己“觀劇數十年”,而“今垂老,乃以神遇”[13]44-45,已經上升到講究神交的境遇。清末譚鑫培演出《天雷報》(《清風亭》),觀者“并肩累足,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余地”,無非欣賞譚鑫培的精彩表演,“慷慨激烈,千人發指”[14]5120,還有譚鑫培扮演的張元秀痛斥忘恩負義的張繼保一節,引得觀者“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氣不能泄,故竟不去”,直到張繼保被天雷擊死,觀者“乃相率出門。時雷雨方來,霑塗顛躓者,踵趾相錯。早去刻許可免,而人人意暢神愉,雖牽裳蒙首,扶掖而行,而口講指道者,……咨嗟嘆賞,若忘饑餓,天雨道滑不顧者,評笑百出,旁觀疑癡”[14]5120。當然二者也有不合之處,如彭天錫“多扮丑凈,千古之奸雄佞倖”[15]202,與清末名凈黃潤甫等,觀者既為其所演人物而深惡痛絕,又為其表演技藝之高超而歡呼叫絕,在看戲與看藝的分裂沖突中獲得強烈震撼的舞臺效果,真是“作戲者瘋,看戲者傻”。[16]88故而,藝人-觀者的互動演賞影響場上效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方面藝人的精彩表演帶動觀者情緒的變化,鋪展較強的舞臺效果;另一方面觀者的欣賞反應也影響藝人的表演,甚至促進他們技藝的提升。藝人的精彩表演帶來轟動的場上效應多有記載。袁中道《游居杮錄》記載萬歷年間一次演出:“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造此堂既成,招石洋與予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17]81清代王載揚《書陳優事》記載陳明智飾演楚霸王時,在場觀眾“皆屏息,顏如灰,靜觀寂聽”,等到結束才“哄堂笑語,嗟嘆以為絕技不可得”[18]198。張岱《陶庵夢憶》記載演出《冰山記》時“聲達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嚄唶。至顏佩韋擊殺緹騎,嘄呼跳蹴,洶洶崩屋”[15]271。可見藝人的精彩表演所帶來的震撼效果。
觀者的欣賞反應也反過來影響藝人的場上表演,所以不少藝人十分在意觀者的在場情緒。程長庚“性獨矜嚴,雅不喜狂叫,嘗曰:‘吾曲豪,無待喝彩,狂叫奚為聲繁則音節無能入。四座寂,吾乃獨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則徑去”[19]725。認為觀眾如果隨意喝彩則會影響表演的順利進行,從而導致“音節無能入”的尷尬效果。潘之恒《鸞嘯小品•技尚》記載無錫鄒光迪家班表演時,“主人肅客,不煩不苛,行酒不嘩,加豆不迭。專耳目,一心志,以向技,故技窮而莫能逃。”[13]44-45正是如此環境才有利于藝人才能的最佳發揮,“拜趨必簡,舞蹈必揚,獻笑不排,賓白有節,必得其意,必得其情。”[13]44-45藝人的精彩表演同時又使觀眾深受熏染,出現“坐中耳不寧傾,目不寧瞬,語交而若有失,杯舉而亟揮之”[13]44-45。這樣良好的互動效果直接推動戲曲藝術的最佳演繹。觀者的在場態度和反映也大概在于兩方面:一方面無論是喝彩歡呼還是羞辱倒喝,都會影響藝人現場表演水平的發揮,如徐珂《清稗類鈔》記載清末北京皮黃戲演出場面:“販夫豎子,短衣束發,每入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采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而同。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客群焉指目,必致嘩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商之延譽為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為辱。”[14]5107另一方面觀眾水平的高低和評價的優劣,也能促使藝人不斷提升自我技藝水平。觀眾的水平越高,評價要求越苛刻,也反過來督促藝人更加出色地呈現最佳藝術效果。李漁《閑情偶寄》所云“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20]74。正是說明觀演相長的互動現象。李開先《詞謔》記載明中葉藝人顏容在《趙氏孤兒》中扮演公孫杵臼,雖然他“備極情態”,“喉音響亮”,但還是“聽者無戚容”,于是下場后“左手捋須,右手打其兩頰盡赤。取一穿衣鏡,抱一木雕孤兒,說一番,唱一番,哭一番,其孤苦感愴,真有可憐之色,難已之情”。故而再演出時則是效果大變,臺下“千百人哭皆失聲”[21]353-354。更有甚至明末南京戲班中興化部的馬錦,為扮演好《鳴鳳記》中嚴嵩角色,馬伶去北京宰相顧秉謙家中當三年仆人,“察其舉止,聆其言語”[18]202,歸畢再演終究驚倒四座。因此,舞臺效果的最佳呈現既是藝人與觀者之間互動而成,又可以說是他們之間默契的結果。藝人還要緊扣觀者的心理,形成臺上臺下的心靈契合,才能實現最佳的舞臺效果。焦循《花部農譚》記錄花部劇本《清風亭》與昆劇劇本《雙珠記》的不同效果,回憶自己年幼觀劇前天演《雙珠記天打》“觀者視之漠然”,第二天演《清風亭》則“其始無不切齒,既而無不大快。鐃鼓既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說明從主體創作層面,效果的影響因素還有花部“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為之動蕩”[22]229。所以作者考慮愛憎分明的情感要素、合情合理的戲劇結構、入木三分的人物塑造,都是緊扣觀者的欣賞心理,才能取得較好的戲曲效果。此外,不少戲曲的結局也可謂作者、演員、觀者共同默契的結果,無論是大團圓的結局,還是如“戲文之首”《趙貞女蔡二郎》的結尾是蔡伯喈棄親背婦并為暴雷震死,都是強烈愛憎下的一種默契通合。觀者與演者之間的約定謀合,才能促成震撼人心的強烈效果與戲曲呈現。
三、結語
通過對文本效果與場上效果的雙重梳理,文人曲家、藝人演員、讀者觀眾之間的多重互動,基本展現出古代戲曲接受效果的獨特魅力,如《西廂記》《牡丹亭》等經典作品的登臺亮相,都是“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唱者聽者,皆苦事矣”[1]9。經過案頭與場上不斷地潤色刪改,真正做到“十年磨一戲”,慢慢形成文本效果與場上效果俱佳的審美狀態。同時,古代戲曲的接受效果也為我們提出很多值得深思的命題,這既是對古代戲曲演變的審視總結,又是對當下戲曲發展的借鑒參考。比如當下戲曲界不少作品演出問世后,各種新聞報道或評論刊物中專家好評如潮,但是卻無法實現與之對應的票房收入,專家的好評與所獲的獎項無法彌補其舞臺效果的迷失。所以,如何實現專家叫好與觀者叫座的理想效果、劇本效果與舞臺效果的完美融合等,既是戲曲接受效果研究的重要內容,又是當下戲曲界共同發展的時代命題。
[參考文獻]
[1]孔尚任.桃花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2]王世貞.嘲梁伯龍[M]//弇州山人稿:卷四九.四部叢刊本.
[3]伏滌修,等,輯校.西廂記資料匯編:上冊[M].合肥:黃山書社,2012.
[4]洪昇.長生殿[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5]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M].徐朔方,校箋.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6]王驥德.曲律[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7]史震林.西青散記:卷二[M].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7.
[8]劉世珩.匯刻傳劇自序[M]//暖紅室匯刻傳劇:卷首.貴池劉氏暖紅室刻本.
[9]祁彪佳.遠山堂曲品[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六).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
[10]徐大椿.樂府傳聲[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11]鐵橋山人,等.消寒新詠[M].周育德,校刊.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
[12]包世臣.都劇賦[M]//趙山林.安徽明清曲論選.合肥:黃山書社,1987.
[13]潘之恒.與楊超超評劇五則[M]//汪效倚,輯注.潘之恒曲話.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14]徐珂.清稗類鈔:十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5]張岱.陶庵夢憶[M].蔡鎮楚,注譯.長沙:岳麓書社,2003.
[16]王夢生.梨園佳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15.
[17]袁中道.游居杮錄:卷四[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18]焦循.劇說[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19]陳澹然.異伶傳[M]//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
[20]李漁.閑情偶寄[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21]李開先.詞謔[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三).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22]焦循.花部農譚[M]//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
作者:汪超 單位:安慶師范大學
- 上一篇:新媒體影響下的藏傳佛教文化范文
- 下一篇:洋節熱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