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青年的社會文化心理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當前青年的社會文化心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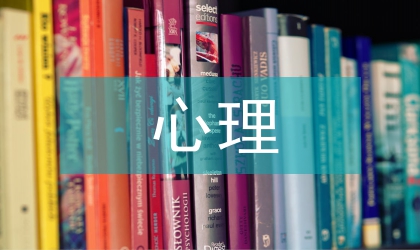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底,我國網民已達5.3億,手機網民3.56億,而文學網民就有2.68億。[1]在文學與網民的交集中,青年人占據著主體地位;網絡寫作者和閱讀者大多是年輕人。自由、平等、獨立、隱秘和個人化的網絡特性與青年率性而為的心理特征的巧妙契合,使網絡寫作和閱讀成為很多青年人感情宣泄和焦慮釋放的有效途徑。
一、網絡小說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心理
無發表限制的開放網絡空間,使得青年人的生活感悟和思想光芒不再被遮蔽。在此意義上,網絡小說滿足了青年階層的文化心理需求。網絡小說中生活原型化的敘事,天馬行空的虛構和類型化的故事堆疊,無論對于寫作者,還是對于閱讀者,都能夠有效地消解現實生活的煩悶與壓力。因此,作為一種文學活動,網絡小說即時地反映現實生活,寄寓著青年一代豐富的情感和思索。作為社會文化的一面鏡子,網絡文學直接反映了青年階層的自我意識和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
第一,從寫作和閱讀的心理機制來看,網絡小說中既有青年人內心情感的坦率表達,也有對現實的逃避和消極反抗。很多最初從事網絡寫作的年輕人,只是懷抱對文字的熱愛,對文學的夢想,執著地記錄和抒寫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情懷和記憶,感悟和思索。另外,對現實的失望和逃避,也是寫作和閱讀的內驅力之一。青年人從校園踏入社會,開始了從理想到現實的跨越。然而走出書本和想象的空間,面對諸多理想與現實、名與利、崇高與卑微、美好與丑惡等非此即彼的選擇,他們發現,太多的問題竟然無法用道理和邏輯去解釋和接受;于是,他們轉而在虛擬的網絡世界里開辟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網絡成為青年人在現實和夢想之間生存的自由世界。諸如玄幻、仙俠、穿越、架空和女尊類的作品,給人展示出一個個光怪陸離的虛擬世界。或仙、或怪、或魔,抑或普通人的青年主人公,擁有超凡的能力,馳騁在這個虛擬世界中,能夠打敗看似不可能打敗的對手,能夠實現看似無法實現的理想。本質上講,這不過是寫作者通過虛擬和幻想來表達自己在現實中無奈的情緒。這種幻想式的成功是一種壓抑下極大的放松與快樂,也是無奈情緒下的一種消極逃避和心理抵抗。
第二,網絡寫作和閱讀屬于一種補償心理機制。在心理學上,當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和阻礙使個人的目標無法實現時,個人就會設法以新的目標代替原有目標,以現在的成功體驗去彌補原有失敗的痛苦,這種心理被稱為“補償心理”。青年個體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總會和預期存在偏差和失落,甚至是失敗。為求得心理的補償,他們用文字克服自身生理或心理的自卑,填平失敗的空洞,滿足深埋于心底的欲望,成就人生的圓滿,從而獲得心理的滿足。例如,在玄幻類作品中,多數小說讓平凡的男主人公經過奮斗和神奇的機緣,在短時間內獲得地位、智勇、權勢、美女和財富,輕松地實現坐享齊人之福的完美人生。《尋秦記》中的項少龍,《誅仙》中的張小凡和林驚羽,《凡人修仙傳》中的韓立都算得上有缺點的平凡小人物。他們借助天分和機緣,在玄幻世界中由無名小卒逐漸成為聲名鵲起的英雄。在網絡寫作中,無論是以男性作者為主的玄幻系列,還是以女性作者為主的穿越系列,所創造的“虛構世界并非現實世界的影子,而是人類心靈的鏡子……”[2]再版前言作者的主體意識想象,構建出一個個理想的世界模式。文字中的大膽想象和設想,也滿足了讀者的閱讀快感和期待心理,滿足了讀者的想象欲望,使其在閱讀之中暫時地忘卻現實社會生活的艱難、生存的壓力和種種不盡如人意之事。
第三,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網絡小說的寫作和閱讀心理受完美原則的支配,體現著“自我”的完美,也即“超我”的人格結構。對男性寫作者和讀者而言,玄幻小說中的個人英雄主義,無疑是“超我”的最好詮釋。每個即將扛起或已經肩扛家庭生活重擔的男性,都有無法逃避的工作、生活和社會壓力。實現人格上的“超我”,幻想著自己成為英雄橫空出世,經過苦難磨煉,數度生死的驚險,終以一人之身拯救天下,恣意揮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豪情,是所有日常生活中平凡普通、三緘其口的男性們內心深處時刻洋溢著的急切的渴望。他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天下無敵,快意恩仇,并且有善解人意的美女環繞左右。這種幻想只能在奇思妙想的網絡小說中得到滿足。對女性寫作者而言,都市言情中高干系列和豪門系列的男主角通常是帥氣、多金,同時又兼霸氣與溫柔,他們含著金鑰匙出生,集萬千美女迷戀于一身,曾經留戀花叢中,遇到或漂亮或溫柔或知性,或活潑可愛或沉靜可人的女主人公后卻又癡情專一,至死不渝。凡此種種,不無充溢著寫作者與讀者對自身“超我”的渴望。《步步驚心》等穿越小說之所以引來廣泛的女性追捧,源于她們試圖在幻想中解決現實生活中無法回避的焦慮,本質上是潛意識中隱蔽的“超我”的現實化。
第四,從存在主義的哲學角度來講,從事網絡寫作和閱讀的青年人,更深層的心理機制在于人生存于世無法消除的孤獨感。存在主義哲學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個體本位主義,它把絕對孤獨的個人看作自己唯一的出發點,并且從本體上認定孤獨是個人的本然的存在狀況。[3]27網絡寫作者,面對生活、社會和現實的種種不自由,在網絡的虛擬世界中尋求安慰,通過文字書寫自己的孤獨,消弭自己的孤獨。無限的網絡鏈接足以使讀者找到能夠打動他的文字,使他克服孤獨,獲得心靈的寧靜。網聊、網絡寫作、網絡閱讀以及評論,是孤獨處境中的青年人渴望交流心理的外化。也正是這種孤獨,造就了數以億計的青年人從網絡文字中尋求溫暖和安慰,造就了網絡文學的盛世和浮華。
第五,不可否認,網絡小說的寫作者鮮有“作家是社會之良心”的嚴肅態度,也缺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責任感,因此,網絡小說本質上是一種消解性寫作。它以游戲、玩耍和發泄的特性,削平意義、剔除教育功能,使文學的審美精神被激烈的感官刺激所取代。有人說網絡小說帶動文學審美進入了本雅明所謂的“后審美時代”,文學書寫不再是“有光暈的藝術”,開始從“凝神關注式”到“消遣式”的轉變。[4]
這種現象的極端表現是網絡小說中存在的隨處可見的有關性的話題和私生活的想象片斷。那些有關欲望的直接宣泄,以肆無忌憚的筆觸,把網絡寫作完全作為一個“生理事件而非精神事件”[5]。例如,《趙趕驢電梯奇遇記》寫從農村出來的平凡白領趙趕驢情場得意,與俏麗的小寡婦、純情的女大學生以及半老徐娘的女上司之間的種種曖昧和意淫。《現代嬌女之女王后宮三千》描述了一個普通女子因一個偶然的機遇,成為至尊女王,身邊環繞男妃三千,并俘獲了各種各樣男人的忠愛之心。網絡小說中的性描寫,帶著濃厚的意淫色彩,不復有傳統作家在處理此問題時立足于人性的高度考問。這既是官能享樂的浮躁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也契合著青年人體能旺盛、生命力高亢昂揚的身心特征。但是這種宣泄卻消解著傳統的道德規范,也顛覆著傳統文學的審美心理和價值追求,使網絡小說“思想的世俗化表現為取消深度追求,放棄啟蒙思想和價值追問,使一切變成平面的當下的欲望滿足;精神的世俗化則是放棄批判精神,以游戲的方式卷入世俗的物象和文本的狂歡”[6]。由此可見,網絡小說“提供給人們一個新的觀看世界和表現世界的通道”[7]。青年人的網絡寫作和表達、閱讀和接受的心理機制中,有著自身的精神和文化追求,折射著當今青年階層的社會文化心理,又反映著身處社會與歷史大結構中的青年一代的價值取向。
二、網絡小說中的價值取向
網絡小說很少刻畫人物形象,而是著意于故事情節的構建。多數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彰顯出人物鮮明的趨己利己姿態。例如玄幻小說《飄邈之旅》的主人公李強,原本只是一個精明商人,因失手殺死老婆的情夫而逃走。后因機緣巧合,成為修神者。每逢強敵當前,李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逃”。《凡人修仙傳》中的韓立,行為處事的首要準則是“利益”,要他出馬必須“利”字當頭,但他也從不憑空去占別人的便宜。在這些小說中,無論是得道前的平凡小人物,還是超凡脫俗之后的仙界、神界角色,抑或是各種妖、怪、魔,無不蘊含著個體利己主義立場。無論是江湖稱霸,還是職場奮斗,無論是對金錢、美女和權力的渴望,還是被人賞識的需求,他們完全遵從著個人的自我意識。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層面。從網絡小說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到在當代青年的文化心理中,已經把個體的自由和發展作為人生的主要目標,價值取向也越來越多地以個人主義和自身利益為基礎。例如,“我吃西紅柿”的修真作品《星辰變》,如果把男主人公置換到現實社會中,對照“80后”“90后”的青年來解讀,有關孤獨、暴力、追求個體的強大,無明確道德和是非觀念等心理特征尤為突出。這種完全尊崇自我意識引導的普遍心態,是青年主體意識的無窮彰顯,個人本位的無限追求,功利色彩的無度膨脹,走上極端即表現為對財富的渴求,對權力的膜拜,以及對女人赤裸裸的迷戀。因此,網絡小說中所彰顯的青年人所崇尚的自發性、享樂主義、直接性以及某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不加節制的情感強度,很容易使其陷入現實價值選擇與終極價值迷失的困境,而且以個人主義取向為思考與行動的指南,勢必蘊涵著一種極大的消解社會價值的危險。丹尼爾•貝爾在20世紀70年代就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在現代人的千年盛世說的背后,隱藏著自我無限精神的狂妄自大”,而由此引發的價值危機就在于“現代人的傲慢就表現在拒不承認有限性,堅持不斷的擴張;現代世界也就為實際規定了一種永遠超越的命運———超越道德,超越悲劇,超越文化”。[8]96
一些網絡小說拋棄了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傳統情感態度,以娛樂消遣性來消解世人對崇高價值的追求,以對生活的調侃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宣泄自身的焦慮,甚至以追求感官的享受和刺激來消極避世。在對暴力、同性戀、縱欲主義、頹廢、個人主義等的宣揚中,墮入精神空虛的深淵。因此,網絡小說中的文學娛樂化的傾向,就思想性而言,具有消極性、非建設性,也隱含著對主流文學的抵制和反叛。這一傾向在現行體制下對青年與社會的融合,對大眾文化環境的構建,以及當代青年精神信仰和人生意義的追尋都是極為不利的。在青年亞文化運動中,有種稱為“零點結構”的文化后果和社會影響。“零點結構”,顧名思義,就是將傳統價值歸化為零的無差異結構,從而顛覆一切既定的社會界限,拆除一切文化壁壘。從積極處說,“零點結構”意味著廢除各種界限、打破各種禁忌、決裂各種范式,體現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理想。從消極處說,它是一種反常的社會狀態,因取消了一切禁令而使社會活動處于無序之中,是一種普遍越軌和犯罪盛行的溫床,可能使社會陷入普遍的困境。當代青年在網絡小說中所宣揚的價值觀念和世界秩序,無異于一個個“零點結構”。他們以各自所營造的可替代的理想世界,以直接的感染力和感官的誘惑,使青年一代迷失在文本的狂歡中。網絡小說在精神提升、意義建構方面的功能非常脆弱和稀薄。昆德拉在闡述“生命之輕的文化”的含義時,說道,“生命‘輕’化的文學”就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欲望文學,是一種自己面對自己、自己為自己尋找意義和價值的文學。[9]185
在此意義上,網絡小說舍棄了對人性和生命本質的探索,在本質上就屬于昆德拉所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文學。因此,對網絡小說,一方面要承認它作為青年自我身心需要和情感釋放的獨特空間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在大眾文化背景下包含的一些負面因素。青年只有具備了成熟的心智,能夠甄別網絡信息,才能使個體心靈和精神健康發展,才能提高個體對泡沫文學和文化垃圾的免疫力,減少低級趣味的東西的傳播和泛濫。因此,厘清網絡寫作和閱讀活動中的種種心理暗涌,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