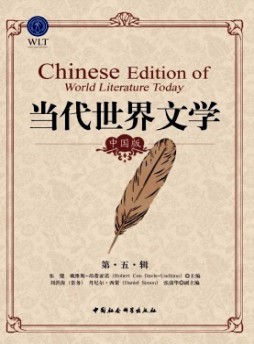世界文學視閾下康拉德的閱讀模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世界文學視閾下康拉德的閱讀模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回望康拉德在東西方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的歷史,不難發現,康拉德是一位受世界文學給養又反哺于世界文學的作家:斯拉夫民族的出身(波蘭的血統和俄羅斯文學的熏陶)、拉丁文學(法國作家福樓拜、巴爾扎克、莫泊桑)的洗禮、對英國文學與語言的膜拜(盎格魯-撒克遜尤其是莎士比亞)以及在亞非地區的冒險經歷(海洋叢林小說的背景),無疑都對康拉德作品在世界文學中的生成、閱讀和傳播產生了重要的意義.當“英語的枝葉長在波蘭的干上”時[1],康拉德文學已經猶如一棵樹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文學波浪中.波浪的沖擊,造成了這棵樹在不同文化地理空間樹狀的斷裂和分叉[2],也造就了世界不同文化空間各不相同的康拉德.事實上,康拉德在世界文學中流通得越深廣,在不同國家和民族中的形象也越復雜.作為波蘭和英國文學的驕傲,他令俄羅斯愛恨交加,也令法國這位洗禮者極富熱忱,更讓歐美其他國家(尤其是英美)對他推崇備至;而后殖民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理論的興起,尤其是阿契比和薩義德的研究批評,更讓康拉德在亞非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形象褒貶不一.無論康拉德的形象如何“復雜多變”,毋庸置疑的是在世界文學領域中,他總能在不同歷史文化語境的解讀中提供新的意義,賦予新的形象.康拉德成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不斷生成、“賦形”和“變形”的經典對象,恰好體現了達姆羅什提出的世界文學理念.在達姆羅什的理念里,世界文學不是指一套經典文本,而是文學作品通過翻譯和流通,進入新的文化空間的一種閱讀的模式[3].他將世界文學隱喻為“橢圓形折射”,即“譯入語文化與譯出語文化分別作為兩個焦點,構建起一個完整的橢圓”.在這個橢圓形的世界文學場域中,譯入語文化和譯出語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磁場所形成的張力,會造成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態、乃至作家的形象發生變化.達姆羅什進一步指出“不同文化的規范和需求深刻決定了世界文學的選擇,影響了進入該文化中文學作品的翻譯、銷售和閱讀方式”[4].以達姆羅什的世界文學理念為觀照,可以通過梳理康拉德在中國不同時期的譯介情況、存在方式、閱讀模式和批評研究,甄別出他在三個歷史階段“賦形”、“變形”和“正形”的歷時性時代性特點,以及當前的共時性“百家爭鳴”特征,從而挖掘出康拉德在中國形象變遷的深層動因.
11924~1949:康拉德的“賦形”期
1.1康拉德在民國時期的譯介及其歷史文化語境1924年,隨著世界文學著名作家康拉德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現代文壇陸續對康拉德進行了介紹、翻譯和評論.到1949年,康拉德作品中文譯本有8部,除去譯者的譯序,已知評介文章4篇.康拉德在民國時期的譯介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自1924年開始,康拉德引起了中國文壇的關注.作為20世紀前20年西方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康拉德在世界文學領域中已享負盛名.走入中國,被中國翻譯、傳播和閱讀,是世界文學波浪沖擊的大勢所趨,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縱觀文學的史海沉浮,一個作家的去世未必一定引起其他國家民族的關注.正如福特所言“每一個偉大的作家在去世后有30~60年的沉寂期”[5].而康拉德卻能夠在20年代提前走入中國,并逐漸引起文學批評界、翻譯界和文學創作界的共同關注.這一現象從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來看,是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成為開創新文學渴求“他山之石”的內在動因.20年代,國內由郭沫若與鄭振鐸掀起的關于翻譯文學與創作文學之間“處女與媒婆”的一場爭辯,引發了國人對文學翻譯的深層思考.1922年8月11日《文學旬刊》上的《雜譚》中,鄭振鐸[6]再一次指出:“現在的介紹,最好是能有兩層的作用: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相接觸.”這一觀點,引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共鳴.比如胡適在北大任教授時,就擬定了幾條翻譯西洋文學的具體方法[7]:一是“只譯名家著作”,二是“譯為白話散文”.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作為世界文學“名家名著”之一的康拉德作品,不僅肩負著“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的責任,同時也擔任著中國白話文運動的“他山之石”角色.康拉德走進中國,成為當時文評界、翻譯界和文學創作界不斷“賦形”的產物,既是世界文學的大勢所趨,也是中國文學的內需迸發.
1.2康拉德在民國時期的早期“賦形”———具有“愛國情結”和“追求自由生活理想”的“浪漫寫實主義”海洋和叢林小說家康拉德走進中國,濫觴于文評界的兩篇紀念性文章.1924年,為紀念康拉德的去世,《文學》和《小說月報》很快刊出誦虞和樊仲云的兩篇文章.誦虞的《新近去世的海洋文學家———康拉德》只是簡單地介紹作家的生平,而樊仲云的《康拉德評傳》應該說不僅是國內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康拉德研究性論文,也是中國為康拉德“賦形”的開山之作.樊仲云以茅盾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鋒期刊《小說月報》為平臺,擲地有聲地向國人闡述了作家生平、作品主題、作品分類、語言特色和作家的藝術主張,寫下了康拉德走入中國文化空間的第一筆.樊文在英語文化和漢語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磁場所形成的張力中,評介并賦予了康拉德三方面的形象特征:①康拉德的波蘭民族出身、性情中的懷疑猶豫以及為擺脫沙俄束縛的理想造就了康拉德具有“愛國情結”和“追求自由生活理想”的作家身份.②基于康拉德在《“水仙號”上的黑水手》序言中提出的“使你聽到,使你感到———而最重要的是使你目擊其事”的藝術宣言,證明例如康拉德“浪漫的寫實主義者”形象.③從作品的銷售角度,分析了康拉德之所以“有趣味的故事才暢銷,那些最好的反掩末不彰”的原因與其海洋和叢林作品中的“懷疑主義與現實的流行精神不和”有關.自此,“愛國主義”、“寫實主義”為康拉德在中國的通行打上了合理的標簽.而“浪漫的”、“懷疑主義”的形象也成為他不斷被爭辯和詬病的焦點.以樊文為代表被“賦形”的康拉德,雖然來自西方,卻代表了弱小民族的“愛國情結”和“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這樣的形象恰恰可以引領國人對“現代人生問題”的思考,也正好契合了當時中國的歷史語境.至于,康拉德被賦形為出生波蘭、充滿懷疑主義、兼具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色彩的海洋和叢林小說家形象,能否在中國的譯語文化空間被接受,則還是取決于其作品的翻譯、流通和閱讀模式.
1.3康拉德“賦形”的促成動因如果說以樊仲云為代表的文評界是引進并“賦形”康拉德的發源者,那么后來翻譯界的出版機構和譯者、讀者和作家,便是康拉德廣泛“賦形”的真正推動者.20世紀30~40年代,譯者對康拉德作品的選材和翻譯、讀者對原作和譯作的批評以及國內作家對康拉德的選擇性推崇,都是這一時期促成康拉德最初“賦形”的基本動因.首先,康拉德作品的翻譯,盡管譯者和出版機構具有計劃性和系統性,但翻譯選材一直沒有突破海洋和叢林小說的局限.1931年,北新書局出版的梁遇春譯注的《青春》,封面上“世界文學名著之一”的標簽,反映了當時的中國文壇已經將康拉德列為“他山之石”的經典文本叢書之一.根據《吉姆爺》的編者附記所言,梁遇春發愿要翻譯康拉德的小說全集,胡適不僅極力鼓勵他做此事,更在行動上予以支持.不幸的是,梁遇春翻譯了前15章便染病去世.剩下的章節,在胡適和葉公超的督促下,由梁遇春的朋友袁家驊完成,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后,在基金會的贊助下,商務印書館1936~1937年又出版了袁家驊翻譯的《黑水手》、《臺風及其它》以及關琪桐翻譯的《不安的故事》.康拉德在中國的譯介一度繁榮,其形象也有望更為全面地向讀者推介.然而,抗日戰爭爆發,翻譯康拉德小說全集的計劃被擱淺.40年代,雖然零散出現了魯丁改譯的《激流》和柳無忌翻譯的《阿爾邁耶的愚蠢》,但當時中華民族和社會歷史的特點以及譯者對康拉德作品中反映“自由生活理想追求”的海洋和叢林小說傾向性先譯,在偶然中也必然性地推動了第一階段康拉德“海洋和叢林小說家”一葉障目式的“賦形”.其次,譯者的認識和策略也促進了梁遇春、袁家驊、關琪桐較為“忠實”地向讀者傳輸了康拉德“出生波蘭、充滿懷疑主義、兼具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色彩的海洋小說家”的“賦形”.相比而言,魯丁的《激流》(《吉姆爺》)與30年代的譯本相比,是一個特例.小說的情節基本未動,原名“吉姆爺”用醒目的“激流”所代替.小說每個章節都加上了奪人眼球的副標題,如“海的熱戀”、“生之掙扎”、“荒島行”、“拯救一位孤女”、“仇敵的會見”等詞語.小說人物海盜頭目布朗被翻譯為“白龍”(Brown),極具中國古典游俠小說特征的名字.這種“歸化”與其說是“文化過濾”后的中國式“吉姆爺”,毋寧說是譯者有意回歸晚清至五四前的翻譯文學特點.將“詹姆”(吉姆)的故事比擬為中國傳統的行俠仗義、游走天涯的章回小說,以滿足讀者獵奇探險的期待視野.客觀來說,魯丁的翻譯雖沒有梁遇春的版本“忠實”,卻讓康拉德的小說有了“中國味兒”,反而推動了康拉德在大眾讀者間的“賦形”與接受.這一階段,康拉德在翻譯中的“賦形”與流通,不僅得到了機關(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的力贊,也引起了讀者、尤其是文評家的聲援.1936年5月4日,《國聞周報》刊登了一篇常風的《兩本翻譯的康拉德小說———〈黑水手〉,〈不安的故事〉》,及時對同年1月和2月出版的兩本翻譯小說做出反饋與評介.常文與譯文之間的這種同時代超文本互動,不僅代表讀者和文評界加強了對康拉德藝術性的“賦形”,也鞭策了譯者注意到“賦形”過程中的規范性和藝術性.再次,文學創作界的推崇和模仿,更推動了如此形象的康拉德文學猶如一棵樹受到世界文學的波浪沖擊后,在中國的文化地理空間開始斷裂分叉,甚至生根發芽.1935年,《文學時代》的創刊號刊登了老舍的一篇《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作者———我最愛的作家康拉德》.承認從康拉德那里偷學了一些敘述方法招數的老舍,不僅將康拉德奉為不能募仿的“海王”,更是聯系當時白話文學興起后“文藝的義法不受拘束,大家覺得創作容易,因而不慎重”[9]的創作文學背景,倡導國人視康拉德為楷模、學其對待英文的“嚴重”態度來認真創作.可見,老舍一方面在海洋小說的評論上與其他文評家、翻譯家“賦形”遙相呼應,另一方面從創作層面發出了建構白話新文學需認真對待語言藝術的匡正心聲.綜觀第一階段,康拉德在中國的譯介與流通、影響與借用,伴隨著文評家、翻譯家和作家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的逐步“賦形”,不僅是世界文學沖擊到中國文學的必經歷程,更是中國當時社會文化的必然產物.如果沒有之后歷史文化語境的阻滯,毫無疑問康拉德在中國的翻譯、流通和研究,必然與西方一樣隨著不同流派和不同思潮的興起更為循序漸進.相反,康拉德在中國經歷了一段長期的“變形”期.
21949~1978:康拉德的“變形”期
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受當時歷史文化語境的影響,康拉德的譯介和研究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下53第3期程香,等:世界文學視閾下康拉德在中國的“賦形”、“變形”與“正形”收效甚微,“反動的帝國主義”作品更是鮮被提及.這段時間,一共就兩部譯作,準確來說,這兩部譯作并非新中國成立后完成的新譯.《芙麗亞》出版于1951年,實際上是譯者劉文貞1947年與夫李霽野赴臺灣期間譯完.《吉姆爺》出版于1958年,卻是1934年梁遇春和袁家驊合譯的再版.僅有兩個譯本反映出的康拉德形象,與上一階段“賦形”期的形象相比大為改變,成為一直同情民族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作家;同時受世界觀的限制,康拉德也被斥為看不到國內外階級斗爭,只能成為追求抽象的人性和單純的人道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作家.譯本《吉姆爺》的“編者后記”指出芙麗亞和吉姆爺兩個主人公都曾試圖反抗帝國主義,卻又只能局限在狹隘的資產階級道德準則的范疇內,最終只能走上一條孤獨和死亡的道路,其革命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顯而易見.由此,康拉德“新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藝術風格被當時的歷史語境予以“革命性”的變形.這種“革命性”的變形,放置于二戰后譯入語文化與譯出語文化分別作為兩個焦點構建起的橢圓形世界文學場域中來看,是兩種不同文化磁場形成張力的結果.已故的康拉德經歷了20年的“沉寂期”后,在西方文學界逐步掀起了一個研究高潮.60~70年代,西方“批評的重點開始放在康拉德的哲學和政治傾向及其與19世紀意識形態的關系上”[11].而紀念康拉德逝世5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謝利的《康拉德的東方世界》與《康拉德的西方世界》,更是讓康拉德在世界文學場域中的作品形態和內容,甚至康拉德的作家形象愈發富有政治性.尤其是后殖民主義興起,《黑暗之心》、《吉姆爺》等歷險小說分別成為東方主義學者有關帝國和種族優越性的論爭對象.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文學的階級性和進步性首當其沖是當時國內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的首要標準.極富帝國和種族爭議性的康拉德經典作品自然成為這一時期被有意無意回避和遺忘的對象.兩本譯作選擇性的出版和“編者后記”的“革命性”變形,即可管見當時中國譯入語文化對康拉德的譯介與研究留下了鮮明的時代烙印.
31979~:康拉德的“正形”期
康拉德經歷了期間選擇性的遺忘后,1979年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的到來,在翻譯界、文評界和創作文學界共同的努力下重新回到了讀者的視線.而此時的西方文評,經歷過幾十年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歷史積淀和洗禮后,從80年代開始,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康拉德,康拉德的小說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的極佳注腳[11].相較而言,中國的康拉德從90年代開始才逐步地走進“正形”.這里的“正形”并不是指為康拉德在中國樹立一個唯一正確的作家形象,而是以開放的世界文學眼光和深刻的民族文學自省意識,回歸康拉德作品中反映人類共通的“詩心”和人性,使其形象更加動態化、多元化和民族化.鑒于此,我們將康拉德在這一時期的翻譯、閱讀和研究分為兩個階段:逐步放開80年代前奏期和突飛猛進的近20年“百家爭鳴”期.
3.11979~1989:“正形”期的前奏1979~1989年,康拉德作品在國內的譯作一共5部,如表3所示.如果說1979年《世界文學》第4期刊載的《羅曼親王》(薛詩綺譯)是一個探試,那么緊跟著第5期趙少偉翻譯的《“白”水仙號上的黑家伙序言》則意味著“新時期康拉德文藝批評風向的轉變”.康拉德逐步走出“階級性”的“變形”,一方面與早期“賦形”期的形象一脈相承,另一方面也與世界文學場域中多元化的形象嘗試接軌.重譯的5部作品,仍然聚焦于康拉德的海洋叢林小說.這既與當時“極左”思潮的緊箍咒依然存在有關,同時也是因為這些文本內容形成過程中作家的感傷基調、白人的尋根趨向、主人公的懺悔意識和人類的超越渴望與新時期中國的“傷痕文學”不謀而合,產生了文學上的互文關系.相比翻譯界,文評界走的更遠.據中國期刊網統計,這一時期刊載的康拉德譯介、研究論文20篇左右.康拉德的形象開始復雜.期間,概括性的作家綜述和具體的文本分析以及以伍爾夫所代表的西方康拉德文評的譯入,不僅在作品范圍上豐富了康拉德的形象,更是在研究視角上開拓了對康拉德的認識,體現出在世界文學整體互動格局中,中國的“康拉德”形象即將開始多維度的“正形”.例如,受到譯入語文化和譯出語文化兩種不同文化磁場所形成的張力影響,《黑暗的心臟》不僅成為80年代海峽兩岸翻譯的熱點,也是文評界論爭的焦點.在有關康拉德“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論辯中,章衛文的馬克思主義剖析,與胡壯麟[14]基于西方人類學研究回顧后提出的地域、政治的多重釋義,基本可以看出康拉德在海洋和叢林小說中體現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形象開始走向深刻,趨向“正形”.此外,侯維瑞的《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創作》,從文學史的角度,與50年前的老舍一樣對康拉德的現代主義形式實驗予以肯定,客觀上也推動了國內對康拉德現代主義先驅作家形象的認可.除了對康拉德“賦形”與“變形”時期的海洋叢林小說家形象逐步匡正外,值得一提的是,康拉德之前所謂的“政治小說”或“頹廢小說”研究也初步走入中國.如1981年張健的《論康拉德的小說〈間諜〉》首次向國人介紹了康拉德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間諜小說家”身份.而關于電影《現代啟示錄》和小說《黑暗的心臟》的跨學科比較研究,則展現了康拉德作品中“能動的敘事空間和時間變形”[15]與現代電影(大眾媒體)敘事相契相合的無窮魅力.康拉德由早期的海洋叢林小說家到間諜小說家,再到具有現代電影敘事魅力的身份定位,以及從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的形象變遷,在80年代的中國,緩緩拉開了康拉德“正形”期的前奏,并為后來的“百家爭鳴”做好了鋪墊.
3.21990~:“正形”期的“百家爭鳴”自90年代開始,西方經歷過不同歷史時期沉淀的文學流派和哲學思潮,短時間內大量涌入中國.西方“理論熱”和“文化熱”的涌入極大地拓寬了文學批評者和文學創作者的視野,并促進了國內康拉德的翻譯與研究逐步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一門“顯學”.這種歷史語境的錯位,同時也造就了中國康拉德文學批評研究的“百家爭鳴”.這一時期,康拉德的翻譯一方面繼續海洋叢林小說的重譯,另一方面開疆破土觸及到早期不被看好或故意忽略的“政治小說”,如《諾斯托羅莫》、《間諜》、《在西方的眼睛下》以及散文《文學與人生札記》.康拉德的文學批評隨之蓬勃發展,呈現出系統化和多元化的趨勢.以王松林、胡強和寧一中為代表的學者對康拉德在中西方的譯介和研究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向我們展示了動態化的康拉德形象.而西方心理批評理論、原型批評、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敘事學批評、新歷史主義和戲劇理論等文藝理論的傳入,使康拉德在中國文評界的形象愈發多元化.當然,對理論的生搬硬套和對西方文藝理論的過分依附,也伴隨著康拉德形象的誤讀和曲解.殷企平撰寫的《〈黑暗的心臟〉解讀中的四個誤區》評述了當下國內康拉德研究存在的問題,以此引發的王麗亞的爭鳴、張和龍的回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康拉德在中國趨于理性的研究動向.康拉德的形象正是在學者論文、碩博論文和文評專著中一次次建構、解構、再建構、再解構的過程中,一步步走進“正形”.另外,受新加坡學者王潤華的啟發,康拉德與老舍的影響研究領域也有所進展.隨后,康拉德與郁達夫,康拉德與沈從文等比較文學的個案研究,反映了康拉德與中國五四新文學互文性關系.同時,中國文學的批評者針對國內當代海洋文學“重抒情缺冒險”的現狀,呼吁文學創作應吸取康拉德海洋小說的精髓.可見康拉德在中國的“正形”不再局限于國別文學的研究領域,而是被置身于世界文學的宏觀場域,隨著世界文學的波浪走進中國,真正的影響并扎根于中國民族文學的土壤.康拉德在當前的中國逐步走進“正形”,不僅具有上述動態化、多元化、民族化的特征,同時也具有大眾化的特點.譯著《間諜》和《傻瓜》展現出的康拉德“間諜小說家”和“懸疑小說家”的形象,可以幫助作家走出學者型讀者群的局限,令大眾讀者更愿意親近和接受他.另外,海洋學校的教育者甚至賦予了康拉德塑造學生堅強品質的導師形象.毋庸置疑,康拉德研究在中國已發展成為一門欣欣向榮的文學產業.
4結語
厘清三個歷史階段中,康拉德在中國經過“賦形”、“變形”和“正形”的存在方式和閱讀模式,可以發現:一方面,在世界文學場域里,中國“康拉德”的形象受到西方影響呈現出一種動態、衍生和多樣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語境下,不同的社會歷史特點以及翻譯家、文評家、作家和讀者不同的個人喜好,造就了康拉德在中國的文化地理空間雖然幾經沉浮,卻開始斷裂分叉、生根發芽.隨著當前學界的“百家爭鳴”,康拉德在中國讀者乃至中國的民族文學中將會有更加鮮活持久、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作者:程香 黃焰結 單位:安徽工程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