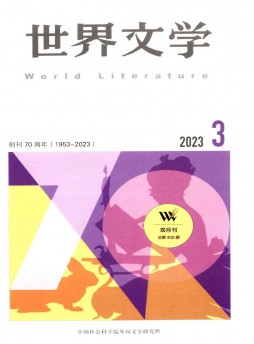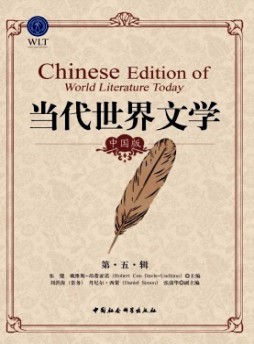世界文學(xué)視域下《水滸傳》的價(jià)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世界文學(xué)視域下《水滸傳》的價(jià)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世界文學(xué)”與“復(fù)雜性思維”
學(xué)術(shù)界長(zhǎng)期以來(lái)一直把“世界文學(xué)”的概念首倡者歸到德國(guó)作家歌德身上。但據(jù)德國(guó)學(xué)者魏茨(Hans-JoachimWeitz,1904-2001)考證,最先提出“世界文學(xué)”概念的當(dāng)屬德國(guó)文學(xué)家、翻譯家維蘭德(christophMartinWieland,1733—1813)。[1]不管首倡者是歌德還是維蘭德,“世界文學(xué)”這一概念的提出與被接納都源于和體現(xiàn)了一種“世界性”的思維和眼光。人類(lèi)在物質(zhì)領(lǐng)域與知識(shí)精神領(lǐng)域的發(fā)展和交流,不斷地強(qiáng)化著對(duì)人類(lèi)知識(shí)總體性和共性的認(rèn)知。在這一概念倡導(dǎo)以及闡釋中,毫無(wú)疑問(wèn),夾雜著對(duì)民族性(文學(xué))與世界性(文學(xué))關(guān)系的認(rèn)知和理解。民族性(文學(xué))是什么?世界性(文學(xué))又是什么?兩者關(guān)系是怎樣的?建構(gòu)怎樣的世界性(文學(xué))思維?回顧“世界文學(xué)是什么”的爭(zhēng)論史,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在各種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的闡釋中總是存在著“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甚或各種“民族主義”的觀念。由這些觀念建構(gòu)的“世界文學(xué)”,或者一味地抵制對(duì)抗“世界文學(xué)”,都不利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對(duì)話。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不同國(guó)家、民族、種族和文化,越來(lái)越像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日益須臾不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樣的背景下,倡導(dǎo)一種共識(shí)顯得比任何時(shí)候都重要而迫切。
當(dāng)代法國(guó)著名思想家愛(ài)德加•莫蘭(EdgarMorin)的復(fù)雜性思維的思想對(duì)于理解當(dāng)今我們的時(shí)代和我們的處境有著深刻的啟示。“莫蘭主張走出人本邏輯中心主義、單維主義、單向發(fā)展論、進(jìn)步主義、主客真假善惡美丑二元對(duì)立、技術(shù)主義、語(yǔ)言中心主義、功利主義、經(jīng)濟(jì)決定論以及規(guī)則秩序崇拜等傳統(tǒng)思想定勢(shì),嘗試以非定則、無(wú)中心、非線性、非平衡、混沌、模糊、不確定、分叉、無(wú)限區(qū)分化的模式,面對(duì)自然界和社會(huì),跳出猶太/基督教式的時(shí)間循環(huán)論和救世論的框架,把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混合在無(wú)參照系統(tǒng)的游戲活動(dòng)中,漫游在充滿(mǎn)審美樂(lè)趣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里。”
莫蘭是在對(duì)傳統(tǒng)思維系列批判的基礎(chǔ)上,提出“復(fù)雜性的思維”思想的。從復(fù)雜性思維來(lái)看,“普適性和差異性,‘可通約性’和‘不可通約性’都是可以同時(shí)并存,互相滲透、互相轉(zhuǎn)化、共同發(fā)展的。”莫蘭認(rèn)為,人類(lèi)應(yīng)該努力賦予每一種文明以其自身方式揭示人性本質(zhì)追求的合法權(quán)利,并承認(rèn)所有文明都同樣渴求真理和世界性,只不過(guò)這種真理和世界性是以不同文明的特殊形式來(lái)加以表現(xiàn)的。又認(rèn)為,各種文化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并不是以減少鋒芒、彼此自我抑制為代價(jià)而換來(lái)和平,換句話說(shuō),解決之道并不是在妥協(xié)而是在理解里尋得。基于這種認(rèn)識(shí),對(duì)話的基本目的“應(yīng)是理解和尊重‘在他者的自身文化多樣性’中的他者,而絕不是將其抽離原有的文化語(yǔ)境而加以扭曲、同化,甚至使之湮滅。”莫蘭談到對(duì)《水滸傳》的閱讀時(shí),他說(shuō):“我一邊讀,一邊不停地思量:‘他們與我們多么相似!’‘他們與我們多么不同!’”他用復(fù)雜性思維閱讀、思考文化間的“多樣性中的統(tǒng)一性”和“統(tǒng)一性中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中的統(tǒng)一性”和“統(tǒng)一性中的多樣性”的復(fù)雜性思維,“認(rèn)證了我們的地球公民籍,同時(shí)又包含著我們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變性。”[2]莫蘭的這種思想對(duì)于跨文化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和世界文學(xué)研究亦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用“復(fù)雜性思維”才能理解當(dāng)今文化融合、文化雜交與深層文化差異同時(shí)并存、相互交錯(cuò)、變幻莫測(cè)的世界,也才能避免文化或文學(xué)的殖民,防止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的研究重新落入傳統(tǒng)式的預(yù)定的規(guī)范和模式之中。因此,由“復(fù)雜性思維”來(lái)建構(gòu)的“世界文學(xué)”理想,才更適合全球化時(shí)代的人類(lèi)知識(shí)的總體性和共性的認(rèn)知與期待。用“復(fù)雜性思維”重新審視“世界文學(xué)”,重新審視跨文化的文學(xué)譯介行為和現(xiàn)象,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種“復(fù)雜性思維”與賽珍珠的文化觀念和思維存在著一種暗合關(guān)系。賽珍珠雙重文化身份和超越性的文化視野及其所倡導(dǎo)的跨越地域和邊界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寬容的文化精神與莫蘭的“復(fù)雜性思維”是異曲同工的,有一致性的。
二、賽珍珠“雜糅性”文化身份和“超越性”思想
賽珍珠的文化身份比較特殊,以國(guó)籍、血統(tǒng)或種族來(lái)論,她毫無(wú)疑問(wèn)是個(gè)在中國(guó)生活多年的美國(guó)人;而從文化背景來(lái)看,她成長(zhǎng)并長(zhǎng)期生活在中國(guó),深受中國(guó)文化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又更像是一個(gè)中國(guó)人。在文化認(rèn)同上,她處于中美或中西兩種文化之間。賽珍珠的文化身份已經(jīng)超越了純粹的“中國(guó)人”或“美國(guó)人”的范疇,而呈現(xiàn)出典型的“雜糅性”和“混血”特征。正如賽珍珠在她的第一部自傳《我的幾個(gè)世界》里所說(shuō):“生活在這一個(gè)世界,但并不置身其中,置身于另一個(gè)世界,卻又不在那里生活”。
兩種不同的社會(huì)和文化存在,讓她反復(fù)體驗(yàn)著文化身份認(rèn)同與局外的雜糅和多重,也讓她成為文化上的“異鄉(xiāng)人”和“異邦客”。賽珍珠的文化身份、文化視野和文化觀念,不同于薩義德后殖民主義理論中所說(shuō)的東方主義者———“白種東方人”。“白種東方人”是以東方為業(yè)但卻完全瞧不起東方的西方白人移民。賽珍珠與“白種東方人”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白種東方人”身心分裂,有意或無(wú)意地帶著殖民者種族優(yōu)越意識(shí)看待“他者”。他們可能具備在中國(guó)社會(huì)里游走自如的文化能力,但對(duì)待“他者”卻是一種屈尊或厭惡的態(tài)度。賽珍珠則將東方人特別是中國(guó)人視為自我實(shí)現(xiàn)的個(gè)體,以理解、同情、尊重和關(guān)懷的態(tài)度對(duì)待“他者”。賽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了兩類(lèi)傳教士,其中安修士便體現(xiàn)了賽珍珠的文化間相互理解、尊重的觀念,而在夏女士身上則體現(xiàn)了“白種東方人”的特征。從中世紀(jì)的馬可•波羅到18世紀(jì)法國(guó)伏爾泰,西方對(duì)東方或中國(guó)的認(rèn)識(shí)和想象完全是烏托邦式的,以浪漫、崇拜、向往的文化心理矚望和神往著東方帝國(guó),把中國(guó)想象成“夢(mèng)幻般的國(guó)度”、“人間天堂”、“詩(shī)意國(guó)度”;從英國(guó)特使馬嘎?tīng)柲釒еY品朝見(jiàn)乾隆皇帝,到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1894年甲午海戰(zhàn)等近代一系列屈辱事件,西方對(duì)中國(guó)的認(rèn)識(shí)發(fā)生了反轉(zhuǎn),中國(guó)成了“陸沉”、“東亞病夫”、“怪異”、“野蠻”、“原始”和“專(zhuān)制”的代名詞。甚至,到今天,西方人也總是以怪異的眼光來(lái)看待中國(guó),視中國(guó)的和平崛起為“威脅”。在西方文化中,中國(guó)形象的真正意義不是地理上一個(gè)確定的現(xiàn)實(shí)的國(guó)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個(gè)具有特定倫理意義的虛構(gòu)的空間,一個(gè)比西方更好或更壞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間地獄。
同一個(gè)中國(guó),在西方文化中卻表現(xiàn)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形象,而這兩種形象在歷史不同時(shí)期重復(fù)出現(xiàn)在各類(lèi)文本中,幾乎成為一種原型。20世紀(jì)西方的中國(guó)形象,在可愛(ài)與可憎、可敬與可怕兩極間搖擺,從黑暗開(kāi)始,到黑暗結(jié)束;從一種莫名的恐慌開(kāi)始,到另一種莫名的恐慌結(jié)束。無(wú)論是美化拔高,還是丑化貶低,甚或是恐慌,在他們的心理中始終存在著一種觀念就是:我主,他客。而這種文化觀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偏狹性和武斷性。賽珍珠生活的時(shí)代正是處在西方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和認(rèn)識(shí)最反面、最負(fù)面的階段。她耳聞目睹著西方傳教士在中國(guó)的種族優(yōu)越論和文化霸權(quán)主義思想與態(tài)度以及中國(guó)社會(huì)各階層對(duì)西方人的復(fù)雜心態(tài),也讓她在文化觀念上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心理。她身處在兩種文化之間,深深體驗(yàn)著文化差異所產(chǎn)生的齟齬、矛盾、沖突甚至敵對(duì),同時(shí)她又誠(chéng)摯地相信兩種文化不是吉卜林所說(shuō)的“東便是東,西便是西,這兩者永不會(huì)相遇,……”,更不是“東風(fēng)壓倒西風(fēng)”或“西風(fēng)壓倒東風(fēng)”,而是能夠理解、互補(bǔ)和對(duì)話。賽珍珠對(duì)孔子“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這一思想非常認(rèn)同和贊賞,并表達(dá)了對(duì)儒學(xué)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的認(rèn)知。賽珍珠認(rèn)為,每一種文化都是獨(dú)特的,每種文化都有其長(zhǎng)處,當(dāng)然也有其短處,因此,它們應(yīng)和平共處,互相學(xué)習(xí)。正如學(xué)者劉海平所認(rèn)為的,“賽珍珠的跨文化視角使其兼具當(dāng)局者與旁觀者的眼光,在觀察事物時(shí)既能做到感情上親近又能保持理性的距離,……”正是這樣的文化身份,才使她在兩種文化之間始終是“局外”的“異鄉(xiāng)人”;也正是這樣的存在狀態(tài),才使她始終保持著“局外”者的冷靜和清醒,能夠超越一元化的孤立思維,形成和建構(gòu)起了思想和世界觀的混雜性、多元性和超越性。賽珍珠在多元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文化對(duì)比意識(shí)、“超越性”文化立場(chǎng)和思維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學(xué)觀和世界觀,與由“復(fù)雜性思維”所建構(gòu)的“世界文學(xué)”的精神是一致的和吻合的。因此,在“世界文學(xué)”新思維背景下,考察賽譯《水滸傳》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對(duì)跨文化的文學(xué)翻譯具有重要的借鑒價(jià)值和意義。
三、賽譯《水滸傳》的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
賽珍珠走上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的時(shí)期,正是西方文化強(qiáng)勢(shì)“入侵”中國(guó)之時(shí)。不僅西方人以西方小說(shuō)的標(biāo)準(zhǔn)衡量和否定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而且“五四”新文學(xué)的文學(xué)界也以西方化的“新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徹底否定“舊文學(xué)”。賽珍珠站在雙重文化的對(duì)比立場(chǎng)上,表達(dá)對(duì)中國(guó)小說(shuō)、文學(xué)和文化的看法,極力為中國(guó)小說(shuō)辯護(hù),并依此為參照省思西方文化、文學(xué)的傳統(tǒng)和習(xí)見(jiàn)。在賽珍珠看來(lái),界定一個(gè)民族的身份,依據(jù)的不是地理位置,不是種族,而是各自的文化和該民族的集體意識(shí),因此,要真正地了解一個(gè)民族和民族的個(gè)體,就有必要了解一個(gè)民族的文化,包括其中的風(fēng)土人情、風(fēng)俗習(xí)慣等。為了向西方呈現(xiàn)真實(shí)的中國(guó)(包括中國(guó)人、社會(huì)、文學(xué)和文化等),賽珍珠正是從文化對(duì)話的角度和立場(chǎng),逆“西學(xué)東漸”的潮流自覺(jué)擔(dān)當(dāng)起“東學(xué)西漸”的使命,創(chuàng)作以中國(guó)為題材的作品,把《水滸傳》翻譯成英文。賽珍珠為什么在其熟知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里選擇《水滸傳》進(jìn)行翻譯呢?這可以從她的《〈水滸傳〉導(dǎo)言》中見(jiàn)出她選擇的動(dòng)機(jī)。她指出:《水滸傳》是“中國(guó)最著名的小說(shuō)之一”,“雖經(jīng)歲月流逝,它依然暢銷(xiāo)不衰,充滿(mǎn)人性的意義”。她認(rèn)為,《水滸傳》是一本最具中國(guó)小說(shuō)特征的小說(shuō)。她針對(duì)西方評(píng)論界所指責(zé)的中國(guó)小說(shuō)情節(jié)方面存在混亂拖沓冗長(zhǎng)等問(wèn)題時(shí)指出,“生活中并沒(méi)有仔細(xì)安排或組織好的情節(jié),人們生生死死,根本不知道故事有怎樣的結(jié)局,又為何有這樣的結(jié)局;人們登上生活舞臺(tái),又走下去,沒(méi)有解釋?zhuān)蠄?chǎng)與退場(chǎng)之間也沒(méi)有明確的因果關(guān)系,以后也許會(huì)被人說(shuō)起,也許不會(huì)。中國(guó)小說(shuō)缺乏情節(jié)連貫性,也許就是一種技巧。這種技巧如果不是精心考慮的,無(wú)意中卻也是對(duì)生活本身的不連貫性的模仿。”她對(duì)中國(guó)小說(shuō)中人物塑造非常欣賞。她說(shuō):“他們對(duì)小說(shuō)的要求一向是人物高于一切。《水滸傳》被認(rèn)為是他們最偉大的三部小說(shuō)之一,并不是因?yàn)樗錆M(mǎn)了刀光劍影的情節(jié),而是因?yàn)樗鷦?dòng)地描繪了108個(gè)人物,這些人物各不相同,每個(gè)都有其獨(dú)特的地方。……人物描繪的生動(dòng)逼真,是中國(guó)人對(duì)小說(shuō)質(zhì)量的第一要求,但這種描繪是由人物自身的行為和語(yǔ)言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而不是靠作者進(jìn)行解釋。”在賽珍珠看來(lái),《水滸傳》無(wú)疑是向西方讀者展示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獨(dú)特藝術(shù)的最佳選擇。同樣在《水滸傳》譯序中,賽珍珠也表達(dá)了對(duì)梁山好漢“正義的強(qiáng)盜”的肯定態(tài)度:“這些人的故事一遍遍地頌揚(yáng)了勇敢的精神,表達(dá)了對(duì)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同情,也發(fā)泄了對(duì)為富不仁者和無(wú)道昏君的不滿(mǎn),盡管這些人自己從來(lái)沒(méi)有否定過(guò)他們是與國(guó)家作對(duì)的強(qiáng)盜和叛亂者。”在晚年,她更是明確地表達(dá)了當(dāng)年翻譯《水滸傳》:“……主要是因?yàn)檫@部作品揭示了中國(guó)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個(gè)方面,我稱(chēng)之為造反的一面,因?yàn)橹袊?guó)歷史上總有造反。的確,造反的權(quán)利一直都被認(rèn)為是一種‘不容剝奪’的權(quán)利……。由于到當(dāng)時(shí)為止我在中國(guó)的全部生活都處在這樣一個(gè)時(shí)期里,因此自然而然地會(huì)認(rèn)為《水滸傳》是一部與現(xiàn)實(shí)密切相關(guān)、乃至于非常重要的作品。”
賽珍珠對(duì)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動(dòng)蕩社會(huì)感同身受,親眼見(jiàn)證了底層人民的艱難生活。而這在她的史詩(shī)性作品《大地》中得到了比較真實(shí)的呈現(xiàn)。另外,對(duì)賽珍珠來(lái)講,水滸故事是最為中國(guó)人民喜聞樂(lè)見(jiàn)的,最有群眾基礎(chǔ)的,也最能體現(xiàn)中國(guó)人的人性、生活和思想。因此,為了試圖糾正近代以來(lái)西方社會(huì)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和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的負(fù)面認(rèn)識(shí),為了更真實(shí)傳達(dá)中國(guó)人民特別是底層人民的真實(shí)生活、感情和愿望,這樣一本從內(nèi)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藝術(shù)都堪稱(chēng)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典范的文本,當(dāng)然成為賽珍珠向西方展示中國(guó)小說(shuō)和中國(guó)人的首選。《水滸傳》在漫長(zhǎng)而復(fù)雜的成書(shū)過(guò)程中,出現(xiàn)了眾多的不同版本,諸如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以及七十回本,還有百一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賽珍珠為何從眾多的版本中選擇七十回本《水滸傳》呢?賽珍珠作出這個(gè)選擇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從客觀方面來(lái)看,賽珍珠在選擇版本時(shí),不可能不受到當(dāng)時(shí)水滸學(xué)術(shù)研究的影響。金圣嘆批本七十回本《水滸傳》是當(dāng)時(shí)流行程度最廣,影響最大,評(píng)價(jià)最高的版本。賽珍珠在譯本序中談到她受學(xué)者的影響,“沒(méi)想到我的選擇竟然與學(xué)者胡適博士不謀而合,他在近幾年重印該小說(shuō)時(shí)也選擇了同樣的版本。”
從主觀上來(lái)看,賽珍珠對(duì)底層人民的同情和對(duì)“造反”的認(rèn)同態(tài)度是與七十回本的現(xiàn)實(shí)意義相吻合的。賽在譯序中說(shuō):“我選擇的是第一種版本(指七十四本),因?yàn)橹辽俅税姹镜母骰馗袷浅鲎酝粋€(gè)折中主義的作者筆下。另外三種版本的添增章節(jié)講述了那些好漢的垮臺(tái)及他們最終被官府捉拿的經(jīng)歷,其顯而易見(jiàn)的目的是為了將該小說(shuō)從革命文學(xué)的領(lǐng)域中排除出去,以迎合統(tǒng)治階級(jí)的道德倫理。正像或許可以預(yù)見(jiàn)的那樣,這些增補(bǔ)部分無(wú)論是內(nèi)容還是風(fēng)格都與前70章的精神和活力格格不入。”賽珍珠把七十回本看作“革命文學(xué)”,看重它的革命主題和好漢英雄的義薄云天的豪俠之氣。此本的亂自上作、官逼民反、造反合理的革命主題,與賽珍珠對(duì)底層人民的同情和造反的認(rèn)同是一致的,也是賽珍珠“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理想的體現(xiàn)。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時(shí),采取了怎樣的翻譯策略呢?賽珍珠把《水滸傳》作為翻譯的首選,體現(xiàn)了她對(duì)中國(guó)文化價(jià)值觀念和審美感受的認(rèn)同,也體現(xiàn)了她致力于東西方文化之間平等、尊重和寬容關(guān)系的愿景與動(dòng)機(jī)。賽珍珠在《〈水滸傳〉導(dǎo)言》中表達(dá)了翻譯的初衷:“在我看來(lái),這本小說(shuō)的中文風(fēng)格與素材配合得天衣無(wú)縫,因此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我盡可能地采用直譯的方法。我的努力無(wú)非在于盡可能地保留中文的原汁原味,以使不懂中文的讀者至少產(chǎn)生一種他們正在讀中文原著的感覺(jué)。……但我已盡力保留原著的意義及風(fēng)格,甚至到了不惜將中文原著中一些了無(wú)生氣的部分盡量保持原味。”可見(jiàn),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時(shí)選擇的主要是直譯的翻譯策略,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和凸顯原著的語(yǔ)言風(fēng)格,讓西方讀者領(lǐng)略中文的韻味,從而達(dá)到文化互識(shí)、共存的目的。賽珍珠在“西強(qiáng)中弱”、“西方學(xué)者對(duì)于中國(guó)小說(shuō)幾乎還是一無(wú)所知。”
的背景下,堅(jiān)持“直譯”為主的翻譯策略,體現(xiàn)了她的勇氣,也顯示了她思維的超前性。賽珍珠跨文化的翻譯觀念與20世紀(jì)60、70年代興起的后殖民主義的翻譯觀不謀而合。“在后殖民翻譯理論看來(lái),翻譯本質(zhì)上就是語(yǔ)言和文化之間的權(quán)力博弈,而翻譯的過(guò)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圍繞話語(yǔ)策略———亦即異質(zhì)話語(yǔ)的保留或抹消———而展開(kāi)的斗爭(zhēng)。后殖民翻譯理論主張從弱勢(shì)文化譯入強(qiáng)勢(shì)文化時(shí)應(yīng)盡可能保留‘異’于譯入文化的話語(yǔ)特征,并將此視為破壞譯入文化規(guī)范、張揚(yáng)弱勢(shì)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在進(jìn)行跨文化的翻譯時(shí),賽珍珠和后殖民理論有著一致的主張,就是在由弱勢(shì)文化譯入強(qiáng)勢(shì)文化時(shí),要尊重弱勢(shì)文化,盡可能地保留弱勢(shì)文化的“異質(zhì)性”和特點(diǎn),以至于在跨文化的交往和對(duì)話中保持平等和獨(dú)特。因此,在翻譯文本中必然呈現(xiàn)出一種“雜糅性”或“混雜性”的特征,而“這種文本顯示出一些對(duì)于目標(biāo)文化來(lái)說(shuō)有些‘不正常/奇怪’的特點(diǎn),……一是保留原文中原文化的一些或所有特點(diǎn),從而在目標(biāo)文化中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文本類(lèi)型;二是反映了與目標(biāo)語(yǔ)規(guī)范相沖突的具體的(詞匯、句法、風(fēng)格等)文本特點(diǎn)。”
正如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愛(ài)爾蘭詩(shī)人希尼(SwamusHeaney)在談到“翻譯的影響”時(shí)所提出的:“翻譯過(guò)程中,譯者適當(dāng)拋棄語(yǔ)言的一般表達(dá)方式,將目的語(yǔ)的表達(dá)世界變得‘陌生’,以更新譯者和讀者已喪失了的語(yǔ)言新鮮感的接受能力,使譯者確實(shí)能夠?qū)⒃髦械牟町愋詡鬟_(dá)出來(lái),以促進(jìn)不同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7]363-364翻譯往往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也不可能盡善盡美。“直譯”是賽珍珠主導(dǎo)性的翻譯策略。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學(xué)者唐艷芳的博士論文《賽珍珠<水滸傳>翻譯研究———后殖民理論的視角》主要從詞語(yǔ)、句法和篇章三個(gè)層面進(jìn)行了細(xì)致且扎實(shí)的分析論述。在詞語(yǔ)方面主要體現(xiàn)于語(yǔ)言(字面對(duì)譯、固定詞語(yǔ)拆解、詞序及搭配的移植,以及譯文本身的陌生化表述等)和文化(陌生化的時(shí)間語(yǔ)匯、姓名及稱(chēng)謂語(yǔ)、詈詞、用典及其他文化語(yǔ)匯)等方面;句法方面主要體現(xiàn)在原文并列句式、句子順序、主體變換及句子節(jié)奏等;篇章層面主要表現(xiàn)對(duì)原著說(shuō)書(shū)體形式的尊重和對(duì)人物話語(yǔ)風(fēng)格的傳達(dá)。關(guān)于具體的案例可參看唐文。賽珍珠除了主要采取直譯的策略外,并未排除意譯的策略。比如:對(duì)于中國(guó)古代的官職,如“提轄”、“教頭”譯為“captain”,“五路廉訪使”譯為“anofficialoverfivedifferentdistricts”等;文中涉及佛教的特色詞,如“全堂水陸道場(chǎng)”譯為“anassemblyofpriestsingreatmass”,本是和尚做的佛事,在譯文中變成基督教神父的宗教行為。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對(duì)書(shū)名的翻譯。賽珍珠在《〈水滸傳〉導(dǎo)言》中講到了書(shū)名的翻譯,“由于中文原著的標(biāo)題異乎尋常地難以譯成英文,因此譯著的標(biāo)題并非是原著標(biāo)題的翻譯。中文里,‘Shui’一詞指‘水’;‘Hu’一詞指‘邊緣或邊界’;‘Chuan’一詞與英語(yǔ)中的‘小說(shuō)’相當(dāng)。至少在我看來(lái),將這幾個(gè)詞的英語(yǔ)意思并置在一起不但幾乎毫無(wú)意義,而且對(duì)原著有失公道。因此,我個(gè)人武斷地選擇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作為譯著的英文標(biāo)題。這個(gè)標(biāo)題恰如其分地表達(dá)了書(shū)中這群正義的強(qiáng)盜精神。”
賽珍珠用孔子的“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AllMenAreBrothers”)作為譯著的標(biāo)題。賽珍珠這一譯法,體現(xiàn)了“異化”和“歸化”的調(diào)和,既體現(xiàn)了她對(duì)中國(guó)文化和原著的理解,也是她對(duì)中西文化中所具有的共同思想的認(rèn)知和表達(dá)。從總體來(lái)看,賽珍珠自覺(jué)地盡可能地采取直譯的“異化”策略,以“陌生化”文本凸顯中國(guó)文化特色和文學(xué)特色;另外,賽珍珠在兩種文化、兩種語(yǔ)言轉(zhuǎn)譯中,也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進(jìn)行了調(diào)和折中的處理,采取意譯的“歸化”處理,以幫助譯入語(yǔ)的讀者消除閱讀障礙和對(duì)文化間共性的認(rèn)知。有時(shí)我們也會(huì)看到一些難以操作的地方賽珍珠表現(xiàn)出的猶豫兩難和無(wú)奈無(wú)力。賽珍珠對(duì)《水滸傳》的翻譯實(shí)踐體現(xiàn)了她在跨文化的翻譯時(shí)的用心、用力、兩難、尷尬和焦慮,細(xì)細(xì)考察其中有頗多值得考究引以思考的地方。如果說(shuō)直譯是異化,是對(duì)“異質(zhì)”的尊重的話,意譯是歸化,也是對(duì)譯入語(yǔ)文化的讀者接受習(xí)慣的考慮和照顧。譯本的好壞不是取決于對(duì)原語(yǔ)言文化認(rèn)定的完全的“異化”式的直譯,也不取決于對(duì)目的語(yǔ)文化認(rèn)定的完全的“歸化”式的意譯,而是基于對(duì)雙方文化的平等性認(rèn)知基礎(chǔ)上的兩者的“混合”和“雜合”。這樣的翻譯,才是更有利于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文學(xué)交流。賽珍珠雙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超越性”、“混雜性”的思維使其在跨文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譯介和傳播方面具有得天獨(dú)厚的優(yōu)勢(shì)。這一點(diǎn),在中國(guó)的西方傳教士、西方的漢學(xué)家以及中國(guó)翻譯家都是很難勝任的,也是很難比得上的。他們很難超越和擺脫本身的第一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甚或第三世界的“愛(ài)國(guó)主義”、“民族主義”的心態(tài)和思維,從而從跨民族、跨文化的視野持守尊重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同異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價(jià)值理念。總之,賽珍珠的雙重文化身份以及所形成的思想觀念正體現(xiàn)了莫蘭的“復(fù)雜性思維”,她所進(jìn)行的跨文化的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譯介對(duì)全球化時(shí)代的文化交流、文學(xué)交流提供了一個(gè)可資借鑒的范例。
四、結(jié)語(yǔ)
說(shuō)賽譯《水滸傳》是目前為止最好的譯本,很多人會(huì)不同意,但說(shuō)它是一本有特點(diǎn)有影響有價(jià)值的譯本沒(méi)人反對(duì)。賽譯《水滸傳》在美國(guó)出版后,引起轟動(dòng),非常暢銷(xiāo),之后《水滸傳》又相繼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傳播。可以說(shuō),賽珍珠在傳播中國(guó)文化和文學(xué)方面功不可沒(méi),成為“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強(qiáng)勢(shì)文化的全球化,是強(qiáng)勢(shì)文化對(duì)弱勢(shì)文化的殖民化。它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同質(zhì)化、統(tǒng)一化、標(biāo)準(zhǔn)化。自近代以來(lái),在面對(duì)西方強(qiáng)勢(shì)文化的入侵之下,我們經(jīng)歷了從被動(dòng)接受到主動(dòng)學(xué)習(xí)再到調(diào)整調(diào)和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盡管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有探索的掙扎、曲折、痛苦和糾結(jié),但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我們?nèi)谌胧澜绲目释团Γ踩〉昧讼喈?dāng)?shù)某删汀kS著綜合國(guó)力的提升,增強(qiáng)中國(guó)文化軟實(shí)力,重新塑造中國(guó)文化和文學(xué)大國(guó)的形象,成為當(dāng)前十分緊迫的任務(wù)。在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堅(jiān)持“引進(jìn)來(lái)”,同時(shí)還要“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就是翻譯。“我們當(dāng)下翻譯的重點(diǎn)無(wú)疑應(yīng)該由外譯中轉(zhuǎn)向中譯外,尤其是要把中國(guó)文學(xué)的優(yōu)秀作品翻譯成世界語(yǔ)言———英語(yǔ),……在這種中譯外的過(guò)程中,為了更為有效的實(shí)施‘本土全球化’戰(zhàn)略,我們尤其需要國(guó)外漢學(xué)家的配合和幫助,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使中國(guó)文學(xué)走向世界。”[9]而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有更多如賽珍珠這樣文化身份的人士所作的翻譯,無(wú)疑在推動(dòng)中國(guó)文學(xué)走向世界方面才更為有效和有益。
作者:陳海燕 單位:菏澤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