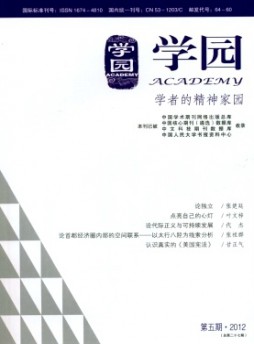學者流動性對文化研究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學者流動性對文化研究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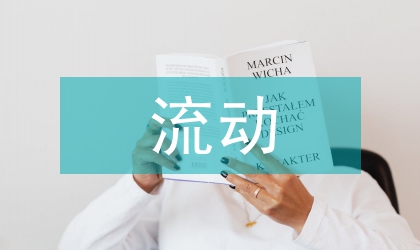
一、費斯克給澳洲文化研究帶來的影響
費斯克是文化研究的先鋒,也是文化研究與法蘭克福學派經典立場分道揚鑣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促成了20世紀80年代整個文化研究出現的“后現代轉向”[8]。費斯克在劍橋接受教育,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是威廉斯的學生,因而他的學術觀點與威廉斯一脈相承,從日常生活和社會經驗的視角來理解文化,并且深受霍爾的影響。由于70年代末與哈特利合著的《解讀電視》(1978)一書,費斯克逐漸展現了其在文化理論界的學術影響。在費斯克尚未到達澳大利亞之前,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澳洲并沒有正式的文化研究活動,只有零星的文化實踐。但是,盡管澳洲文化沒有像英國文化研究那樣有明確的起源機構和先行者,但歷史、文學研究、電影評論、傳播和媒體研究、期刊文化、工人教育協會、女權主義等都是促生當代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澳洲的文化研究學者們當時也已開始致力于界定具有澳大利亞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他們研究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實踐,包括報紙、電視、電影、劇院、雕塑等。1979年PeterSeparritt等編寫的合集《澳大利亞流行文化》就展現了這一早期發展的歷程,書中收集的文章涉及了收音機、電影、展覽、流行文學和節日等。所以,費斯克等人的到來使70年代末誕生的澳大利亞媒體研究專業人士與作為一股嚴肅的學術力量的英國文化研究不期而遇了。費斯克對澳洲文化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文化理論和研究范式的影響如果說階級問題是英國文化研究的主題,那么澳洲文化研究的特點則是凸顯大眾文化和文化政策,這與費斯克和貝尼特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費斯克繼承和發展了霍爾的理論,接受了霍爾可有多種解釋、積極主動的大眾和文化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場所等理論。他不僅將霍爾的理論在澳洲發揚光大,還結合澳洲的本土情況,逐漸提升了自己的理論。費斯克被認為是最早按照后結構主義傳統將符號學引入媒體文本之中的學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傳播研究導論》系統地介紹了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理論,至今這本書仍是該領域的經典教材。他在1983年發表的“SurfalismandSandiotics:TheBeachinOzPopularCulture”一文中,將沙灘看作一個文本,運用符號學的所指和能指進行多層意義的構建,對沙灘、草坪、城市,尤其是沖浪進行了意義闡釋,對自然和文化進行了區分。此時的費斯克仍然深受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在分析的沙灘的時候,階級還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他還引進了巴特(Barthes)的“快感”概念,極大地拓寬了文化研究的詞匯。費斯克曾說過:“意義的闡釋對霍爾來說太重要了,無法用快感理論來準確地解釋。快感可以視作是鮑德里亞(Baudrillard)所討論的大眾反抗的一部分,而霍爾極力回避。”[9]受巴特影響,費斯克將快感看作是大眾反抗的形式之一,而且快感的這部分功能是在試圖否認意識形態想要分配的權力和社會結構中意義傳播之間的必要聯系。結合澳洲本土的實際,費斯克以歐洲理論為源泉,借用布爾迪厄、德塞都、霍爾和巴赫金的理論,以歐洲人的視角,對澳大利亞文化現象展開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后霍爾時代”由此在澳大利亞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接受了霍爾理論的同時,費斯克也提出了另一個基本概念:文化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分離,即從文化經濟角度來分析文化現象,開拓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金融經濟流通的是財富,而文化經濟中流通的則是意義和快感。1987年,費斯克在澳大利亞出版了兩本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澳大利亞的神話:解讀澳大利亞大眾文化》(MythsofOz:ReadingAustralianPopularCulture,1987)和《電視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他透過霍爾的范式對文化進行解讀,力證存在于其中的權力關系,超越了馬克思批判的藩籬,充滿了對文本快感的分析。例如,他指出,沖浪可以視為一種反抗的幸福形式;而麥當娜成了一位性解放者[10],這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菲斯克的帶動下,澳大利亞學者們對形形色色的大眾文化現象展開了全面的研究。所以,可以說,正是在費斯克和約翰•哈特利的率領下,大眾文化在澳大利亞首先成為一支解放力量[1]26。1988年,費斯克轉戰美國,翌年出版了兩本重量級的著作《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和《解讀大眾文化》(Read-ingthePopular,1989)。這兩本著作雖然是在美國出版,但也帶有澳洲文化研究的印痕,有些分析文本都基于澳大利亞文化現象。費斯克在促進澳洲文化研究發展的同時也促成了自身的進步。多克爾認為,費斯克在80年代末逐漸從原先操縱性、被動性視角來考察和研究受眾轉而關注受眾的抵制和顛覆[11],并因此成為西方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2.創立了文化機構和文化期刊20世紀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亞的一些研究機構和期刊大大促進了其文化研究的發展。費斯克、貝尼特等著名學者的引入和澳洲政府不斷注資讓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日益學科化,尤其是在一些新興的邊緣學院里。例如,科廷大學自1987年開始的西澳技術學院,主攻文化傳播研究項目;莫道克大學的文化傳播與文化研究項目;格里菲斯大學的人文系里的文化傳播;南澳大學自1991年開始的文化傳播研究項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學自1988年開始的新南威爾士科技學院。西澳科技學院以費斯克為首,莫道克大學以哈特利和佛柔為主,格里菲斯大學的領軍人則是貝尼特。可見這些英國文化學者們在澳洲文化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1983年由費斯克牽頭,莫道克大學和西澳科技學院合辦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是澳大利亞第一本明確以文化研究為主題的期刊,主要刊發帶有澳大利亞本土色彩的文化理論與實踐、文化接受與創作、澳大利亞獨特文化所賦予的文化身份,以及澳大利亞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文章。很快成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中心論壇,并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推向了國際舞臺。TaniaLewis曾認為,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獲得國際聲譽,部分由于費斯克和他所創立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期刊[12]。1987年,該期刊被麥秀恩出版社(Methuen)購買,更名為《文化研究》,成為國際期刊,搬遷到美國,費斯克也隨之轉到美國。但費斯克一直是該期刊總編輯,為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論構建。文化研究學者們也互相合作,共同研究,通過期刊或研究中心形成彼此之間的交集,促進了澳洲文化研究的發展。
3.課程設置20世紀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亞相繼成立了新的科技學院,政府也鼓勵他們不斷創新,因而文化研究課程首先出現在這些新興學院里。費斯克所在的西澳科技學院就是其中之一。費斯克抵澳后大刀闊斧,開辦了文化研究課程,將傳播學、符號學和后結構主義都引入課程體系中,并確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奠定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地位。他的著作《傳播研究導論》,目前仍是該領域里的經典教材,其研究和分析文本的方法至今備受推崇。
4.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播散到美國費斯克所創立的期刊《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將澳洲文化研究推向世界,增加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國際能見度,打出了品牌效應。澳大利亞蓬勃發展、自具特色的文化研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越來越多的澳洲文化研究理論家成為《國際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編委成員。隨后,許多澳大利亞的學者流動到其他國家,例如,貝尼特再回到英國接任霍爾的職位,費斯克受邀到美國執教,墨美姬轉戰香港等,這不僅將澳洲文化研究播散到了世界各地,也證明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知名度。費斯克到美國后又出版了兩本專著,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成果帶到了美國。正如DavidMoley所說,費斯克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論影響了美國整整一代人[13]。這應該也包括澳大利亞整整一代人。
二、對中國文化研究的意義
知識分子的跨國流動對澳大利亞的學術構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澳大利亞與英國、美國同屬英語國家,相同的語言是學者流動的基礎,這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興起、發展到鼎盛和衰落過程,對中國的文化研究也有一些啟發和值得借鑒之處。首先,文化研究需要與具體國情和歷史相結合。費斯克曾說過:“作為學者的好處之一就是理論也可以很好地旅行,只是有點時差罷了。結果在過去的十年里,我很幸運能夠自由地穿梭在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之間,所以,我的游歷生活也在體現在我的一系列書里。”[14]費斯克將自己的游歷生活體現在著作里其實是與居住地的日常生活實踐相結合了,正因如此,費斯克才能在文化研究界里聲名顯赫,創建出獨具特色的理論和研究范式。而有學者已經指出,目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大量移植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用這些理論來生搬硬套中國的文化現象,結果造成了中西方語境錯位問題[15]。從這方面看,我們需要向費斯克學習,學習他對法蘭克福學派到伯明翰學派觀點的靈活駕馭與實踐應用。其次,學者之間的互助合作對形成體系化的學術思想至關重要。盡管澳大利亞學者的流動性較大,但他們在某個時間或者地點會出現許多交叉點,所以他們并非單槍匹馬,而是協同作戰,一起合作完成一系列項目和著作。本土知識分子也并非被動地接受引入的理論,他們與外來學者雙向交流。正是在頻繁的交換和交流之中,跨國和本土文化智識的交融催生了澳洲文化研究的繁榮。例如,費斯克就曾與哈特利、特納、鮑勃•海智(BobHedge)等多次合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論文,并創立期刊。費斯克幾部著作里的致謝部分每次都會提到澳大利亞的許多文化研究學者。如若中國學者也能協同合作,那中國的文化研究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次,澳洲文化研究繁榮的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在七八十年代也不斷地向文化產業注資,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澳大利亞文化研究90年代的繁榮。中國近年來開始注重文化產業,強調文化繁榮和文化強國,這勢必為未來文化研究注入活力。文化研究正在迅速全球化,我們需要從新的全球流動視角進行文化研究,將澳大利亞文化研究打上澳大利亞的標簽難免具有狹隘性,但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和學者大幅流動帶來的興衰,卻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近三十年來,中國大眾文化從興起到蓬勃發展,文化研究已逐步實現本土化,但國內學者們經常會談及歐洲文化研究,并引之為理論落腳點,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卻知之甚少。我們不僅要借鑒歐洲文化研究的理論,也要學習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實踐經驗,進而提升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本土結合,促進中國文化研究的長遠發展。
作者:李炳慧 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應用英語學院
- 上一篇:歷史文化為軸心的商業街區研究范文
- 下一篇:檔案文化研究文獻定量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