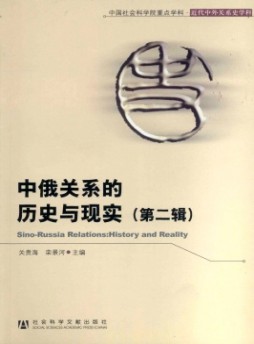現實主義精神之主潮的貫通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實主義精神之主潮的貫通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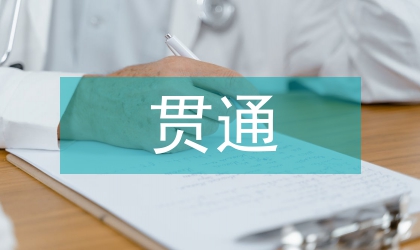
摘要:文學創作方法是作家藝術地認識和反映現實生活的基本方法,它客觀地存在于文學創作實踐的過程中,并通過文學作品反映出來。這些作品無論怎樣充滿了獨特的個性特征,但卻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著一些共同性的創作規律。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其創作理論的形成絕非偶然,絕非一成不變,尤其是現實主義精神的貫通與傳承有其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古典傳統現實主義、歐洲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疑問地構成了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三大理論淵源,并由此推動了“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建國后十七年現實主義文學和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三次高潮。
關鍵詞:20世紀中國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詩學
20世紀中國文學之于現實主義,遠非一個創作方法的簡單采借和運用,而是現實主義精神于文學內里織人與貫通的根本性問題。精神的內存和依憑,使得百年文學之詩學質涵有了鮮活的常青生命力。從史學格局看,現實主義精神的以一貫之和邊界的不斷擴容雖已為學界所共識,然而每當面臨文學新變時,其理性思維的游浮與疑慮又導掖著認知上的迷失與盲亂,致使現實主義這一知識學問題在百年文學中備受逼仄,幾經沉浮而又命運多舛。新近,直逼“三農”問題的《我是劉躍進》(劉震云)、《高興》(賈平凹)、《馬車》(孫惠芬)三部標志性作品的出現,又一次彰顯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及其在新的文學語境下其質涵的更加放闊與充盈。因此,挖掘和考理百年現實主義精神這一知識學理論淵源和藝術魅力,就有著廓清其理論困惑與浮躁的學理性認知意義。本文從兩方面就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百年貫通和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在不同歷史時期變形與放闊的流變史作一史線性闡發。
勾畫和考量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百年文學,其中國古典傳統現實主義的潛在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作為一種文學精神要素,深深地嵌入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每一個歷史進程中。高爾基認為:“在文學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兩個:這就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較早開創20世紀中國現代美學理論先河的梁啟超認為:小說一方面能“常導人游于他境界”;另一方面還能將人之種種生活狀態和思想感情“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后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范圍外者也”。王國維也認為:“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這些論述都是基于文學的兩分視界,但實際上無論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其內在現實主義精神的主體要素是明顯的。以中國文學的發展為例,《詩經》里的作品既有如《國風》關注社會的現實精神,也不乏有率意直言的浪漫情懷;《離騷》既體現了屈原愛國主義的現實憂患,也表達了其冰清玉潔的剛烈火焰;諸子百家中既有反映直接參與改造社會生活的現實行為,也充盈著諸子時代縱橫捭闔的生命豪氣;《史記》中既有大義微言、信筆實錄的春秋筆法,也有大風飛揚、義薄云天的人杰鬼雄。可以說,《詩經》和《離騷》分別開辟的寫實原則和幻奇手法,諸子百家和《史記》分別開創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精神,均深深地影響和規定了中國傳統文學的基本總體基調。漢魏兩晉時的建安風骨和玄學清談延續了這一基調,唐代的詩學氣象在李白和杜甫那里得到了相得益彰的繼承。宋代以后,中國文化中心東移南遷的態勢,整個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很大的改變。元、明、清既是中國封建社會回光返照、達到另一個光輝頂點的時代,又是中國封建王朝逐漸走向沒落、萌生新生的痛苦涅槃。從現實主義真實性的觀念之演變來看,從《史記》至《紅樓夢》就是一個從信實到真實、從實錄到寫實的逐漸演變和不斷分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從史學的信實現實提升為藝術的真實觀念、從實錄精神提升為寫實理論的過程。通過這樣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才最終確立了中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精神、審美體系和詩學原則。這說明,中國文學傳統中關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從創作精神方面的結合已經源遠流長,從審美體系的構成方面出現了雙水分流的淵源流變,從詩學原則方面呈現為雙峰對峙的壯麗景觀。
一般認為,中國文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主要以抒情文學為主流和正宗,相形之下,敘事文學一直居于次要地位。這既有客觀的社會方面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國文學傳統自身演化的內在原因。當敘述體式的小說被籠罩在史傳傳統的濃重陰影下,敘述文學的成長是多么的艱難!石昌渝先生這樣說:“史傳在文體中孕育了小說,換句話說,小說來源于史傳;但是史傳在精神上阻滯了小說的發展,小說克服了‘史統’的強大阻力之后才走上康莊大道。”史傳創制的敘事方式為后世文學提供了基本敘事模式,而史傳中記敘歷史的秉筆直書的最高原則和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創作精神。
綜上所述,從宋元至明清以來,業已成熟的中國式的現實主義或寫實派已形成了自身鮮明而固定的史學原則,即模擬性、逼真性和客觀性特征。相對而言,中國式的浪漫主義或奇幻派也有了自身的詩學標識,即虛擬性、奇異性和寄托性。這種既相互對立,又相互滲透,“幻中有真,極幻極真”,“說謊亦須說得圓”的創作理論,構成了我國古典主義文學的美學雙翼及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點,它對中國文學的后續發展產生了奠基性作用。雖然,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在世紀初曾以其反叛的姿態企圖和自己的傳統斷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毫無疑問,從較為長期的發展歷史來看,這種斷裂又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幼稚的。事實上,整個20世紀的文學就是在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框架下游走,其中盡管出現了諸如80年代中期以來的現代主義流派的沖撞,但其文學內里的現實主義精神仍見主色,所以說,離開了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淵源,就無法理解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
文學現實主義的另一分支,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形成對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顯在影響是一個基本的文學事實。20世紀初葉的許多作家如魯迅、瞿秋白、巴金等無不受其影響而寫下了許多批判指向至深的作品,既完成了20世紀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應有使命,又接替與延伸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19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之所以被稱為“批判”的現實主義,主要表現在其充滿了強烈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精神。從審美心理機制的總體構成來看分為兩種類型:即內傾型和外傾型。以司湯達、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為代表的具有內傾型審美心理機制的作家,以表現內部世界為側重點,重在對人類的心靈世界和精神文化進行分析、批判和反思;以巴爾扎克、狄更斯等具有外傾型審美心理機制的作家,以再現外部世界為側重點,重在對人類社會的生活現象和物質追求進行暴露、鞭撻和諷刺。19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具有鮮明傾向性的文學,就其作品的內質、創作觀和審美體系而言呈現出別一番意味:(1)作品的內質。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著重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生活現象和社會弊端給予大膽、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可謂鋒芒畢露,入木三分。從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總體背景來看,它正處于資本主義進行原始積累的不斷上升時期:一方面,它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代表的比較先進的生產力發展方向,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血腥殘暴、赤裸裸的貪欲,包括物欲、性欲和情欲也空前地膨脹起來。對此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種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又作為歷史發展的杠桿在不斷推進社會前進。正是在這二律背反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自身所孕育的一種反抗力量,從本質上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做了嚴厲的批判。因而,這種批判絕非是一種來自于外在的批判,而是一種源于內在本質上的揭露和批判。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陀斯妥耶夫斯基對“黑暗王國”人性的殘酷拷問,都讓人們對特定社會制度下的人性異化和扭曲產生了巨大的心靈震撼,令人不寒而栗。(2)創作觀。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創作觀念,建立在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他們無情地否定和批判封建統治與大資產階級的專制、殘暴,憐憫和同情普通人生活的不幸。但在政治理想上卻并不贊成階級和暴力革命。應該說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觀念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可視為是合理的。比如巴爾扎克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寫了一曲無盡的挽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呼吁各階級的“和解”,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表明這種“和解”在客觀上的不可能性。正是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時代的“浪子”身份,決定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這一基本特征。他們普遍在情感的直覺和理性的認知兩者之間的二元選擇中,表現出相互矛盾的態度和立場。假如我們都以階級和暴力革命來衡量他們,以社會主義的理想制度來要求他們,就不僅是幼稚的,而且是錯誤的。(3)審美體系。19世紀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它特定的時代條件下,在其特定的審美體系中,確立了現實主義文學基本的詩學原則。從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審美體系來看,求“真”向“善”是其審美體系構成中的最大特點。他們無論是立志作為社會歷史的“書記官”,還是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都是以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作為其最高的美學追求的。而在具體的從生活真實到藝術真實的不斷升華的過程中,他們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具體的詩學原則:即把非常宏大的歷史場景和高度典型的環境、人物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了對歷史的縱深感和美學的修辭方式的自覺體認。不僅如此,他們還從社會文化心理的角度展開了對人物形象的內在氣質、對時代精神的心理變動以及社會環境的精神氣象等等多方面的深情描畫。巴爾扎克對金錢時代的社會群體心理的透徹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對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的疏離和分裂狀態的雙向叩問等,所有這些關于心理描寫的精彩華章,作為一種具體可感的詩學原則,體現了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所達到的空前的藝術成就。
如果說,中國古典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是一種潛在的、存在于心理文化結構的深厚積淀中的話,那么,歐洲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影響則是顯見的,尤其是恢宏的史詩意識以及嚴肅而真誠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對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20世紀初人類文化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不僅影響了20世紀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格局,而且也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中國作為20世紀由落后、傳統的封建國家,開始向先進、現代的文明國家逐步實現艱難轉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深受這一巨大歷史進程的影響。于是,在大量的西方諸種思想理論流派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就成為人們的最高理想,成為中國思想解放、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指導思想。其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文藝觀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從哲學層面講,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一方面繼承了西方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也恰好適應了東方文化向天人相分思維方式轉變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在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深入考察的基礎上,為克服主客兩分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以主客不分的思維方式建立了對立統一的矛盾觀,從而形成了唯物辯證法。這就是說,在中國是以天人合一式的思維方式來理解唯物辯證法,以唯物辯證法自由通達天人相分觀來理解主客兩分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這樣最終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有效溝通和互相理解。應該說,這種內在的溝通深刻地影響著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形成,廣泛地接受著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及其相統一的哲學觀,如強調現實主義細節的真實性,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主張“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認為“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衡量最高的藝術標準是從“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出發;設想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等等。可以看到:這些顯示著現實主義文學元理論的觀點,從積極方面看,無疑對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形成是極大的補充,對作家們的創作實踐是一種及時的指導,對理解何為現實主義,怎樣才能實現和通達現實主義創作的至境是一種有意義的破解。正是這一現實主義主潮的涌動,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的相關理論體系才得以完善,現實主義創作實踐才如火如荼,才出現了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空前的新高潮。這是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范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導向與萌發,其意義顯而易見。可以說,在我國,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人到人們的廣泛接受,一直就在政治的和藝術的兩極擺動,甚至有時候兩極相通,這些有關現實主義的經驗與教訓,在漫長的文學長河中反反復復被爭論著。新時期以來,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傳統,也隨著社會現實的不斷調整,開始自覺地向開放體系靠攏。新時期文學的創作成就,就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的開放體系的文學新進程,其邊界的放闊與主潮的貫通是可持續的。
二、現實主義精神:邊界的放闊
現實主義文學三大理論主潮的貫通,不僅推動了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三次高潮,同時在新的文學語境下,現實主義的邊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放闊與深化。概括起來說,一是“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期,以新文學運動為起點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為界標,這是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一次高潮。二是建國十七年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期,以1942年為起點至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為界標,這是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二次高潮。三是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期,以1976年“四五”運動為起點至世紀末,這是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三次高潮。
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曾經有過聚散整合的演變歷程。前期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一水分流、雙峰對峙,期間經過了中國式的現代主義的短暫興起和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靠攏歸趨,現實主義漸漸成為無可爭議的主潮。這一時期,魯迅肩起了新文學現實主義的閘門,從黑暗王國給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帶來了一線光明。同時,在以魯迅思想啟蒙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中,還派生出了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派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形成了兩個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的文學潮流。總體來看,兩種潮流都繼承了魯迅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傳統,都以“啟蒙主義”和“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為出發點。所不同的是前者側重的是魯迅“為人生”的個性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后者則側重于魯迅“改良這人生”為實踐目的的集群主義和革命人道主義。這一潮流的創作以革命文學為開端,以左翼作家群為主體,以社會批判和政治革命為思想主題,從而形成以革命理想主義為支撐的社會剖析派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魯迅則是從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家轉變的中心人物。魯迅從現代思想啟蒙運動的先驅者,走到階級解放的思想領導者,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代表了具有現實力量的進步的文化階層。魯迅從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所特具的角色意識,走到現代工業文明影響下的小資產階級行列,規定了他作為當時進步文化的代表所能進行的實踐活動的特殊內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現代社會,使魯迅不可能把眼光只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現代生產關系矛盾的揭露上,更重要的是,魯迅在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兩極結構中形成的現代小資產階級(即市民等級)和傳統農業文明條件下的農民角色的國民性批判過程中成為了時代的先驅。魯迅文學活動終其一生,主要從四個方面對社會人生進行批判:從政治角度對中國現代官僚政治加以批判;從文化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載體加以剖析;從人格角度對介于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層面的現想人格給以匡正;從審美角度對中國現代人生存價值給以終極的情感關懷。這就使他能夠站在政治自覺的高度,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文化給予批判,對現代小資產階級精神支柱的理想人格給予鞭撻。所以,魯迅不僅是結合著兩個時代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超越了這兩個時代的文化代表。因為作為中國現代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現代中國沒有可供其依附的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這是他們的悲劇根源。因此,他們既沒有親娘,也吮不到乳汁,只好驀然回首,從中國傳統的小國寡民、心性自由的文學天地中看到了西方現代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在生產關系上的投影。于是,他們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洪流中,只好拐進“第三條道路”。另外,作為中國現代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右翼勢力,在他們無以強大到能控制整個社會局面的時候,他們不得不妥協并依附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現實,使他們從經濟和政治方面都無法強大起來。魯迅正是肩負了對中國現代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右翼勢力的雙重批判,他站在新的起點上,完成其思想實踐對兩個時代的結合和超越,從而推動了20世紀初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一次高潮。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發表,使現實主義文學發展到了又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已被民族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硝煙所彌漫,浪漫主義也已滲透在革命現實主義的理想中成為作品的傾向性呈現出來。這就使得這一階段的國統區、淪陷區、解放區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在不斷的爭鳴和創作實踐中獲得了成熟。以的講話為引導,確立了后來的革命現實主義大一統的局面。這是左翼革命文學在中國現代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的特定條件下政治革命需要的自然延伸;同時,以胡風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在自覺繼承魯迅所開創的以思想啟蒙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也從文藝思想理論中不斷成熟起來。正是在革命現實主義的理論旗幟下,的講話代表了政治現實主義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胡風的觀點則代表了“體驗現實主義”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解放區的作家趙樹理、丁玲、周立波等自覺地以的政治現實主義理論為指導來進行文學創作實踐,而國統區的路翎和七月派的一些作家則與胡風的體驗現實主義理論相應來進行自覺的文學創作實踐,從而推動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高潮的到來。在這些問題上,應該看到和魯迅有著同樣的歷史起點,但無疑比魯迅以更為激進的姿態,探索著中國強國立本的實踐途徑。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了中國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早年,踏遍千山萬水尋找革命真理和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從歷史經驗和實踐教訓中,看到了農民力量。這樣,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的共同召喚下,魯迅從思想認識活動的角度,達到了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體認,體現了從真到美的審美傾向;而從革命實踐活動的角度達到了對中國國民性的理性引導,體現了從善到美的審美傾向。魯迅和分別從各自的思想層面出發,在現實主義美學體系的旗幟下走在了一起,也就是說從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真、美的審美原則,到當代現實主義文學善、美的審美原則的流變中,在對藝術審美的共同追求下走到了一起。這是在前后相繼的歷史時期里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和詩學原則相互作用于審美體系的一次歷史發展。誠然,《講話》對新文學現實主義主潮的影響延續到了20世紀60年代,并促使文學創作很快出現高潮期。從20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整個審美系統出發,從創作精神、審美體系和詩學原則角度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者自身并沒有獲得長足、獨立的發展。兩者的完全統一還缺乏實踐契機。兩極相通,是建立在中介哲學的基礎上的。沒有審美中介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就必然會走向自身的反面。這正如,任何文化悖論的消解必須以文化悖論存在的矛盾相互發展、需要和化解為客觀的內在要求和基本條件。現實主義的“兩結合”理論在消解自身存在的思維悖論時,還必須以矛盾雙方的相互發展、需要和化解為客觀的內在要求和基本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相信:“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藝術應該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剝削制度廢除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土壤之中,因而它不可能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簡單發展,而應是二者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的融合”。因此,考量“兩結合”、現實主義理論創作的放闊,其理論要點的認識就顯得極為重要。
以天安門“四五”運動為起點,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標志,形成了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三次高潮。首先,表現在前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恢復和回歸上,主要以傷痕文學等為既相互交錯又互相興替的文學思潮。同時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和挑戰顯得生機勃勃,從而形成了兩種文學思潮互相補充、共競共存的審美格局。后新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不但使文學相對地走出了時代的中心地位,而且使20世紀中國傳統文學本體觀面臨著徹底解構的可能,文學真正成為一項艱難的事業。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考量,新時期以來的現實主義詩學特征,經歷了這樣一個“之”字型審美形態的演變過程,構成了三個易變動律的求異審美層面:即從真到美又從善到美的真善盡美的審美原則;從雅到俗又從俗到雅的雅俗共賞的審美格調;從情到理又從理到情的情理兼勝的審美情趣。
新時期文學的初始,是建立在對“”文學的“假、惡、丑”的批判上,并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理論邏輯起點拉開了審美的惟幕。首先用“真”來批判“假”——即虛假的政治社會理想,用“雅”來批判“俗”——即特定的藝術創作模式,用“情”來批判“理”——即極端的絕對理性觀念。這一走向首先集中反映在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兩個方面。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實際上就是要求重新確立以真和客觀實踐為標準,對政治路線、方針、政策以及社會理論、思想、觀念進行具體的價值判斷,從而對庸俗的社會學和機械唯物論的教條主義和固定經義的僵化作法做了徹底的批判。對于文學創作來講,就表現在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及其關系的討論,以最終確立以真為美的審美標準。新時期前十年以真為美的審美特征的形成,主要表現在對反封建主義這一思想主題的深入開掘上。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反封建主義的思想啟蒙運動是與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聯系在一起的話,那么,新時期的反封建主義的思想主題卻是與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嚴重失誤和重大缺陷聯系在一起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新時期前期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部分尋根文學中所表現出來的藝術結構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戲劇沖突性結構模式,一種是散文詩淡化型結構模式。前者是以1979年后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代表的敘述模式,主要以故事情節的矛盾沖突為主線來編織作品,其小說思維方式仍不脫二元對立的模式。但這種模式主要是從心理和思想層面上的沖突來構成戲劇沖突的原動力,較之于十七年文學從動作和行為層面上的沖突來構成矛盾發展的主要線索,反映出在藝術真實方面所構成的巨大差異。后者是以1983年前后出現的反思文學和部分尋根文學為主的一種敘述模式,主要是出于對人物心理的內在思想加以藝術表現的需要,其敘述模式受西化影響十分明顯。這種敘述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對十七年文學、文學等古典“三一律”式的極端化的一種解構。90年代后,隨著時代精神內在走向的趨動,人們開始以比較理性的目光審視思想啟蒙中的觀念上的誤區。對普遍把中國傳統文化一概視為封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觀念給予了理性的思索。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90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對真實性的藝術追求和理解,開始由比較單一的反封建主義的思想啟蒙主題向重建新的經濟、政治、文化倫理秩序轉移,也即由從真到美的審美原則向從善到美的審美原則的轉移。比如“新寫實主義”開創的非深度平面型藝術結構模式,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體驗、新市民小說創作中得以延伸,逐漸向深度立體型藝術結構模式實現轉移。同樣的問題反映在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的審美嬗變上。在新文學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使典型環境具有了各自所能包含的特定的深刻思想內涵。比如,魯迅筆下的魯鎮、未莊,其閉塞落后的環境給人以沉重壓抑之感,這是濃縮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后浸泡熏染下的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南方鄉村小鎮的典型環境。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由于建設新中國、歌頌新事物的主題,使典型環境的描寫具有了濃重的政治內涵、充滿了堅定的必勝信念。如路遙筆下的雙水村、黃塬、大牙灣煤礦等既落后閉塞又受現代風氣所感染的“城鄉交叉地帶”的典型環境,給人以與現實生活抗爭的勇氣和奮斗的希望。正是在新時期這樣一個具有較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卷中,在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形象就成為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最主要的詩學特征之一。在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典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很快打破了梁生寶(《創業史》)、高大泉(《金光大道》)式的單一化、程式化,一個階級一種典型的偏差,人們更多地是把社會主義的“新人”作為普通的但卻具有一定思想和個性的人來理解。從整個創作演變來看,先后出現過一種身份一種典型、一種身份兩種典型和非善非惡、亦善亦惡的典型化塑造模式。尤其在人物性格組合論命題的提出和西方現代小說美學中關于圓形人物、扁形人物等理論的吸納,應該說,這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有著很大的助力,使本時期一些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們都能普遍把人物形象的塑造放在歷史與倫理、感性與理性、正義與公理、大是與大非、善與惡、物質欲望與精神追求、個人與全局等二律背反的矛盾斗爭的砧子上乃至文化悖論的旋渦中,給予無情透視和殘酷錘煉,因而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而久遠的。可見,真的初始,美的推衍,善的趨成,構成了本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真善盡美的基本審美原則。
陳平原認為:“如果用民間文學(俗文學)、高雅文學(文人文學)和通俗文學三者的消長起伏把握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那么,20世紀以前基本上是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對峙。”可以這樣理解,文學的雅與俗,只有在雙方對峙中才獲得意義。因此,把雅俗文學的有限間隔作為一種重要文學現象來考察,就很有必要。實際上,正是雅俗文學的中心與邊緣的相對位移,才構筑了20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的重要的詩學特征。新時期以來,由于審美屬性的強化和新的美學原則的不斷崛起,雖然政治文學的單一審美屬性被打破,但文化的“雅”化一時還不能完全被人們所認同,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商品經濟的誘致,通俗文學便乘勢而興,于是促使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在雅俗互動中交替崛起,形成了以大量雅化的通俗文學和俗化的高雅文學兩極共構的景觀。這一走向表現在以下問題上。(1)創作主體意識的演變。從新文學運動的“新民”意識到當代文學中的呼喚“新英雄人物”,創作主體意識的著眼點實現了從俗到雅的變遷。新時期以來,從文學中的“假大空”和“高大全”式的新英雄人物身上下移到了有血有肉、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身上,創作主體意識的審美視角的進一步下移,表明了新時期文學從雅到俗的內在轉換。這種轉移到了90年代以后,又以新寫實小說等人物角色的徹底下移,體現了作家創作主體意識的平民化與當下的底層寫作熱點,昭示著作家創作主體意識的新的企圖,這表明當雅文學沉入谷底時,另一種雅化的創作主體意識又會重新崛起。(2)作品敘述語言的變化。新時期前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反封建主義思想啟蒙的文學主題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時代任務共同規定了政治化敘述話語在一定時期和特定文體中的存在。對此的解構是以大量的通俗文學的興起,西方現代文學的引進,古代漢語語言功能的重新發現和其他各種藝術語言的大膽吸納為開端的。通俗文學中大量的俗語、方言等,使這種被政治化觀念嚴格過濾后的純凈的敘述話語變得不再純凈;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另類“陌生化”敘述語言,更使政治化敘述話語的表述功能顯得捉襟見肘;古代漢語質地厚重、凝練含蓄的語言特性使政治化敘述話語顯得語義淺狹;而其他藝術形式如音樂語言等的移用,加強了語言的旋律感、簡明性。這些優長之綜合使現實主義文學語言表達更為開放與鮮活。(3)讀者接受類型的聚散。有論者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新文學接受史主要經過了“啟蒙”、“正視”、“主導”三個階段。“啟蒙”是作家以一種“俯視”姿態看待讀者大眾,“正視”則是以平等甚至欽仰的姿態去看待讀者大眾,“主導”則是指以工農兵大眾為作品主人公的主導性創作傾向。如果說,上述三個階段是新文學的讀者接受類型的話,那么,建國十七年文學接受史則主要經歷了“正視”和“主導”兩個階段。而新時期文學的讀者接受類型卻有其聚散兩間的特點,即有對建國十七年文學的“主導”型接受類型的批判,又有與讀者從眾關系的新變化。如前期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關注和參與現實的激情,尋根文學里作家們看到了自身所負載的同樣深重的精神奴役的創傷,90年代中后期,以新寫實小說為開端,標志著作家平民意識與參與現實生活的審美視角的出現。這樣就造成了80年代與90年代之間的一種差異:由新時期前期的熱情關注大眾和啟蒙民眾向后期的只關注個體自身的物欲和情欲轉變;由新時期前期的作家具有明確的價值判斷和道德立場向后期的亦善亦惡、非善非惡的純客觀中立的立場轉變,并把淡化政治、躲避崇高、消解深度、反審美作為一種時尚。至此,文學由“雅化”沉淪到“俗化”的最低點。而90年代后期以新現實主義文學為起點,重新調整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系和以雅抗俗的努力,又顯露出了新的端倪。
新時期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為契機;另一方面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傳統觀念給予批判。表現在文學創作中的理性思維,前者以提倡真實性為文學審美的基本前提;后者以張揚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為文學審美的基本態度。作為以反封建思想啟蒙為基本主題的80年代文學,正是以理性的審美意識,吸納了西方現代個性主義和個體自由觀念,以及文學主體性理論來匡正“”時期以情的擠壓學理的偏執,從而以承認個體的欲望為現代人生的基本權利、正當要求和人性的重要內涵的學理指歸,實現了從情到理的審美情趣的演化。1985年,尋根文學的衍起,文學主體性與“文化熱”的粘連,使得以情反理的審美情趣發生轉向,即由絕對的個體主體性原則通向了絕對理性原則。因此,文學創作再次充斥著大量的政論色彩和文化決定論的迷霧。然而,90年代以文學個人的價值實現為中心的泛道德和價值觀念,以拒絕中心、躲避崇高以及價值中立等方式來回避價值觀和世界觀的重建,使理性觀念急落下移,再次伸向了個性自由觀念的情感回路。與此同時,90年代后期,被譽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新現實主義”文學,又有從這種以個人價值實現為中心的泛道德化觀念中走出來的跡象,如談歌、劉醒龍、關仁山、何申等作家的創作。這從一個側面透露出9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再次從理到情的演變,可見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的審美情趣是在一個不斷從情到理,從理到情的觀念滾動中推進,其情理兼勝的審美效果是為鮮明。
綜上所述,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在以下三個層面上產生了三大審美流變:一是創作精神。從80年代的思想啟蒙到90年代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演進。這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規律的歷史過程,是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審美體系時代精神的本質對象化;二是審美體系。以真為美向以善為美的轉折,在審美活動中尋求主觀世界的合目的性和客觀世界的合規律性的統一(美)的轉折過程。這標志著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真善美審美體系的本質自由化。三是詩學原則。從真實性、典型性和傾向性角度,界定真善盡美、雅俗共賞、情理兼勝的審美特征。這標志著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審美體系多樣化修辭方法的本質具象化。現實主義作為惟一貫穿了一個世紀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三個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是經由分化而獨立、獨立而強化、強化而斷裂之后,又開始由斷裂而強化、由強化而獨立、由獨立而淡化這樣一個演變過程。作為20世紀一個最有影響的文學思潮,它的文本求異的演變史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