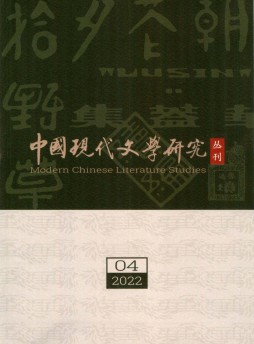現代文學角度下農民觀與文學修養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文學角度下農民觀與文學修養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大農民的麻木愚昧不僅是他們自己的不幸,也是國家與民族的不幸。如果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覺醒,而要去追求社會革命的光明前景,那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即使革命發動起來,也許都無法取得預期的目標,甚至出現事與愿違的悲劇結局———要么是阿Q式的革命,要么像《風波》的隱喻敘事一樣,革命的果實反而被地主等權貴階級所摘取,要么像《藥》的隱喻敘事一樣,革命不但最終未能拯救農民,革命者反而讓被拯救者所吃掉,被拯救者的麻木不仁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反革命的幫兇。因而,在廣大作家看來,在那個時代,農民最為核心的問題還不是貧困與健康的問題,而是他們能否覺醒、如何覺醒的問題,亦即思想與精神的問題。在當時的情況下,解決這些問題最為有效的辦法無非是思想啟蒙運動,這也是魯迅當年棄醫從文最為重要的原因。在左翼文學的鄉土敘事中,農民常常處在尖銳的階級矛盾之中,甚至也面臨著慘烈的民族矛盾。在中國共產黨的引導與教育下,他們開始覺醒并走向反抗,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中值得依賴的人群之一。對他們來講,反抗與革命不僅僅是理想信念問題,也是生存的需要。如茅盾的《子夜》中雙橋鎮的農民在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奮起反抗。雙橋鎮農民的集體斗爭不僅使資本家吳蓀甫鄉下的一些產業蒙受重大損失,也打破了吳蓀甫三年來苦心經營的王國美夢。《春蠶》通過農民老通寶豐收成災的悲慘故事,告訴人們,農民日子過得好還是不好,不僅僅取決于收成的好壞,還取決于是否存在階級壓迫及其程度的大小。
因此,在階級壓迫依然沉重的情況下,農民真正的出路,還要在豐收之外去尋找。葉紫的《豐收》、《電網外》、《山村一夜》都是以大革命前后的湖南農村為背景,表現農民在殘酷的生活面前從覺醒到反抗的過程。①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通過對農村婦女春寶娘形象的刻畫,從反面說明了沒有反抗意識的農民是難以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尊嚴的。洪深的劇作《農村三部曲》以江南農村為背景,在表現廣大農民不幸遭遇的同時,也展示了他們從不幸中覺醒,并走向自發反抗的歷程。艾青詩歌《中國農村底故事》與《大堰河》唱出了特定時代里中國農民的憤懣情緒,為1930年代的詩壇帶來了抗爭氣息。“九•一八”事變之后,蕭軍、蕭紅、舒群、端木蕻良、白朗、羅烽、李輝英等東北作家還在國破家亡的沉痛體驗中,書寫了東北人民保家衛國的英雄事跡。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中,就出現了一群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農民戰士形象。
無論是在革命斗爭中迅速成長起來的戰士陳三弟、崔長勝,還是作為這支隊伍中層指揮員的鐵鷹隊長,都是農民出身。他們不但英勇善戰、斗志堅強,而且還是抗日隊伍的中堅力量。鐵鷹隊長率領隊伍伏擊了日軍運送給養的火車,奪得了大批火藥,敵軍聞訊襲擊了革命軍的根據地,大肆搶掠,進行圍剿。在此期間,革命軍一邊發動農民群眾參軍參戰,一邊決定撤退,留下知識分子出身的帶兵人蕭明保護傷員,但蕭明此時正與女秘書安娜戀愛,斗志渙散。在關鍵時刻,還是陳三弟挺身而出,帶領留守部隊掩護并轉移了傷員。這一構思不但凸現了農民的覺醒、成長及其堅定的革命信念,也帶有一點知識分子改造的意味。《八月的鄉村》雖然描寫的只是北方人民抗日斗爭生活的一個側面,但它卻代表著當時全中國抗日軍民的精神風貌。蕭紅在《生死場》中,也寫了東北三省人民的覺醒。另外,蕭軍的《第三代》、蕭紅的《呼蘭河傳》、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駱賓基的《幼年》、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郁》、羅烽的《呼蘭河邊》等作品也真實地再現了東北人民的悲慘命運及其被異族統治的痛苦與對之反抗的怒火。這些作品既屬于左翼文學的范疇,也被稱之為中國抗戰文學的先聲。在“東北作家群”的鄉土小說中,“‘抗日話語’及其強烈的民族意識是其鄉土敘事的顯性層面”,“‘階級話語’成其為鄉土敘事的‘左翼’標識”。
②1930年代,除左翼作家之外,還有許多作家也以不同的視角表達了他們對農民的關注。老舍的《駱駝祥子》講述了進城農民祥子的悲慘遭遇,曹禺的《原野》講述了民國初年一個農民復仇者的故事,這兩部作品都揭示了尖銳的階級矛盾。總之,在尖銳的階級矛盾與沖突中,1930年代的鄉土敘事揭示了充滿階級仇恨的農民從覺醒走向自覺反抗是歷史的必然。1940年代,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鄉土敘事中,農民既面臨著民族矛盾,也面臨著階級矛盾,他們是真切感受到國恨家仇滋味的群體,也是抗戰的中堅力量之一。老舍的《四世同堂》在盧溝橋事變的背景下,講述了北平淪陷后,畸形世態中,北京各個階層、各色人等的榮辱浮沉、生死存亡。雖然《四世同堂》主要寫的是抗戰背景下的北平市民社會,但作者的文筆也觸及鄉村。國難當頭,普通農民也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拒絕使用偽幣。丘東平的《第七連》和《我們在那里打了敗仗》以“八•一三”淞滬抗戰為背景,表現了農民出身的抗日軍官和士兵的愛國精神和頑強的戰斗意志,同時也揭露了國民黨當局對日作戰中倉促應戰、武器裝備低劣、士兵缺乏軍事訓練等導致戰爭失敗的不良現象,揭示了國民黨長期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惡果,這些作品彌漫著戰爭失敗的濃重的悲劇氣氛。沙汀的《還鄉記》通過青年農民馮大生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廣大農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相互交織的復雜社會關系和雙重壓力中,由個人反抗走向集體斗爭的歷史進程。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和《牛全德與紅蘿卜》受到學界高度重視的原因之一,也是成功地運用了活潑生動的群眾口語,寫出了農民在抗戰中從覺醒走向斗爭的轉變過程。從這一時期國統區與淪陷區文學鄉土敘事的總體情況來看,廣大農民常常面臨著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雙重壓力。在不幸的遭遇中,他們不但由覺醒走向了反抗,而且不少人還表現出了較高的政治覺悟———懂得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輕重關系。因而,有學者認為,從“五四”到抗日戰爭,鄉土文學的敘事主題也從“啟蒙”轉換到了“救亡”。“五四”時期的鄉土敘事,不僅是對農民自身的啟蒙,也是對建構在“鄉土中國”之上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召喚,而抗戰文學則是通過對“救亡”的敘述,最終完成了對于現代民族國家形象的重構和確認。
③在1940年代解放區文學的鄉土敘事中,農民具有高度的政治優越感,他們取得了當家作主的權力,已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區文學面向工農兵,深入生活,積極開拓鄉土題材,深化鄉土敘事主題,創作了眾多優秀作品。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賀敬之的歌劇《白毛女》,戰斗劇社的歌劇《劉胡蘭》,李季的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都涉及到鄉土敘事。“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取得了主人公地位。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兒和劉胡蘭、王貴和李香香等人物形象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新一代農民的成長。他們從被壓迫、被損害的對象變成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成了被歌頌的對象”。
④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中的青年農民牛大水積極追求上進,有自我犧牲精神,最終成了革命英雄。柳青的《種谷記》以陜北農村王家溝集體種谷的事件為線索,展現了解放區農村生活的一個側面。孫犁的《荷花淀》塑造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農村婦女,水生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熱愛勞動,有嫻熟的勞動技能;她體貼丈夫,溫柔細心;她開明穩重,剛毅勇敢;她關心國家興亡,并最終投身于抗日洪流。水生嫂作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富有魅力的典型人物,有說服力地解構了傳統文化對農村女性的偏見。傅鐸的歌劇《王秀鸞》中的王秀鸞一面投身抗日活動,一面積極參與生產。她熱愛勞動、勤儉持家、孝敬公婆,積極支持丈夫參軍上前線,也是一個新型勞動婦女的典型形象。在《荷花淀》中,男性雖然居于次要地位,但仍然是申明大義的堂堂漢子,如水生像他的父親一樣,思想豁達,英勇果敢。大敵當前,他沒有過多地“惦記”家事,而以國事為重,決然去干“光榮事情”。解放區反映和表現“”的小說以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為代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一系列農民形象,作者把農民放在尖銳的階級矛盾中,一方面歌頌了其要求翻身、追求進步的本質,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其身上的弱點與缺陷。在小說看來,農村不僅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且要引導和幫助廣大農民在斗爭中不斷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點和缺陷,逐步成長起來。《暴風驟雨》成功地塑造了趙玉林、郭全海等貧苦農民形象,在黨的領導下,他們通過有力的斗爭,最終鏟除了韓老六與韓老七等地主惡霸勢力,使黨的政策落到了實處。《小二黑結婚》中的小二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張裕民、《暴風驟雨》里的趙玉林、郭全海都是進步農民的典型形象。他們已經是革命信念最堅定的人群,他們不僅是土地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人,還是進步、未來、光明、革命的象征。這些農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進步的、疾惡如仇的人,他們形成了這個國家中最先進、最有發言權的階層。
作者:李科平單位:渭南師范學院教育與公共管理學院
- 上一篇: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研討范文
- 下一篇:現代文學課教學革新思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