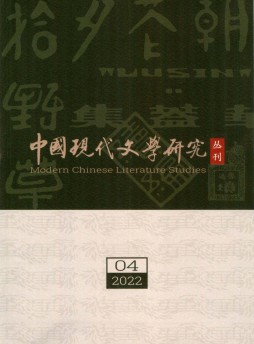現代文學中的海洋認識論述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文學中的海洋認識論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先鋒與日常:現代海洋意識的內在向度
作為一個開端的五四文學,其在現代中國的多重意義已多經闡發,不過由于晚清視野的引入,“五四”在諸多方面獨領的開創性意義似顯模糊。然而,如果審視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海洋書寫,猶可感到五四時期一種突變的新質所襲裹而來的沖擊。應該說晚清以降,一種建基于新的物理時空和世界版圖之上的海洋認識已為國人所習得,由《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勾勒的世界形勢,由“只身東海挾風雷”(秋瑾)、“茫茫煙水著浮生”(蘇曼殊)的人生志途帶來的海洋行歷,由“太平洋舟中望月”帶來的“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黃遵憲)的渾茫感受,這些均非五四的新見。但,中國人對于生存其間的空間體認方式的劇烈變遷,引發心理、文化和歷史體驗的全面變更,“海洋”所象征的一個新的時空敞開了,它激烈重組中國人關于“世界”的想象和體認,這卻是五四典型的思維特征。這在五四的海洋書寫中,則不僅體現為“海洋”意象的大量涌入,更在于這個“海洋”承載著嶄新的現代意識、文化氣質和生命覺悟,以及五四通過賦予“海洋”內在價值和大寫的意義,而建構起新的價值秩序和不可逆的向度。
五四文學中最具沖撞力的海洋書寫無疑來自郭沫若,他筆下的大海激情迸射地傳達了新生體驗:“青沉沉的大海,波濤洶涌著,潮向東方/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喲———新生的太陽。”(《太陽禮贊》);充滿了迥異于日常經驗的力與美的自由想象:“無數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情景喲!/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帶來了狂熱的顛覆力和無限的生命感受:“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涌著在呀!/萬籟共鳴的symphony。”(《筆立山頭展望》)。在郭沫若筆下出現的大海,顛覆了天地俱足、純寧歸化的古典感受,卻接續了西方浪漫主義以來拜倫、海涅、普希金等建構的那個激涌叛逆的大海。同時,在徐志摩的《海韻》和廬隱的《海濱故人》里,向往自由的新女郎徘徊在海邊,“對著海浪低吟,對著海潮高歌”(《海濱故人》),大海象征著自由的遠景,帶來新生活的氣息。而冰心訴說的大海,純凈、深美、寬博,是愛的哲學的化身:“我要至誠地求著:我在母親的懷里/母親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
郭沫若連同徐志摩、冰心、廬隱等人,這五四一代將新生萌現的自我表達與熱情充沛的海洋書寫融合,建構了一個象征著新生、自由、浪漫、愛與美等現想的“大海”,一個承載著簇新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識的新自然。于是,“大海”成為了具有深度內涵和理想意義的符號,成為召喚生命朝向和價值信念的文化密碼。它生發了中國人對大海所象征的廣闊世界的全新想象,形塑了向外憧憬、希翼探尋的現代中國新的海洋意識。從此,面向海洋、仰贊大海與追求新生、理想、愛、自由與美一樣成為某種不可逆的現代意識,成為具有潛在的自我規范性的生命向度,逐漸于意識和無意識之中成為某種“應當如此”的現代中國人的價值信條和人生模式。斷裂傳統、對抗現實、以激進的情緒破壞舊的文化秩序、以挑戰性的姿態張揚新的價值意念,這是五四文學突出的精神特征,其中內蘊著強烈的先鋒意識。這種對過去的激進批評,以及對變化和未來價值的無限推崇具有強烈的現代性特征,它與西方現代自浪漫主義以后崛起的“先鋒派”具有內在相通的精神氣質。西方的“先鋒”起源于軍事術語,以激烈挺進的軍事前鋒的形象標榜自身的特征,“強烈的戰斗意識、對不遵從主義的頌揚、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對于時間與內在性必然戰勝傳統的深信不疑”。
這一先鋒派起源于啟蒙主義的知識先鋒,在浪漫派處獲得了情感和想象的支持以挑戰世俗,隨后廣泛滲透在政治和美學領域,并衍化為未來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各種激進的美學實驗。先鋒意識的基礎是時間和進步的觀念,突破自身所屬的時代,反抗現存凝固的制度,為未來奮斗,以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抵近精神目標。對于五四文學來說,其對海洋理解和書寫就內蘊著強烈的先鋒氣質。將海洋的空間性存在化為時間性的意識,對空間做時間化的理解,賦予其發現和產誕的意義,是五四海洋書寫的特征。一個標志是“海上日出”的景象獲得大力的書寫,如郭沫若的《太陽禮贊》:“青沉沉的大海,波濤洶涌著,潮向東方/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喲———新生的太陽。”在那一刻,詩人體驗到“時間開始了”的瞬間,擁有嶄新意義的世界景觀突然爆現的狂喜。富有五四精神的青年巴金,也這樣描述海上日出“太陽慢慢透出重圍,出現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紫色或者紅色。這時不僅是太陽、云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這不是偉大的奇觀么?”
在新生主體充滿自信的視景中,混沌的海洋霎那間內爆出一種光明的新景觀,這世界和自我更新的激越體驗宣告了時間進步的起點。先鋒意識要求摧毀靜態凝固的秩序,崇拜“動”的精神。在五四以后的海洋書寫中,波濤、海浪、潮頭這些動感形態,往往被激情地呈現。郭沫若的《鳳凰更生歌》中開場即詠嘆“昕潮漲了,昕潮漲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漲了,春潮漲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這是“動”的精神的贊歌,動的潮流載來了光明和更生,“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動的實在之表現”,宇宙萬物由此體現出了生發不息的自由意志。這種對海洋之“動”的精神的抒寫,彌漫在此后的各個時期,艾青曾這么寫道:“你也愛那白浪么———/它會嚙啃巖石/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櫓/撕碎布帆/沒有一刻靜止”(《浪》);蔡其矯亦寫到“永無止息地運動,/應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一切都因你而生動,/波浪啊!沒有你,天空和大海多么單調/……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誰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統治?”(《波浪》);舒婷也這么說:“大海變幻的生活/生活洶涌的海洋”(《致大海》)。從20世紀30年代的艾青到20世紀60年代的蔡其矯直至20世紀80年代的舒婷,從涌動不息的海洋中發見常變常新的運動意志和激情自由的進步力量,在不可遏制的激情中呈現了勇往直前的先鋒性。
這種海洋意識中的先鋒性對于20世紀的中國文化有著深刻影響,塑造理想大海的激情書寫并沒有因為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革命化所中斷,卻因為高爾基的《海燕》和蘇聯民歌如“從前在我少年時,朝思暮想去航海”等的流傳而更增激越動人的情調。當然,又一次面向海洋、詠贊大海的熱潮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這與后擺脫文化禁錮、重新探求自我價值的思潮密切相關。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與朦朧詩人舒婷的《致大海》之間,卻不難發現深度象征模式背后那種希翼探尋的精神相通,那種不平靜的內心對理想價值的渴望,從“啊,大海/我真想張開雙手/縱身跳入你的波濤中/但不是死亡/而是永生”(郭小川)到“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把我的心緊緊貼上你胸膛的風波”(舒婷《海濱晨曲》),可以看到充滿意志的主體之不可逆的生命向度,大海正標志著那個內在的方向。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王蒙復出后的小說《海的夢》里那個年屆五旬的翻譯家,經歷了謬不可言的人生,耽誤了青春和事業之后,依然如此執著熱切地奔向大海,“大海我終于見到你了,經過半個世紀的思戀和磨難,你我都白了頭發———浪花!”
在日常人生中灌注強烈的理想精神,在不可遏止的內在激情中不斷奔向精神目標,探索、沖突、叛逆,建立一種有意志有向度的生活。這原本屬于少數前驅者的孤獨奮激的人生樣態,卻幾乎貫穿20世紀現代中國,成為啟蒙———革命浪潮中的主流。于是,理想之余、激情之外,生活在日常感性經驗中,以現實欲求之解決為依歸的人生反而在文學書寫中、在文化表達中處于隱匿、潛行、失聲的狀態。有的學者即將晚清以來的文學分為日常與先鋒兩個態勢,“一種是依循社會生活發展變化而自然演變的文學主流,一種是以超前的社會理想和激進的斷裂態度實行激變的先鋒文學。”
以海洋書寫而言,晚清描寫僑民下洋生涯的小說《黃金世界》、《僑民淚》等,其中的海外想象多是“聞南洋爪哇島多金屬礦及金剛石,以我國絲茶易彼土貨,獲利倍蓰,不覺毅然挾貨附舟行”(《僑民淚》)。20世紀40年代黃谷柳的《蝦球傳》中描寫的海上生活也充滿著黑幫、飄泊、碼頭爆倉等雜穢的人生百態。在現實生計功利驅推下隨流逐波的生涯,是不會給海洋涂抹上浪漫瑰麗的理想色的,它凸顯出海洋平凡卻切近人生的一面。在五四時期楊振聲的《漁家》《玉君》等小說,即以對濱海漁家的寫實性描述著稱,從中可見晨昏雨雪中的海上風景,以及種海網釣的勞作細節,這提供了海洋的一付現實主義面影。此后眾多小說中的海洋敘寫也一直延續著刻畫海的現實面影。但,真正以裸露的生命扎進海濤,被它燒烤又冷卻,在海潮、急流、暗礁、漩渦之中摸索大海隱秘的脾性,從而真切刻骨又激情迸射地展現大海深邃的真實,這是鄧剛的《迷人的海》的貢獻。作為曾把生命拋進大海碰運氣的海碰子,鄧剛熟稔那片拼命的海,他的身體記憶中存刻著海的親熱和威力,他所揭開的大海是奇絢的力與美、感恩的寬博和嚴峻的兇狠的混一,因而迷人。經過血肉絞搏,以生命真實抵近海洋復雜的內蘊,呈現它真實不可測的生存本相,由是鄧剛的海充滿了生命直感和現實深度。
然而,從日常中祛除詩意,從現實中消除象征,解散大海形象的魅力感召,切斷大寫的海的建構傳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這個翻轉。第三代詩人韓東的《你見過大海》以“見”和“想象”的對立,裂現出兩種認識大海的方式。“你見過大海/你想象過/大海”,在親見大海之前通過想象賦予其崇高和浪漫,在韓東看來這是虛幻的,真實的是“你不是/一個水手……你不情愿/讓海水給淹死”,人們面對大海暢想時,卻熟視無睹一個日常真實。韓東說“就是這樣……頂多是這樣……人人都這樣”,你以為自己能實現超越,最終還是要回到世俗中來。在消除層疊的詩意建構以后,日常的海不過那個蹩腳的形象,“大海把身子扭來扭去/大海從來不是一個好的舞蹈家/但很愛表演”(孟浪《反世界印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以日常名義出現的解構性話語,不應僅僅看做審美趣味的轉向,它以高度凝縮的方式涵攝了現代中國進程的變化;從“大海”回到日常的海,不僅是觀照海洋的意識變化,它以反象征的方式高度象征地解散了大海所蘊含的理想、意志和向度。一種祛除了理想的日常,一種毋需意志和向度的內在建構的人生,這實則是當代中國恣肆的新意識。以深刻斷裂的方式暴露理想與日常的鴻溝,以日常名義長驅直進地推行功利理性,在短暫的20世紀80年代過后,這種意識如此頑固地盤踞下來,似乎已宣告了激進的先鋒意識的終結,標志了以意念力量推進現實的現代中國啟蒙———革命精神的中斷,標志了解除精神負載以后世俗情緒恣意狂歡的來臨。縱觀現代中國海洋意識的遷變,先鋒和日常所標示的內在向度雖有所分野,但更多時二者亦是相激相生的,先鋒理想氣質的書寫賦予海洋魅力的感召,召喚人們以進取的姿態朝向新自然,但往往疏于豐富質實的日常感覺。在日常經驗的范圍內書寫海洋,通常能帶來更多的自然細節和蕪雜的生命感受,但在現代中國先鋒意識的籠罩下,日常感覺里往往滲入了詩性理念,無視那建構性的精神感召和價值詢喚,只需一個轉身的姿態就可輕易走出現代中國的精神傳統亦是虛薄的假想,正如一首詩所說的“從此海就在我身后/不管我怎樣轉身/它總是在我的身后/嘩嘩作響”(鄒進《鐘聲》)。
二、通洋與望鄉:陸與海的糾葛
“市喧山賊破、金賤海船來”、“海人無家海里住,采珠役象為歲賦”,向海洋中討生活,或是以通海之便舶販財貨,或是耕海采漁以養生計,是傳統中國習見的生活方式。而自明清已降,泛海離鄉遙遷異域的“下南洋”等移民活動,進入現代以后規模更大,目的地不僅有南洋臺灣還有更為遙阻的美洲新大陸,于是出海下洋在晚清以后的小說中大量出現,諸如《黃金世界》《僑民淚》《豬仔還國記》等。這類小說反映了一些近海省民的新的海洋化生存心態,或是“時汽輪初通,華民皆炫于海外多寶窟……如夢得黃金世界”,或是“少有遠志,每思破浪乘風,遨游海外”,流露出面對海洋、面對莫名的海外機會浮躁、興奮而又徘徊的心態,海洋給原先靜止的人生帶來多少沉浮升降、生死悲歡的變化。在現代的出洋經歷中,還充滿了異質的西方科技文明帶來的震驚和迷惘,西洋火輪船“楫轉而為帆、帆轉而為輪,瀛海茫茫,只知咫尺”(《黑籍冤魂》)的快捷進化,太平洋上“一舟而外無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的渾茫,以及“九州腳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的時空錯置感(黃遵憲《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同時,西方文明跨洋而來造成急劇沖擊“洋布洋紗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6],在滬粵等通商口岸,“在洋行寫字樓辦事”,靠為洋人趨奉周轉“發一注洋財”的買辦職員階層興起,也傳播了挾洋自重、崇洋媚外的心態。當然,海洋勢力的侵入,資本、貨物、教會、軍火雜沓而至,易于引起近乎自發的抗拒心態,茅盾小說《春蠶》中的老通寶,看著繭廠的小輪船來滿臉恨意,“向來仇恨小輪船這類洋鬼子的東西……常常想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取了。”對于海洋陌生的疑忌與本能的利益自衛相攪纏,在文化表征上往往就表現為陸與海的對峙。
“走異鄉、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向海外尋求新知,經過西方去尋找民族自救的新路,這是現代中國青年飄洋越海的又一意愿。無論“只身東海挾風雷”(秋瑾)還是“難酬蹈海亦英雄”(),對于向外求索的現代青年,海洋是一條人生必經的茫茫志途。以大海喻新知,以航船喻進程,在歐風美雨沐刷下,在狂風急浪的淘洗中,走向新生走向未來,這一條海上的去國歸國路,曾激動多少學子,巴金激情贊美的印度洋日出,即是一代青年的情志寫照。而錢鐘書對一班庸碌學人的辛辣諷刺,也是從歸國海途開始,“紅海早過了,船在印度洋面上開駛著……但看這船上的亂糟糟,這船倚仗人的機巧,載滿人的擾攘,寄滿人的希望,熱鬧地行著”(《圍城》),碌碌世態掩過了家國情懷,匆匆一條海上歸國路擁擠著多少紛呈的世象。然而,對于海外失意的游子來說,海則是家園的阻隔,是欲歸不得的異路,甚至是葬生之所,郁達夫《沉淪》中抑郁的零余者最終走到海邊,“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他忽想跳入海里去死了。”在蹈海之前回望故鄉,“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他發出的家國呼告,刺穿了海的遙隔,成為沉痛的警聲“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大陸鄉關對于海外游子所具的磁吸力,因為重土懷鄉的頑強的鄉土精神,因為難舍神州的深沉的家國意識,而更顯強韌。這對于現代中國因為政治分裂而懸隔在臺海對岸的遷客漂人來說,更是一種撕扯心腸的長久隱痛。面對大海,他們發出鄉關何處的哀嘆,難斷天涯飄零的情思,感懷親情慰貼的桑梓故園。“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余光中《鄉愁》);“當故國的鷗啼轉悲,死去/當船首切開陌生的波峰和浪……值更水手如果是歌者/他應高唱‘春江花月夜’/使遠遠的姐妹諸邦/感覺到中國。”(痖弦《遠洋感覺》);“黃昏時,港在流著薄霧的眼淚/那幽幽的眼色,那幽幽的焦急之心/多象我那憂戚的白了期待之發的母親!”(辛郁《黃昏的港》)海洋,因其渾闊浩瀚,曾激勵人的遠志,巍巍而遠行,又因其浩渺蒼茫,倍添人的離愁,佇望鄉園憂懷家國。出走與望鄉、異域與故土、海洋與大陸,現代中國多少人躊躇徘徊、焦慮憂困于這兩種情懷的交激沖撞之間。對于幾千年以大陸文明為主體的民族,海洋意識的每一延伸,難免會從相反維度里觸發回應,這種回應往往是深層無意識的,或者思鄉、或者戀土、或者嗟零身世、或者感懷家國,由隱在的大陸情懷彌散出千百種心腸思緒,攪拌著扭結著纏繞著回旋著,構成陸與海之間無言無聲但難解難分的糾葛。
一種深厚的大陸意識,在現代中國的海洋書寫中還表露為“近海”性的特征,與歐美文學比較,現代中國的海洋文學明顯缺乏遠航、歷險、漂流、海外墾拓和孤島生活等主題,主要的小說題材為近海民眾(漁民、島民等)的生產生活,大多表現為沿海采漁、涉海近泛,或者濱海警戒、向著海外不時投以警惕注視的眼光(如《海島女民兵》)。五四作家楊振聲可視為開現代海洋小說之風氣的人,其作品《漁家》《玉君》等主要描寫濱海漁家生活,展現的海上景觀也是濱海外望之風景。解放后的一些敘事類作品如《海的女兒》《西沙兒女》《海盜》等也主要講述近海故事,鄧剛筆下的海碰子也是赤身搏海的近海捕撈者。值得注意的是張煒的海洋小說所展現的比較寬闊的維度,他的小說《黑鯊洋》《海邊的風》《古船》等表現了難以割舍的大海情結。《黑鯊洋》里的曹奔是一個充滿闖勁與大海勇敢搏斗的硬漢,《海邊的風》中老筋頭則把夢境伸向海底世界,想象“在這個粉丹丹的鮮花一樣晶瑩的世界里”,人類與大海完美融合。而最具浪漫不羈的漂泊精神的是《古船》中的隋不召,他有著鄭和式傳奇生涯,大半輩子在海上過著“獨與天地相往來的”逍遙生活。晚年回到故土,仍反復宣讀《航海針經》、念念不忘遠航的精彩,在放浪形骸的生命之中充滿自由開拓的海洋氣質。但同時張煒又通過隋不召與擱淺村口的古船的命運合一,預示陸地對海洋精神的束縛,表現海洋的絕對流動精神最終擺脫不了大地羈絆的悲劇宿命,這也是現代中國陸與海的糾葛的深刻隱喻。
三、鏡像與愿景:現代主體的自我認同與想象
在傳統中國,中土神州與茫茫四海在天地秩序中的位置是確定的,海洋被想象為環繞中土的邊緣他者,中國人習慣以中心的視點外望四海,海的蒼茫混沌、恢詭奇譎,映現了中州大地的穩定和安實。然而,現代中國的動蕩徹底顛覆了這種穩定的秩序觀,在海上激涌而來的西方強勢文明面前,傳統中國的自我認同與想象崩解了,中心與邊緣的位置發生痛苦的移換,從新的海外視點看來,中國反成了距西方主導文明遙遠的他者,身份模糊、形象尷尬甚至污穢。當留美的聞一多“鞭著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歸來時,他發現中國成了陌生者,成了噩夢,他這樣驚呼:“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發現》)。對于現代中國,在現代性的世界邏輯中,重新確立自我認同,建構新的現代主體,以此實現民族國家的更生,就成為了必然的使命。
雅克-拉康用“鏡像”理論來說明“我們在精神分析中所感覺到的標志主體身份的‘我’的形成過程”,他認為人從外界的映射物(鏡子或水面)中獲取自我鏡像,憑借這種映像,人才能確立自我形象,將自己與別人區分開來,進而實現自我認證。對于現代中國而言,海洋就是這一個外在的映射物(鏡),百年以來的中國人無疑從其中看到了某種中國的形象,從海上的舟楫縱橫、船堅炮利看到自己的固步自封、落后閉塞;從海外文明的強勢挺進、步步緊逼看到自己的積貧積弱;從萬國通航、環瀛無疆的世界海洋空間看到自己亞洲之東的地理角色,從蔚藍色生機起伏的海洋看(想象)到自己黃色文明的基因。就這樣,從海洋的鏡像中現代中國人看(或是想象)到關于文明與落后、強勢與弱勢、中心與邊緣等一系列現代性概念。
正如劉再復在1980年代所表達的“大海!我在你身上體驗到自由和偉力,體驗到豐富和淵深,也體驗到我的愚昧、貧乏和弱小”(《讀滄海》),將大海與陸地相映照,從海的鏡像中辨認自我,這是現代中國人實現自我認識的一種途徑。無論這一幅鏡像是否變形或者單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映照,現代中國由此將自我與他者區分開來,進而面向著海洋完成現代主體的建構。在海洋這一他者面前,現代中國怎樣凝聚和建構起自身的主體意識?一種比較本能的反應是,將自我與他者區隔開來,通過區分強化自我認同,以建構一種強烈的主體意識。在解放以后的一些海洋小說中,渲染著對于海洋的高度警惕和戒備的意識,如《海島女民兵》《海盜》《西沙兒女》等,海洋是敵特出沒的淵藪,是保衛和平家園的前哨,時刻警惕的沿海軍民總是英勇地挫敗威脅和破壞,保衛身后祖國大陸的安全。在這些充滿戰斗意識的敘述中,強化了陸與海之間的異在感,通過自我保衛意識的渲染,凝聚起大陸人民的共同體認同。然而,將海洋設想為異在的他者,以自我與他者的區隔來加強主體認同,這并不是主要的。
面對海洋,現代中國通過激發一種進取的姿態,向著海洋所代表的陌生的異域、興奮的未來挺近,以自我動員的方式凝聚意志、建構新的主體意識,這是一種更積極的姿態。對于現代中國人而言,當他們察覺到天下之大變的時候,幾乎就激起了重新進入世界格局,以自身介入去扭轉它的強烈愿望。從五四時期的“春潮漲了,春潮漲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郭沫若)到革命年代的“啊,大海/我真想張開雙手/縱身跳入你的波濤中”(郭小川)到1980年代的“一早我就奔向你啊,大海”(舒婷),他們以新生的姿態、飽滿的意志奔向大海,在掙脫傳統追求理想的進程中,以一種不可逆的先鋒意識實現積極的動員。于是,大海這個異在的他者,轉化成了主體的向度和目標,實現了自我與他者之間深層的互動。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封閉與主動開放地應對海洋這一他者的兩種意識,在現代中國也經常是相融互激的,如通常被視為一段自我封閉時期,但在敵我意識高漲,對海洋充滿疑忌的同時,一種現代主體的自我動員也達到高峰,整個新生的民族國家被想象成前進的航船,在偉大舵手的導引下,經歷大風大浪的考驗,排除萬難駛向未來,駛向遠方。
在對海洋的關注和凝望之中,包涵了現代中國自身的強烈意愿,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意志專注于其本身,也即專注于它所意愿的東西,這種專注乃是強力的力量運作”。正是強烈的意愿投注,使得海洋不再是蒙著迷蒙面幕的陌生他者,而成為現代中國主體意識的投射,成為一片積極的愿景。作為新世界的表征,現代中國關于海洋的理想自然包涵對于未來世界秩序的想象,梁啟超即熱情誠達地表現了中國人的新世界愿景,他的《新中國未來記》開篇描述了一個大博覽會,想象在上海舉行維新成功的祝典,列強泛海而來,“這博覽會卻不同尋常,不特陳設商務、工藝諸物品而已,乃至各種學問、宗教皆以此開聯合大會是謂大同。”這樣在屈辱的世紀初的想象遠景中,大海翻轉了方向,向中國圍攏來,它不再是障限或威脅,而成為新中國展現自己的舞臺,又發自中國向全世界播散著大同的理想。雖然歷經坎坷,但大同作為現代中國所能成就的最熱烈的想象,一直深隱在中國人意識之中。張煒在《海邊的風》里勾畫了一個夢中的海底世界,“在這個粉丹丹的鮮花一樣晶瑩的世界里,生命是最有光彩、最有力量、最受尊重的……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植物、男人與女人互相之間不可說謊、不可背棄、不可欺騙、不可侵犯。”在海洋的最深處,人與海終于實現了融合的大同,這是一幅包涵了生態、倫理和普世道義的深廣愿景。只有了解到現代中國所遭受到的來自海上的威脅、侵害和侮辱,了解到19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地位錯置和心理挫折與海洋的關系,才能夠理解中國人面對海洋展開的大同遠景所蘊含的力量,這種愿景超越了以征服易征服、以傷怨對不幸、以利益補所失的常態心理,而以寬闊的理想、平等的追求還諸大海、投諸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現代中國精神之核,它溝通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古老理想,正如痖弦的詩中所言:“值更水手如果是歌者/他應高唱‘春江花月夜’/使遠遠的姐妹諸邦/感覺到中國。”(《遠洋感覺》),這是中國“在場”的大海,是中國精神浸潤的大海,不是異己和物理性的海,而是充溢著審美性和道義性的海。
作者:彭松單位:南通大學復旦大學
- 上一篇:古代文學作品的體驗式教課研討范文
- 下一篇:英語教課中中國文化的研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