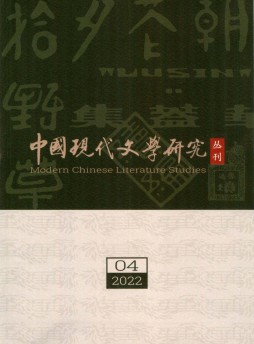現代文學和文論的啟蒙特質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現代文學和文論的啟蒙特質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啟蒙運動最為主要的任務就是反對宗教神權,以理性的原則重新樹立起作為主體的“人”的生存自信。而這一理念在中國20世紀得到了延展和發揮,文學啟蒙和審美救世的原則貫穿于“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新啟蒙的歷時脈絡中。文學和文論的超越性價值得以彰顯。
關鍵詞:
文學;啟蒙;魯迅;傷痕文學;主體性
啟蒙運動作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現象,不僅推動了知識和學術的發展,更是和政治革命、主體解放等密切聯系在一起,成為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啟蒙”一詞的本源含義來自從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內涵,英語詞匯為“Enlightenment”,意為使之呈現“光明”的含義。后來引申為通過科學、文化等知識促使人民獲得真理與智慧,并且確證自身存在的過程。啟蒙最先的合法性來自柏拉圖的“洞喻”理論。在長長的洞穴中有一批罪人被綁縛在洞中,他們必須面壁坐在洞內,不能扭頭看洞口。而在罪人和洞口之間有一條橫向的矮墻,矮墻后面有很多火把能夠照亮整個洞穴。為了戲弄這些罪人,人們就在矮墻上唱歌跳舞,但與此同時罪人是不能回頭觀看的。罪人只能看到墻壁上演員的“影子”。
這些影子在罪人們看來也許就是“真實”。要真正能夠把握住主體,還必須通過自己的力量對世界進行認知。這一理論在黑暗的中世紀被湮沒,宗教神學成為統治人們思想的最高工具和“邏各斯中心主義”,而到了17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通過文學藝術上的改良以及恢復希臘感性的認知模式,思想家們紛紛尋求能夠重新使主體獲得完滿生存的方式,啟蒙運動就伴隨著文藝復興的腳步姍姍到來。可以說,自17世紀到19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經歷了將近三個世紀之久。啟蒙運動最為主要的任務就是反對宗教神權,以理性的原則重新樹立起作為主體的“人”的生存自信。所以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就肯定了理性的力量。不僅是自然科學領域,在政治和思想領域也紛紛出現了學術大師,他們突出了三權分立、民主自由、法律憲政、天賦人權等等。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伏爾泰的《哲學通信》等等,都樹立起了以人為本的政治體系理念。由此同時,康德、盧梭、狄德羅等理論家也紛紛通過美學、哲學、文學等不同領域確立各自學科的合法性地位。正是在啟蒙的語境中,西方全面展開了現代化和現代性的進程,所以啟蒙思想也基本上可以視為“現代性”的話語內涵。由于西方現代性浪潮深刻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與經濟態勢,所以“啟蒙”就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與含義。而中國近代以來的啟蒙焦慮同樣來自于西方或者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思潮,并且先后經歷了兩次較大的啟蒙浪潮。
一、“五四”時期的啟蒙浪潮
在20世紀早期,中國處在經濟社會的嚴重憂患之中,政治格局的動蕩、經濟社會的落后以及文化和民眾的愚昧等等,都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深刻的“焦慮感”,尤其是經歷過西方文化熏陶的諸如王國維、朱光潛、宗白華、魯迅等人,他們立足于文化啟蒙的視角,賦予了文學和美學的啟蒙價值。正如西方社會是以理性對抗神性,最終取得主體性話語權的確立。而中國的文化啟蒙則是通過感性的張揚和審美的彌補,試圖對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所以文學和審美就構成了重要維度。而此時也出現了眾多的文學家和理論家,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審美獨立性價值,試圖從政治的窠臼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也將視角集中在人的生存、人的反思和人在社會制度的壓抑場景之中。表現在文學中則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加強;表現在文論和美學中則是對西方“人學”理論的譯介和重視。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壇的“斗士”,從文學到文論都體現了其強烈的審美“介入性”和“反思性”價值。他的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諸如閏土、祥林嫂、阿Q等,體現了主體在生存中的無奈和面向生活的妥協,此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視角也完成了“封建人”向“現代人”的轉換。而雜文則更加凸顯了強烈的情感指向和對市政的反思,《記念劉和珍君》《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等都是直接針砭時弊,給人以震驚的效果。不僅表現在文學領域,在文學理論和美學領域,魯迅表現出了更加強烈的啟蒙意識。一直以來,魯迅對西方注入尼采、叔本華、克爾凱郭爾的存在主義思想都體會頗深,他接受了西方理論界對個體存在的重視,并且將“悲劇”的力量轉化成為積極進取的時代啟蒙精神。在《摩羅詩力說》等文論著述中首先肯定了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和文藝的啟蒙功能,僅能認為摩羅詩人正是試圖揭示真理的歷程。在魯迅看來,文學首先要集中于表現個體的反思能力,進而實現對社會的介入和對整個民族精神的體察。不僅是現實層面的審美啟蒙,還有超越性和人性論的啟蒙文學觀。西方學者卡西爾曾經論述:“啟蒙運動最強有力的精神力量不在于它摒棄信仰,而在于它宣告的新信仰形式,在于它包含的新宗教形式。”[1]
所以啟蒙不僅僅在于現實領域,更是內蘊于文學和藝術的神性與超越性之中。中國現代以“京派”為代表的學者就試圖建構一個與世隔絕的“精神烏托邦”,在“神話小廟”中重新找到失落已久的人文信仰。朱光潛和梁宗岱就是明顯的代表。朱光潛在建國前的美學研究中一直強調“審美即直覺”“審美即距離”,在吸收尼采、克羅齊的理論資源之后希望建構文學和審美的獨立場域。這種文學不關涉政治,也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社會,而是首先使主體的精神得到升華、信仰得以完滿。此種論調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審美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也可以算是獨特的嘗試,而且在審美自律論和審美現代性的進程中做出了自身獨特的貢獻。而京派的著名學者梁宗岱則更加凸顯了象征主義詩學的神秘性和獨特性。在他看來,文藝就如同“神性”的信仰產物,是具有使人靈魂凈化的魅力。所謂純詩,主要指涉的是破除了一切外來干擾和影響,只是通過文學自身的象征系統、隱喻系統以及審美系統完成的自我滿足的文本。
“純詩”放逐了現實社會的宏大政治、激進革命論的呼吁以及介入現實的努力,而是放在了微觀個體的人生超越和美的吟詠之上。“快樂的境界”和“不朽的宇宙”成為其主要的價值指向。與此同時,還有一種積極的政治審美啟蒙論,主要是以“左聯”等為代表的作為革命斗爭的美學。比如蔣光慈在《無產階級革命和文化》中就直接指出,共產主義者雖然也有自己的花前月下的小資情調,但是依然要被統攝納入宏大的革命事業之中。文學和藝術僅僅是革命的“工具”與“螺絲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世界概括了文藝的創作原則,正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號召中國的文藝家要深入到廣闊的生活場景之中,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生活中找到創作的靈感。由此,文學和美學就成為了政治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此種文藝理論在當代備受質疑,但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卻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正是通過審美對整體社會的精神改造,廣大民眾在革命的激情中獲得了一次生命的洗禮,從而以積極進取的精神面對社會。這也可以視為啟蒙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1980年代的新啟蒙
進入1980年代以來,面對政治領域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政策,在文學和美學領域同樣進入了一個高潮期。面對“”極左的政治思潮,文學家和美學家紛紛從審美的視角試圖彌合分裂的人性,完成自上而下的啟蒙任務。而啟蒙的核心則是重新恢復“人”的感性力量和道德水準,重新解決人的精神生存問題。一方面,知識分子以“焦慮”的情結試圖以人道主義和人性論話語介入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廣大民眾也掀起了熱愛美和學習美學的浪潮。比如傷痕文學就將視角集中在對“”的反思之上。而這種反思又不是僅僅停留在控訴的層面,是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探究時代給主體留下的精神創傷,并且進一步復活“五四”以來的個體解放精神傳統。巴金、冰心、蕭乾等作家在其散文和雜文創作中就表現了強烈的審美反思特質。巴金在《隨想錄》中就表達了強烈的啟蒙意識和反思意識。
巴金創作《隨想錄》的動力和意志非常明顯,正是反思“”的非人歷史和人間浩劫,通過對個人的痛苦反思和覺醒,試圖以文學的形式喚醒民眾,彰顯民主和自由的信仰理念。與此同時,巴金也秉承了傳統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以一種“自上而下”的反思姿態將“五四”精神進行銜接,倡導新文化運行精神的回歸。與此同時,不僅是在文學領域,尤其是在思想領域出現了更為強烈美學啟蒙浪潮。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論哲學正是將馬克思主義和康德哲學進行嫁接的結果。在李澤厚看來,主體性的實踐活動分為幾個不同的層面,分別是集體主體性和個體主體性;還有社會物質實踐和精神實踐等幾個層次,若干層次之間構成了相互遞進的關系。
由此,李澤厚通過扎實的哲學理論建構和對主體性實踐能力的發揮,在馬克思主義范圍內確證了主體的能動性功能,這也就肯定了康德哲學的合理性價值。從“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啟蒙到1980年代的文學美學的人性論啟蒙,其內涵都是審美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二元對抗關系。文學家和知識分子試圖通過啟蒙來恢復人性并實現人生超越,由此也彰顯出了一條清晰的文學和理論脈絡。
作者:張璇 單位:南陽醫學高等專科學校
- 上一篇:班組安全文化建設方法思考范文
- 下一篇:現代漢語與現代文學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