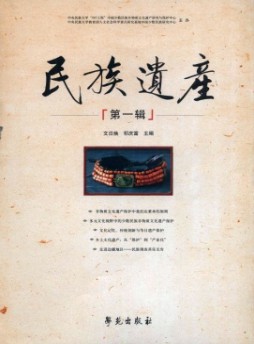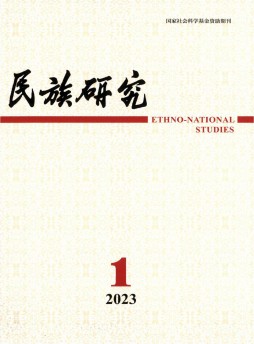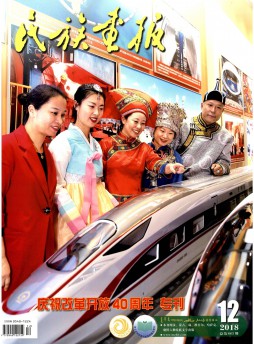民族歌劇與戲劇的關聯性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歌劇與戲劇的關聯性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韓瑞芳單位:山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目前,很多高校都把民族民間音樂、民歌、戲曲音樂等學科定為必修科目。學生們在課堂上能夠系統的對各地民族特色的相關器樂、歌曲、戲曲等作品進行深入學習,作為聲樂專業學生而言,很好的學習這些課程將對自己把握不同風格作品提供具體的依據和參考。近來,有很多專家學者對戲曲唱法做相關研究,有的還把戲曲唱法借鑒到高校聲樂教學的課堂上來。但實際上,在聲樂學習中,尤其是在民族歌劇的演唱上,了解戲曲并不只是在發聲法上有聯系那么簡單。
一、在民族歌劇的創作上,很多以戲曲為創作元素
中國歌劇的發展,始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人此時對歌劇這種新體裁展開初步探索,在形式上,很多都是對傳統戲曲形式進行改造而來,也有的是根據話劇,或者根據民間曲調直接填詞而來。代表作品閻述詩的《高山流水》,該作品為民族樂器伴奏的舞臺歌劇,呈現出春秋時代的音樂盛況。此外,還有《夢里桃花》、《瘋人淚》、《孤島鐘聲》、《憶江邊》等也都閻述詩所創作的歌劇作品。只是,在后來,這些歌劇沒有大規模流傳,以至于現在很少有人聽過這些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張曙曾以昆曲曲調創作的小型歌劇作品《王昭君》成為中國歌劇發展過程中較成功的探索和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歌劇進一步發展,涌現了許多優秀的歌劇,影響至今,如繼承戲曲傳統的代表性劇目《小二黑結婚》、《紅霞》、《紅珊瑚》、《竇娥冤》等,其中以《小二黑結婚》與《竇娥冤》影響甚廣。
1.以戲曲為創作元素的民族歌劇,在曲調上有著非常明顯的戲曲特征。我國地大物博,不同區域,因風土人情的差異,在音樂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的風格。戲曲作為一種民間藝術,恰恰像民歌一樣,與流行地的語言以及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我們國家的戲曲以省、地區為界,風格迥異,盡管某部分作品有著同樣的題材,在曲調上卻因所在地區的語言差異而各不相同。作曲家在創作歌劇作品時,會根據選用題材故事所在的地區來借鑒當地的戲曲元素。如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與山陜地區的眉戶劇曲調極其相似,《劉胡蘭》與山西晉劇曲調有相似之處。《小二黑結婚》則與評劇、晉劇曲調相似。如果演員在唱以上幾部作品時,對相關作品的戲曲種類曲調不是很了解的話,將會影響演員準確刻畫人物形象,因此,作曲家在創作時,安排每一個字與旋律的結合時都是有特定的目的,如歌劇《紅珊瑚》中的《海風陣陣愁煞人》,其中第一句,“海風陣陣愁煞人哪”中“哪”字的拖腔就具有強烈的戲曲行腔特點,在演唱這一句時,能不能把當中的倚音、波音等裝飾音唱好也是決定演員能不能準確表達作曲家創作本意的關鍵。但是,單憑譜面上的裝飾音記號是無法真正再現出濃郁的地方曲調特色的,據此,我們一定要對全國各戲種多接觸多了解,只有具備了多種戲曲曲調的資源,在演唱時,才能游刃有余的把相關戲種的相關風格與歌劇準確對位,從而讓演員把相關的民族特色準確無誤的融入到歌劇的演唱當中去。
2.在曲體上借鑒戲曲創作元素歌劇《江姐》中,《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貢獻》當中的“粉碎你舊世界,奴役的鎖鏈,為后代換來那幸福的明天”,在創作上吸取了戲劇中獨有的“緊拉慢唱”,“緊拉慢唱”指的是演員慢速的唱,伴奏同時很快的進行。這種表現手法一般用來形容事情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但是過程卻又很漫長。作曲家在在劇中人物趕路時常運用此創作手法來設計唱腔,表示行路緊急的同時又表示路途漫漫,跋山涉水。在《江姐》當中,此處運用緊拉慢唱,也是為了表示,革命事業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此過程也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表現出演員不畏艱難險阻,堅信勝利早晚會實現和與敵人斗爭到底的決心。也有一些后期創作的民族歌曲當中運用戲曲的一板一眼,如《江河水》中有一句“這山在水在偏你不在”就是一字一拍,起到一個強調作用,在戲曲中這也常見的一種表現手法。雖然《江河水》不屬于民族歌劇范疇,但是在歌曲的體裁與演唱上,與詠嘆調具有相同的特征。
二、民族歌劇的肢體表演與戲曲表演
中肢體語言的相似性我國歌劇的發展與戲曲的緊密聯系除了聲腔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以外,在肢體語言上也有相似之處。肢體語言具體來講又可分為手、眼、身、法、步,在戲曲中,人們把這五種技藝稱作五法。“手”,指的是手上的動作,即“手勢”,“眼”指的是眼睛的各種神態,“身”指的是身段工架,“步”指各種形式的臺步。“法”則指前面所說的幾種表演技術的綜合規程和法則。解放前后,涌現了不少以革命為題材的歌劇,如《白毛女》、《黨的女兒》、《洪湖赤衛隊》等。在這些劇目中的人物刻畫上,性格可謂鮮明,我們從人物的表情,眼神,舉止上基本就可辨別正反面人物,這也與戲曲有著很大的聯系。因為在戲曲表演中,表情要遠比生活中的表情夸張,在花臉行當中演員借助臉譜來標榜人物性格的特征,演員隨著打擊樂器一亮相,臺下的觀眾基本上就能夠判斷人物的個性特征。當時,電影界也頗受戲曲刻畫人物形象的肢體語言的影響,解放后的老電影,如《閃閃的紅星》,《風云兒女》等,劇中演員在眼神上的表現很夸張。在歌劇當中,革命烈士劉胡蘭,玉梅,江姐等角色的表現,與戲曲當中的武旦的肢體語言動作有著極大相似性。如,女演員手臂肘關節微微撐起,顯得英勇無畏,在戲曲中,這樣的動作是武旦站立的基本姿勢。雖說現在歌劇發展,有很多新的劇目產生,但是,在刻畫以上劇目中的人物形象時,演員必須從這些細節上來準確刻畫人物的時代性特征。如歌劇《白毛女》中,喜兒起初用的蘭花指,表現一個少女天真爛漫的形象,而后,喜兒躲入深山后,肢體語言與起初產生很大對比,多用握拳等手勢,表現了天真的喜兒被地主欺壓后的滿腹仇恨。作為聲樂演員或學習者,了解和借鑒戲曲肢體語言表現手段,并將其適當的與我們所學專業相結合,將從很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
三、民族歌劇的咬字上與戲曲行腔發聲咬字的聯系
歌劇不同于藝術歌曲,歌劇片段充滿戲劇性沖突,旋律節奏對比較大,演員在演唱歌劇曲目時,在發聲咬字上更要注意語氣的多變,以便更加夸張的表現人物內心沖突,在不同情緒下,有時候咬字要重咬,有時候要輕咬,有時候要含著唱,有時得噴著唱,吐著唱。如歌劇《白毛女》中,《恨是高山仇是海》片段,歌唱家對劇中詞與旋律,一字一句認真推敲,把很多戲曲中的特有板式用的淋漓盡致。在咬字上,演員要重視字頭字腹與字尾,有時候強調字頭,有時候在字腹上停留,有時候在字尾上突出。如歌劇《黨的女兒》中的《萬里春色滿家園》片段第一句,“我走,我走,不猶豫不悲嘆”中,“走”字在拖腔時,在字腹部分加力往出推,在“不猶豫”和“不悲嘆”中的“不”字上強調字頭,方顯走的堅定。當代歌唱家劉斌在成名前期曾是京劇演員,在他后來的歌唱生涯中,我們不難從歌曲咬字當中感受到京劇當中演員依字型腔的特點。所以,這一點也告訴我們歌唱演員要成功表達人物情緒,可多借鑒戲曲當中的咬字吐字方法,對其加以提純運用,以便更生動的表現人物心理。
我國戲曲發展融匯了中華的歷史文化,戲曲作為一種載體,融進了各地語言腔調。反之,我們又可以從語言腔調的區別上研究人們在地域間的交流障礙與痕跡。我國的民族歌劇扎根于中華民族這塊沃土,離不開民族藝術形式的滋潤與灌溉。而我們要不斷讓民族歌劇發展壯大,就要多對戲曲,民歌,說唱等形式的民間藝術進行挖掘,從而推動我們民族歌劇的不斷進步與成熟。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