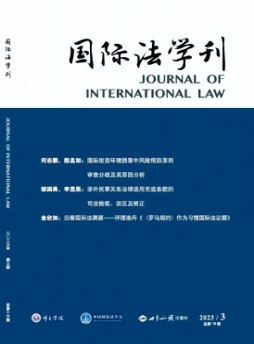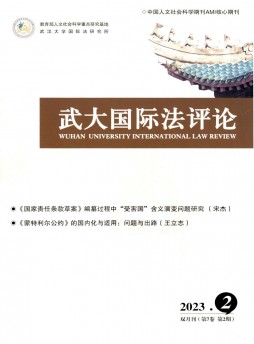國際法上獨立宣告的合法性要件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國際法上獨立宣告的合法性要件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獨立宣告是一種突破主權隸屬關系并宣布主權創立的單方行為。一份獨立宣告欲實現前述目標,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須滿足相應的合法性要求。具體而言,即應保證國際法對該獨立宣告秉持“支持”或“中立”的態度。獨立宣告挑戰既存主權秩序,國際法對相關實踐的態度可分為三種:“支持”、“中立”和“禁止”。前兩種情況都不違反國際法的規定———國際法積極倡導,或尚無明確的禁止性條款予以限制。第三種情況則會導致相關獨立宣告當然無效。對于合法性要件的具體內容,可以從正、反兩個角度進行論證:從正面角度來看,國際法支持的獨立宣告是依據傳統的自決原則提出的;國際法保持“中立”的獨立宣告包括“科索沃獨立案件”和“國內法允許之獨立訴求”兩種情況。從反面角度來看,一旦國內法授權下的獨立宣告違反了國際法禁止性規定,如非法使用武力或種族壓迫與歧視,將被視為不具有法律效力。為此,國際法設置了“不予承認”的國際義務以阻止和懲戒相關實踐。
[關鍵詞]國際法;獨立宣告;自決原則;科索沃案
一、關于獨立宣告之國際法合法性要件的分析
所謂“獨立”即主權上脫離隸屬、新設主權之狀態。獨立主權實體有權平等與他國交往,獨立承擔國際法義務,行使主權性權利。“獨立宣告”即是宣布其主體取得主權獨立地位的政治和法律文書,以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為典型代表。獨立宣告的性質體現于三個方面。首先,獨立宣告是欲割裂原始主權、創設嶄新主權的政治和法律訴求。這使其區別于普通的政治叛變。在辛亥革命時期,我國多省份曾電告“獨立”。但結合其電文措辭和之后的實踐,可知此類“獨立”意在叛變于清政府之中央政權,而非希望永久脫離中華、創設新的主權國家。是故,此類電文自然不能被視作國際法意義上的獨立宣告。其次,獨立宣告蘊含摒棄母國政府統治、渴求國際承認的意思表達。一個實體通過“宣告獨立”可以達成兩層目的:一方面向國際社會表明其母國政府的政治權力將在“獨立”領域內失效;另一方面也迫使國際社會和母國對尋求該實體的“身份”進行重新定位和確認。最后,獨立宣告具有一定的政治效力。宣告獨立的實體通常可以使其國際交往能力得以大大加強。獨立訴求的提出有助其主體取得“民族解放組織”或“交戰團體”的國際法身份,以增加其參加國際組織、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同時,“獨立宣告”的發表共同向外國干涉勢力發出了“邀請函”,一旦否定了其獨立訴求的“內政”性質,自然便于尋求“獨立”的實體尋求國際援助,置母國政府于不利。
作為一種突破主權隸屬關系、宣布主權創立的單方行為,對相關合法性要件的滿足自然是獨立宣告產生效力的根本前提。關于“合法性要件”的概念范疇,可概括為“排除為國際法所禁止的獨立訴求或實踐”。具體包括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國際法支持的獨立宣告,即那些獲得國際法明確授權、依據自決原則提出的獨立訴求。此類實踐主要集中于“去殖民化”領域。第二種情形是國際法保持中立的獨立宣告。由于并未受到國際法的禁止,依據“法無禁止即可為”的邏輯,此類獨立宣告也是滿足合法性要求的。實際上,該分類的存在是基于國際實踐中的特殊情況:國際法或是出于不便反對的曖昧立場,或是由于不言而喻地理由,而對于一些獨立宣告保持了“中立”態度。與第一種情形相比,此類實踐例子較少,主要包括作為特例存在的“科索沃獨立事件”以及經國內法許可的獨立訴求。前者之所以有必要特別討論,只因國際法院在“科索沃案”的咨詢意見中的表態。該意見認定科索沃宣告獨立的行為“不違反現行國際法規范”,從而為獨立宣告突破自決原則的傳統適用范圍埋下了禍根。后者因為有國內法基礎,經過了母國政府的認可,除非因違反國際強行法規范而被禁止,否則國際社會沒有理由對此類獨立訴求橫加阻攔。與上述情形相對,違背合法性要件的獨立宣告是因為其相關行為或主張違背了國際法的禁止性規定。在實踐中,主要包括借由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方式推行的“獨立訴求”和為了執行種族壓迫與歧視的制度而操辦的“獨立事業”。國際法將上述兩種獨立宣告視為當然無效,并對其他既存國家施以“不予承認”之國際法義務。
二、作為獨立宣告之國際法基礎的自決原則
幾乎每一份獨立宣告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引用“自決原則”來證明其“合法性”,這便造成對該原則的曲解和濫用層出不窮。自決原則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不僅是因為其所代表的國際法之人權精神與民主道義,更重要的是該原則可被視為衡量一個獨立訴求是否有資格獲得國際法支援的標準———這種“支援”以一定的國際法義務予以體現:任何國家或組織不能為自決權的正當行使設置障礙。因此,對于自決原則概念的準確把握是討論獨立宣告合法性要件的先決性問題。自決原則概念的界定歷來爭議頗多。最初,自決原則是與“民族”概念相伴隨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被國際社會所接受。(P.201)之后的發展使得該概念的性質和適用范圍都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自決原則經歷了“由哲學概念走向政治概念,并終于成長為法律原則”的蛻變;另一方面,自決原則的適用范圍由最初僅限于歐洲地區,逐步發展為世界范圍的共識。自決權的概念大致可追溯至15世紀的民族主義思想源頭。但直到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后,人們才正式樹立起對這一理念的信仰。其中,美國獨立戰爭中發表的《獨立宣言》被視為對該原則的最初實踐。雖然在內涵上包含了“民族”和“民主”的元素,但當時的自決原則仍未跳出地域偏見的思想枷鎖。19世紀時,歐洲列強一方面承認巴爾干地區人民的“民族獨立”權利,另一方面卻為“如何征服和瓜分非洲”而爭論不休。這表明當時的“自決權”遠非為世界人民所普遍享有,而僅被視為歐洲民族的一項地區性“特權”。在凡爾賽體系中,“自決原則”變成了當時國際社會的熱點話題之一。那個時期的“自決”實踐可被分為兩種:其一是真正意義上的“自決”,即由居民以投票方式決定其所生活之土地的主權歸屬狀態。其二是通過大國(主要是當時的協約國)同多民族國家簽署《少數民族條約》的方式,將“對一國內的少數族裔進行保護”轉化為一項積極的國際法義務。(P.182-183)可惜的是,當時的“自決原則”仍然未能上升到“獲得普遍承認”的高度。盡管美國威爾遜總統作了不懈努力,國際聯盟仍拒絕將其接受為正式的國際法原則。直到《聯合國憲章》的頒行,自決原則才真正完成了這一飛躍。對“自決原則”的全面把握首先要從國際法律文本入手。《聯合國憲章》雖然在開篇第一條中就明確將“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列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但這種表述過于寬泛,其作用也僅是確認“自決原則”在國際法中的存在。
至于該原則的具體內容和實現方式,則要通過后期的國際實踐來認定。在聯合國主持下,先后產生了一大批關于“自決原則”的國際條約。其中主要包括《關于民族與國族的自決權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和《聯合國土著民族權利宣言》。這些國際法文件中關于“自決原則”內容的闡述多有重合,基本上可以概括出如下共識:自決原則具有對外和對內的雙重性質。首先,自決原則是一項有效的國際法規則,也是保障基本人權的條件之一。其次,自決權的主體雖然被表述為“所有人”(AllPeople),但自決原則所針對的主要是非自治領土和托管領土的情況,尤其旨在徹底結束殖民統治。最后,自決原則也被視為一國內少數人團體避免遭受歧視和不公待遇的國際法保障。依據目前學界的通說,真正確立“自決原則”的實踐領域僅包括以下三個:反對殖民統治、反抗外國軍事占領和反對國內種族壓迫與歧視政策[4]。相應地,也只有在上述三個領域中發表的獨立宣告,才能被視為是對自決原則的真正實踐。其中,尤以去殖民化的例子最為典型和常見。因此,我們可以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后簡稱《宣言》)這一法律文件,來分析國際法對此類獨立宣告的態度。《宣言》于1960年由第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以決議的形式予以通過,其目的在于“無條件結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同時,《宣言》也強調“自決原則”的適用應限定于“非殖民化”的領域,而不能被用來損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非殖民化過程的基礎”,《宣言》的內容可見于幾乎所有關于自決問題的聯合國決議之中。為盡快瓦解殖民體系,支援反抗殖民統治而提出的獨立訴求,《宣言》提出了諸多具體措施,并要求一切國家予以遵守:如“在托管地、非自治領土等一切未獨立之領地內將權力無條件移交其人民”、“不得以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準備不足為借口拖延獨立”以及“務必制止武裝鎮壓、保證和平自由實現獨立”。這些要求被轉化為切實的國際法義務加以貫徹,也為真正踐行自決原則的獨立宣告在之后獲得國際承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許多以“自決”之名喚起的“獨立”訴求,實際上是一種“分離”訴求。既然自決原則被規定為“不得用于侵犯主權完整”,則將“自決權”與“分離權”的混淆便是對“自決原則”本質上的扭曲。為明確“自決原則”的概念和適用,我們有必要辨析“自決權”與“分離權”的概念。“分離權”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至今沒有得到任何國際法律文件的認可。(P.181-182)正如國際聯盟的專家委員會在“奧蘭群島案”的意見中所言:承認一國內少數人享有“分離”的權利,必然會導致國際秩序的混亂。而保護主權完整、維護國際安全和穩定一直是國際法的根本宗旨。之所以會產生“自決權等于分離權”的誤解,部分源于國際法律文件中有關“保護性條款”(SafeguardClause)的規定。該項規定首現于1970年《國際法原則宣言》中,之后被1993年《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所繼承并予以修訂。其內容可大致表述為:自決原則不能被援引用于損害那些遵守國際法、維護人民平等和自決權利之國家的主權完整。如果我們從反面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它似乎存在如下暗示:那些在有違國際法或侵犯人權的國家內部掙扎的人們,有權訴諸自決原則予以獨立。從這個邏輯出發,有學者引申發展出了“救濟性分離”的概念。其代表人物為詹姆斯•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他認為“分離權”是一種救濟性權利,當一國政府大規模壓迫和侵犯人權時,受害的人民即可享有此權利作為救濟。需要說明的是:首先,“救濟性分離權”在性質上并非原生性權利,而是一種次生性的補救方式,其行使需要滿足特定而苛刻的前提條件。一方面,應當有足夠證據證明人民權利確實受到普遍、且程度足夠嚴重的侵害;另一方面,受害群體應在內部協商、區域干涉和國際救濟均告失敗的情況下,才能夠援引“分離權”作為一種“最后的救濟手段”。其次,“救濟性分離權”作為一種理論上的道德性權利,尚不存在相關法律制度的保障。對該權利概念的引用完全是基于政治性、觀念性的評判。這使得該概念難逃大國話語權的濫用和政治博弈的歪曲。最后,“救濟性分離權”在學理上仍然存在諸多漏洞。譬如作為該權利行使的前提,關于“一國政府是否存在大規模、嚴重破壞人權之行為”,學者們無法提出客觀且獲得普遍接受的評判標準。因此,不僅國際法遲遲不愿接納“救濟性分離”的概念,相關國際實踐在承認或踐行“救濟性分離權”時也都秉著最為謹慎的態度。
三、獨立宣告合法性的底限———國際法的中立態度
(一)科索沃獨立宣告———滿足合法性要件的特例
2008年,在科索沃總理宣讀《科索沃獨立宣言》之后,國際法院在聯合國大會的請求下對“科索沃案”提供了咨詢意見。在論述了自身裁量權的正當性與案件事實之后,國際法院的最終結論主要有四個層面:其一,國際法并不禁止單方面宣告獨立的行為;其二,關于科索沃的獨立宣告是否可以被視為踐行自決權的實踐,國際法院避免作出認定;其三,國際法院認定由聯合國科索沃特派團通過的《憲法框架》具有國際法效力;其四,科索沃獨立并不構成對先前安理會通過的1244(1999)號決議的違反。該決議作為一種臨時性安排,也不禁止科索沃進行獨立宣告。其中第二項關于科索沃獨立是否基于自決原則的回避態度,成為該意見書最受爭議的一點。國際法院首先肯定了自決原則從20世紀以來經歷了重大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否導致自決原則可以超出其傳統適用范圍(殖民或遭受外國統治剝削等非自治領土)而被引用?科索沃是否可以通過援引“救濟性分離權”而獲得獨立資格?國際法院認為這些問題尚無定論,也沒有必要在此作出解答。至于其對于“科索沃獨立未違反任何國際法規則”的結論,更有利用邏輯游戲避重就輕之嫌:“沒有違反”并不等于“完全符合”,其背后的含義是既未明確肯定這種行為符合國際法,也不認為該行為應該遭到禁止。同時,“不違反現存國際法”的表述也意味著相關規則或許尚處在形成過程之中。事實上,這種婉轉的表述也暗含著國際法態度的差異:“符合國際法”意味著擁有國際法的授權和鼓勵,而“不違反國際法”則表明國際法對此情勢保持中間立場。科索沃案是一個危險的先例。不僅僅因為它是大國政治操縱的產物,更因為科索沃的獨立訴求既違反其國內法規定,又缺乏國際法基礎。國際法院在對該案的咨詢意見中未能秉持一貫立場,而是采用了不甚明確的曖昧態度———這種放任被證明貽害無窮。一方面,科索沃獨立無論在國內法還是國際法層面都缺乏客觀法律依據。科索沃的獨立宣告顯然為其國內法所禁止。此外,科索沃的獨立也很難說是對自決原則的實踐,因為當時科索沃的狀態既非殖民地,也未遭受外族軍事占領,而是依安理會1244號決議所建立的聯合國托管地。另一方面,國際法院不斷強調科索沃案“不可被重復”的特例性質,但這并不能阻止大國干涉他國內政、策動獨立勢力的嘗試。在2008年的南奧塞梯沖突中,俄羅斯借口該地區的“種族屠殺”需要其進行“人道主義干涉”而發兵。其說辭自然是想套用科索沃案情中的特定用語,來為自己的單方面軍事行動進行辯護。在2014年爆發的“克里米亞事件”中,俄羅斯也頻頻援引科索沃案的“先例”。然而,俄羅斯的自我辯解并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接受,其所得到的回應是西方國家的政治孤立和強烈的經濟制裁。由此看來,國際社會對于效仿科索沃案的做法并不認可。所幸俄羅斯的行為和辯解都未能突破科索沃案作為“特例”的性質,但難說國際上的類似行為不會再次出現。而這一切都可歸咎于當初國際法院在科索沃問題上留下的“法律空子”。
(二)國內法許可的獨立訴求當一份獨立宣告
基于其母國國內法而提出,即便超越自決原則的傳統范圍,只要未侵犯國際法的底線,便仍然應當被包容和接納。此類獨立宣告因為獲得母國政府的承認,故而面對的國際爭議最小。大部分國家的國內法都對“單方面獨立”和“分離”訴求予以禁止。盡管極少部分國家的法律為“獨立”訴求留下了宣泄口,但多加以極其苛刻的限定條件,以將“合法獨立或分離”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如美國最高法院在“Texasv.White”案的判決中否定了州政府有“單方面脫離聯邦”的權利,認定一個獨立訴求只有經過所有其他州政府的同意,才能被視為合法。此限定條件在實踐中幾乎不可能實現。在1995年魁北克獨立公投失敗之后,加拿大聯邦政府積極在法律和政策上堵死“分離主義”的出路。同美國一樣,加拿大最高法院判決認定魁北克的獨立不僅需要獲得省內絕大多數公民支持,還需通過憲法修正案被聯邦所有成員接受。目前只有個別國家對國內的“獨立”訴求秉持較為開放的態度。2011年2月16日宣布成立的南蘇丹共和國便是經其母國(蘇丹共和國)國內法允許而獲得獨立地位的。國際社會對這個新國家展開懷抱,聯合國于當年7月即接納其成為最新成員國。2014年的蘇格蘭公投也有著堅實的英國國內法基礎。基于特殊的歷史事實,英國政府并未像美、加一樣對蘇格蘭的獨立公投進行法律和政治上的圍追堵截,而是確確實實地忍受了一場有驚無險的政治賭博。各種證據都顯示:倘若蘇格蘭公投獨立成功,英國國會大概也只有吞下苦果。由于不存在任何可以將蘇格蘭公投歸于“違反國際法”的事由,如果英國政府決定認可蘇格蘭的獨立事實,國際社會的承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原因在于,對于那些符合國內法規定,獲得母國承認或默認,又未違反國際法規則的獨立宣告,國際法沒有任何理由橫加干涉和反對。
四、違背合法性要件的獨立宣告
所謂違背合法性要件,即是遭到了國際法的明令禁止。此類實踐主要包括兩種情況:“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脅”和“施行種族壓迫和歧視制度”。國際法對這兩種獨立宣告采取“零容忍”的態度,主要是因為它們違反了國際法中的強行法規范,逾越了法律和道義的“紅線”。為確保這兩種獨立宣告維持“無效”的狀態,國際法設置了相應的“保險措施”———要求國際社會對于此類獨立宣告承擔“不予承認”的義務,以阻止相關實體在事實上融入國際體系和秩序。
(一)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下的獨立宣告
國際法不承認任何通過非法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而導致的情勢或狀態。這主要緣于以下兩個原因:第一,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脅構成對國際法宗旨的根本性違背。正如國內的刑法并不能杜絕犯罪,國際法也無法完全保證弱國免受強國欺凌。對于一國妄圖通過武力侵略實現吞并或分裂別國主權和領土的行為,國際法設立了“不承認原則”作為事后性保障措施,以阻止相關違法情勢因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而成為法律事實。這一原則可追溯至1932年美國政府所奉行的“史汀生主義”政策,即拒絕承認日本武力侵華所造成的一切情勢。該原則最初被《國際聯盟盟約》吸收,之后由《聯合國憲章》所繼承,最終使發展成為一項強制性的國際法義務。第二,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脅排斥了人民意志的自由行使,有悖于自決原則。自決原則作為獨立宣告的國際法基礎,強調獨立訴求應當是人民自由意志的反映。人民有權獨立、自由地決定其經濟、政治事務,這在根本上也是與民主和尊重人權的國際法精神相契合。在異族侵略或者外國武力干涉扶植下的獨立宣告,基本上都會試圖偽造出“獨立”乃是遵從當地人民意愿的假象。然而在武力攻擊或脅迫之下,不可能存有自由意志的空間。1932年2月,在扶植“偽滿洲國”獨立前夕,日本關東軍曾召集諸多親日軍閥和政客出席了所謂的“東北政務會議”,由該會議決議發表一份滿蒙地區脫離中國政府的“獨立宣言”,并厚顏無恥地聲稱之為順應滿蒙人民的呼吁和意志。這種拙劣伎倆顯然未能欺過國際友邦的明鑒。雖然當時松散而混亂的國際社會未能組織有效力量對此行為予以制裁,但這種無奈情形主要是受限于特殊的歷史條件,而非代表國際法的容忍和默許。事實上,即便沒有國際法權威的號召,國際社會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導演的鬧劇也反應寥寥。這使得“偽滿洲國”根本未能完成“主權國家”的建構。
(二)為施行種族壓迫與歧視制度而發表的獨立宣告另一種阻礙人民自由意志表達的形式就是種族壓迫與歧視制度,因為其剝奪了被壓迫、歧視族群的政治權利和表達自由。自決原則排斥制度化的種族壓迫與歧視,因為自決權的主體應當足夠廣泛,且自決權的行使不能成為一個族群壓迫和歧視另一族群的理由。1965年,英屬殖民地羅德西亞的白人政權為了避免賦予領地內的黑人居民以平等權利,單方面宣布脫離英聯邦取得“獨立”。盡管羅德西亞憑借“殖民地”的身份作為說辭,但安理會仍然認定該“獨立宣告”并非合法行使自決原則的實踐。理由就是其“獨立訴求”不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因為它根本不能代表當時占據總人口大部分的黑人族群的意愿。安理會通過一系列決議明確禁止國際社會承認羅德西亞的“獨立”身份,并要求各國對羅德西亞進行經濟和外交上的孤立:不得派遣代表與其交流聯絡,不得承認其護照,禁止與其貿易以及否認羅德西亞白人政府之“選舉”的法律效力。任何國際組織也應拒絕其加入的申請,驅逐其現存代表,并不得允許其參與任何活動。
20世紀70、80年代,為了緩解國際社會對種族隔離制度的非議,南非政府提出將施行“班圖斯坦制度”,即意圖將黑人依據族群分別限制在十個相互分離的、被稱為“黑人家園”或“自治領地”的領土單位之內。盡管這項制度被粉飾為“消除殖民統治的嘗試”,但南非政府的真正意圖是徹底拋棄黑人人口,強制性地將他們劃歸這些獨立領土,從而避免在南非國內賦予黑人以平等的政治權利。因此,安理會認定“班圖斯坦制度”的本質是施行變向的種族歧視和隔離制度,從而對其下達了嚴厲的禁令。上述實踐表明,國際法禁止通過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脅而達成的獨立宣告,也反對任何為推行種族壓迫與歧視政策的獨立訴求。相關獨立宣告被視為不具備國際法效力,嘗試此種做法的主體將會面臨國際制裁和孤立的懲罰。
參考文獻:
[1][英]馬爾科姆•N•肖.國際法(上下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李紅杰.由自決到自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5]白桂梅.國際法上的自決[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
[8]王英津.有關“分離權”問題的法理分析[J].世界政治與經濟,2011(12).
[10]余民才.“科索沃獨立咨詢意見”評析[J].法商研究,2010(6).
[13]秦珊.“不承認主義”政策在美國對華外交中的首次使用[J].史學月刊,2003(8)
作者:鄧烈;蓋然
- 上一篇:誠信在國際法中的地位范文
- 下一篇:高職行政管理分析(4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