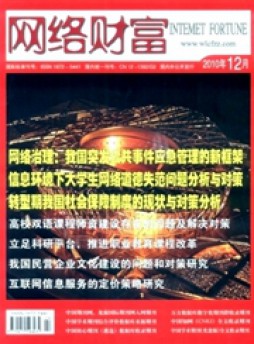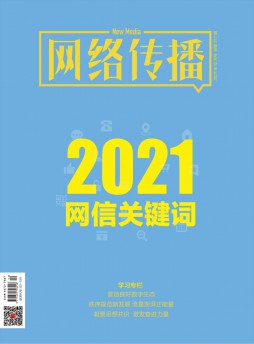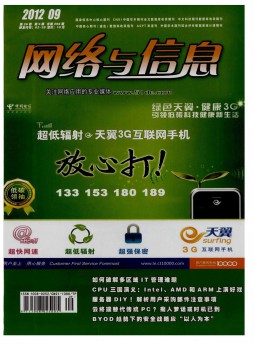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與流動人口個體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與流動人口個體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隨著網(wǎng)絡(luò)應(yīng)用的逐漸普及,流動人口使用網(wǎng)絡(luò)的數(shù)量逐漸遞增,其中占主體的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使用手機上網(wǎng)現(xiàn)象更為普遍。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tài)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其與實體社會的互構(gòu)趨勢越來越明顯。網(wǎng)絡(luò)社會的虛擬性、匿名性及高流動性特征使得其與實體社區(qū)差異巨大,而流動人口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更是如此。調(diào)研發(fā)現(xiàn),流動人口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出現(xiàn),不僅未能有效推動其群體意識和集體行動的形成,反而成為其個體化的加速器。
[關(guān)鍵詞]
流動人口;網(wǎng)絡(luò)社會;文化認(rèn)同;孵化器
一、問題的緣起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抽樣調(diào)查結(jié)果,2014年全國農(nóng)民工①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其中,外出農(nóng)民工16821萬人,比上年增加211萬人;本地農(nóng)民工10574萬人,增加290萬人。在外出流動的農(nóng)民工中,高中及以上農(nóng)民工占23.8%。接受過技能培訓(xùn)的農(nóng)民工占34.8%。分年齡段看,青壯年勞動力是農(nóng)民工的主力群體。數(shù)據(jù)顯示,21歲至40歲的農(nóng)民工占53%,41歲至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農(nóng)民工占17.1%。[1]這些數(shù)據(jù)能夠有效說明外出農(nóng)民工的主體已經(jīng)由第一代農(nóng)民工轉(zhuǎn)變?yōu)榈诙⒌谌r(nóng)民工。②第二代、第三代外出農(nóng)民工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民工的主體,相比第一代農(nóng)民工,他們自身具有年齡優(yōu)勢和學(xué)歷優(yōu)勢,更能適應(yīng)城市,享受城市中健全的公共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和便捷的技術(shù)服務(wù),尤其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使用過程中,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并不缺場。2012年,大谷打工網(wǎng)《基層藍(lán)領(lǐng)手機上網(wǎng)調(diào)查報告》顯示,全國受訪者中74%的農(nóng)民工使用手機上網(wǎng)。[2]2015年2月3日公布的《中國第35次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統(tǒng)計報告》顯示,農(nóng)村外出務(wù)工人員、制造業(yè)企業(yè)工人、商業(yè)服務(wù)業(yè)職工三者合計占網(wǎng)民總數(shù)的10%。[3]農(nóng)民工使用網(wǎng)絡(luò)的數(shù)量逐漸遞增,其中占主體的新生代農(nóng)民工手機上網(wǎng)行為更加普遍。根據(jù)筆者的調(diào)查和其他一些媒體的發(fā)現(xiàn),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使用最多的手機功能是QQ和微信,并且會長時間在線。隨著網(wǎng)絡(luò)社會的出現(xiàn)③,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tài)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已然形成,其與實體社會的互構(gòu)趨勢越來越明顯。然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虛擬性、匿名性及高流動性特征使得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與實體社區(qū)差異巨大,而農(nóng)民工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比如QQ群、微信群等更是如此。農(nóng)民工網(wǎng)絡(luò)社區(qū)這種新的社會形態(tài)對中國未來社會結(jié)構(gòu)變遷、政府治理的影響等問題是當(dāng)代中國學(xué)界和政府研究的重要課題。“雙重二元結(jié)構(gòu)”和“雙重脫嵌”[4]背景下的農(nóng)民工,通過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尤其是QQ和微信的線上和線下的交流、溝通和互動,能否形成新的文化認(rèn)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這種認(rèn)同能否成為推動農(nóng)民工群體意識形成的助推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這一新的社區(qū)形態(tài)是促進農(nóng)民工群體的組織化還是消解了農(nóng)民工群體的組織化?這是筆者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的出發(fā)點。
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興起的原因、條件及特征
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又稱虛擬社區(qū),指在網(wǎng)絡(luò)某個空間活動區(qū)域中,由網(wǎng)絡(luò)相鄰或相關(guān)的若干社會群體和社會組織構(gòu)成的網(wǎng)絡(luò)網(wǎng)民共同體,即在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某個空間區(qū)域”共同活動的若干人類群體。④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一般涵括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地域為基礎(chǔ)的網(wǎng)友通過共同活動而形成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另外一種是依據(jù)某個主題或話題分享興趣過程中形成的興趣群組,這種興趣群組并不依賴成員在地理上的分布。在這兩種大的分類基礎(chǔ)之上,當(dāng)前學(xué)界所指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主要有以下幾種具體類型:BBS/論壇、貼吧、公告欄、群組討論、在線聊天、交友、個人空間、微博、微信等。與實體的社區(qū)不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是一種利用現(xiàn)代技術(shù),通過地域觀念、共同興趣或愛好而聚集的網(wǎng)友形成的一種虛擬交流空間。因此,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與實體社區(qū)有著顯著不同。這種不同首先表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之間的互動并非是面對面的,而是通過網(wǎng)絡(luò)介質(zhì)進行的。其次,網(wǎng)絡(luò)中的互動不是在傳統(tǒng)的地域當(dāng)中,通過血緣、地緣或業(yè)緣而聚集在一起,而是通過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在網(wǎng)絡(luò)虛擬空間中進行的。再次,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互動主體的身份異質(zhì)性強,什么人都有。相對而言,實體社區(qū)中的互動主體身份同質(zhì)性強。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興起的原因主要在于現(xiàn)代社會呈現(xiàn)的時空分離、個人眾多角色扮演、社會信任的變遷及面臨的不確定性風(fēng)險讓人感到無所適從,難以形成前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關(guān)系和依賴感。在前現(xiàn)代社會,空間和地點總是一致的,而現(xiàn)代性帶來的現(xiàn)代社會,通過人們的不在場,空間與地點開始逐步分離,進而空間與時間也逐步分離。這種時空分離就導(dǎo)致了吉登斯所稱的“社會系統(tǒng)的脫域問題。所謂脫域,我指的是社會關(guān)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guān)聯(lián)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gòu)的關(guān)聯(lián)中‘脫離出來’”[5](P18)。隨著現(xiàn)代性在中國的擴張,由流動性增強而體現(xiàn)出來的時空抽離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和突出。伴隨現(xiàn)代性和流動性而來的就是個人扮演的眾多角色。前現(xiàn)代社會中,個人在實體社區(qū)中一生可能僅僅扮演相對較少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倫理性角色就足夠了,而在現(xiàn)代社會,個人在實體社區(qū)中扮演的倫理性角色已經(jīng)不能適應(yīng)社會需求,與工業(yè)化相關(guān)的眾多職業(yè)性角色開始成為人們角色的主流。這種職業(yè)性角色的扮演不僅在一地的實體社區(qū)中出現(xiàn),甚至隨著流動性的增強,在許多地域的實體性社區(qū)中出現(xiàn)。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基于前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方式也發(fā)生了改變,基于特殊主義基礎(chǔ)之上的信任模式開始向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轉(zhuǎn)變。特殊主義的信任模式是一種具體的信任,這種個體信任是基于彼此熟悉的個人之間的信任。普遍主義的信任模式是一種抽象的信任,這種抽象的信任是基于專業(yè)基礎(chǔ)之上的信任。無論是前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還是現(xiàn)代社會的信任,都能夠有效降低個體在面臨不確定時需要支付的成本或者說避免特殊的行動方式可能遇到的風(fēng)險或?qū)L(fēng)險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傳統(tǒng)的風(fēng)險是個體化的,現(xiàn)代性之下的風(fēng)險卻是群體化或者普遍化的,能夠影響聚居在一起的人類集體的安全。
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形成必須要具備一些前提特質(zhì)。這些前提特質(zhì)包括:第一,要有作為傳播媒介的互聯(lián)網(wǎng)的存在;第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成員能夠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進行信息的共享與日常的交流溝通;第三,網(wǎng)絡(luò)社區(qū)還需要能夠滿足其成員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實際需要;第四,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成員會對這個社區(qū)具有程度不一的歸屬感。《中國第35次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統(tǒng)計報告》顯示,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一種新型傳播媒介的地位已經(jīng)足夠牢固并不可撼動,甚至傳統(tǒng)平面媒體的地位已經(jīng)開始讓位于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基礎(chǔ)的新型自媒體。而在各種新型自媒體中,無論是QQ、微博,還是微信,其成員的信息共享與交流溝通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其頻率甚至超過日常的面對面溝通與交流。在這些新型自媒體形成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其成員的一些需要能夠得到滿足。筆者參與的一些QQ群、微信群經(jīng)常會有網(wǎng)友以“萬能的群呀,請幫我…”⑤類似的語句開頭,然后就會有熱心的群友進行幫助。類似的語句只有在宗教性的話語中才會出現(xiàn)。在筆者有關(guān)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對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歸屬感的調(diào)查中,他們告訴筆者:“如果不感興趣,當(dāng)初就不會加入。既然加入了,如果不是特別反感,也不會輕易退出。覺得有感興趣的話題,就多參與。覺得和某個成員聊得來,就多聊。甚至可以線下多互動。沒有感興趣的話題,就干脆不參與,不發(fā)言。”從這個角度考察,成員對于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認(rèn)同感是存在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與實體社區(qū)不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社區(qū)空間具有跨地域性。實體社區(qū)的地域性限制特別明顯,離開了其所在的地理空間,個體也就脫離了其所屬的實體社區(qū)。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則無此限制,只要有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就可以隨時隨地與其他成員進行同步或者異步的互動、溝通和交流。第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互動具有匿名性。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完全可以在不知曉對方的所有信息背景下,與對方進行互動。這與實體社區(qū)成員之間的知根知底的互動完全不同。盡管現(xiàn)在某些QQ群或者其他網(wǎng)絡(luò)社群要求加入的成員均為實名,然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匿名性本質(zhì)并未得到實質(zhì)改變。第三,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是一種自組織,這與某些實體社區(qū)的強制特征有所區(qū)別。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作為一種因流動性而找尋歸屬感產(chǎn)生的社區(qū)類型,無論是以地域為基礎(chǔ)而形成的社區(qū)還是以興趣為基礎(chǔ)而形成的社區(qū),都屬于一種網(wǎng)友自組織。這個自組織還會自發(fā)產(chǎn)生管理者、參與者、社區(qū)規(guī)則[6]等。第四,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邊界是開放的,其對成員資格甚至沒有任何要求。反觀實體社區(qū)的成員資格,往往以血緣、地緣或業(yè)緣為特征,并且成員資格和社區(qū)邊界非常清晰,不屬于社區(qū)成員的人想要突破社區(qū)邊界加入進來并獲得成員資格,途徑非常有限且面臨著諸多實際困難。
三、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個體化互動
在中國城市化、現(xiàn)代化和市場化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面對著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文化資源的不平等分配,雙重脫嵌的流動人口群體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通過對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使用,表達(dá)和建構(gòu)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和權(quán)利,為促進集體賦權(quán)和社會平等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現(xiàn)代科技所帶來的虛擬化的社會結(jié)群和社會流動并不能等同于社會化流動,現(xiàn)代科技帶給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的只是一種虛幻的個體認(rèn)同而非群體意識,這種虛幻的個體認(rèn)同不僅沒有讓流動人口以群體化、組織化方式應(yīng)對資本的盤剝和外界的歧視,反而讓他們體驗到一種更加個體化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尤其在面臨權(quán)益保護等方面的困境時,現(xiàn)代科技并不能給第二代、第三代流動人口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網(wǎng)絡(luò),反而推動了他們的個體化。[7]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網(wǎng)友盡管沒有發(fā)生面對面互動,但依然可以交換各種信息,進行溝通,也能從中獲取一些社會支持。然而由于這種關(guān)系的建立只是片面的,網(wǎng)友隱藏了真實的身份及其他個人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換、溝通互動的開展和社會支持的獲取并不能像實體社區(qū)中那樣有效。比如,筆者參加的一些流動人口的QQ群,他們在上面交換的信息類型大致包括娛樂、提供工作信息、尋求租房信息、孩子教育等方面,在這些信息交換中,娛樂、聊天信息占據(jù)信息交流80%以上,筆者的調(diào)查對象對此稱之為“吹牛”。至于對流動人口來說比較重要的工作信息等,只占20%左右。
筆者在訪談和調(diào)查的過程中,試圖通過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圈子”來找尋流動人口的群體意識和組織化方式,而令人失望的是,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互動基本是個體之間的互動,即點對點的互動模式,也就是平面媒體傳播中的人際互動,而平面媒體所具有的面對面互動、點對面互動比較少見。H市是長三角的省會城市,流動人口眾多,并且流動人口就業(yè)的企業(yè)基本為民營企業(yè)。筆者根據(jù)H市流動人口所在主要行業(yè),將流動人口調(diào)查對象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出租車司機、環(huán)衛(wèi)工人、工廠工人、建筑工人。對于分類別的流動人口參加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QQ或者微信圈的活動,筆者對訪談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得出如下結(jié)果(見表一)。從表格中的百分比數(shù)據(jù)能夠解讀出來一些問題。比如出租車司機都是上網(wǎng)的,但他們既然上網(wǎng)怎么會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活動參加不多呢?環(huán)衛(wèi)工人怎么沒人懂網(wǎng)呢?工廠工人上網(wǎng)怎么與建筑工人有區(qū)別呢?如果結(jié)合進一步的訪談,我們就能得出更進一步的結(jié)論。對于H市的出租車司機來說,他們上網(wǎng)是必須的。因為當(dāng)前智能手機的發(fā)展,包括各種打車軟件的興起,逼迫他們必須在手機上安裝微信和QQ。然而,對于出租車司機來說,他們使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頻率也不高。問:平常你們上網(wǎng)嗎?通過何種方式上網(wǎng)呢?QQ、微信玩嗎?答:上網(wǎng)我們基本很少上的,很少上網(wǎng),手機可以玩一下的,看看新聞,QQ、微信也沒像以前那么聊了,有一個群從早上7點鐘聊到晚上睡覺,那段時間是聊得蠻長的,聊了好幾個月,后來就斷掉了,有微信后聊天就很少,基本不聊天,基本就看看新聞。問:那你們朋友圈的人多嗎?浙江的多嗎?答:那多了,有老鄉(xiāng)、有戰(zhàn)友、有同學(xué)、有以前的同事。有很多很雜了。問:那你上QQ的時候,是你開出租車的時候,平時還是晚上?答:上班的時候,一般不大會上QQ,很少聊天。現(xiàn)在微信都不大玩,玩膩了,這些東西,剛出來的時候,新鮮嘛,玩得很起勁。(其他司機:QQ也幾乎都不用了。)問:那你在微信圈里,經(jīng)常都和朋友們聊什么?答:吹牛啊,吹牛啊,哈哈!我們有工作的,又不可能微信上跟他們……,各個行業(yè),你不可能講那種工作上的事情,沒法講的。大家行業(yè)都不一樣的。大家主要是聊聊天,吹吹牛啦。另外一司機答:關(guān)鍵是我們?nèi)ψ犹×耍淳褪情_出租車的朋友,要么就是老鄉(xiāng),其他然后外面就懶得走,一天開車很累,走到很遠(yuǎn)的地方去。遠(yuǎn)的,偶爾就是電話聯(lián)系一下,問一下怎么樣。這個圈子里面太小了。也沒時間。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與流動人口個體化H市的出租車司機透露出來的信息是盡管他們上網(wǎng),也參與了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但因為職業(yè)的關(guān)系,他們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并沒有太多活動,與社區(qū)中其他人的互動的內(nèi)容就僅限于吹牛,互動的對象也就兩類:要么開出租車的朋友,要么老鄉(xiāng)。出租車司機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活動非常個體化。環(huán)衛(wèi)工人基本不參與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原因在于筆者調(diào)查的環(huán)衛(wèi)工人,基本屬于年紀(jì)都比較大的一群人,他們對于現(xiàn)代科技的敏感度并不高。網(wǎng)絡(luò)或者智能手機對他們來說,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對于工廠工人來講,情況又會有差異。一位工廠工人如此回答:我現(xiàn)在基本是離不開網(wǎng)絡(luò)吧,上班下班,基本離不開網(wǎng)絡(luò),我業(yè)余時間真的都是靠網(wǎng)絡(luò)打發(fā)的。問:那你上網(wǎng)平時是在哪里上呢?答:我自己有電腦。在辦公室就是工作電腦,回家就自己的電腦。我上網(wǎng)基本上就是逛逛淘寶,或是文學(xué)的散文類的。我的微信基本是同事、同學(xué)比較多,同事離得比較近,同學(xué)離得比較遠(yuǎn),基本上是半年同學(xué)聚會時才能聚到一起。我的微信朋友圈不大,但我自己老是發(fā)微信,心情、動態(tài)都是通過微信的形式發(fā)的。問:那你發(fā)的這些是點贊的人多,還是評論的多呢?答:評論的挺多的,一般是同學(xué),都是些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也不會評你的。我的QQ、微信一般討論的話題就是對以后有什么打算,然后不可能永遠(yuǎn)打工。我覺得現(xiàn)在我們經(jīng)常討論的熱點話題,對我的思想和行為還是有影響的,就是會跟著外面的形勢吧。我比較喜歡追流行,今天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我比較喜歡跟著潮流走。我在QQ、微信中經(jīng)常扮演的角色是別人有什么心事經(jīng)常會跟我講的。對于在工廠工作的流動人口來講,他們的空閑時間比較多,再加上工作性質(zhì)的關(guān)系,他們呆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時間也比較長。盡管如此,筆者通過訪談看到的是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互動依然非常個人化,很少有群體性的互動,也很難形成所謂的社區(qū)意識或者群體意識。從對數(shù)據(jù)和訪談資料的考察,筆者發(fā)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互動非常個體化,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性質(zhì)所致;二是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網(wǎng)友之間的信任很難建立。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性質(zhì)首先是匿名性,匿名性使得在虛擬社區(qū)中活動的網(wǎng)友互動時面臨某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將會阻止網(wǎng)友的進一步深入了解和互動。其次,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這便使得加入社區(qū)的成員因為沒有付出一些成本,而不會產(chǎn)生珍惜心理,再加上現(xiàn)實中工作的流動性,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流動性也特別強。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流動性使得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的互動呈現(xiàn)出一種“個體化、碎片化”的模式。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這種“個體化、碎片化”的互動,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之間無法產(chǎn)生基本信任。在吉登斯看來,“在個人的早期發(fā)展過程中,對自我認(rèn)同的穩(wěn)定環(huán)境和周圍環(huán)境的基本信任…是從對個人的信任中派生出來的”[5](P99-100)。也就是說,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個體化互動,既無法產(chǎn)生前現(xiàn)代社會中的私人信任,也無法產(chǎn)生現(xiàn)代社會中的制度信任。這種個體互動在某種程度上導(dǎo)致了吉登斯所說的“親密關(guān)系的變革”[8](P101-109)。這種變革對于未來社會的影響正在逐漸顯現(xiàn),畢竟親密關(guān)系的獲得是以信任關(guān)系為基礎(chǔ)的。一個無法產(chǎn)生信任關(guān)系的社區(qū),親密關(guān)系也不會產(chǎn)生,那么群體意識和群體認(rèn)同將更難形成。
四、作為個體化加速器的網(wǎng)絡(luò)社區(qū)
正如閻云翔觀察到的:“農(nóng)村青年正努力緊跟城市主流文化,模仿他們認(rèn)為是現(xiàn)代時尚的城市生活方式。他們喜歡時尚和娛樂,追求個人獨立和幸福,沉迷于物質(zhì)收益…他們對更為物質(zhì)主義、個人主義及現(xiàn)代生活方式的追求。”[9](P159)當(dāng)代中國農(nóng)民工的第二代、第三代進入城市,受到城市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的影響,接受了現(xiàn)代科技的洗禮,在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方面與城市青年已經(jīng)沒有了鴻溝和差距。筆者在調(diào)查和訪談時,工廠工人身邊的手機不斷刷著微信,間或還在回復(fù)。這足以說明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在這些方面與城市已經(jīng)沒有任何代差。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積極融入城市的同時,卻面臨著殘酷的現(xiàn)實。筆者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每一個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身上都流露出強烈的向上流動的愿望,都希望通過自身努力而改變命運。但是,他們無力改變僵硬的結(jié)構(gòu)和體制,只能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換一個工作再換一個工作,學(xué)者用“漂泊化和失根”[10]群體、“短工化”[11](P2)群體描述他們的現(xiàn)狀和困境。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從原有鄉(xiāng)村社會結(jié)構(gòu)中被抽離出來之后,無法重新嵌入到城市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當(dāng)中,出現(xiàn)一種被動個體化的過程。[7]在此情況下,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會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是實現(xiàn)自我認(rèn)同和突破僵硬體制的一種方便、快捷途徑。然而,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的匿名性、流動性、虛擬性特征卻并不能支持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通過網(wǎng)絡(luò)社區(qū)突破僵硬體制的愿望,反而以個性化、多樣化功能讓他們沉迷于其中,倘佯在虛擬世界的認(rèn)同和對虛擬世界的突破中,暫時忘卻現(xiàn)實的困頓,在這里實現(xiàn)了主動的個體化過程。一旦進入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每個個體就會完全分化。無論是從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成員的虛擬身份,還是從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交往方式、交往對象,甚或從網(wǎng)絡(luò)社區(qū)中的自我表達(dá)來看,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既非能夠推動社區(qū)成員形成整體的社區(qū)意識,也非能夠推動社區(qū)成員形成統(tǒng)一的社區(qū)行為,更談不上通過網(wǎng)絡(luò)社區(qū)意識和社區(qū)行為影響現(xiàn)實中的意識和行為。顯然,在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他們出現(xiàn)了一個“個體化過程”,而這個個體化過程包括被動的個體化和主動的個體化兩個層面。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第二代、第三代農(nóng)民工主動個體化的加速器。
作者:董敬畏 單位:浙江行政學(xué)院 社會學(xué)文化學(xué)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