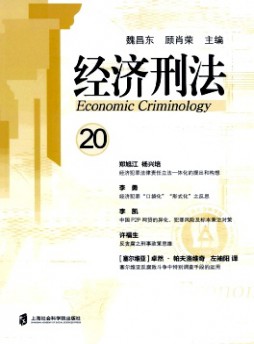談刑法中期待可能性判斷尺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談刑法中期待可能性判斷尺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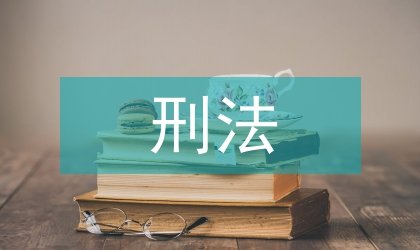
一、關于期待可能性判斷標準的學說
第一,國家標準說(法規范標準說)。以上兩說,都是從被期待一方提出判斷標準,而國家標準說則是從期待一方提出判斷標準,即主張以國家或國家的法秩序的具體要求為標準,來判斷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因為所謂期待,是指國家或法秩序對行為人的期待,而不是行為人本人的期待,因此,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只能以國家或法秩序的要求為標準,而不是以被期待的行為人或平均人為標準。該說受到的批判是:期待可能性的理論本來是為了針對行為人的人性弱點而給予法的救濟,所以,應考慮那些不能適應國家期待的行為人,該說則未考慮這一點;而且究竟在什么場合國家或法秩序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是一個不明確的問題,因此,該說實際上未提出任何標準。[4]
第二,折衷說。第一種觀點認為,“以國家標準說為前提,任何表明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條件不能與國家的意志即法律的要求相抵觸;以普通人標準為根本,結合日常生活中多數人的活動規律確認期待可能性的條件是否合理;以個人標準說為補充,從行為人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行為人與一般人的差別,承認行為人的特殊性。”第二種觀點認為,“期待可能性的標準,應以行為人標準為主,而輔以普通人標準和國家標準。在國家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以行為人標準為主,參照普通人標準。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根據行為人行為的情況,可以確定行為人有無期待可能性,則不須考慮普通人標準。”第三種觀點認為,行為人標準、平均人標準說與法規范標準說事實上回答的是,實施其他合法行為的可能性達到何種程度時,行為人才有責任。就有無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準而言,應以行為人的主觀的、個人的事實為基礎,再根據處于行為人地位的平均人標準進行判斷。如果完全以平均人為標準,而不考慮行為人主觀的、個人的事實,就是只照顧了一般化的正義,而沒有照顧個別化的正義;如果既考慮行為人主觀的、個人的情況,又以該行為人為標準,結局是任何人在當時實施該行為都是不得不實施的,否則他不會實施,這樣就無法律可言。確信犯的概念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在認定行為人具有實施其他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時,還應判斷可能性的程度,即具有何種程度的可能性時才承擔責任,這里當以國家要求或法秩序為標準,而這種要求又是以一般人的規范意識為基礎的。
第三,類型人標準說。該說是有學者基于對行為人標準說的修正而提出的。日本的植田重正教授認為,“即縱令依據行為者標準說,然亦非以單純的行為者個人為標準,而系以行為者本人所屬之類型人(由于本人之年齡、性別、職業及經歷等等所構成之愿望)為標準者……然有無期待可能性之判斷,亦非個人的以及主觀的判斷,而常具備某種程度之類型性及客觀性。”
二、對以上學說的評價
針對以上各說,筆者認為,第一,針對行為人標準說的幾點批判,實際上并未抓住問題的關鍵。行為人標準使責任非難具有個別性,而主張根據行為人的個人狀況為標準判斷期待可能性,這一出發點是正確的。但是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責任判斷雖然是個別化的判斷,但是責任判斷從行為人自身出發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只能得出行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期待可能性的結論。因為責任判斷必須是將行為人與其他人相比較才能夠作出,無比較也就無所謂非難。也就是說,沒有參照物,行為人在主觀上就沒有值得非難的地方可言,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期待可能性,從而否定責任的存在。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行為人標準說根本就不是一種標準。對此,我國也有學者指出,期待可能性判斷的標準不能取決于行為人,必須以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作為標準。前述提到的對行為人標準說的幾點批判并未認識到這一點,反而都是以承認行為人標準說是判斷期待可能性的標準為前提的。并隱含著這樣一種預設,即在有些情況下該說能夠正確地判斷期待可能性。例如,前述對該說的第三點批判認為確信犯常常無期待可能性被認為無罪,言下之意是,確信犯之外的犯罪有可能根據行為人標準說而被認為有期待可能性從而被認為有罪,這一邏輯顯然是對該說未深入了解所造成的。
持行為人標準說的大塚仁教授認為,針對行為人標準說,從來就有批判指出,站在行為人標準說的立場上,所有的行為人都會被允許,從而使刑法失去基礎。但是,以行為人作為判斷標準,并不是無條件地肯定行為人的主觀立場的感傷主義。即使說要考慮具體場合中的行為人的情況,那也總是客觀地評價行為人的能力,在行為人具有低于平均人的能力時,也應該在其能力的最大限度內予以評價。因此,即使根據行為人標準說,不能期待是責任能力者的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的事態也不會像所擔心的那么多,說會帶來刑事司法的軟弱化,只不過是杞人之憂。大塚仁教授針對行為人標準說受到的批判所作出的上述反駁并不能成立。其將責任能力與期待可能性相混淆,責任能力作為主觀的能力當然必須從行為人自身進行個別的判斷,但這種判斷不能等同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斷。其所謂“行為人具有低于平均人的能力”,即是將行為人與平均人二者的責任能力相比較,而并非將平均人在行為人行為時的具體狀況下實施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與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相比較。
第二,針對國家標準說的上述批判是成立的。按照該說來判斷期待可能性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行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實施合法行為的期待可能性,因為行為人的行為必須要符合國家或法秩序的期待。該說與行為人標準說一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第三,平均人標準說避免了上述兩說的缺陷。該說在日本是通說與判例的立場。前述該說受到的批判,筆者認為,首先,針對第一點批判。通常人、平均人雖然是模糊的概念,但是其他學說的標準同樣模糊,而且對通常人、平均人的判斷只要基本符合社會的一般觀念即可,不可能做到絕對地精確。其次,針對第二點批判。對行為人期待可能性的判斷原本就必須與他人相比較才能作出,即同時考慮行為人與其他人的具體情況,如果行為人也屬于平均人,這一批判就不成立。最后,針對第三點批判。該點批判將責任能力等同于狹義的期待可能性,顯然不正確。由此可見,平均人標準說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是其缺陷實際上在其受到的第二點批判中已被涉及,即如果行為人不屬于平均人或者說如果行為人由于具有某種特殊的身份從而使其期待可能性的判斷不能與社會上的一般人相比較時,平均人標準說就顯得不妥當。這一缺陷正好可以為類型人標準說彌補。
第四,各種折衷說實際上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不能成為判斷期待可能性標準的行為人標準說或國家標準說,因此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第五,類型人標準說的首倡者植田重正教授雖然認為該說屬于行為人標準說,但該說本質上是對平均人標準說的修正。內藤謙教授認為,所謂的“行為人本身所屬的類型人”,可以認為接近于平均人標準說中的平均人。期待可能性有無的判斷,不具有個人的、主觀的因素,而應該認為具有一般程度的類型性、客觀性。如果進一步解釋,那么所謂“行為人本身所屬的類型人”,絕對不能簡單地與“平均人”的類型化同樣對待。這一評價是正確的。我國有學者認為,“筆者傾向于將‘類型人標準’視為增強‘行為人標準’可操作性的一個方案,而不是將類型人標準獨立出來。”這一觀點與植田重正教授的觀點類似,因而是不妥當的。類型人標準說作為平均人標準說的修正與行為人標準說有本質不同。
我國有學者贊同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準應采用類型人標準說,其理由是:一,類型人標準說較為全面地反映社會關系中的不同人群及其屬性。二,類型人標準不僅可以在決定有無期待可能性時適用,也可在判斷期待可能性大小時適用。三,類型人標準能夠適用于刑法實踐的不同環節。對此,筆者原則上贊同。但是,類型人標準說及該學者的某些認識尚存在問題。類型人標準說在行為人具有法律所規定的特殊身份時,其判斷結論較平均人標準說合理。筆者認為,這里的行為人的特殊身份主要有兩類:一是刑法分則條文對行為人可以成立單獨正犯所要求具備的某些身份。主要是指特定職業身份與特定性別身份,如貪污罪中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強奸罪中的男性身份。但是不包括一般人也可能具有的身份,如偽證罪中的證人身份。二是行為人具有的刑法總則條文所規定的未成年人的身份與限制責任能力人的身份。在我國主要是指,單純的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犯罪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人所具有的未成年人身份;單純的具有限制責任能力的人的身份,包括單純的具有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身份,單純的又聾又啞的人和盲人的殘疾人身份。在具有第一種類型身份的人實施違法行為的場合,判斷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當然不能以社會上一般的平均人為標準,而必須以具有該特定身份的同類人為標準,此時平均人標準說不妥當。在具有第二種類型身份的人實施違法行為的場合,則需分情況討論。首先,單純的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犯罪而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未成年人實施違法行為時,判斷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應以同類的未成年人為標準,而不應以社會一般的平均人為標準。其次,單純的具有限制責任能力的人實施違法行為時,又可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行為人所實施的違法行為受到了自身責任能力的影響,此時判斷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應以具有與該行為人同等性質與程度的同類具有限制責任能力的人為標準,而不應以社會一般的平均人為標準。第二種情況是,行為人所實施的違法行為未受到自身責任能力的影響,此時判斷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當然應以社會一般的平均人為標準。當然,同一行為人也可能同時具有第二種類型的幾種身份中的一種以上的身份,這時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斷可以參照以上標準進行綜合考量。
三、結論
上述分析可以說明,雖然在一些場合,期待可能性的判斷要受到行為人具有的特殊身份的影響,此時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準應是類型人標準說。但是在有些場合,期待可能性不受任何特殊身份的影響,此時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準仍應是平均人標準說,并且這是從最廣義上以能夠實施犯罪的所有人為對象來確定“平均人”。實際上本來意義上的平均人標準說只是將“平均人”限于社會上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一般人”,因而是一種狹義的平均人標準說。此外,在不具有上述特殊身份的完全責任能力人實施的不要求特定身份的違法行為中,判斷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的標準也是平均人標準說,只不過是本來意義上的狹義的平均人標準說。當然,如果將類型人標準說的“類型人”無限擴大解釋,將平均人也作為一種“類型人”,即與無責任能力者相區別的“類型人”,那么類型人標準說也可解決所有期待可能性的判斷問題。但是這種無限的擴大解釋顯然不符合類型人標準說的本意,而且將所有的社會一般的平均人作為一種類型也失去了劃分“類型人”的意義。因此,筆者認為,類型人標準說僅僅是對平均人標準說的有益的補充或修正,而不能取代平均人標準說。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準應是平均人標準與類型人標準的結合。
作者:毛冠楠單位:河南省潢川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 上一篇:水電局學習科學發展觀活動工作意見范文
- 下一篇:水利建設工程竣工驗收管理辦法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