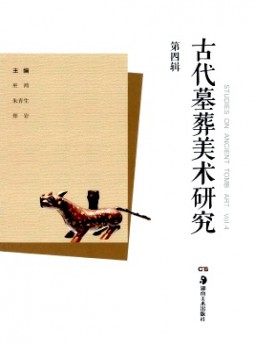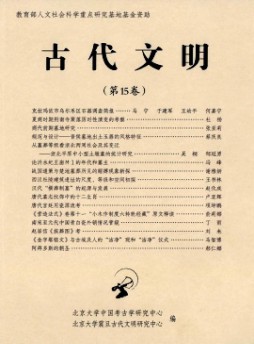古代繪畫與音樂藝術(shù)理論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古代繪畫與音樂藝術(shù)理論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著名代表作品有《溪山行旅圖》《雪山蕭寺圖》《雪景寒林圖》等,對中國山水畫的發(fā)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范寬的繪畫風(fēng)格被歷代畫家競相模仿,現(xiàn)當(dāng)代畫家依然在畫風(fēng)上會受到范寬繪畫風(fēng)格的影響,其影響不僅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繪畫歷史中也非常突出。在范寬的作品中,《溪山行旅圖》最為著名,這幅作品也在中國繪畫史上頗具影響力。《溪山行旅圖》軸,絹本,是由兩塊寬約52厘米的絹絲拼成,畫幅長206.3厘米,寬103.3厘米,畫作上方題有“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圖,董其昌觀”十四字,此畫還得到了明代著名畫家董其昌的題跋,現(xiàn)珍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從畫面上看,巍峨巨大的峰巒平地矗立,占有三分之一的畫面,矗立在畫面正中,頂天立地,壁立千仞,具有撼人的視覺沖擊力,歷代觀者很少不為其雄偉威重,渾厚堅實的浩壯之氣所震懾。山頭灌木叢生,結(jié)成密林,狀若覃菌,兩側(cè)有扈從似的高山簇擁著,把大山刻畫得堅實與傳神。樹林中巨石縱橫,有樓觀微露,從外形看上去像是道觀,終南山自古以來就是道教名山,此樓如是宗教建筑也在情理之中。在巖石和上方的樹林之間出現(xiàn)了一條曲折蜿蜒的夾雜著泥濘的山路,小丘與巖石間一隊商旅馱隊正沿路艱難行進。走在前面的是一個手拿鞭子的人,此人坦露上身,腰中系著黑色的腰帶,頭部向后扭著,似乎在招呼同伴緊跟隊伍,四頭毛驢緊隨其后,身托重物,步履矯健,隊伍最后的人頭裹包巾,手拿鞭子,背后扛著貨物。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畫中在靜謐的山野中仿佛使人聽到水聲和驢蹄聲。細如弦絲的瀑布一瀉千尺,潺潺的溪聲在山谷間回蕩,景物的描寫極為雄壯逼真。全幅山石以密如雨點的墨痕和鋸齒般的巖石皴紋,刻畫出山石渾厚蒼勁之感。整個畫面充滿幽深、靜謐和偉大的氣象。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之所以給人以雄偉壯觀,天人合一的和諧意境,不是以描繪人物的渺小來凸顯山的巍峨,關(guān)鍵是在于對近景的處理。作品中近景的逐漸推遠,在每一層次的轉(zhuǎn)折處都處理得微妙精準(zhǔn),使得一層比一層遠,到達主峰山麓時,已經(jīng)緲不可測。當(dāng)人們的視覺從極度虛遠的山麓再轉(zhuǎn)向畫面中的主峰時,主峰那種由遠及近的撼人視覺沖擊力就由此產(chǎn)生了。人們越是能體驗到山麓的虛遠,越是能夠感受到山體的無限之大,體現(xiàn)出一種超凡脫俗的意境。劉道醇在《宋朝名畫評》對《溪山行旅圖》大為贊賞,并列為神品,謂:“宋有天下,為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座外”,“范寬以山水知名,為天下重”。《宣和畫譜》評價《溪山行旅圖》“恍然如行山陰道中”,使人感覺身臨其境一般。明代大書畫家董其昌令其愛徒王時敏將此圖縮小臨摹,精心與其他作品裝訂成冊,以便傳播。郭若虛對《溪山行旅圖》贊賞有加,把范寬、關(guān)同和李成列為“三家鼎峙,百代標(biāo)程”的“三家山水”。《平生壯觀》中評價:“山頭直上,而接于水涯。不作瑣碎斷續(xù)之狀,俯視但一氣焉。樹石簡略,設(shè)色深沉,真大手也。諦視此本,則舉世所謂寬者,不足記也”。徐邦達評:“此圖絹本,墨筆畫,濃重粗壯,氣象雄偉”。徐悲鴻對此畫更是推崇:“中國所有之寶,故宮有其二:吾所最郭熙的《早春圖〉,畫中峰巒疊嶂,流泉飛瀑,林木參差,行人隱于山中,整幅畫淡且潤,包含早春生機盎然,萬物復(fù)蘇的生機。畫中的蟹爪樹枝用筆柔韌挺健,秀拔舒展,山石以卷云皴和披麻皴相結(jié)合,虛實相生,濃淡相宜,輕嵐薄霧的早春景象躍然紙上,撲面而來。應(yīng)物象形傾倒者,則為范中立的《溪山行旅圖》,大氣磅礴,沉雄高古,誠辟易萬人之作,此幅畫系巨幀,而一山頭,幾占全幅面積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全幅整寫,無一敗筆,北宋人治藝之精,真令人拜倒”。《溪山行旅圖》是涵蓋范寬獨到筆墨技法的經(jīng)典之作,此畫在當(dāng)時乃至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禮記•樂記》論音樂起源時,則明確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在我們民族的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中,是把宇宙境界與藝術(shù)意境視為渾然一體的同構(gòu)關(guān)系,是一種生命形式,中國傳統(tǒng)音樂所表現(xiàn)的對宇宙境界的體驗就是一種生命律動的體驗,而音樂意境恰恰就是這種生命律動的表現(xiàn)。《樂記》的“音由心生”的觀點,則強調(diào)心的作用,重視內(nèi)心感悟的審美取向,認為音樂意境本質(zhì)上是一種心理現(xiàn)象,一種人類心靈的生命律動。中國傳統(tǒng)音樂在長期的發(fā)展中因獨特的審美取向,展現(xiàn)出優(yōu)雅美妙的生命弦律。在每一個社會、每一個歷史時期,音樂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國古代,音樂是最為發(fā)達的一門藝術(shù),是各門藝術(shù)的中心和源泉,因此《樂記》中的“物感說”既出,便成為包括“意境”在內(nèi)的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范疇和主體精神。作為六朝時期卓越的文論家,劉勰主張“情以物興”,“物以情觀”,認為由感物抒情,必然會導(dǎo)致物情相觀,心物交融,基本提出了關(guān)于“意境”的概念和內(nèi)涵。與劉勰同時期的詩論家鐘嶸,在《詩品序》篇首即講:“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鐘嶸論詩,極推崇詩的“滋味”,鐘嶸所說的“滋味”,指的就是詩的形象和感情。他除了強調(diào)“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之外,更看重感情與形象的有機融合即意境的創(chuàng)造,這從他評論范云和丘遲詩作的見解中可窺斑知豹。劉勰和鐘嶸,一個論文,一個論詩,各自都承襲了《樂記》的“物感說”的觀念,可見《樂記》的“物感說”為“意境說”美學(xué)概念的提出做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貢獻。中國古代的音樂一般是以追求幽婉深邃、淡泊含蓄,虛實相生和意象共存為最高藝術(shù)境界。在“意境”理論提出之前,中國的古琴音樂已經(jīng)在作品中呈現(xiàn)出含有深刻意蘊的“意境”,特別是以山水創(chuàng)作作為題材并形成獨特“意境”的音樂作品要比文學(xué)與繪畫作品出現(xiàn)的早的多。如后世傳誦的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早在《呂氏春秋》和《列子•湯問》等文獻都有記載。《列子•湯問》說“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鐘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鐘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鐘子期必得之。”《風(fēng)俗通》亦說:“伯牙鼓琴,鐘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傾之間,而意在流水”,“及其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于琴以抒其意。”曲中表現(xiàn)“意在高山”“意在流水”“抒其意”,可見古琴是作為一種寄意的表現(xiàn)方式來到達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古代及傳統(tǒng)的音樂意境的風(fēng)貌完全可以從古琴這門藝術(shù)中找到闡釋。古琴藝術(shù)是一種儒道思想相互融合的藝術(shù),在古琴音樂中既體現(xiàn)了儒家思想中的溫柔敦厚、平和雅正,又體現(xiàn)了道家思想中的順應(yīng)自然、大音希聲與清微淡遠。古琴曲采用的是五聲音階,即“宮、商、角、徵、羽”正五音,而在《樂記》中的說法則為: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這五音代表著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音樂上的落實,而琴樂中追求的清虛淡靜、深靜幽遠以及表達弦外之音的意境則為道家思想的體現(xiàn)。道家思想對于古琴音樂中意境的產(chǎn)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響也是頗為深遠的。古琴音樂中由于虛靜與深遠的相結(jié)合,體現(xiàn)的是一種無限和深微的境界。正所謂“弦外之音”“韻外之致”“味外之旨”,這種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的境界乃是體現(xiàn)意境的最高層次。明末古琴家徐上瀛的《溪山琴況》中對于意境的描述如:“其無盡藏,不可思議。”;“琴中有無限滋味,玩之不竭”;“其有得之弦外者,與山相映發(fā),而巍巍影現(xiàn);與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變也,虛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閣流春。”“迂回曲折,疏而實密,抑揚起伏,斷而復(fù)聯(lián),此皆以音之精義,而應(yīng)乎意之深微也。”“深山邃谷,老木寒泉”;“山靜秋鳴,月高林表”;“松風(fēng)遠拂,石澗流寒”;“山居深靜,林木扶蘇”。琴樂中體現(xiàn)出的“無盡”、“無限”、“深微”的境界以一種最少的聲音物質(zhì)來表現(xiàn)最豐富的精神內(nèi)涵,所以琴聲音淡、聲稀,琴意得之于弦外,正是言有盡而意無窮。陶淵明之“但識琴中趣,何勞弦音”,正是將琴樂之重意、重弦外之音的思想推至窮極的哲學(xué)思維。沈括評北宋琴僧義海為:“海之藝不在于聲,其意韻蕭然,得于聲外”。古琴是偏向靜態(tài)之美的藝術(shù),因此彈琴要講求幽靜的外在環(huán)境于閑適內(nèi)在心境的配合,方可追求琴曲中心物相合、主客和一的藝術(shù)境界。
在中國古代作為美學(xué)范疇的“意境”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相當(dāng)漫長的過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這時的“意境”理論還未被概括出來,但在現(xiàn)實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早已出現(xiàn)了“意境”。清人潘德輿在《養(yǎng)一齋詩話》中對《詩經(jīng)》進行評價說:“《三百篇》之體制音節(jié),不必學(xué),不能學(xué),《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xué)也。”①由此看來,清人潘德輿認為《詩經(jīng)》有意境的存在,并認同意境的重要性。魏晉南北朝時期美學(xué)思想中所出現(xiàn)的詩味說、言意論、形神論等都對意境理論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當(dāng)盛行的“詩味說”,以“味”論詩。如陸機在《文賦》中說:“闕大羹之遺味。”這是用羹湯遺留在嘴中的滋味來比喻詩文的藝術(shù)韻味。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多次以“味”論詩文,他所說的“味”,與藝術(shù)的善于描述豐富與真摯的情感、表達言外之意等都有密切聯(lián)系。鐘嶸的《詩品序》中也強調(diào)詩歌要能達到“滋味”醇厚的目的,使人產(chǎn)生美感的余味要有“滋味”。②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詩味說”與“意境”理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聯(lián),事實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味說”確實為后來“意境”理論的孕育與發(fā)展做出了鋪墊。“意境”說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由王昌齡的《詩格》中開啟先河。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解境象,故得形似。”“物境”就是指詩人的頭腦中所產(chǎn)生的山水之境象。它是由主體對客觀景物的觀照而產(chǎn)生于實景之中的心物交融的一種境界。“二曰情境。娛樂悉急,皆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情境”是作者內(nèi)心感情體驗和生活感受之境。它是詩人用心靈觀照生活、體驗生活而產(chǎn)生的。“三曰意境。亦張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意境”是指詩人頭腦中的思想意識之境,是詩人內(nèi)心深層的體驗并在體驗中發(fā)展與升華的界域。但這與后來的文論中提及以情景交融為基本內(nèi)涵的意境是不同的概念,它側(cè)重于主體的精神狀態(tài)。皎然的《詩式》中多次提到境和境象等概念,可見他對意境理論進行過深刻的思考與探討,如“文外之旨”、“情在言外”、“采齊于象”,由于皎然受佛學(xué)影響,他所提出的境和境象與禪學(xué)是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的。權(quán)德輿也明確提出了“意與境會”,這并不代表意與境的簡單結(jié)合,而是含有意境渾融,含蓄蘊藉和發(fā)人想象的意思。他初步概括了意境理論的基本特征。權(quán)德輿與皎然一樣,他的意境和禪宗學(xué)說有密切的聯(lián)系。中唐劉禹錫的詩論開始提到意境,他在《董氏武陵集紀》中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這個觀點的提出對“意境”論的創(chuàng)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劉禹錫的意境觀也受到禪宗境界說的影響,通常把詩和禪相提并論。晚唐司空圖在吸取前人“境界”說成果的基礎(chǔ)上,在的《二十四詩品》中提出各種境界,即如何創(chuàng)作出“雄渾”、“高古”等境界,比較深入地體會了意境的基本內(nèi)涵,創(chuàng)造性的提出了“思與境偕”說,指詩人在創(chuàng)作審美過程中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契合,創(chuàng)造出“意與境渾”境界的作品。對于境界理論的產(chǎn)生,佛學(xué)禪宗境界說可以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目前雖然沒有較可靠依據(jù)認定王昌齡的“三境”說是否受了佛學(xué)境界理論的影響,但是,中唐詩僧皎然提出的“取境”“造境”“緣境”說則肯定來自佛教境界觀的啟發(fā)。皎然以后,雖然詩論家們對“境”的理解各有側(cè)重,但以“境界”論詩蔚為風(fēng)氣。如唐人權(quán)德輿的“意與境會”(《全唐文•左武衛(wèi)胄曹許君集序》);劉禹錫的“境生于象外”(《劉禹錫集》之《董氏武陵集紀》);晚唐司空圖的“思與境偕”(《與王駕評詩書》)等這些唐代詩文人的觀點中來看,都或多或少受到過佛學(xué)思想的熏染和影響。宋代對意境理論的采用已經(jīng)開始廣泛,對“意境”理論有所突破的分別是蘇軾、釋普聞、嚴羽等。蘇軾是繼承了司空圖關(guān)于“思與境偕”的思想,認為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采菊次之,偶見南山,境與意會。”③釋普聞在《詩論》中強調(diào)“意出于境,意與境合”,這也是對于境界論的一個頗有價值的說法。
釋普聞釋意境為“境意”,說:“大凡但識境意明白,覷見古人千載之妙,其猶視諸掌”。④這把意境看作是評判詩歌成功與否的最科學(xué)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南宋嚴羽指出:“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⑤。嚴羽的相關(guān)論點提出標(biāo)志著意境說基本思想的成熟,同時也說明我國古代的意境說的興衰更替是有跡可循。清末民初的王國維是意境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繼承發(fā)展了古代詩歌理論的意境說并在《人間詞話》中發(fā)揮盡致。使人們對“意境”理論的審美特征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在美學(xué)理論體系中,現(xiàn)代有關(guān)的“境界”理論首創(chuàng)于王國維,而王國維也是第一個將王昌齡作為藝術(shù)理論的“意境”提升到人生意義視域?qū)用娴摹熬辰纭闭摰牡谝蝗恕M鯂S強調(diào):“詞以境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四“意境”是我國傳統(tǒng)美學(xué)中的一個重要研究范疇,它具有醇正而又濃郁的中國特色,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的藝術(shù)精神與審美特征。它有著源遠流長的衍變過程,它的生成與完善得益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影響和中華民族的審美創(chuàng)造。“意境”也是藝術(shù)家在藝術(shù)作品中表達藝術(shù)內(nèi)涵與抒發(fā)內(nèi)心情感所追求的最高藝術(shù)境界,是通過藝術(shù)作品使欣賞者充分發(fā)揮想象與聯(lián)想,使其身臨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強烈感染的一種藝術(shù)效果。對于在一部優(yōu)秀的藝術(shù)作品中“意境”進行成功的塑造,能夠使情與景、意與境、物與我、情與理、形與神等因素和諧地交融,從而塑造出鮮明生動的藝術(shù)形象,作品也得以產(chǎn)生出強烈的認同感與感染力。中國古代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藝術(shù)作品,無論是音樂、舞蹈、繪畫、書法還是詩歌,都是以創(chuàng)造一種具有深刻內(nèi)蘊的、融合和諧元素的“意境”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為最高審美準(zhǔn)則。
“意境”是藝術(shù)家在藝術(shù)作品中表達藝術(shù)內(nèi)涵與抒發(fā)內(nèi)心情感所追求的最高藝術(shù)境界,是通過藝術(shù)作品使欣賞者充分發(fā)揮想象與聯(lián)想,使其身臨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強烈感染的一種藝術(shù)效果。一部優(yōu)秀的藝術(shù)作品的中“意境”的塑造,往往能使情與景、意與境、物與我、情與理、形與神等因素和諧地交融在一起,塑造出鮮明生動的藝術(shù)形象,使得作品給人以強烈的認同感與感染力。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意境論產(chǎn)生的重要性,學(xué)術(shù)圈眾多學(xué)者紛紛闡明了各自的觀點。宗白華先生曾說:“藝術(shù)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xiàn)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diào)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gòu)成藝術(shù)之所以為藝術(shù)的‘意境’。”(但在音樂和建筑,這時間中純形式與空間中純形式的藝術(shù),卻以非模仿自然的境相來表現(xiàn)人心中最深不可名的意境,而舞蹈則又為綜合時空的純形式,所以能為一切藝術(shù)的根本形態(tài)。)”⑥宗先生的意思是說,在關(guān)于藝術(shù)所有的領(lǐng)域中,“意境”必然能包括各個藝術(shù)形態(tài)。蒲震元在《中國藝術(shù)意境論》一著中提出:中國藝術(shù)意境理論是一種東方超象審美理論,其哲學(xué)根基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論,他從意境的審美內(nèi)涵的界定、虛實相生與意境的構(gòu)成、意境的歷史形態(tài)與時代面貌、中國意境理論與西方典型理論、意境深層結(jié)構(gòu)中氣之審美與道之認同境層的美學(xué)特征六個方面進行了探索,最后在余論中指出藝術(shù)意境的獨特創(chuàng)造是中國藝術(shù)理論“特別東方的(黑格爾語)的表現(xiàn)之一。”⑦因此意境是中華民族藝術(shù)獨秀于其他民族藝術(shù)之林的“重要標(biāo)志”,意境作為一種審美崇尚己經(jīng)深深地積淀于中華民族的藝術(shù)文化心理中,并已成為一種評價標(biāo)準(zhǔn)。劉綱紀認為意境在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里占據(jù)“中心位置”。孫學(xué)軍等人認為意境與中華民族思維方式密切相關(guān),意境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藝術(shù)精神的獨特追求,強調(diào)中國特色文藝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gòu)須以意境美學(xué)范疇的建設(shè)為基礎(chǔ)。⑧自20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不斷的受到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沖擊,并在“西學(xué)東漸”的強勢文化傳播下,中國文化主動吸收西方文化的態(tài)勢也日趨明顯。當(dāng)然,隨著與西方文化交流的越來越頻繁與密切,科技文化與藝術(shù)也隨之進步與繁榮,但筆者認為如何發(fā)揮中國藝術(shù)的重要性,保持好中國藝術(shù)的民族性與獨特性并發(fā)揮在世界藝術(shù)中的引領(lǐng)作用是當(dāng)下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所以,我國成立藝術(shù)學(xué)這門學(xué)科是十分必要的,從藝術(shù)學(xué)的角度建構(gòu)中國藝術(shù)意境說,以此來確立中國的藝術(shù)話語體系更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只有藝術(shù)學(xué)這門學(xué)科才能從宏觀的角度去把握和研究我國各藝術(shù)門類,才能統(tǒng)領(lǐng)藝術(shù)的整體發(fā)展方向并肩負起民族藝術(shù)復(fù)興的重任。意境論本是我國文學(xué)的一個研究范疇。近年來,意境論也開始涉及到我國各藝術(shù)門類領(lǐng)域。所以,從藝術(shù)學(xué)的角度去探究中國藝術(shù)中的“意境”并嘗試用意境論來打通各藝術(shù)門類之間的關(guān)系,在中國藝術(shù)史論研究領(lǐng)域具有重要意義。這也為中國藝術(shù)保持民族性與爭取在世界藝術(shù)中的話語權(quán)打下了夯實的基礎(chǔ)。
作者:徐子涵單位:東南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
擴展閱讀
- 1古代文化古代美學(xué)
- 2古代習(xí)俗的演變
- 3古代禮儀形式
- 4古代詩歌修辭
- 5古代中國判例法
- 6中國古代旅游
- 7高考古代詩歌
- 8古代小說話本
- 9古代皇后婚檢致辭
- 10古代城市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