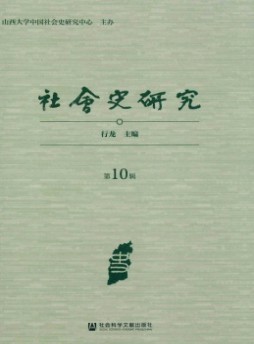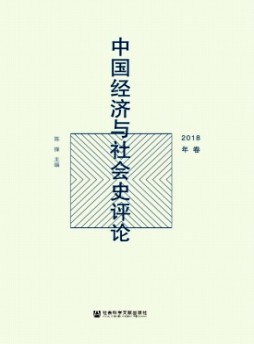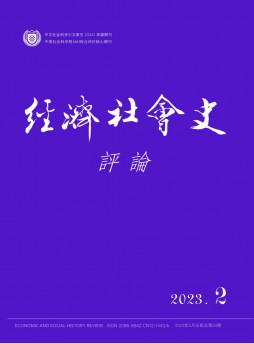社會史與概念史的哲學討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史與概念史的哲學討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盧梭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生而自由的人之“生”,可以做兩方面的解釋。一是從自然中走出的人,即從人類起源的角度上談人的“出生”狀態;二是就個體生命而言,未經現代文明“污染”的孩童,才是盧梭眼中自由之人“生”。“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的判斷,把文明和文化當做束縛自由的枷鎖,無論是人類還是生命個體,都是在自由的生命的起點上,逐步套上自己定制的枷鎖,并且由此展開生而自由的人因不自由而渴望自由的全部旅程。盡管盧梭對現代文明的“枷鎖”做了大量的分析,并且在這些分析中對這些束縛自由的枷鎖鞭撻討伐,但是和其他啟蒙主義思想家一樣,盧梭本人絕不是反對人類進步,更不是反人類的。他并沒有把文明理解為全部社會罪惡的淵藪,相反,他所推崇的“自然”,恰恰是在自由基礎上容納著人類進步全部內容的真正文明。如果把盧梭的判斷當做一個“問題”的話,那么,這個判斷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人,是如何“生而自由”的?人,能否走出“無往而不在的”“枷鎖”,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兩個問題引發出本文的主題。以自由存在形態之反映的自由社會史,以及以對自由社會史之反思、批判、領悟為內容的自由概念史,就是人類關于自由的全部歷史。而這一歷史的展開,無疑是在現代社會中,體貼和領悟自由的基本方式。當我們在兩個歷史參照系中品味人類自由之里程時,社會史與概念史的敘事方法,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手段”問題,它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問題。
一、社會史中的客觀性與解釋原則
人類社會總是以文化的形式譜寫自己的文明歷史。在歷史中呈現的文化,可以表現為未必言說、任由歲月侵蝕,但卻以自身的存在而彰顯歷史的“器物”,也可以表現為貌似可以任意言說、但實際上一定有著內在規定的“觀念”。器物文化與觀念文化交織出的歷史,構成人類歷史的基本表現方式,也由此成為走出歷史、并且仍然以各種方式創造歷史的現代人的寶貴財富。現代人之所以為現代人,不是因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如何“現代”,而是因為身處現代的人,擁有歷史。作為觀念史的表達方式,社會史和概念史是任何一種關涉到歷史的理論的基本研究路徑或方法。前者指“歷史表述史”,后者指“歷史反思史”。在研究實踐中,這兩種研究路徑互相闡發并相互參照,瑞因哈特•考斯萊克認為,社會史表現為“在將人類生活的所有‘歷史表述’還原為‘社會狀況’的同時,也由‘社會狀況’引出‘歷史表述’”;概念史表現為“把‘社會史’特別是‘政制史’的分析與‘概念史’的問題結合起來。”①顯然,社會史是關于“存在”的歷史,它更加傾向于歷史的真實表達,因此它以還原歷史的方式表述歷史,并且由此構成歷史學的基本方法。但是,社會史畢竟不是自然史,它的存在是以歷史中的人以及人和人之間的事情為核心的。確切說來,是以過去的人和過去的事情為歷史描述對象的。那么,如何還原歷史的真實性,以哪種方式才能夠獲得歷史的真實性,就不再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了。比如,歷史“表述”的方法問題上,就存在著“言談”和“書寫”真實性問題的爭執。傳統理論中,“眼見為實”的生理習性使我們更加相信感官所獲得的直接信息,因而也就相信與感官同一維度上的“言談”。我們相信第一次實現直立行走的猿是人類擺脫必然從而獲得自由的開端,我們相信文藝復興運動是近代社會擺脫神的桎梏爭取人的自由的努力,我們相信攻打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中為自由而戰的悲壯努力,我們也相信,歷史上的馬克思曾以一部“工人階級的圣經”引發了自由發展史的空前革命。
我們之所以“相信”,是因為我們認定,在人類歷史上,不僅有著自由的渴望,更有著自由的奮爭。由奮爭所譜寫的歷史是有據可查的,是一種可以歸結為“言談”的科學———任何科學,直面的都是經驗。以“經驗”為“實”的認識原則是亞里斯多德伊始的西方經驗哲學所固守的基本原則。近代社會的科技革命、工業化大生產以及包括宗教改革在內的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輝煌成就,進一步固化了由培根、伽利略、牛頓及洛克等堅持的經驗主張在現代化社會中的地位。但是,這種以求實為特征的基本原則,即便是在傳統哲學中也同樣屢遭詬病。和科學不同,歷史中的“事”必須通過“說”的手段才能展現出來,如何“敘事”的問題,不能仰仗著感官通道所獲得的感覺或印象。所謂的間接經驗,已經是被人們言說過的經驗,因此不再是經驗了。現代哲學對科學的重新理解,也在這個層面上給出了人類認識的非科學通道。德里達站在后現代的立場上,對“言談”和“書寫”兩種表達“真實”的方法進行了分析。按照他的理論,傳統哲學和人類歷史中所看重的“言談”方式,不具有、也不應該具有以“更加真實”的身份統攝書寫歷史的權力。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書寫”的真實性分量更重,在解構主義看來,“言談”與“書寫”的任何偏重,都可能導致形而上學的二元對峙和主客二分,其結果必然是邏輯帝國的形成。于是,歷史的真正意義,不在于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而在于以何種方式“解構”出來。德里達的解構是歷史的現代解構。它不僅包含著歷史中器物文化的解構,也包含著歷史中觀念文化的解構。于是,歷史的“表達”與關于“表達歷史”的解構,同樣成為現代哲學的重要課題。無論怎樣,解構主義關于“言談”和“書寫”關系的探究,再次觸及到歷史的“表達”問題。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基本途徑,社會史不可能離開觀念的表達。在這種表達中,社會史力求以“客觀性”的筆觸完成對社會或歷史的描畫。
問題在于,應該如何界定這種客觀性呢?社會史中的客觀性,絕不是歷史中所有客觀存在的泛泛例舉,更不是社會中種種瑣事的簡單鋪敘,否則,就不會有黑格爾所強調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了。歷史與邏輯之統一中所強調的“邏輯”環節,鋪墊了社會史所選擇的范圍及其意義。因此,這里的“客觀性”,不再是拘泥于歷史中所有存在的客觀性,而是一種具有標志性的存在,即形成此種歷史的那個時代的一種標志。由此而構成的歷史客觀性,被稱之為“時代的客觀性”。換句話說,只有那些能夠展現歷史的時代性的東西,才能納入社會史的眼簾,并且能夠在社會史的“求真”過程中,解釋其客觀性問題。比如,在“自由”的社會史中,我們之所以選取了直立行走、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等等,是因為這些“事實”標志著人和自然關系的處理、人和神的關系處理、以及人和人關系的處理過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時代,完成了自由的一個段落,因而也就構成了客觀譜序自由社會史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這樣,在這種客觀性的解釋中,就已經暗含著一個基本內容,我們是根據什么來確定時代的標志性問題,并由此而把此問題納入社會史的樂章之中?哲學把構成社會史樂章的主旋律,稱之為“解釋原則”。社會史的解釋原則,不是歷史中普通存在的客觀性原則,而是某個歷史階段人類所形成的共識的客觀性原則。某個歷史時期共時性的客觀存在,是人類精神發育與發展的標度,是人類認識水平與實踐水平的標志,也是歷史承接與延續、并且在承接和延續中顯現歷史階段性的關鍵環節。
能夠構成時代共識的尺度,即時代的解釋原則。海德格爾說,存在是向“此在”敞開的狀態,作為此在的“人”,以哪種方式表達“在者”的“在世之在”,那么“存在”就以哪種方式規定并顯現你的存在。我們的存在是既定的和無法改變的,但世界如何展開,卻依賴我們的時代性的共識。金錢拜物教成為基本共識時,世界以經濟方式向我們展開;官本位成為基本共識時,世界以制度腐敗形式向我們展開。這樣,社會史所追求的客觀性問題,便以時代性的共識性解釋原則表現出來。當一個時代認可了某種解釋原則,意味著這個時代已經以時代性的共識為自身打下了歷史性的標志。那么,社會史以此為前提,論證此種解釋原則所能包容的社會之全部,就不過是一項技術工作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時代的社會史或問題史,所形成的應該是在時代性解釋原則基礎上以概念形式表現出來的“觀念史”。在這里,概念不過是“觀念”的表達方式,而“觀念”所反映的,則一定是共識基礎上的解釋原則。比如,工業革命,宗教改革,契約精神,是以概念的形式表達了近代西方社會整體進步的觀念,而這一觀念,是建立在“社會進步”這一共識原則基礎上的。社會史要尋求的,首先是構成觀念的共識“是什么”,其次才是在這種共識原則下對歷史中的社會的解釋或描述。當我們找到了一個時代的共識性解釋原則之后,就意味著我們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上”去看待歷史的存在和歷史中生發的問題,這就是社會史的客觀性所指。當整個近代社會都把自由理解為“擺脫束縛”的時候,那么,認識束縛自身的枷鎖,就是理解自由的前提,而如何從束縛中解脫出來,就成為爭取自由的社會活動。康德在《什么是啟蒙?》中關于啟蒙的經典解釋,是對自由認識的時代性標度,而500年來西方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調節處理和構建,就是在這樣一些理解中,逐步走向人們所期待著的自由的存在史。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結論,以客觀性追求為目的的社會史,在“表達”歷史內容時,任何一種形式的“求真”,都以客觀性的解釋原則為前提,而這種解釋原則,又來自一個稱之為時代的人類或人類群體的共識。然而,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可能化為歷史的永恒,歷史不可能永久地駐足于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段。當一個時代以結束自身的方式開啟另一個時代時,該時代所謂共識性的解釋原則,便會被新的時解為一種“合法性的偏見”。于是,討論、質疑、反思、批判這種時代性的共識,就成為思想由“現存”設法移居為“現實”的一種努力。這種思想的努力,構成概念史的基本篇章。
二、概念史的邏輯主張與普遍性追求
由概念構筑的歷史和社會史一樣,也一定是思想的產物。從形態上看,概念總是以“反思”的方式力求將觀念提純,并且在這種提純過程中,形成可以獨立于直觀的經驗世界之外的理論形態。正是這種獨立性的求索,使不同時代關于某種思想所形成的概念,按照某種理論的要求鏈接起來,形成概念自身的歷史。同樣是一種歷史,同樣是關于歷史的觀念性表述,社會史和概念史當然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概念史有著自身形成的歷史,有著在自身歷史中所形成的有別于社會史的鮮明特點。首先,概念史中的概念,不再是觀念的表達形式,而是任何一種觀念得以建樹的根基。我們知道,文明的發育仰仗著思維能力的提升,由“抽象”而形成的概念,曾力求將概念所要反映的內容進行一般性的整理,因此,概念以“一般”的特征作為思想形成和思想交流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種觀念,都首先仰仗著概念作為基本單位,并以概念的形式完成觀念的鋪敘。在這種鋪敘中,觀念將遵循概念的邏輯完成自身的整體性構建,由此,能夠解釋歷史的觀念,不再是單擺浮擱的概念,而是一個能夠具有概念史意義上的概念集合,一個能夠為觀念的解釋獲得支撐的概念體系。其次,概念史中把概念當做對象時,它所涉及到的概念不再是某種解釋原則下對事實的表述工具,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解釋原則。關于世界的說明或解釋,來自于概念本身,而不是解釋原則下的概念。顯然,構成解釋原則的概念,不僅僅是具象事實抽象的結果,它的形成,經歷了“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和“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②的基本路徑。
由此而構成的概念,是一個理性的綜合,它不僅以概念之間的邏輯鏈接著彼此的關系并由此形成概念的歷史,并且在這種鏈接中不斷以反思和批判的手段審視著“鏈接”的合理性問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概念的歷史有可能區別于歷史中的其他,獨立為人類可以作為一個“對象”來加以把握的歷史性存在。概念與經驗事實的觀照,是概念史要解決的第一要務:它必須要在概念的主觀載體中映照出客觀性的特質,從而解釋和解決經驗世界所遇到的一切問題。在概念史中,這個問題被理解為對“普遍性”的追求問題。傳統哲學中,如何獲得最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是其建構概念史的最為關鍵的邏輯步驟。蘇格拉底、柏拉圖在西方哲學挺立兩千年的理由,就是由于他們所設定的理念世界,能夠以“本體”的形態實現概念最大普遍性的欲求,并且由此而解決概念自身的客觀性問題。康德利用先驗范疇的合理性演繹所完成的“立法”過程,也是通過將知性的普遍性訴諸于先驗的手段,實現了有限認知領域中的客觀性、普遍性及其必然性問題的解決。而不滿足于知性思維方式的黑格爾,則用自身所搭建的辯證思維方式,將古希臘哲學中的理念世界擴展為絕對精神的世界,并在絕對精神的邏輯力量支撐下,完成了傳統哲學歷史上最為完美的概念史演繹。第三,從功能的角度上看,概念史和社會史也有很大區別。社會史以“表述歷史”為基本功能,因此它對歷史的表述,一定會在確立相應的社會史解釋原則的前提下得以成立。而這個解釋原則,來自于被解釋的歷史中的“共識”,因此,社會史一般以觀念形態的靜態表述作為表達歷史的基本方法。換句話說,社會史是一種靜態觀察,靜態描述的過程,它的理論也是在相對穩定的歷史階段性中構造出來的。黑格爾認定“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時才飛出樹林”,十分準確地描述了社會史的這一“歷史之后述說歷史”的特征。概念史則不然,構成概念史的概念,不僅僅要觀照歷史,而且更要觀照現實和未來。因此,在時間上,它不以過去所發生的歷史為唯一的解釋內容和參照,也不以現實所生發的一切存在為唯一平臺。恰恰是在歷史接續現實、現實走向未來的重要環節中,構造出能夠作為解釋原則的基本概念,從而構造出概念史中一個個理論環節。也就是說,概念史是思想變動中概念的生發過程,這些概念對其內容的彰顯,不是靜態的說明,而是動態的、批判性的超越。而由這些概念鏈接起來的歷史,有著可以獨立于內容的自身邏輯。傳統哲學中,無論是康德的先驗邏輯還是黑格爾的辯證邏輯,都是服務于概念史的基本邏輯的。從方法上說,社會史是一種分析的結果,即以已經形成的某種歷史為對象,分解之后形成觀念的歷史,概念史則是綜合的結果,即在一個確定的或不確定的邏輯路向上祭起批判之大旗,以思想的邏輯批判思想的觀念。
社會史立足于某個解釋原則之普遍認定的求解和應用,它往往以某個歷史時段解釋原則的形成,以及這些解釋原則如何獲得共識性作為理論前提。對于社會史來說,存在的合法性是第一位的,它要表述的,就是歷史中合法的、因而是現實的存在。概念史則立足于自身邏輯的演繹,它不僅要考慮構成解釋原則的概念能否解釋歷史或現實的存在,更要追求自身的合理性問題。因此,社會史對社會的種種形態和現象的認定,是以其合法性的追溯為核心,而概念史在概念的理性演繹中,則以合理性的求證為核心。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社會史強調的是解釋原則的共識和認同,而概念史則以社會史的解釋原則之反思和批判、以社會史的存在之討伐為內容。概念史最為輝煌的成就,莫過于近代社會伊始的理性主義所構造的邏輯大廈。當笛卡爾以“我在懷疑”的手段展開理性自身的審視后,由“清楚明白”而確定的“我在”,就以主體的身份成為一個認識論中的理性原點。“清楚”的含義首先要排除任何經驗性的東西,因為任何經驗都會由于被遮蔽而不能被理性直觀;“明白”則是理性邏輯的要求,任何“清楚”的直觀對象,都應該在邏輯的引領下與經驗世界對接。顯然,在這個原點上,無論是天賦觀念還是單子或實體,都以“普遍性”的認定完成了哲學認識論轉向之后關于主體的自信。近代社會關于理性的“神話”確立了人追求理性的崇高,關于科學的“神話”堅定了人認識自然的執拗,而關于人類解放的種種“學說”,又在人的世界里譜敘和構造了一個又一個理想世界。人類關于自由的歷史,就在理性之普遍性的旗幟下,以獨特的邏輯主張譜寫了概念史中自由篇章的全部內容。
近代社會關于理性的濫觴一方面以普遍性的堅守捍衛了概念史的邏輯至上,但另一方面,又在啟蒙運動的反思過程中,對理性的普遍原則,以及由此而構筑的概念史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比如,在康德看來,啟蒙運動關注的應當是人的理性脫離了自然狀態進入文明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權利的問題。為啟蒙運動所熱衷的理性之光,如何能普照人類文明的角角落落,并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永恒的普適性原則?人類“不成熟狀態”的擺脫,是自由的理性限定還是自由的信仰訴求?啟蒙運動的口號是“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③那么怎樣才能在理智的運用中擺脫對理性自由的種種限制,從而可以“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④呢?康德時代的啟蒙運動,已經在激情甚至狂熱的理性崇拜中開始了對自身的反思:休謨關于理性普遍性的懷疑使得理性有限性問題暴露于陽光之下;盧梭對自由與必然關系的另類解說,又在對人類罪惡歷史的解剖中,為似乎已經是晴空萬里的傳統意義世界理論帶來了一片烏云。從解構主義的立場上看,休謨與盧梭在他們的問題和思想中,實際上已經消解了人類仰仗理性信念建構起來的意義世界。嚴格說來,啟蒙運動之后擺脫理性權威的吶喊,不是要在人的活動中尋找并回歸某種不變的終極本質,而是要改變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只有站在這個角度上,才能充分理解作為社會史中“事件”和作為概念史中“意義”的啟蒙運動。人類的歷史,既不是社會存在史的簡單鋪敘,也不是概念邏輯的理性演繹。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一個現實的層面上,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
三、“世界觀”旗幟下的社會史與概念史
無論是“表述”一個社會的社會史,還是“反思”一個社會的概念史,都有著各自的歷史成因,因而也有著各自的不同。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駐足于一個時代的概念史,就是這個時代的思想驛站,因而往往重合于這個時代的社會史。換句話說,任何一種歷史的表述或演繹,都是以“在場”的現實為平臺來表達“不在場”的歷史,那么,如何實現“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統一,就是社會史與概念史紛爭乃至各自努力的方向。不得不以存在的歷史證明概念的合法性,或不得不以邏輯的形式證明存在的合理性,不僅成為概念史或社會史擺脫不了的夢魘,而且也往往成為滋生的基本土壤。恩格斯甚至由此給出一個頗有爭議的論斷:“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⑤思存關系的角逐,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社會史與概念史各自的偏執及其局限。黑格爾之后的哲學逐漸意識到,“自由”不能是自由存在歷史白描基礎上的渴望,也不能是自由概念歷史演繹中所寄托的激情,自由和自由的爭取,應該是同一個問題。因此,社會史與概念史中的自由問題,必須在一個有別于傳統哲學的新世界觀創立中重新認定。當馬克思認定以往的“哲學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⑥,并以此為根基創建改變世界的哲學時,“觀世界”的哲學理論變成“世界觀”的理論,世界,不再是僅供“解釋”的世界,而是可以“改變”的世界。
世界觀旗幟引領下,社會史與概念史有了走出舊有局限、重新審視自身并開辟全新領域的可能。在這種世界觀中,時間的一維性不再是歷史展開的唯一依托,因而歷史不再是一個簡單存在的所謂客觀史;同樣,理性邏輯的自洽性不是概念鋪敘演繹的唯一法則,因此概念體系的完滿,不意味著歷史及其指向的完美。人類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容納著未來、以有別于理性邏輯的實踐邏輯構造出來并且努力展現未來的實踐史。這意味著,求真求實的社會史之客觀性依據,不過是科學體系真實所求之憑據在歷史領域的再現,而科學是回答不了自身何以客觀的問題的。同樣,以規律或目的為歸宿的理性之普遍性推演形成的概念史,同樣無法解釋動變之歷史何以有不變之初衷的終極問題。馬克思“改變世界”的視角,實際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歷史視域,這種歷史視域的構建消解了形而上學的舊有旨趣,并以“世界觀”的形式締結了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在場性與不在場性問題的因緣。包含“天才世界觀萌芽”的《提綱》關于以往“哲學家”性質的判斷,絕不是虛無主義或獨斷主義的產物。在馬克思眼中,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的傳統哲學,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放棄了“改變世界”的要求。以自由問題為例,在任何一位哲學家的理論中,無論是社會史中關于自由的理論再現,還是概念史中關于自由的理性渴望,都從來沒有放棄過關于自由的爭取。以笛卡爾和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西方歷史,不僅僅是自由探究的歷史,而且也是自由爭取的歷史。這種自由開辟了人與自然、人與上帝、人與人關系解釋的新路徑,也在主體的設置、人性的恢復、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人權問題上,譜寫了輝煌的樂章,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啟蒙運動的興起。
馬克思認定這些哲學家們不過是在“解釋世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們對世界的“改變”,永遠閾限于對世界的“解釋”之中。無論是理性的訴求還是現實欲求的伸張,社會史的解說與概念史的演繹,都以理論自身合理性的論證為基本原則。綜觀近代哲學的自由訴求理論,有著如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等以契約論求得自由的主張,也有著如康德、黑格爾終極意義上的自由理論。前者毫無例外的以某種“原初社會自然狀態”的理論假設為前提,后者又都以理論的自洽作為合理性的基本依據。在這樣一些理論中,自由不過是來自歷史或理性本身的延續,而不是人類現實活動爭取的結果。由此而構造出的改變世界之舉措,也曾有過鞭撻現實世界黑暗的言論,卻無法找到現實世界黑暗之源頭;也曾對未來社會給予無限憧憬,但卻無法找到由現實世界通向未來世界的實踐途徑。因此,在解釋世界的框架下所從事的改變世界的行為,無法越過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溝壑,對于世界的局部性改變,不過是調整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上帝的某種關系,它不能保證在新的關系中確立自由的永恒天地,更不能保證新的關系中根除不自由、不平等、不博愛的根由。在這樣一種理論中,康德所希翼的永久和平,只能化為永久的期待。同樣,把新哲學的旨趣聚焦于“改變世界”的馬克思,也從來沒有放棄解釋世界的理論要求。在馬克思的全部理論中,從來沒有放棄理論解釋世界的功能。而這個思想,來自于馬克思關于人及其人之自由的認定。
《巴黎手稿》中的馬克思曾經憧憬著“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組織,其中“自由人”的概念卻仍然保留著由異化而異化復歸的精神演繹痕跡。“萊茵報”及其“德法年鑒”時期的生活踐履,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由質疑到批判的出發點,而二者分界的地方,恰為對現實世界的解釋方式和改造方式之不同。在馬克思看來,關于解釋世界的美好和證明不是來源于理論自身的邏輯,而是要來源現實世界自身的邏輯,所以馬克思解釋世界的邏輯,只能產生于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之中。恰恰是在確立改變世界的理論宗旨基礎上,才有了在對私有制的現實批判基礎上完成的關于人的本質的現實性規定,而自由的問題,也在馬克思的這種規定中,擺脫了社會史與概念史的對峙關系,在人類的物質性實踐活動中得到充分說明。《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來說,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⑦在這個判斷中,馬克思一反傳統哲學的邏輯路向,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彼岸世界的理論懸置,任何以“非現實性人”為基礎的關于人的抽象規定,都無法真正解釋人和人的所謂本質問題。傳統哲學在2000多年歷史中憑借著邏輯的力量而抽象出來的各種“本質”,構造了關于人之本質的概念史的重要內容,而這些停留在概念上的本質,只能把人理解為一個不具有感性存在意義的純粹理性存在。在這個基礎上關于人和人的活動的所有解釋,只能淪為“醉醺醺思辨”中的空洞概念。離開現實世界去構筑關于現實世界的完滿體系,用解釋世界的框架來推演和判定現實世界的合理性,不可能說明人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
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只能在現實性的基礎上才能加以認定的理論,已經消解了概念史所奉行的理性邏輯之神圣性。當馬克思把人理解為感性存在時,同樣拒絕了以日常生活簡單活動的白描作為本質規定的社會史習俗。在批判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基礎上,馬克思把人的本質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它表明了人的本質不是單一的、不變的,而是在包含著物質關系與思想關系在內的社會關系的制約中形成,并隨著社會關系的改變而改變的。人的思想關系、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等內容,都是“存在著的”現實關系,哲學的任務既不是要撇開這些關系去追求純粹的存在,也不是要把這些關系做簡單的社會史般的白描,而是要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手段,在力圖改變世界的基礎上解釋人的現實本質的決定性因素。馬克思的結論是,在現實社會的各種復雜關系中,真正能夠決定人的現實本質的,是經濟關系。于是,關于現實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成為馬克思“解釋世界”理論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既然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由人的活動所構成的社會關系又是不斷變化的,那么,傳統哲學中,以人的本質之確定性和不變性為前提的種種“本質前定論”或“本質終定論”,就不過是借助形而上學思維習性描述出來的無法實現的主觀愿望而已。《資本論》中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運行規律的分析中,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得到完整的闡釋。譬如,剩余價值理論不僅揭示了現實社會苦難的淵藪,而且認定世界歷史狀態下私有經濟的蔓延,一定會使人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浸淫出越來越多的自私和貪婪。在這樣一個僅靠物質欲望支撐的社會中,任何道德說教和宗教的信仰,都無法掩飾和改變社會關系的邪惡,由此而塑造出的不自由的人性,也不可能在任何一種單純的理性批判中得以改善。這一切說明,實現社會革命,改變并創造新型社會關系,才是創造以自由為本質的人的唯一手段,而在自由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群體,才是被稱之為“共產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
縱觀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理論我們會發現,作為一種理論,馬克思當然是在用概念去述說和解釋歷史,但是這種概念不是邏輯上的定義或演繹,事實上,馬克思從未為任何一個概念做過邏輯學意義上的嚴格定義,這些概念不是來自簡單的邏輯抽象,而是來自改變世界的現實需要。在這樣一種需要下,不在場的歷史不是“過去了”的“史實”,而是一個完全可以服務并解釋現實的在場行為。同樣,包括自由人聯合體在內的社會圖景,也不是僅僅以未來形式召喚現實的一種理想,而是一個孕育在改變世界之中并且化為改變世界行為的在場性現實運動。恩格斯把馬克思的哲學稱之為“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僅僅是改變了我們觀世界的結論或方法,更重要的是讓本來就置身于世界中的我們,在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完成了解釋世界的任務。世界觀旗幟下展開的社會史與概念史所孕育的問題,涵蓋著人類精神最為執著的追求;能夠以哲學的形式產生全新世界觀的時代,是一個能夠喚醒思想變革的偉大時代。與人類文明共生的自由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它涵蓋了人類所關注的所有問題的基本旨趣;以自由為主題的世界觀所創造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它刻畫了人類歷史的每一次發展與進步,并以未來撲向現實的視域開辟,完成了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對接。因此,無論是自由的社會史之表述,還是自由的概念史衍生,都將在世界觀的旗幟下開墾出屬于人類的自由之路,并且在人類自由之旅的行進中,朝向自由本身。
作者:侯小豐 單位:遼寧省社會科學院
- 上一篇:高中生的音樂鑒賞能力培養范文
- 下一篇:哲學的基本問題與根本轉向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