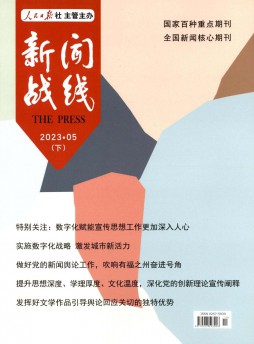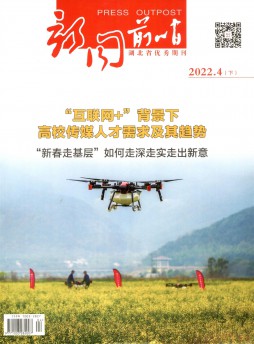“新聞執政”基本理念和實踐路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聞執政”基本理念和實踐路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西北大學學報》2015年第四期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從幼年走向壯年,其間新聞宣傳是活躍而強大的顯性力量,在國內樹立了公信力,同時形象也為全世界感知和理解。黨關于新聞宣傳的若干基本原則在此得以確定,于是延安時期也成為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時期。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技術條件下,靠著一系列政治觀點議題傳播的廣泛性和穩定性,靠著符合著傳播規律的傳播,使得黨在延安時期全面的執政能力中,關于“新聞執政”理念和實現路徑顯得清晰而樸素。“新聞執政”似乎是一個新興名詞,但在黨長期的新聞實踐中一直運用著。執政的理念,“是指執政主體對其執政活動的理性認識和價值取向,是產生執政綱領、主張、方略、政策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礎,是執政活動的理論指導和執政能力的思想基礎”。于是筆者認為新聞執政理念,實質上就是黨和政府對新聞宣傳原則和原理的認知,也代表著一種相對穩定的新聞宣傳總體價值觀取向。當然除理念之外,實現和印證理念的延安時期新聞實踐的特征,以及在當時各種新聞文本中體現出的風格也是重要的方面。
一、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的事實原則與人民利益
黨的新聞執政理念集中體現和反映著執政黨的價值取向和目標訴求。延安時期關于新聞宣傳最基本的原則和目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真實,符合客觀事實規律;二是強調為了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在戰爭環境中總結新聞宣傳的基本規律的。強調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和其他黨派的宣傳鼓動有基本的原則性區別,具體體現的第一條,便是“我黨所宣傳的理論、綱領、政策等,是符合于客觀真理的,符合于客觀發展的規律的”[2](P103)。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原則,就是說實話,“只有大喊大叫地去宣傳實話”,“在那里面才存在著和生長著我們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①。在延安的這一段時間里,曾經有過新聞虛假和失實,《解放日報》社論認為這是主觀主義作風,要“作堅決的斗爭”;也有過夸大,《解放日報》有論點鮮明的社論《新聞必須完全真實》,直到1943年,陸定一在《我們關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中,確定了“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而“事實是第一性的”,“新聞報道是第二性的”的基本原則,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也成為中國新聞學的基本理念。接下來的1944年,《新華總社關于通訊社工作致各地分社與黨委電》中對分社希望的第一條便是:“新聞的真實性關系黨的宣傳工作的信用,應引起最大的注意,在新聞宣傳上,我們同樣應有實事求是的態度,無論是發揚成績或是檢討錯誤,都應老老實實講求分寸,不應夸大吹噓。解釋為什么做的理由時,對外,是“要知我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愈高,各方對我們所發消息的注意愈切”;對內,是“對中央供給不準確的材料,將使上級難以正確了解情況,如根據此指導工作,勢必招致錯誤”。從中可以看出,其實新聞真實已經不僅僅限于新聞宣傳報道,更成了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對自己形象和信譽自覺維護和傳播的價值觀取向的第一標準。選擇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最簡潔、最核心和最基本的執政起點和理念,則是延安時期一直強調和不斷明晰的。1944年9月8日,在悼念張思德會上發表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使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明確闡述了為人民服務的內涵,“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會議的政治報告中,系統闡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在這次黨的代表大會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首次被提到了“黨的唯一宗旨”并被寫進黨章。從此,這一政治準則或曰執政理念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出發點和目標所在,也自然成為新聞宣傳的目標與使命。延安時期,哪怕是類如當下的“負面輿情”。主席曾因一位農民的“怨言”引起重視,立即派人深入調研并調整相關政策②。直到1945年,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三提此事,特別強調和提醒黨的政策必須以人民的滿意作為依據。當時在延安,邊區經濟發展是個重要而迫切的任務,一系列發展措施如實行減租減息、開墾荒地、組織勞動互助、發展工商業等實施,到堅持“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組織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精兵簡政”,都是基于“為人民”的目的,而這些理論、政策、措施等廣泛且長時間地通過報紙、電臺、各種鄉村小報告知、溝通,對邊區干部百姓增強積極性和凝聚力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成為黨“執政為民”理論的先期實踐和新聞報道的總體準則。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塑造、建設、維護、傳播,最主要的理念保障就是為人民服務,最基本的前提便是強調客觀原則,尊重事實。延安時期理論和實踐都在證明,延安時期的新聞立場就是人民的立場,黨的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人民。
二、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的文風改進
黨在延安時期執政過程中如何保持政治性議題廣泛性和穩定性幾乎是一個奧秘,在探秘的過程中,文風培育和自覺改進是一個有價值的觀察點。聯系延安時期這一特殊的時代背景,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還未實現真正的新聞事業大眾化,共產黨執政的方針政策等一系列政治議題不可能主動進入社會底層民眾的活動區域,特別是在地理位置偏僻,經濟和文化水平都非常落后的陜甘寧地區。從傳播需要的物質條件而言,這樣一種社會現實下,政治議題似乎并不能夠廣泛、持久、有效地傳播,然而黨最終將穩定的執政議題和革命方針傳達給邊區民眾,使之成為喚醒民眾國家、民族意識的重要精神武器。斯諾在去延安之前,聽到的傳說中的延安所謂“紅色中國”是“更大的謎”和“更混亂的傳說”;所謂“紅軍”,只不過是“幾千名饑餓的土匪”,南京方面的解釋,“紅軍”是“文匪領導下的新式流寇”,是“共產”“共妻”,斯諾列舉了70個問題決定了他的“延安之路”,從中我們可以推斷當時延安鏡像的“妖魔化”程度。這其中文風似是一個表征,但其實無論是當時落實執政理念、工作作風或傳播效果,還是現今判斷其延安的新聞宣傳是否暗合傳播理論和規律,文風都是關鍵性因子。延安時期需要團結聯合、組織動員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行動起來,爭取自身解放。于是黨延安初期關于宣傳方式與方法上的第一要求便是:“一切的宣傳必須普遍深入、通俗簡明,改正過去一些高談闊論使人厭煩的宣傳。”
延安時期的一向重視文風建設,他所倡導的運動整頓的“三風”之一就包括“文風”,他的文風和對文風的獨特見解極大推動了延安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深入人心,這集中體現在反對黨八股和力倡并且身體力行生動活潑的新聞文風上。批評空話連篇的長文章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倡導“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延安時期寫消息、寫評論、寫發刊詞、寫按語、寫征稿信、寫研究報告,留下眾多名言佳話①。他借批評說明了什么是所需的文風,并且提出,“洋八股必須廢除,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延安時期鄉村治理的三大渠道是報紙、識字組、黑板報。1943年5月19日的《解放日報》上,刊登了一則來自綏德縣延家川二鄉張家村“村民公約”②借助鮮活的語言進入鄉村,有了讀得懂記得住的全新的公約和生活制度,生產、支前、讀報、識字、衛生等行動便成為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延安時期留下了許多約定俗成的話語,有“小米加步槍”和“飛機加大炮”的比喻,有“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豪邁。初到延安的幾年,延安經濟困難,描述:“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這嚴峻的現實還有什么更好的表述么?自然地,在1939年,“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邊區大生產運動蓬蓬勃勃開展。自然地,斯諾的紅色中國印象也得到了徹底的刷新。習在2010年號召革新官話和文風體系時提倡黨員領導干部要力戒長空假,力求短實新,他總結道:“我們黨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特別是以來,一直為培育和弘揚馬克思主義文風而努力。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整頓文風”。“同志筆下的愚公、白求恩、張思德,我們今天記憶猶新,就是因為這些人在他的心靈深處產生過激烈震蕩,所以講出的話飽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鳴”,這也就闡明了黨在延安時期官方話語和文風的創新意義。
三、延安時期新聞宣傳的動員引領
重新回顧延安時期的新聞媒體角色定位,在于其雖居喉舌和工具地位,卻能夠藝術地保持與黨的決策目標一致而表現出的同向平行關系。新聞宣傳是延安時期黨中央聯系群眾的紐帶,黨運用新聞宣傳報道與人民溝通、互動,進而動員引領,“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黨報就是黨的教科書”[4]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突發事件最能集中體現當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應急處置能力,尤其是事件傳播中與各方的溝通對話,以及在失速情勢下的輿論引領能力。延安時期,有一例典型的“媒介事件”便是“黃克功案件”①。這一案件的關鍵的環節在于,借給當時審理此案的審判長雷經天同志信件,闡述和解釋了中央的處理決定,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這封信即時公開發表,國內外對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坦率和近乎赤裸的信息公開回應大為震驚。之后又化危為機,引領輿論,在抗大作了一場“革命與戀愛”的講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戀愛時應遵循的“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和學習的原則、自愿的原則。后來李公樸先生也稱贊其為“為將來的共和國樹立了很好的法律榜樣”。黃克功事件的新聞傳播中,處置決定和處置的過程,對決定的解讀和決策的過程,都借助當時并不發達的多種傳播渠道廣為傳播。中,《解放日報》改版社論《致讀者》提出了黨報基本的采訪方法規定,注重調查研究,崇尚實事求是,提倡新聞工作者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同時,還要求新聞工作者注意自覺地深入群眾,虛心地向群眾學習。1942年3月18日,他為《解放日報》寫了“深入群眾,不尚空談”的題詞,鼓勵解放區新聞工作者深入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延安時期,黨運用所掌握的傳播工具有效有力展現出自己的媒介形象,獲得了理解與支持,更凝聚起不可戰勝的民族力量。
四、結語
延安時期的新聞傳播,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進行中國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媒介記憶,而且也成為新中國建立后新聞出版管理體制的源泉和標桿。延安時期的新聞傳播體系具有思想宣傳與信息傳播同構并體、組織傳播與大眾傳播同形合一等特點,其中一些經驗對當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仍具有全面指導效能。當然,本文的一個認識起點,便是基于現今對黨在過去的新聞宣傳歷史中形成的某些好傳統、好經驗,存在著淡忘甚至丟棄的問題。無論是在歷史和現實背景中評判,延安時期具有魅力和活力的新聞宣傳以至于從中體現出的“新聞執政”理念與路徑,價值與意義都非常顯著。如何深度解讀延安時期黨的新聞執政方式,創造多樣化的、具有親和力的官方話語和文風,也是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應有之義。如今政府執政的媒介生態業已發生巨大的變化,政府提高對新聞事件的議程設置能力和國內輿論的駕馭能力正在成為加強執政能力的突破口[5]。政府要學會把政治價值變成新聞價值,把政府工作變成新聞工作的一部分。對執政者而言,運用新聞傳媒的能力是其執政能力的重要構成部分。“發揮新聞傳媒的作用,很重要的是要通過它來體現執政黨的意志和人民的心聲,達到兩者的統一,并在政黨執政規律與新聞傳媒運行規律之間尋求統一[6]。延安時期的經驗也給今天網絡背景下如何管理運用媒體提供了基本精神營養。所以,梳理其理念,探求其路徑,完善黨的新聞執政理論,就成為一件重要的職責和使命。
作者:韓雋 單位: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
- 上一篇: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利益范文
- 下一篇:環境經濟系統分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