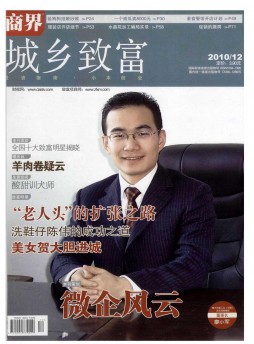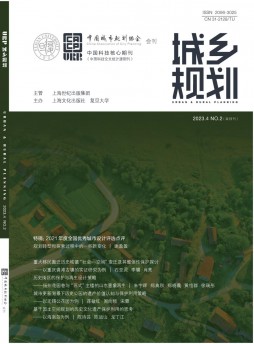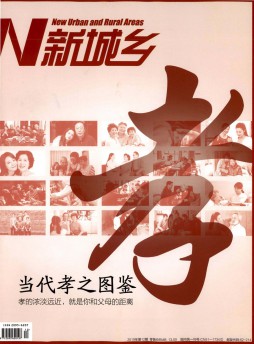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制度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制度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統(tǒng)計與信息論壇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模型構建
(一)Logistics模型制度系統(tǒng)研究可以從制度系統(tǒng)目標入手。設X為制度系統(tǒng)的目標指標,假定X的變化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制度系統(tǒng)指標自身的增長;資源條件的限制,指標不會無限的增長。當X達到某一確定的受資源容許的最大值時,則不再增長。為此,可以采用最高項為2次項的一階微分方程來進行描述:這個方程就是被廣泛應用于化學、生物、醫(yī)學以及社會科學等領域的Logistics模型。Logistics模型是二次非線性微分方程,包含有正、負反饋項,能夠反映出制度系統(tǒng)存在促使指標不斷增長的因素,也能夠反映出制度系統(tǒng)存在資源限制使指標下降的因素。制度系統(tǒng)的演化正是在一些正、負反饋因素共同作用下進行的,可以選擇Logistics模型描述制度系統(tǒng)演化運動過程,其中α表示系統(tǒng)指標成長速度,N表示資源條件限制下指標的最大值。得到兩個解:X=0或X=N,這兩個解是制度系統(tǒng)指標X演化運動的均衡值。達到穩(wěn)定均衡值表明制度系統(tǒng)進入一個定態(tài),此時有序性為0,無序性最大。因此應用此方法可以確定制度系統(tǒng)均衡值,并可以利用相關參數進行穩(wěn)定性分析。
(二)公平與效率目標下的制度系統(tǒng)模型構建制度系統(tǒng)的目標可以分為公平和效率,二者存在競爭性。制度系統(tǒng)如果以效率為目標,則有序性表現(xiàn)為效率增加,無序性為公平下降;相反如果以公平為目標,則有序性為公平提高,無序為效率下降。1.構建制度系統(tǒng)模型假設制度系統(tǒng)的目標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協(xié)調,設公平為X,效率為Y,公平和效率不僅是競爭性的,也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不能只重視一個而完全忽視另一個。追求效率的代價是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地位和權利的不平等[20]49。公平缺失將會導致收入差距持續(xù)拉大,努力卻沒有與之匹配的回報,這將會減少激勵,從而降低效率,甚至會出現(xiàn)社會矛盾和社會混亂,使效率完全喪失。同樣,重視公平而忽視效率最終會損害公平,正如阿瑟•奧肯所說,“任何堅持把餡餅等分成小塊的主張,都會導致整個餡餅的縮小。”因此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兩個目標之間的交叉影響,構建Logistics演化方程組:2.穩(wěn)定性分析采用對于非線性方程平衡點的穩(wěn)定性分析方法對4個均衡點進行穩(wěn)定性分析,得到的結果見表1,說明β1和β2在不同的條件下,均衡點是否穩(wěn)定。表中空缺表示沒有經濟意義。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數據來源本文試圖從制度系統(tǒng)的角度分析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因此對公平目標的變量選擇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而效率則選擇人均GDP。通過對歷年的人均GDP和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比較,選擇1983-2009年共27年的數據,選擇原因在于作為一個系統(tǒng)目標行為發(fā)生改變應該體現(xiàn)出一定連貫性,這27年的人均GDP和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整體上都呈現(xiàn)出不斷增長的趨勢。這個時期可以以1997年為界分成兩段:1983-1997年和1997-2009年,原因有二:一是1997年前后中國正面臨內憂外患的經濟形勢,同時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和戶籍制度的松動等制度改革都表明兩個時期的制度系統(tǒng)存在差異;二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在1996和1997年呈現(xiàn)出一個明顯波動,一改之前持續(xù)擴大的趨勢,如果以上升下降作為一個完整趨勢的話,1997年正是前一個時期下降之后的最低點,同時也是后一個時期上升開始的最低點,并假定兩個時間段的制度系統(tǒng)各自維持連貫。數據中人均GDP是根據當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后的實際人均GDP。
(二)模型擬合本文選擇利用Origin軟件對Logistics演化方程組(3)進行擬合。為了便于利用Origin軟件對方程組的擬合,自定義了一個函數。1.制度系統(tǒng)中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交叉影響的驗證利用同一段時期的數據對忽略交叉影響的模型(2)和考慮交叉影響的模型(3)分別進行擬合,用擬合結果對比哪個更符合實際,以驗證公平和效率之間是否存在交叉影響。對模型(2)的擬合,簡便起見采用Origin軟件中的函數間接進行:這兩個擬合的檢驗結果見表3。可以看出,第一次擬合中,檢驗結果中ReducedChi-Sqr、調整后的R2都表明非線性平面擬合的擬合優(yōu)度均優(yōu)于非線性擬合,F(xiàn)值以及P值顯示擬合效果比較顯著。第二次擬合中除了F值略有下降之外,其余各項指標顯示非線性平面擬合的擬合優(yōu)度較好,擬合更為顯著,并且F值的下降幅度并未影響擬合的顯著性。因此,可以斷定制度系統(tǒng)中公平與效率之間存在著交叉影響,采用模型(4)更符合現(xiàn)實規(guī)律。2.相關參數的估計值將1983-1997年和1997-2009年看成兩個制度系統(tǒng),對各自數據分別進行擬合,應用擬合結果求出各種參數估計值和均衡點。擬合的檢驗結果見表4,可以看到ReducedChi-Sqr和調整后的R2這兩個指標顯示擬合的優(yōu)度較好,F(xiàn)值檢驗也通過,擬合效果比較顯著。系數的轉化。根據系數換算公式以及表5中擬合得到的參數估計值,計算得出方程組(3)的各個參數值,見表6。進一步根據表6中換算后的相關參數估計值可以計算得出制度系統(tǒng)在各自時期的均衡點,結果見表7。3.均衡點及其穩(wěn)定性分析上述過程得到兩個時期制度系統(tǒng)的相關參數值,據此做出圖2。圖中虛線所構成的圖形是1983-1997年制度系統(tǒng),N1、N2表示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X和Y的極限值,這也就意味著系統(tǒng)的均衡點只能在這兩個極限值與橫軸、縱軸限制之內。點P1.335,(4468.747)是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的均衡點,β1=2.884>1,β2=5.345>1,二者同時大于1說明均衡點穩(wěn)定。穩(wěn)定的均衡點說明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均衡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1.335,均衡的人均GDP為4468.747。這一均衡點是比較低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和較高的人均GDP,是非常理想的狀態(tài),而1997年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2.4689,人均GDP為1452.8582,距離均衡點比較大。長期來看,制度系統(tǒng)將會不斷降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同時增加人均GDP,向均衡點不斷演化。但是長期來看不確定性很大,可能某些因素的變化促使制度改革導致制度系統(tǒng)發(fā)生變化,從而改變均衡點,改變系統(tǒng)的演化方向。圖2中實線所構成的圖形是1997-2009年制度系統(tǒng),N1'、N2'表示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X和Y的極限值。點P'5.848,3803.()566是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的均衡點,即這一時期制度系統(tǒng)均衡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5.848,均衡的人均GDP為3803.566。β1=0.010<1,β2=0.750<1,由于二者同時小于1,說明均衡點同樣是穩(wěn)定的。如果不進行變革,制度系統(tǒng)向均衡點不斷演化將會出現(xiàn)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繼續(xù)上升,同時人均GDP卻不斷下降,這將非常糟糕。
三、制度系統(tǒng)的評價分析
1983-1997年和1997-2009年兩個時期制度系統(tǒng)存在的共同點有二:一是兩個制度系統(tǒng)都存在穩(wěn)定均衡點,具備有序演化的必備前提,而且兩個制度系統(tǒng)中人均GDP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影響都小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對人均GDP的影響,說明代表著公平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對效率的限制一直都高于效率對公平的影響,要想釋放效率,就應該認真解決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問題。二是兩個系統(tǒng)的α1都大于α2,說明系統(tǒng)中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成長速度要高于人均GDP的速度。兩個時期制度系統(tǒng)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從均衡點上來看,前一個制度系統(tǒng)極低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和較高的人均GDP水平,要遠好于后一個系統(tǒng),而均衡點是制度系統(tǒng)演化的方向。這也就意味著任由前一個制度系統(tǒng)演化可能會出現(xiàn)一個極其令人滿意的趨勢,但是制度系統(tǒng)卻發(fā)生了改變,這種改變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1997年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對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意識上的轉變成為這兩段時期制度系統(tǒng)發(fā)生重大變革的標志。同時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的低迷,為了應對這種周圍經濟環(huán)境的變革采取的種種政策措施,也能夠算是一個非人為因素。從其他擬合得到的參數估計值來看,1983-1997年制度系統(tǒng)β1=2.884>1,β2=5.345>1,二者均大于1說明均衡點穩(wěn)定。同時,這兩個系數也能反映出人均GDP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交叉影響都很大,并且人均GDP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影響小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對人均GDP的影響。而1997-2009年制度系統(tǒng)β1=0.010<1,β2=0.750<1,二者同時小于1,同樣能夠說明均衡點穩(wěn)定,并且人均GDP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影響小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對人均GDP的影響,但是也顯示出與之前制度系統(tǒng)的不同,這兩個系數反映出人均GDP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交叉影響都很小。比較兩個時期系統(tǒng)的α1和α2,第一個時期的α1和α2都小于第二個時期,反映了第一個時期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和人均GDP的成長速度都低于第二個時期,尤其是α1,從前一個時期的1.141變成了第二個時期的4.490,說明變革之后,公平的損害程度非常嚴重。前一個系統(tǒng)人均GDP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交叉影響相對比于后一個系統(tǒng)都很大,對此嘗試做出解釋。改革開放初期,可能受之前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的思想沒有完全放開,仍然存在“姓資”和“姓社”的疑惑和顧慮,對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既想追求效率又怕違背社會主義,違背公平,這也導致束手束腳,可以看出這段時期效率與公平之間的交叉影響極大[21]。隨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和黨的“十五大”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確立,促使人們解放思想,意識得到逐步扭轉,效率與公平之間的交叉影響都出現(xiàn)下降。
作者:劉偉茶洪旺韓喜艷單位: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濰坊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