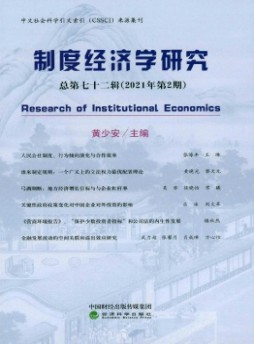制度變遷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績效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制度變遷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績效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達(dá)龍•阿塞莫格魯從理論視角出發(fā)考察了制度變遷的原因、制度及其變遷如何影響經(jīng)濟(jì)績效,從而形成其制度增長理論。從實證視角出發(fā),他通過運用經(jīng)濟(jì)史研究的方法證實了制度對長期經(jīng)濟(jì)績效具有關(guān)鍵作用,為其制度增長理論提供了經(jīng)驗證據(jù)。阿塞莫格魯?shù)闹贫仍鲩L理論的貢獻(xiàn)在于開啟了經(jīng)濟(jì)學(xué)不同領(lǐng)域新的綜合,并為經(jīng)驗事實提供了更可靠的解釋。中國經(jīng)濟(jì)已進(jìn)入新的發(fā)展階段,阿塞莫格魯?shù)睦碚撆c實證研究對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啟示意義。
關(guān)鍵詞:達(dá)龍•阿塞莫格魯;制度增長理論;制度變遷;經(jīng)濟(jì)績效
一、引言
自羅伯特•索洛建立新古典增長框架以來,在解釋“長期增長的源泉是什么”這一經(jīng)濟(jì)增長理論的核心問題上,技術(shù)進(jìn)步和人力資本積累一致被視為兩種最重要的源泉。但是,隨著研究的擴(kuò)展,不少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尤其是制度學(xué)派的學(xué)者們,認(rèn)為這種要素積累式增長并未對長期增長做出根本性解釋。比如,諾斯和托馬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一書中認(rèn)為,所有要素,包括人力資本、思想和知識,它們的積累都不是增長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增長本身。也就是說,經(jīng)濟(jì)增長,雖然在統(tǒng)計意義上可以用GDP指標(biāo)來體現(xiàn),但GDP本身只是最終產(chǎn)品和勞務(wù)的市場價值的加總,真正在現(xiàn)實中增長或變化的,還是那些要素。如果用要素的增長來解釋增長本身,只是以特定的方式分解了GDP并用分解后部分的變化來解釋整體的變化,并沒有能夠充分地解釋增長的原因。為此,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究要素增長、變化背后的原因或機(jī)制。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認(rèn)為產(chǎn)權(quán)制度以及法律、習(xí)俗、文化等難以量化的因素是增長的基本機(jī)制;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則旨在把政治因素納入經(jīng)濟(jì)增長框架。循此路徑,美國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達(dá)龍•阿塞莫格魯區(qū)分了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并重點模型化地解釋了政治制度如何影響經(jīng)濟(jì)增長,政治制度又是如何與經(jīng)濟(jì)制度互動等問題,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建立制度增長理論框架。這一框架綜合了經(jīng)濟(jì)增長理論、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等多個領(lǐng)域的成果,是近年來宏觀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最重要的進(jìn)展之一。本文將通過梳理阿塞莫格魯?shù)闹贫仍鲩L理論的主要框架,對制度增長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績效之間的關(guān)系做一闡釋。
二、制度變遷與經(jīng)濟(jì)績效的理論研究
在阿塞莫格魯制度增長理論的主要框架[1]中,最關(guān)鍵的部分是把政治權(quán)力劃分為名義政治權(quán)力(dejurepoliticalpower)和實際政治權(quán)力(defactopoliticalpower)。名義政治權(quán)力來自政治制度,因為政治制度是規(guī)定各個政治參與者和政治群體行為的一系列規(guī)則。然而,這只是制度或條文上賦予的權(quán)力,在實際生活中,這些權(quán)力是否能夠如法律條文所規(guī)定地那樣實施,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何況,除了制度所賦予的政治權(quán)力,某些群體也可能掌握著非制度化的額外政治權(quán)力。能實際產(chǎn)生影響的政治權(quán)力和額外的政治權(quán)力構(gòu)成實際政治權(quán)力。實際政治權(quán)力有兩個來源:首先,不同群體之間的集體行動本身的差異能夠帶來實際政治權(quán)力的差異。如果一個集體成員越多,且這些成員能夠更有效地做出集體選擇,那么這個集體或集體中的個體所擁有的實際政治權(quán)力就會大很多。其次,實際政治權(quán)力來自擁有的經(jīng)濟(jì)資源。這是因為經(jīng)濟(jì)資源本身能夠?qū)φ沃贫犬a(chǎn)生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濟(jì)資源可以被特定地使用從而使得自己獲益,對手受損。如此一來,一個在制度上擁有相當(dāng)大政治權(quán)力的群體,可能因為缺乏經(jīng)濟(jì)資源,而無法獲得與該政治權(quán)力相稱的實際利益。因此當(dāng)期的政治制度與資源分配共同決定了當(dāng)期的政治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而擁有更多權(quán)力的群體則決定當(dāng)期的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當(dāng)期的經(jīng)濟(jì)制度又影響著當(dāng)期的經(jīng)濟(jì)績效和下期的資源分配。這一框架是在眾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基礎(chǔ)上給出的。我們首先梳理該框架的理論部分,這些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研究:對制度變遷原因的研究以及對這些變遷是如何影響經(jīng)濟(jì)績效的研究。
(一)制度持續(xù)與變革的原因與動力
1.既有制度持續(xù)的原因
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制度的持續(xù)與變革。在制度增長理論框架中,制度的持續(xù)性主要來自某個群體掌握了更大實際政治權(quán)力之后會不斷強(qiáng)化既有制度,產(chǎn)生制度的路徑依賴。代表性文獻(xiàn)是阿塞莫格魯與羅賓遜合作的兩篇論文[2][3]。首先,社會由精英與平民兩個群體構(gòu)成,兩個群體假設(shè)有不同的特性:一是精英人數(shù)較少,在控制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時,通過獲得更多的人均預(yù)期收益,從而用更多的資源和更高的激勵投資于實際政治權(quán)力。二是精英與平民經(jīng)濟(jì)分工不同,精英是生產(chǎn)者,平民是勞動者且勞動供給無彈性。在精英主導(dǎo)的經(jīng)濟(jì)制度下,平民需要把勞動產(chǎn)出中的一部分作為租金交予精英;在平民主導(dǎo)的經(jīng)濟(jì)制度下,平民擁有全部產(chǎn)出,無需繳納任何租金。在這兩種經(jīng)濟(jì)制度下,平民主導(dǎo)的制度無疑會有更高的經(jīng)濟(jì)績效,因為其中沒有租金對產(chǎn)出的負(fù)激勵。此外,政治制度也通過公共品的供給影響最終的經(jīng)濟(jì)資源分配:當(dāng)政治制度由精英主導(dǎo)時,精英能夠獲得所有的公共品;當(dāng)政治制度由平民主導(dǎo)時,平民將獲得所有的公共品。在精英政治下,精英能夠獲得全部的名義政治權(quán)力;在民主政治下,平民能夠獲得全部的名義政治權(quán)力。而在每一期,精英和平民都通過投資來獲取一部分實際政治權(quán)力。哪一個群體掌握更大的名義政治權(quán)力和實際政治權(quán)力,哪一個群體就能主導(dǎo)本期的經(jīng)濟(jì)制度和下一期的政治制度。在上述設(shè)定下,均衡的權(quán)力和資源分配有如下四個特點。第一,一般而言,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具有持續(xù)性。這是因為在精英制度下,雖然精英和平民都進(jìn)行了投資,但精英掌權(quán)的概率更高;而在民主制度下,平民的掌權(quán)概率更高。而政治制度的主導(dǎo)者,往往也是經(jīng)濟(jì)制度的主導(dǎo)者。第二,相比于精英制度,民主制度更容易被顛覆。這是由于精英個體數(shù)量遠(yuǎn)遠(yuǎn)少于平民,對實際政治權(quán)力的平均投資也就更多,因此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精英也有可能掌權(quán)。第三,即使精英在民主制度下沒有辦法掌握政權(quán),他們也可以通過更高的投資擁有更大的實際政治權(quán)力,并維持有利于他們的經(jīng)濟(jì)制度和資源分配方式。這意味著,即使政治制度民主化了,原先由精英主導(dǎo)的經(jīng)濟(jì)制度仍舊可能繼續(xù)維持下去。要維持原有的經(jīng)濟(jì)制度,精英必須過度投資實際政治權(quán)力,這會帶來民主制度下經(jīng)濟(jì)的無效率。第四,如果在民主政治下,平民獲得的收益(比如集體行動效率、得到的公共品)足夠大,那么無論精英如何投資,都無法顛覆政治制度或改變經(jīng)濟(jì)制度,這時民主制度才會與“帕累托最優(yōu)”的經(jīng)濟(jì)制度和資源分配共存。在上述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構(gòu)成的動態(tài)模型中,制度的持續(xù)性表現(xiàn)在某一群體能夠通過既得利益長期維持在政治生活和經(jīng)濟(jì)生活中的優(yōu)勢地位,即使出現(xiàn)了變革,也容易回到原來的軌道上。有趣的是,在阿塞莫格魯?shù)姆懂犞校贫鹊某掷m(xù)往往以精英制度或非民主制度作為案例;而制度的變革往往以平民制度或民主化作為案例。這或許是歷史經(jīng)驗給予阿塞莫格魯?shù)囊粋€潛在預(yù)設(shè)。
2.有效制度變革的動力
制度的變革分為有效制度變革與無效制度變革,前者指社會大多數(shù)群體能夠獲取最大收益的變革,在精英—平民二分的理論框架下意味著確立平民主導(dǎo)的政治與經(jīng)濟(jì)制度。阿塞莫格魯著重研究了能夠引導(dǎo)有效制度變革的動力。
有效制度變革的第一個動力來自于革命的威脅(Acemoglu和Robinson,2001;2006)。在非民主制度下,精英或者權(quán)貴掌握著所有的名義政治權(quán)力和相當(dāng)大的實際政治權(quán)力,實行有利于自己的經(jīng)濟(jì)政策和資源分配。但是,平民雖然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卻多少擁有集會抗議的權(quán)利和革命的權(quán)利。如果在一個非民主社會中,民眾越來越難以忍受不平等的程度,或者由于外部沖擊經(jīng)濟(jì)狀況突然惡化,那么民眾就會對精英產(chǎn)生革命的威脅。這一威脅表現(xiàn)在一旦革命成功,精英就會失去他們的政治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jì)利益。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精英仍然掌握一部分資源,但革命帶來的破壞會使得經(jīng)濟(jì)在一段時間內(nèi)處于蕭條狀態(tài),精英的利益與革命前相比會受到損害。然而,革命也面臨著自身的成本約束:平民人數(shù)越多,革命過程中產(chǎn)生的群體內(nèi)部摩擦和沖突也越多,同時需要使用的經(jīng)濟(jì)資源也越多,這導(dǎo)致規(guī)模越大的革命自身成本也越高,發(fā)生的概率也越低。精英對待革命有三種可行策略:在政治和經(jīng)濟(jì)上不做任何讓步、對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做出政策性改良、全盤改革既有制度。精英采用何種策略取決于鎮(zhèn)壓革命的成本與做出改良或變革造成的潛在損失之間的權(quán)衡取舍:若鎮(zhèn)壓革命的成本很低,精英將鎮(zhèn)壓革命萌芽,不做任何讓步;當(dāng)鎮(zhèn)壓革命的成本與政策性改良對精英造成的預(yù)期損失相當(dāng),精英將通過政策性改良降低革命概率;當(dāng)鎮(zhèn)壓革命的成本遠(yuǎn)遠(yuǎn)超過制度變革產(chǎn)生的預(yù)期損失時,全盤改革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成為精英的最優(yōu)策略。
有效制度變革的第二個動力來自經(jīng)濟(jì)制度本身。無論是非民主還是民主社會,在不同的經(jīng)濟(jì)制度下,精英和平民的資源配置、經(jīng)濟(jì)利益都是不同的,從而導(dǎo)致不同的革命成本與鎮(zhèn)壓革命的成本,進(jìn)而關(guān)系到不同群體的最優(yōu)策略選擇與制度變遷的均衡路徑。比如,在市場經(jīng)濟(jì)下,資源配置由“看不見的手”引導(dǎo),掌權(quán)者的高壓政策帶來的成本可能非常高,而在農(nóng)業(yè)社會中,這種成本相對會比較低。再如,在民主制度以及相應(yīng)的競爭性市場經(jīng)濟(jì)下,土地貴族受到的損害可能最大,而企業(yè)主受到的損害比較小甚至可能獲益,因此經(jīng)濟(jì)的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程度越高,對于民主化的阻力就越小。值得一提的是,阿塞莫格魯還研究了人力資本對于制度變革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首先,人力資本積累越多,鎮(zhèn)壓的成本就越高,這是因為在鎮(zhèn)壓中,個體的死亡比較容易,而個體的死亡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永久減少。其次,人力資本對經(jīng)濟(jì)政策,比如稅收的彈性較大。這是因為人力資本是否被勞動者有效使用,是很難被監(jiān)督的,在稅收高時,人力資本的回報低,勞動者更容易偷懶或閑置人力資本;在稅收低時,人力資本回報高,那么其使用就更有效。這意味著,當(dāng)政治制度從非民主制轉(zhuǎn)變到民主制,并實行有利于民眾的資源分配政策時,人力資本的回報和使用效率都會變高。因此,一個社會中人力資本的存量越大,制度變革的阻力就越小。
有趣的是,這兩種制度變革方式,與庫茲涅茨曲線能夠很好地吻合起來(Acemoglu和Rob-inson,2000)。庫茲涅茨曲線說明隨著經(jīng)濟(jì)增長與人均收入的上升,不平等程度先升后降,呈現(xiàn)倒U型。制度變革理論可以對這種倒U型的原因做出解釋:在民主制度沒有完全建立的近代社會中,當(dāng)人均收入隨著工業(yè)革命而增加時,經(jīng)濟(jì)中物質(zhì)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不斷增加,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會擴(kuò)大。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變化意味著民主化的阻力變小了,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使得革命的威脅變得更為可信。兩者促使掌握政權(quán)的精英實行一系列政治和經(jīng)濟(jì)改革,比如,擴(kuò)大選舉權(quán)、立法救濟(jì)貧困、保障工人權(quán)益等,使得民主制度逐漸完善起來。這些改革反過來降低了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并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經(jīng)濟(jì)的增長。技術(shù)進(jìn)步是有效制度變革的第三個可能動力(Acemoglu和Robinson,2006)。同樣假設(shè)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都由精英主導(dǎo),若外生的或者由投資積累產(chǎn)生的技術(shù)進(jìn)步能夠打破精英在經(jīng)濟(jì)上的壟斷地位,那么平民的經(jīng)濟(jì)收入會增加,從而有利于平民擴(kuò)大政治權(quán)力投資,逐步掌握更多的實際政治權(quán)力,帶來制度變革。基于此,精英應(yīng)該傾向于反對潛在的技術(shù)進(jìn)步,避免對自身的利益產(chǎn)生難以預(yù)料的沖擊。但是,在特定條件下,精英同樣會更傾向于鼓勵技術(shù)進(jìn)步。第一,如果政治制度中的競爭更為激烈,即使沒有技術(shù)進(jìn)步,精英被取代的可能性也很高,那么精英反而會鼓勵技術(shù)進(jìn)步,并利用新技術(shù)來鞏固自己的經(jīng)濟(jì)和政治地位。第二,如果技術(shù)進(jìn)步能夠提高未來的預(yù)期收入,那么精英也會采用新的技術(shù)。第三,如果技術(shù)落后將帶來外國的侵略者,那么精英也會傾向于鼓勵技術(shù)進(jìn)步。不同的社會條件下,不同社會群體對技術(shù)進(jìn)步的策略也不同,從而可能衍生出多種制度變革路徑。
由此可見,阿塞莫格魯研究制度變遷的基本方法是構(gòu)造擁有不同特征和偏好的微觀社會群體,再通過這些社會群體的博弈形成基于策略均衡的制度變遷路徑。這一博弈論的方法為制度變遷的模型化提供了便利,并構(gòu)建了宏觀制度的微觀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之上,阿塞莫格魯及其合作者(Acemoglu、Egorov和Sonin,2011;2012;2014)提出了“動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dynamicpoliticalecono-my)這一更為一般化的理論框架。動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主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證明均衡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穩(wěn)定性問題;第二個是研究外來沖擊(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政黨偏好的變化等)如何改變原有的均衡狀態(tài),改變政治權(quán)力的安排,從而導(dǎo)致制度的變革。本質(zhì)上,第一個問題是對制度持續(xù)的一般化,而第二個問題是對制度變革的一般化。動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主要結(jié)論有二個。第一個結(jié)論是,在滿足一系列偏好假設(shè)下,如果沒有外生的沖擊,那么將存在一個穩(wěn)定的政治權(quán)力安排和政治制度。更為直觀的理解是,當(dāng)不滿當(dāng)前政治安排的政黨缺乏改變制度的權(quán)力,而不存在另一種政治安排使得當(dāng)前掌權(quán)的政黨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時,政治安排就是穩(wěn)定的。如果這兩個條件至少一個不被滿足,則可能存在不穩(wěn)定的政治安排,或者會產(chǎn)生制度變革,收斂于另一種穩(wěn)定的制度狀態(tài)。第二個結(jié)論是,面臨外來沖擊時,如果擁有政治權(quán)力者可以通過變革獲得更大的利益,那么變革就會發(fā)生。然而,面對特定的外來沖擊方式,如果變革在沖擊到來之前完成,那么這種變革可能是穩(wěn)定的,將不受這種特定沖擊的影響。動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可以說是一個研究制度穩(wěn)定與變化的一般框架,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權(quán)力的平等化、激進(jìn)型政黨的出現(xiàn)對政治制度的影響以及鎮(zhèn)壓與革命之間的角力,都是這一框架的特例。更為重要的是,動態(tài)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能夠用來研究隨機(jī)情形下的制度變遷問題,這使得制度增長理論能夠和宏觀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前沿更好地銜接起來。這也是制度增長理論未來的研究方向。①
(二)制度的經(jīng)濟(jì)績效分析
在建立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框架的同時,阿塞莫格魯對制度的經(jīng)濟(jì)績效也做了相當(dāng)深入的研究。具體而言,經(jīng)濟(jì)制度的經(jīng)濟(jì)績效,本身就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的一般研究對象。但當(dāng)政治制度作為核心變量被納入制度范疇之后,制度的經(jīng)濟(jì)績效研究演變?yōu)閷φ沃贫鹊淖冞w規(guī)律、政治制度與經(jīng)濟(jì)制度的互動以及前兩者是如何影響經(jīng)濟(jì)運行的效率與長期增長的綜合研究。這就是阿塞莫格魯?shù)闹贫仍鲩L理論。早期的制度增長理論關(guān)注政治制度對經(jīng)濟(jì)績效的直接影響。例如,“政治失意者(politicallos-er)”理論(Acemoglu和Robinson,2000)認(rèn)為,經(jīng)濟(jì)中未掌握政治權(quán)力的群體因為技術(shù)進(jìn)步而受到經(jīng)濟(jì)利益上的損害時,他們就難以阻礙新技術(shù)的采用,只有那些掌握政治權(quán)力、但權(quán)力會因新技術(shù)的采用而削弱或喪失的群體,才有激勵和能力去阻礙新技術(shù)的采用。①上述理論僅是考察特定政治群體對技術(shù)進(jìn)步的影響,最優(yōu)可持續(xù)機(jī)制理論(Acemoglu、Golosov和Tsyvinski,2008)則在民主制度場景下考察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在一個公民社會中,經(jīng)濟(jì)制度為典型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政治制度則由公民投票選出政治家。政治家在任期內(nèi)可以用政治權(quán)力決定資源如何在自己和公民之間分配。在該制度下,如果政治家不能連任,就有動機(jī)把當(dāng)期產(chǎn)出全部據(jù)為己有。為了防止最壞情況出現(xiàn),公民需要保證政治家能任滿一定期數(shù)并在每一期把部分產(chǎn)出讓渡出去,使得在所有任期內(nèi)政治家獲得的收入總和高于其在某一期能夠占有的全部產(chǎn)出。但如此一來公民的勞動供給就會受到負(fù)激勵,政治家收益也未最大化,經(jīng)濟(jì)績效決非最優(yōu)。要漸進(jìn)實現(xiàn)帕累托有效的最優(yōu)可持續(xù)機(jī)制,必須存在一個耐心高于公民的政治精英,從而能忍受短期內(nèi)的低收益以獲得長期內(nèi)的高累積收益。在更為一般化的隨機(jī)民主場景中(Acemoglu、Golosov和Tsyvinski,2010),社會結(jié)構(gòu)從政治家—公民二分變?yōu)槿坑蔁o數(shù)政黨構(gòu)成。在當(dāng)期,每個政黨獨立做出消費、投資和勞動供給決策,并由隨機(jī)過程決定執(zhí)政黨,執(zhí)政黨有權(quán)分配產(chǎn)出。與最優(yōu)可持續(xù)機(jī)制理論一樣,該制度規(guī)則下資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只有在政黨的耐心足夠大的前提下才能被漸進(jìn)實現(xiàn)。由此可見,從政治失意者理論到隨機(jī)民主場景,阿塞莫格魯著重研究了政治制度———即使是民主制,對經(jīng)濟(jì)績效的負(fù)面影響,其稱之為“政治摩擦力”。要消除政治摩擦力,我們得訴之于耐心足夠高的政治精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系列理論帶有悲觀色彩。
隨后,阿塞莫格魯試圖在更為宏大的、兼具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制度增長理論框架下考察制度與經(jīng)濟(jì)績效的關(guān)系。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Ace-moglu和Robinson,2012)一書中,阿塞莫格魯提出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和掠奪性制度(extractiveinstitution)的劃分。包容性制度指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jì)制度,其特點是多元主義(pluralism)和有效的權(quán)力集中(centralization)。前者能夠保證政治權(quán)力廣泛地分布于社會之中(abroaddistributionofpoliticalpowerinsociety),從而使得盡可能多的社會群體可以平等地參與政治決策、自由地進(jìn)出市場參與交易;后者能夠形成由暴力壟斷、中央集權(quán)的財政和現(xiàn)代官僚制度組成的國家治理能力(statecapacity),從而提供良好的法律體系和完善的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以及足夠數(shù)量的公共品。在包容性制度下,政治上的集體決策是有效的,經(jīng)濟(jì)上則能促進(jìn)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技術(shù)進(jìn)步,形成良性循環(huán)(virtuouscycle),帶來長期增長與繁榮。而掠奪性制度則產(chǎn)生惡性循環(huán)(vi-ciouscycle),即政治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jì)地位的壟斷、當(dāng)權(quán)者對反抗者的鎮(zhèn)壓、既得利益集團(tuán)對革命性技術(shù)進(jìn)步的抑制,將加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導(dǎo)致政治和社會的動蕩。在惡性循環(huán)中,即使反對派成為新掌權(quán)者,也并不必然會改革既有制度,反而會利用這種制度獲得更大收益,補(bǔ)償其在反對活動中付出的成本。在掠奪性制度下,經(jīng)濟(jì)長期增長是無法實現(xiàn)的。更進(jìn)一步,阿塞莫格魯研究了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生成問題(Acemoglu和Robinson,2016)。通過考察古希臘和近代英國的制度變遷路徑,阿塞莫格魯提出了國家與社會互動說,即只有在一個社會文化、習(xí)俗和非正式規(guī)則能夠促進(jìn)具有國家治理能力和權(quán)力分散特征的政治體制的形成,同時該政治體制又能強(qiáng)化其社會文化土壤,包容性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出現(xiàn)。到此為止,阿塞莫格魯逐步修正了其早期制度增長理論中的政治精英“救世祖”特點,與現(xiàn)實的距離愈來愈近,在理論的一般性和現(xiàn)實性上取得了較大的進(jìn)展。
三、制度的長期經(jīng)濟(jì)績效的實證研究
除了理論研究之外,阿塞莫格魯還對制度的長期經(jīng)濟(jì)績效做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這些實證研究主要是從經(jīng)濟(jì)史的角度展開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章(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考察了各個殖民地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的歷史原因。文章提出了三個假說:第一,歐洲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地實行不同的殖民政策,掠奪性的政策是為了攫取盡可能多的經(jīng)濟(jì)利益,并不關(guān)心未來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另一種政策則是復(fù)制歐洲的經(jīng)濟(jì)制度,保護(hù)私有產(chǎn)權(quán),限制政府的權(quán)力;第二,在那些環(huán)境差、死亡率高的地方,殖民者傾向于采取掠奪性政策,而在環(huán)境好、死亡率低的地方,殖民者采取復(fù)制歐洲經(jīng)濟(jì)制度的政策;第三,在殖民地獨立以后,這些政策造就的制度依然存在。當(dāng)這三個假說都成立時,通過把殖民時期的死亡率作為制度的工具變量,選取64個殖民地國家作為樣本,實證檢驗表明制度差異能夠解釋近3/4的經(jīng)濟(jì)收入差異。在另一篇文章(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2)中,阿塞莫格魯通過對比不同殖民地在公元1500年之前和公元1500年之后的經(jīng)濟(jì)收入差異變化趨勢,發(fā)現(xiàn)在公元1500年之前比較繁榮、人口密度比較大的地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卻變得日益貧窮;相反,在公元1500年之前人口稀少、財富貧瘠的地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卻變得日益富裕。實證檢驗表明這一現(xiàn)象的根源還是在于殖民制度:在人口密集、財富集中的地方,殖民者更可能采取掠奪性制度去攫取當(dāng)?shù)鼐用窠?jīng)濟(jì)利益,而在人口稀少、財富貧瘠的地方,大部分人口都由殖民者構(gòu)成,他們反而會復(fù)制歐洲的經(jīng)濟(jì)制度,更多地保護(hù)私有產(chǎn)權(quán)和維護(hù)自由的經(jīng)濟(jì)制度。實行掠奪性制度的地區(qū)的財富增長遠(yuǎn)遠(yuǎn)不如復(fù)制歐洲經(jīng)濟(jì)制度的地區(qū),這就造成了不同殖民地在公元1500年之前和之后迥然相反的經(jīng)濟(jì)狀況。在對殖民地研究的基礎(chǔ)上,阿塞莫格魯又把其研究視角投向了歐洲,以證明制度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具有普遍性[1]。
在16世紀(jì)—19世紀(jì)初,大西洋貿(mào)易的繁榮和殖民主義帶來了歐洲高速的經(jīng)濟(jì)增長。但是,能夠參與大西洋貿(mào)易的國家之間的增長情況卻不同:英國、荷蘭增長較快,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增長較慢。阿塞莫格魯提出了一種假說,認(rèn)為這種差異源自各個國家初始的制度稟賦。在英國、荷蘭,商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大西洋貿(mào)易帶來的財富更多地流入商人手中,商人將這些財富用于經(jīng)濟(jì)和政治上的投資,逐步改變了政治制度,加強(qiáng)了政治的開放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和對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力度,從而促進(jìn)了經(jīng)濟(jì)增長。反觀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家,君主專制的盛行使得大西洋貿(mào)易帶來的財富大部分流入了君主和與君主聯(lián)系緊密的商人手中,他們并不關(guān)心制度變革,因此政治制度在長期中制約了經(jīng)濟(jì)增長。通過對24個歐洲國家構(gòu)建行政約束指數(shù)(utiveconstraintindex,該數(shù)值越小,表明專制程度越高,數(shù)值越大,表明開放程度越高)實證發(fā)現(xiàn),初始行政約束指數(shù)越大的國家,在大西洋貿(mào)易之后經(jīng)濟(jì)的增長更快;參與大西洋貿(mào)易的國家,在其后行政約束指數(shù)都變大了,而沒有參與大西洋貿(mào)易的國家,行政約束指數(shù)卻變小了。這有力地證明了文章提出的制度假說。在最新的文章(Acemoglu、Gallego和Rob-inson,2014)中,阿塞莫格魯?shù)热税讶肆Y本因素放入了之前解釋殖民地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的框架中。研究發(fā)現(xiàn)在以往的核算中,人力資本的回報由于測量誤差而偏高了4~5倍。在糾正了這一測量誤差之后,實證發(fā)現(xiàn)殖民地初始的人力資本差異只能解釋之后6%~10%的長期經(jīng)濟(jì)增長差異,而制度差異仍舊能夠解釋大部分長期經(jīng)濟(jì)增長的差異。考慮到人力資本與經(jīng)濟(jì)增長的內(nèi)生性,當(dāng)我們用傳教士的活動作為人力資本的工具變量時,結(jié)論基本不變。因此,這一研究用更嚴(yán)格的方法論證了制度在長期經(jīng)濟(jì)增長中所起的關(guān)鍵性作用。以上是用跨國歷史數(shù)據(jù)做的研究。阿塞莫格魯還使用了哥倫比亞的歷史數(shù)據(jù)來更詳細(xì)地檢驗跨國研究的結(jié)論(Acemoglu、Garcia-Jimeno和Robinson,2012)。雖然缺乏歷史上奴隸數(shù)量的具體數(shù)據(jù),但由于奴隸被廣泛用于金礦開采,阿塞莫格魯使用了是否臨近金礦作為哥倫比亞各個城市奴隸經(jīng)濟(jì)制度是否盛行的指標(biāo)。
實證結(jié)果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了跨國數(shù)據(jù)的結(jié)論:長期的奴隸制度使得貧困人口增加、教育程度下降、衛(wèi)生狀況惡化以及土地分配不平等狀況加劇,這些因素是哥倫比亞貧窮的罪魁禍?zhǔn)住_@一研究最重要的意義是部分揭示了經(jīng)濟(jì)制度影響增長的一些傳導(dǎo)機(jī)制。另一篇使用國別數(shù)據(jù)的最新文章(Acemoglu、Reed和Robinson,2014)是阿塞莫格魯對塞拉利昂地區(qū)歷史上的酋長(Chief)制的研究。在殖民時代,酋長的職位由當(dāng)?shù)厝舾蓚€政治家族控制,且其任命必須經(jīng)過殖民者的同意。因此,一個地區(qū)政治家族的數(shù)量就成為政治開放程度的近似指標(biāo):政治家族越多,酋長任命的競爭越激烈,上任之后權(quán)力越小;政治家族越少,則酋長任命越缺乏競爭,上任之后權(quán)力也越大。實證結(jié)果表明政治家族越少的地區(qū),今天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就越落后。除了對制度的長期經(jīng)濟(jì)績效做出實證檢驗之外,阿塞莫格魯還就民主化對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作用做了不少研究。在較早的研究中(Acemoglu、John-son、Robinson和Yared,2008;2009),阿塞莫格魯?shù)热苏J(rèn)為只有在長期(500年左右),民主制度才與較高的人均收入相關(guān);最近的研究(Acemoglu、Naidu、Restrepo和Robinson,2014)則通過重新核算民主化指數(shù)以及動態(tài)GDP的衡量,發(fā)現(xiàn)即使年代跨度小于500年,民主還是對人均GDP產(chǎn)生了正向的影響。
四、結(jié)論與啟示
阿塞莫格魯對制度變遷及其經(jīng)濟(jì)績效的研究主要有兩方面的重大學(xué)術(shù)意義。一方面,阿塞莫格魯通過博弈論的方法更深入地刻畫了不同社會群體和政黨之間的互動是如何影響政治制度變遷,進(jìn)而刻畫政治制度是如何通過經(jīng)濟(jì)制度影響長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這就把經(jīng)濟(jì)增長理論、經(jīng)濟(jì)發(fā)展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等經(jīng)濟(jì)研究領(lǐng)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同時深入到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學(xué)、政治學(xué)和歷史學(xué)等學(xué)科的交叉領(lǐng)域,既是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宏觀經(jīng)濟(jì)學(xué)綜合的發(fā)展,也為社會科學(xué)研究提供了更富包容性的框架。另一方面,阿塞莫格魯?shù)闹贫仍鲩L理論為經(jīng)驗事實提供了更可信的解釋。具體而言,它的解釋范圍包括:第一,大西洋航線開辟以來美洲殖民地的制度變遷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第二,西歐的興起,尤其是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其他歐洲內(nèi)陸國家的制度變遷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差異;第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長期貧窮的原因;第四,“二戰(zhàn)”以后各大新興經(jīng)濟(jì)體的發(fā)展;第五,歷史上政治制度變革的原因,比如歐洲的民主化進(jìn)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等,以及變革前后的宏觀經(jīng)濟(jì)變化。在眾多的文獻(xiàn)中,這些并不是解釋范圍的全部,但它涉及的時間長度與地域跨度,比大部分競爭性理論的解釋范圍有過之而無不及。阿塞莫格魯?shù)睦碚撗芯繉π聲r代中國的發(fā)展同樣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當(dāng)前,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動力已經(jīng)逐漸由要素積累轉(zhuǎn)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逐漸由投資部門和傳統(tǒng)部門主導(dǎo)轉(zhuǎn)向消費部門和新興部門主導(dǎo),社會主要矛盾也變?yōu)槿嗣袢找嬖鲩L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現(xiàn)實告訴我們,過去30多年的增長方式,在未來是不可持續(xù)的。為此,中國需要系統(tǒng)地建設(shè)包容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質(zhì)量更高且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務(wù),加快推動政治制度改革,讓更廣泛的社會群體擁有更平等的名義政治權(quán)力和實際政治權(quán)力,以及培養(yǎng)能夠支撐包容性制度的社會土壤。這將帶來中國經(jīng)濟(jì)的持續(xù)繁榮與穩(wěn)定發(fā)展。
作者:杜麗群 單位:北京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