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園文化與國人早期的觀影方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茶園文化與國人早期的觀影方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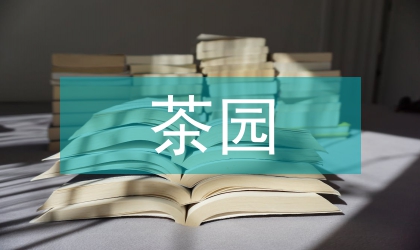
《文藝研究雜志》2015年第七期
早在清代,茶園或戲園都指同樣的地方,并無嚴格的意義分界。如上海“,上海京劇的發祥地,最初在城內縣前街,有幾個吃衙門飯的開辦茶園,最出名的是‘三雅園’,由姓顧的住宅改設演出昆曲。后來,隨著商市的發展,在寶善街一帶開設了大觀茶園、同春茶園、迎仙茶園等。這條寶善街人們稱之為‘戲觀街’。早期的上海名伶……等長期登臺演出。這些京劇藝人在此出名而走紅,成為海派京劇的先行者”①。又如天津,“在清代中葉,天津便出現了稱之為‘茶園’的演出場所,清道光四年(1825)的《津門百詠》中有詩云:‘戲園七處賽京城,紈绔逢場各有情。若問兒家住何處,家家門外有名堂。’這里所說的戲園實際上就是重品茶不重聽戲的茶園,所以均以茶園命名……茶園雖為戲曲演出場所,但實際入園卻以喝茶為主,聽戲為輔,觀眾入園只收茶資,不收戲票”②。京城的茶園、戲園同樣是不分彼此的,“北京人有飲茶的習慣,凡戲園皆賣茶,有的戲園原來就是從茶園發展而來”③。在沒有正式的電影院之前,電影主要的寄身處之一便是茶樓。“早期放映電影并無影院,看影戲都在茶樓飯館里,這大概是沿襲了飲茶聽書的時俗。1897年起,上海天華茶園、奇園、同慶茶園等都放映過電影。但看影戲與聽書到底不同,它須隔絕光亮使觀者置身于黑暗中,所以放映電影從一開始就辟單室于茶樓,另售門票。當時它是新鮮的玩意兒,觀者日益增多,可算是一種賺錢的行業”④。最有代表性的放映電影的茶樓便是上海四馬路上的青蓮閣,因為這里是西班牙商人雷瑪斯租下一間房首次放映電影的地方,但此茶樓也是一個遠近聞名的賭場、妓院和幫會活動的聚集地。程步高在回憶錄中如此評價“:青蓮閣是茶樓,是游樂場,其實是個藏污納垢之處,是個罪惡的淵藪。九教三流,地痞流氓,幫會弟兄,巡捕暗探,互通聲氣,互爭進帳。”⑤作為人肉市場,青蓮閣早在20世紀初就已形成規模。“租界雉妓,向皆聚集于四馬路之青蓮閣”⑥。茶樓除了是電影在上海的早期棲身之處外,也是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放映電影的首選之地。天津的玉順茶園也是較早放映電影的地點之一。1906年12月8日,美國電影商人來到天津,租下了法租界的權仙戲園放映電影“:每三天更換一批新影片,由于連續放映數月,這段時間,電影即成為了該茶園的主要業務,所以不久它就更名為‘權仙電戲院’。”⑦無獨有偶,電影在北京放映并引起轟動的地方也是一家茶園。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經理任景豐憑借著曾經在日本學過照相技術的經歷,決定自己動手拍片。攝影師是豐泰照相館的照相師劉仲倫。任景豐邀請京劇藝術大師譚鑫培主演了《定軍山》里面的幾個片段,“請纓”、“舞刀”、“交鋒”等,“拍攝3天,制成影片3本,可放映20分鐘。影片制成后首先在大柵欄大亨軒茶園放映,在京城引起轟動”⑧。茶園與戲園是中國民間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主要場所之一,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電影放映不約而同地選擇這個地方,顯示出異國文化借助某特定本土空間以期獲得接受的嘗試。因此,當西洋影戲寄身于中國特有文化空間時,也遭遇了一番本土化改造。通過考察可知,茶園文化在國人早期的觀影方式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生動而有趣地顯示了一定歷史背景下外來文化踏足中國之初的碰撞及互融過程。
一、鑼鼓配樂
正如前文所述,茶園與戲園實指相同,很難想象,習慣了傳統戲曲鑼鼓喧天的中國觀眾,如何能夠接受早期的無聲電影?聽覺的享受對他們而言是無法舍棄的,正如人們常常將“聲色犬馬”用來形容糜爛淫樂的生活方式,聽覺之“聲”是位居第一的頭等享受。在一篇關于戲曲欣賞的文章里,我們能夠體會到聽覺的重要性:“居北京久,殆無可樂,而久居北京,或北京土著,乃自有其樂。其所樂者惟何?1.逛胡同。2.聽戲。3.聽落子。4.逛游戲場。5.逛廟。6.吃飯。7.下茶館聽書聽戲。”⑨可以發現,作者在提到戲和書的時候,都是用的“聽”而非“看”,可見聽覺上的享受比視覺來得更加重要一些。又如“受照明條件限制,茶園每天只演日場,從無夜場,冬日天短,遇有戲未終而日已西墜……便燃起亮子油松等物以代蠟燭,高舉于舞臺兩側。舞臺上下煙霧繚繞,光線昏暗,這大概就是當時人們不重看、稱看戲為聽戲的由來吧”⑩。一位親歷當年青蓮閣電影放映的觀眾的描述將我們拉回到歷史現場,去聆聽一段熱鬧非凡的影戲表演。“四馬路影戲之喧嘩:西人有電光影戲,固絕無聲息之美劇也。乃觀于四馬路之影戲場則不然。有雇傭洋鼓洋號筒者,喧嘩之聲不絕于耳。是與西人適成一反比例也。繪影戲喧嘩圖,并綴‘五更調’形容之:一更一點月吐光,影戲鬧忙,呀呀得而噲,將要開場。烏都烏都啥花樣,號筒響,聲氣真長,呀呀得而噲,吹得頭脹。二更二點月橫空,大鼓蓬蓬,呀呀得而噲,耳朵震聾,人山人海門前擁,腳勿動,朝里望望,無啥影蹤,呀呀得而噲,大家勿懂。三更三點月兒高,鑼鼓亂敲,呀呀得而噲,看客坐牢,歇子半刻做一套,好心焦。難得看見,倒說真好,呀呀得而噲,片子勿少。四更四點月更明,影戲做停,呀呀得而噲,賬目結清,為啥勿聽洋錢叮,無開心,市面壞呀,生意不靈,呀呀得而噲,銅錢難尋。五更五點月向西,看客回去,呀呀得而噲,一路雞啼,想想剛剛看影戲,真擁擠,好熱鬧呀,吵得希奇,呀呀得而噲,阿要神氣”。作者反復使用聲音詞匯來描述青蓮閣放映電影的現場情形,似乎聲音元素大大超過視覺感官,以至耳朵被鑼鼓震聾。雷瑪斯此舉本是為了擴大宣傳,招徠生意,卻在不經意間暗合了中國觀眾的戲曲欣賞口味。關于電影與“鑼鼓”的關系,在另一幅早期觀影圖片中也得到了清晰呈現,文字寫道:“借間房子做影戲,戲價便宜真無比。二十文錢便得觀。越看越是稱希奇。人物山川景致新,田盧城郭似身親。一般更是夸奇妙,水火無情亦像真。”配圖為:墻壁左上方懸掛“電光影戲,每位二十文”的條幅,房間不大,陳設簡單,有四、五條長凳,四個戴著瓜皮帽、身穿長衫的中國男子分座兩排,前方有一塊幕布,其上隱約可見樹木、房屋和街道。畫右是三位正在賣力吹喇叭、敲鑼鼓的伙計。可見,國人早期觀影方式中鑼鼓配樂的重要地位,而此觀影習慣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自戲曲的胎記,只是最初的鑼鼓喇叭在稍后的電影配樂中逐漸被與情節相關的電影音樂替代,完成了最初“招徠看客”的使命。世殊時異,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一本關于電影院裝置布局的指導手冊中,對放映電影時的音樂伴奏有明確規定:“今日觀眾鑒賞影片的對象,是映像和音響兩者融合的情緒,所以我們認為電影施教時的音樂伴奏,實為必不可少的一種工作(自然是指無聲默片的場合),不過一般留聲機的唱片,往往與影片無關,如果不能另設樂隊,為適宜的伴奏,那么對于唱片的選擇,必須十分的考慮,萬不可蹈普通電影院之弊。”鑼鼓蓬蓬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此時的觀眾鐘愛的是與影片情節相輔相成、彼此映襯的現場樂隊伴奏。“看過《黨人魂》的總能記憶起,當那銀幕上眾船夫背纖的時候,他們是何等的努力他們不得已的工作,和上他們還很悲壯的引吭高歌那《伏爾加船夫曲》。同時臺前的音樂班也奏著那有名的伏爾加船夫曲起來,這是何等的急奏啊!過了多少時日,如果單單的奏起那只曲子來,定能連帶回憶到在銀幕上他們努力的工作和悲壯的高歌的表演,同時更能引出人一種悲壯的奮斗的感情出來,這是我十分相信的”。盡管此時脫胎于戲曲鑼鼓的電影配樂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伴奏方式,但觀眾仍舊習慣將電影配樂與戲曲鑼鼓等同看待:“影戲院之有音樂,所以增觀眾之樂趣,襯出劇中人之喜怒哀樂,令人生無窮之感想,一如京戲之有鑼鼓也,否則觀者寂然無趣矣。”因此,當年各電影院的廣告宣傳常常將音樂配樂作為一大賣點。1925年,上海中央大戲院的開幕預告上特別寫明:“另請俄國音樂家數人奏樂助演。喜怒悲歡,益見深切,此尤為申江時代所無,而足與其他大戲院相頡頑也。”又如1929年,濟南銀光大戲院的開幕預告列出了電影院的八大特色,其中第四點是關于音樂的介紹:“音樂幽雅:本院特聘精熟音樂家數人擔任奏樂,銀燈乍暗,丁咚錚錚,絕非人間,只應天上。”輶訛輥其實,迷戀“聲”乃人性之本能,默片時期中國觀眾對電影配樂的追求不足為怪。正如我們所知,興起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好萊塢歌舞片,幾乎與有聲電影同時代誕生,遂成為30、40年代的流行時尚,并在50、60年代達到輝煌。可見,有聲片與歌舞片的結合是人性催生的結果,當如精靈一般的聲音元素附體到默片的軀體時,電影觀眾便急不可耐地將處于銀幕之外的大小樂隊挪至銀幕之內,并將其演繹得炫目極致。
二、反購票入場
對于觀影的收費方式問題,國人也經歷了一個變遷過程,這其中還有地域文化的差異性不可忽略。簡言之,上海實行買票入場的方式比北京早,而且阻力甚小。以北京為代表的北方觀影在推行買票入場時,曾受到來自民間的諸多阻力,這恐怕和上海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政治地位分不開。浸淫在西方文化之中的上海灘,常常能夠比其他地方更爽快、更寬容地接納異域文化。以上海為例。從前文“五更調”中所描述的“影戲做停,賬目結清”可見,青蓮閣最初放映電影時,是看完電影再收費。不過,程步高在回憶錄中提到青蓮閣時,這樣記載道:“雷摩斯就在1904年,租樓下一小間,裝成上海第一個電影院了……買票入場,贏得許多顧客,收進許多錢鈔。”可見,青蓮閣的收費方式也在逐漸改變。錢化佛在回憶錄中提及20世紀10年代的上海幻仙影戲館時“,門票每張售兩銅圓”。同樣,在戲園收費問題上,上海也很早實行了購票入場的規矩:“民國初年,(上海)的娛樂場所的種類,還沒有后來那么復雜而廣泛……所以看京戲大班,就成為各階層觀眾唯一的娛樂……那時上海各戲館的票價,一般地都不算高,我住的平安里附近,就有一家毛兒戲館,大概是叫群仙茶園。有一次我跟朋友經過這戲館的門口,我們進去開了眼。一個案目過來招呼我們,我的朋友也就替我買了一張票。我們只站著看了一會兒就走了。”北京的情況與之相反,不管是看電影還是看戲,購票入場的規矩很難得到貫徹實施,盡管有些娛樂場開風氣之先地推行購票入場。在1907年的《順天時報》上,刊載了一篇電影觀后感,作者將在北京平安電影院的觀影體會做了詳細記錄,并特別提到買票入場的問題:“查這電影戲地方,組織得很是文明,進門買票,實在辦理的好,北京電戲雖多,這處可推第一。”言語措辭間,可見平安電影院是北京較早實行買票入場的電影院之一,而當時很多茶園仍然實行后買票的方式。“天橋,在南城之南,靠近天壇,為‘坤角大鼓家’之發祥地,茶肆中奏藝者,比比皆是……飲茶每客五枚銅元,另給茶葉錢,聽唱則每段唱畢,有一執小鑼者,向座收錢,隨意給予,無定額,恒以給錢之多寡,為座客毀譽之表示”。迨至1919年,北京的大部分電影院和戲園仍然延續傳統的后付款方式。1919年1月24號,北京新明戲院開幕,這家戲院開風氣之先在于,不顧社會壓力與反對,堅持將賣票制度貫徹到底,因為此前的北京戲園也曾實行過賣票制,但終因反對聲浪過大,被迫終止。新明戲院開幕前后,在報紙上刊登聲明如下:“本場對號入座,各有定位,原為尊重惠顧諸君人格起見,以免先后凌亂,彼此爭執,至減清興,有失雅儀。務祈,各界格外原諒。購票請早,臨時概不加凳。特此鄭重聲明。”在開幕次日的《順天時報》上,有人評論說:“京師為首善之區,外人瞻觀所系。戲館舞臺,多年來表面雖見改良,而辦法未能革新者尚不能屈指。就中觀客憑票入場一事各戲園無人倡議,以致園內閑人自由出入,秩序極為混亂,詢為都城劇場最為可恥之事也……賣票制度在今日言之因有種種為難情形,不易舉行。然沒有一戲園為之倡議,并要求官廳施適當之保護,其他戲園必效法其后……現新明大戲院已經開幕,實行賣票,須自該戲院始。何以言之該戲院既稱新明,必有一新明特異之點,偏能一改各園舊有之弊,而為他園之模范,諒必受顧客之歡迎也。”
由此可見,當時的北京城在推行“先購票,再入場”時所遇到的阻力,因為其他各園此時仍延續的是“舊有之弊”。國人自己經營的電影院或戲院尚且無力推行新政,西人在華經營的娛樂場所便可想而知了。“中國電影院有限公司的英國總經理桑德森(MarshallSanderson)在1919年的春季去了美國,主要是希望美國電影的銷售商能夠降低電影的價格。他在那次參觀會的采訪中告訴我們,在中國北部,他開設的兩種完全不同形式的電影院。他的14個電影院中有10個是為中國人開設的,另外4個是為外國人服務的,觀眾主要由外國商人和公使館的一些人員組成……看大片的話,外國觀眾需要付2美圓或者4元墨西哥比索。桑德森的中國人電影院卻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經營:中國人對于買票入場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你不能要求他付任何的錢,因為他還什么也沒有看到呢。所以,賣一張票給他,然后才準許他進入電影院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必須把大門打開讓他們全部進來,一般情況時觀眾很多,然后開始放映電影。‘在電影放了幾百英尺之后,他們的興趣也被激發起來了。我們就停止放映,把燈打開,用一個大筐子開始收錢。’桑德森說‘:中國觀眾把銅板放進去,3個,10個,20個,根據他坐的座位的價格來付錢。然后,燈被熄滅,電影繼續放映。’”這種付款方式與北京天橋老百姓在坤角大鼓表演結束后“有一執小鑼者,向座收錢”的收費方式何其相似。可見,西人經營的電影院,若想在華立足,也不得不像中國文化屈服順從,當然這個屈服過程注定是短暫的,因為沿襲自西人的購票入場方式不久后即廣泛推行開來。正如有論者所言“:中國從19世紀開始進入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過程,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與文明示范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啟動要素。”國人漸次接受西人“買票入場”的行為方式,恰恰印證了埃利亞斯在其著作《文明的進程》中對“文明”的歷時性特點的描述:今天所謂“文明人”所特有的行為方式,在西方國家的人來說并非與生俱來。倘若今天西方國家的文明人能夠回到他所處社會的過去階段,比如回到中世紀,那么他所看到的正是在今天被他斥為“不文明”的那些社會中所常見的。其實,何須回到中世紀,百年之間,東西方國家的文明進程就已經顯現出巨大的差異,然而正是由于作為過程或過程結果的“文明”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有了某種程度的減少,因為文明強調的是人類共同的東西,至少對于那些已經“文明”了的人來說是這樣。因此,被西方“文明人”共同認可的“購票入場”成為普世性的文明結果,國人對此行為的接受無形中拉近了東西方的文明差距。一個不起眼的“購票入場”的歷史細節,折射出國人在“文明進程”中的一大邁步,但這一步歷史性的邁進是如此艱難,如此反復,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國人的某種“固執堅持”,而這種保守態度對西人來說也是并不陌生的。
1934年,《密勒氏評論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中國人的堅持態度:以地名為例》的文章:“也許,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像中國人那樣表現出如此強烈的堅持性。這個國民性,毫無疑問,是中國人能夠在幾千年的時間中始終保持一個完整國家的原因之一……例如,中國人曾經給一個地方命名,而后,子子孫孫幾個世紀都絲毫不改變地始終延續使用這個名字,當然,除非是什么政治原因,由政府來改變名字……如電車售票員一直將老的法國市政大廳稱作‘大自鳴鐘’,這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現在,這只鐘已經搬走了,毫無疑問,這幢老的建筑也即將被拆除,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好多年里,中國人還會繼續稱這個地方為‘大自鳴鐘’,就好像這只鐘仍然還在那里一樣,就算這個地方變成了垃圾堆積處,他們還是會這樣稱呼此地。”正如我們所知“,每一種歷史現象,諸如人的行為或社會機構確實都有其‘形成’的過程,所以作為對它進行闡述的思維方式,決不能簡單地滿足于人為地將這些現象從它們自然的、歷史的發展中抽象出來,抹去其運動和發展的特性”。因此,關于國人“固執保守”的思維方式也要“話說從頭”。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在其鴻篇巨制《風俗論》中對中國人的保守風尚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其一是中國人對祖先流傳下來的東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敬心,其二是認為一切古老的東西都盡善盡美。梁漱溟曾說:“中國人雖不能像孔子所謂‘自得’,卻是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點,而不做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質生活始終是簡單樸素的,沒有那種種發明創造。”“先賢”“、祖傳”“、古法”等詞匯正反映了中國社會最核心的保守風尚。因此,當作為外來文化的“電影”落腳于20世紀之初的中國,它們無可奈何卻又別無選擇地接受了“古法”之改造,安靜而耐心地等待著中國社會的變革。
三、熱毛巾、飲茶、開燈觀影
前文已經說過,中國觀眾最初是在戲園和茶園里接觸電影的,所以這些娛樂場所的欣賞習慣很自然地被移植進電影的觀賞方式中。國人賞戲的習慣,早有西人關注并報道。1911年,某旅華外籍人士這樣描繪在廣東戲院的經歷:中國戲院燈光明亮且喧鬧無比,戲院里最好的位置是2角錢的票價,然后加半分錢的稅可以拿一個坐墊,演出從一開始就顯得不正式,男人們在正廳后座抽煙、吃橘子、喝茶,婦女和孩子們則坐在走廊里,她們抽的是一種奇怪的中國水煙,也喝茶,還做著一些我看不明白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她們的金耳環,仔細打理過的烏亮的頭發和前額下充滿好奇期待的眼睛。沒有幕簾,也沒有風景,很多東西需要想象力。女性角色都是男性扮演,沒有真正的女人在舞臺上出現過。賞戲喝茶的習俗被挪至影院確實令外國人驚訝“:我連續去了幾個不同的城市,感受中國戲院的文化……很難用文字描繪這些地方電影院的嘈雜程度,或者身在其中感受到的撲鼻臭味。散發難聞氣味的半裸男人和我一起肩并肩推搡擁擠著。大多數觀眾都喜歡喝茶,吃一種奇怪的甜肉和其他氣味沖人的東西。我一開始還對穿梭在一條條座位中間的東西感到好奇,那東西的速度像子彈一樣飛快,后來才明白是提供給觀眾擦臉的熱毛巾。”中國電影院有限公司的英籍總經理桑德森在20世紀20年代如此感慨道:“中國觀眾不能夠從頭到尾將一部電影完整的看完,他們好像坐不住,中途一定要喝上幾杯茶,或者揩幾次毛巾。所以,每放完一本片子,就會有一個中場休息,讓他們喝茶,或者把毛巾從空中扔給過道上的服務員,服務員會立刻把毛巾在水里搓一下,然后馬上又扔回去,在這一系列動作之后,電影繼續放映。”這方面的記載屢見西人報端,可見此愛好的中國特色。“在電影開始之前,中國人喜歡喝茶,之后男人和女人會略顯疲倦的吸煙”。又如“上海的電影院在中場休息時,走路輕手輕腳的服務員會給你奉上香茶。在電影院的過道里,受過訓練的服務員會提供非常奇怪的服務———扔熱毛巾。每隔一會,都會有觀眾舉手表示要毛巾,此時隔得最近的服務員就會將手中的熱毛巾投擲給這位觀眾,距離大概有50英尺那么遠,但每次都是百發百中,從來不會失手。顧客接過毛巾擦完臉后,就會將毛巾放在座位下面”。旅華外籍人士對中國電影院內的毛巾、茶水等如此關注,正說明此類現象與西方文明的差異,中國觀眾是以看雜耍的心態走進電影院的,正如劉吶鷗的一次觀影經歷所記載的:“有時想去看看本國影片,就不得不走進中國影戲院去,一走進去,我們就感受到各種壓迫———洋大人經營的影戲院里所享受不到的壓迫。隔座的同胞們不時的大吐其痰,這還不算,前面幾位同胞們卻仍然戴住了他們的帽子,把你障住了銀幕上一部或全部的地位。這是已經不易對付的了。至于四座人聲的喧吵,小販的叫賣兜售,把許許多多污濁不堪的東西在你身邊擦過……幸而影片開幕了,于是小孩的叫嗓鼓掌聲,老大哥們朗誦字幕聲,嘴里吃瓜子栗子的聲音,和那不知所云的音樂聲,真的叫你立刻感受到頭疼腦昏,戲未完而已有出院的必要了。然而戲院老板看見國人情愿花三四倍代價到洋大人的戲院去卻還永遠莫名其妙。”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外國觀眾看來,到電影院看電影是社交活動,以20世紀20、30年代僑居上海的外籍人士為例,有論者寫道,在上海出現白俄之前,這個城市除了能為外國人提供偶爾上演的新電影之外,幾乎不能為他們再呈現什么文化生活了。這些電影的觀眾一般都是穿著晚禮服的外國領事們和中國洋行的大班。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好萊塢電影的首輪放映無疑是一次重要的社交活動,所有的領事和洋行的經理富商們穿著隆重的晚裝參加觀看。可以想見,喧鬧的中國電影院內的茶水、點心及飛翔的熱毛巾會給外國觀眾造成如何的感官刺激。國人觀影方式深受茶園文化的影響,正如日本觀眾在觀看方式上的本土化現象一樣。有人這樣描述道“:劇場的裝飾,那是比我們中國的影戲園要好多了。光線也很注意,但是專演他們本國片的戲園,大都沒有椅子,都是坐在席上的,所以我們很覺不舒服,倘使專演西洋片和本國西洋合演的影戲園,那是也有很好的座位,并且也有號碼,一些沒有紊亂的。”席地而坐是日本民族的生活習慣,正如揩熱毛巾、喝茶也是國人在茶園時陶冶出的嗜好。“手巾把兒、糖果案子、茶房合稱為劇場中的‘三行’。清代中葉天津開始有了茶館,初時,單以賣茶為主……后來設立戲園后,經營者見觀眾有此習慣(喝茶),并有利可圖,即沿用茶園舊例,添設茶水,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手巾把兒和糖果案子。手巾把兒一般為兩個人,一個人負責洗手巾,在一樓的前臺放著一個大盆,盆里放滿了熱水。用外國香皂把手巾一條條洗好,再灑上法國香水,綁在一起用漂白布罩著,另一個人不停地在觀眾中穿梭,將手巾把兒強行塞給觀眾,索要小費。兩人在空中以熟練的手法相互傳遞著手巾把兒,扔手巾把兒也是個技術活,像雜技一般。要手巾把兒的人或在樓上,或在樓下,但不管在哪里,都要求他二人配合默契,扔的要準,接的要穩。戲開演前,觀眾們就看他們的表演,并不時地為他們叫好。如果功夫練得不到家,手巾把兒散了,他們也有個說法,叫‘天女散花’”。這方面的服務常常成為戲園的招徠手段。“本國戲園……果餌每碟一角,特泡之茶,每壺一角,手中錢無者為多,看客不可喧嘩,不可亂吹警笛,否則即受巡捕干涉”。又如“京戲院的三樓戲迷……在我們座位前,也是前排椅子的背后,有一長條擱板,上蓋白色罩布,有四到五只銅制高腳盆,盆內有水果、瓜子、糖食和香煙,邊吃邊看”。此項特殊服務往往也容易變味成強制消費“:京戲院座位,大約分包廂,花廳,特等,頭等,二等,三等各種,舊習多用案目,實則此項案目之職責,與影戲院之導路伺役相等。但往往不能由觀客自由選擇座位,并強送茶煙瓜子等,事后需索常在票價之上,以故于觀眾不無煩擾,近已有自動改良者。”在這方面,西人觀影習慣與國人截然不同。“外國戲園……又皆兼演光電影戲……價目1,2,3元不定。包廂大約每間15元。當演劇時,不得吸煙,食物,必俟休息時,入一別室始可為之”。此外,國人早期觀影方式中關于“開燈”的記載,最早出現在1909年8月到1910年8月間出版的《圖畫日報》中。在一幅“做影戲”的圖畫中,一枚燃亮的燈泡懸掛于屋內上方,一位男子面向看客而立,似乎是解畫師在解釋電影情節。這是筆者找到的最早關于國人開燈看電影的圖片資料。此一推測在20世紀20年代一篇西人的文章中得到證實:“中國人常常有眼病,黑暗中銀幕的閃爍對他們而言不太能夠接受,因此大多數電影院是開著燈放映電影的。”這里或否存在早期將看戲時的燃燭習慣一并移植到觀影行為中?有文字這樣記載當年茶園演戲時的盛況“:開演夜戲時,給觀眾以‘地水通明如白晝’的感覺。”即便如前文所述,“舞臺上下煙霧繚繞,光線昏暗”“,看”戲演變為“聽”戲,但其中卻體現出燈火營造的煙煴氣氛,令意識遠離生活日常,進入虛幻夢境。國人早期以茶園戲曲般的文化心態接納電影,燃燈觀影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眼疾”一說赤裸裸體現了西方對東方的一種君臨心態,這一身體缺陷似乎是西方人“發明”的一項區別東西方的標志性特征之一。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闡述歐洲與非歐洲的關系一樣“:這是一種將‘文明’歐洲人與‘那些’非歐洲人區分開來的集體觀念,確實可以這么認為:歐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種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的東西———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于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
四、座椅問題
從看電影時的鑼鼓配樂,到固執的傳統付款方式,再到觀影時的飲茶、揩熱毛巾等習慣,這些無不體現出中國觀眾在接受西方文化時某種意義上的抗拒姿態。茶園是國人休閑娛樂的主要場所之一。在茶園內聽書,一般每場三個小時,半小時一段,停演斂錢,這種書場表演的長時段性特點,再加之說書人使出渾身解數吸引聽眾的職業精神等,都是早期觀影方式所不具備的。與之相反的是,早期電影院為了提高輪演次數,加速觀眾的更替批次,采取不提供座椅或提供使人難以久坐的座椅的方法。關于這一點,就連出錢請觀眾看電影的布拉斯基也深諳此理“:直到現在,中國的電影院也不提供座椅給觀眾,但觀眾仍然喜歡去那里消遣娛樂。一些有錢的中國人會出錢購買座椅,大多數情況支付1.5美元的門票。普通人只能站著觀看,相互之間擁擠在一起。”布拉斯基的很多電影院可以用這種方式容納一萬五千人,最小的也能夠容納五千人。布拉斯基進一步解釋道:“如果有座椅的話,他就無法將觀眾請出電影院,他們會坐在那里一直看下去,直到饑餓難耐時,才會自行離開。”輰輩訛不過,即便提供座椅的電影院,也會在這方面有所考慮。“電影自19世紀末期,由西方輸入我國,當時作為一種新玩意兒,根本談不上藝術,更談不上綜合藝術。放映電影設在臨時搭建的大布蓬里,幾條長板凳,觀眾納幾個銅元,即為入幕之賓。那些長凳,安置在泥礫地上,高低不平,坐著很不舒適。時間長一些是吃不消的。幸而都是短片,一下便完了。”早期電影院不提供座椅或提供不舒服座椅的原因在于,那時放映的多為片與片之間無情節關聯的短片,且也如布拉斯基所言,更便于清場,提高輪演次數。
對歷史研究者而言,還原歷史現場常常是奢侈卻具有誘惑力的沖動。當然,在盡力完成這個企圖后,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對此研究結果的意義反思。就本文而言,可歸納為三點:從藝術層面看,此變遷過程構成了“觀影”的標志性界定特征,正如我們所知,一門藝術之所以成立,在于它的獨特性、區別性與不可替代性,因為這是使它得以存在的根本理據。電影與觀影方式的有機結合成為電影藝術的核心組成部分。國人早期觀影方式中茶園文化的逐漸消失,正是電影與觀影方式漸趨純粹化、獨立化的體現;從文化交流層面來說,此變遷過程無疑是一個觀察中西文化碰撞的絕好“歷史中介物”;從文明進程的角度而言,國人在觀影行為中逐漸滌蕩茶園文化的過程生動地體現了民國初年時期國門洞開的中國社會漸漸西化/現代化的歷史畫卷。
作者:柳迪善 單位: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
- 上一篇:高齡用戶的可穿戴產品設計范文
- 下一篇:近代廣播的興盛與嬗變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