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中國哲學史的方式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重寫中國哲學史的方式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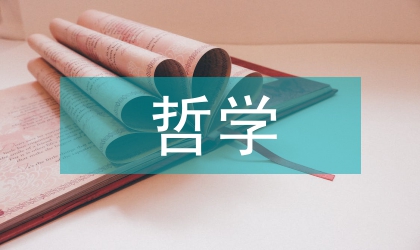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一、評估與定位
重寫中國哲學史,首先應當破除陳舊的道統觀念。按照以往的道統說,堯、舜、禹創立了完美的道統理念,后人只要照著講就可以了。可惜,后人總是講得不到位,或多或少地出現了有悖于道統的情形。即便是孔子也不例外。孔子在五十歲之前,講的是小康學,形成對于道統的疏離;五十歲以后,才講大道學,回歸道統。算起來,孔子回歸道統,只不過二十幾年而已。至于孔子之后的儒者更不足觀了,大多是道統的疏離者。孔子之后,雖然經常有人以道統繼承人自詡,但未得到大家的公認。按照道統說,中國哲學史似乎是一部退化的歷史,而不是發展的歷史,好像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觀點并不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也沒有反映歷史的真實。任何一位哲學家,無論其理論貢獻多大,都是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環節。不能設想,在中國哲學的發端之時,就有人一下子達到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度。對于任何一位哲學家,我們都不能把他當成崇拜的對象,而應當成研究的對象。倘若視其為崇拜對象,往往只能歌功頌德,嘖嘖贊嘆,無法對其作辯證評估和定位。只有把歷史上的哲學家視為研究對象,才會抱著辯證評估的態度,一方面指出其學說中的合理內核,另一方面指出其所受到的時代局限。以王陽明為例,其積極的理論意義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高揚人的主體性。王陽明平生所講的“致良知”,旨在充分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提高人們自己把握自己、認識自己和實現自己的內在潛能。他批評朱熹“析心與理為二”的傾向,在把心與理、心與物合而為一的基礎上,確立人在意義世界的中心位置。第二,不迷信權威和經典。王陽明致力于打破官方化了的程朱理學思想的壟斷,他不贊成“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不迷信權威,也不迷信經典,倡導理性主義的態度,客觀上具有沖擊舊權威、舊教條的積極作用。第三,強調道德自律和人性自覺。陽明學主張通過主體的自覺、自悟“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大學問》),簡易直捷,活潑開闊,給當時的學術界帶來一股新風氣。至于陽明學的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在糾正程朱理學的局限時走過了頭,引導出“束書不觀”、放任不羈的不良學風。
評估是從分析的角度判斷哲學家的貢獻與局限,而定位則是從綜合的角度判斷哲學家在哲學史上的地位。每位哲學家作為哲學史上的一個環節,都扮演著承上啟下的角色。大致說來,哲學家“承上”的方式有兩種:一是順承,接著前人的話題講,但找到自己獨到的講法,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有超越前人之處。例如,朱熹是接著“二程”的理論講的,但他圍繞著理氣關系做文章,講出了新意,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后人把“程朱”連稱,叫做“程朱理學”,就是對其學術地位的肯定。二是逆承,顛覆前人的講法,開辟新的話題,豐富了中國哲學的內涵。例如,王充舉起“疾虛妄”的大旗,就是針對天人感應論而講的。章太炎對王充的學術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對他的贊譽是“漢得一人足以振恥”。哲學家“啟下”的方式也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正面啟迪。前輩哲學家的成就為后學提供了思想資源,對后學有所啟發,幫助后學推進學理的發展。例如,孔子提出仁學理念,提出“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但語焉不詳,還是一種比較模糊的想法。孟子繼承孔子的思路,進一步發揚光大,形成了性善論學說,把孔子模糊的想法變成了系統的說法。如果沒有孔子在前,也就沒有孟子在后。在后人“孔孟之道”的稱謂中,足見孔子對孟子的巨大影響。二是負面啟迪。前輩哲學家的局限引起后學的反思,促使后者揚棄舊話題,開辟新話題,創立新思潮。例如,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觀點,就是在批評經學家的局限中形成的。在他看來,經學家就事論事,沒有用“體”為名教提供價值擔保,乃是導致名教失效的重要原因。為名教尋求本體論支撐,這正是玄學所要承擔的理論任務。
二、比較與評判
書寫哲學史并非要把古代哲學家當作報道的對象,而是當作評論的對象。書寫者必須從自己的視角看待研究對象,有所“見”,即提出獨到的看法。這種看法包括對哲學家的比較研究、特色概括等項內容。
(一)比較維度如果孤立地看待某位哲學家,書寫者很難形成自己的看法。書寫者必須敞開眼界,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哲學家做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也就談不上評判。書寫者的看法,在比較研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般來講,人們可以選擇以下三個比較維度:(1)縱向比較。這種比較維度適用于屬于同一學派但生活在不同時代的兩位哲學家。一個大的學派,可以跨越不同的歷史時代。屬于這個學派的兩位哲學家,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思想上自然會形成差異。兩者之間存在著“大同”,否則便不能歸為同一個學派;但也存在著“小異”,否則便無發展可言。對于這樣兩位哲學家,可以做縱向的比較:看他們之間的“大同”是什么,“小異”是什么,看后學如何發展了前輩的學說。例如,同屬于儒家,王陽明與孟子相比,共同點在于維護儒家倫理,但采用的手法不同:孟子用人性善說明儒家倫理的普適性,而王陽明則運用致良知之教對儒家倫理作出本體論證明。(2)橫向比較。這種比較維度適用于處在同一時代的兩位哲學家。兩位同時代的哲學家,處在共同的語境中,面對共同的問題,但他們解題的方式未必相同。每人各有各的獨到之處,因而可以進行比較。例如,同為南宋理學家,朱熹與陸九淵都認同“存天理,滅人欲”的原則,可謂之“大同”;但對“天理”的理解有所不同,可謂之“小異”。朱熹主張“性即理”,強調天理的超越性;陸九淵主張“心即理”,強調天理的內在性:各有各的理論架構和論證方式。朱熹由超越而內在,陸九淵由內在而超越,可謂“殊途而同歸”。(3)跨文化比較。這是對中國哲學家與外國哲學家做大跨度比較研究。跨文化比較研究應當是具體的,而不是籠統的。對兩種文化做籠統的比較沒有什么意義。比如,有人說“中國文化是筷子文化,西方文化是刀叉文化”,這有什么意義呢?這如同說中國人是黃種人,西方人是白種人一樣無聊。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前提是找到相似點,確立可比性。比如,印度佛教和中國禪宗,同屬于佛教范疇,當然具有可比性。呂澂曾對二者做了精當的比較:印度佛教講究“心性本凈”,禪宗講究“心性本覺”,有同亦有異。再如,黑格爾哲學中的“絕對精神”與中國哲學家講的“太極”,同屬于哲學本體論范疇,對此,賀麟可以做比較研究,指出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和差別性。比較絕不等于比附。比附是把一方的觀念硬套到另一方頭上,弄得不倫不類。比如,有人把韓非的歷史觀稱為“進化史觀”,就是如此。進化是西方近代的觀念,怎么可以用到古人身上?韓非講的是“變化”而不是進化,不能把他等同于達爾文主義者。比較研究的目的在于從異質文化的視角,加深對所研究對象思想實質的理解,而不是評判兩種文化孰優孰劣。那種出主入奴、菲薄固有的心態,有害無益,應該摒棄。
(二)概括特色比較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書寫者應當準確地概括出所研究對象的理論特色。能概括出某哲學家的特色,說明你對他的研究真的到位了;不能概括出他的特色,說明你研究的深度還不夠。當你說“我認識某某人”的時候,你一定是對他的相貌特征有所了解,能夠把他與別人區別開來;否則,你憑什么說認識他?研究哲學家的思想,道理也是如此。只有把他的思想特色找出來,才算進入到了研究的層面。筆者把老子的思想特色概括為“天道學”,認為這種特色是通過老子的三個哲學話題體現出來的。第一個是“以道說物”,從道的觀念解釋宇宙萬物,并涉及到了宇宙觀。第二個是“以道看人”,探討怎樣從“道”的角度來看待人,涉及到了人生觀。他從人生觀的角度講辯證法,講的不是黑格爾哲學中的辯證法,而是人學的辯證法、做人的辯證法。第三個是“以道救世”,講怎樣從“天道學”出發解決政治問題,探討如何走出紛紛擾擾的亂世的辦法,試圖給亂世找到一個出路。老子以“道”為核心理念,把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這三個哲學論域全都涵蓋了,因而是中國哲學當之無愧的奠基人。老子的這種講法,前無古人,后有來者,開創了道家學派,特色十分鮮明。筆者把孔子的思想特色概括為“人道學”,認為孔子確立了儒家學派。在天道觀方面,孔子基本上是接著老子講的,接受了動態的、有機的宇宙觀,創見不多;他的貢獻主要在人道學方面。他接受了“道”的觀念,但把“道”同“人”緊緊聯系在一起,著重闡述“人道”這一新的理念,實現了中國哲學在歷史發展中從天道到人道的轉折。在中國哲學史上,孔子對老子的第一點推進,在于把哲學話題由天道轉向人道,確立了中國哲學以人生哲學為主導的風格;第二點推進則是由“無知之行”轉向“有知之行”,首先涉足認識論領域。筆者把孔學要義歸納為六條。除了上述兩點轉折外,還有禮、仁、中庸三個觀念和一幅藍圖即大同之世。孔子的這種講法,前無古人,后有來者,特色也十分鮮明。
三、引證與論證
撰寫哲學史論著要以古代哲學家為研究對象,這就需要通過引證原文來解釋哲學家的思想,但是,引證不能代替論證。有一種說法,認為引證就是論證。對此,筆者不敢茍同。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古代學案編纂,就是以引證為論證,好處在于讀者可以直接從原著中了解哲學家的思想,不受解釋者的影響。對此,筆者也不敢茍同。受上述說法和看法的影響,在現有的哲學史論著中普遍存在著以引證代替論證的傾向。有些著作引用的原文甚至超過了三分之一,不堪卒讀;即便不引用原文,也只是把古文翻譯成現代漢語,把幾段引文串連起來。這種寫法,同讀書筆記有什么兩樣?恐怕不能稱之為學術論著。論著一定要以論者所立的觀點為主導,不能以被論述對象的原文為主導。在論著中,史料是觀點的證據,但觀點不是史料的簡單歸納,而是書寫者對原著的創造性詮釋。書寫者必須有所“見”,必須把“見”的理由講充分,然后再引用原文作為證據。引用原文不等于堆砌史料,應當把哲學家最有代表性的說法選出了,貫徹少而精的原則,盡量避免出現大段引文的情形。此外,引用原文以后,還應當作出解釋,并且同自己所提出的觀點掛上鉤。
學術論著除了引用第一手材料外,有時還要引用第二手材料,即引用其他研究者的說法。引用第二手材料,更應該注意避免出現以引證代替論證的情形。書寫者必須樹立自己的觀點,不能把別人的觀點引用過來,直接當作自己的觀點,把自己擺在“打工仔”的位置上。自己所樹立的觀點,必須在經過充分論證以后才可以引用他人類似的說法作為旁證。在任何時候,他人的說法都不是書寫者立論的主要根據。引用他人的說法,必須是被引用者具有說服力和獨創性的說法,而不是被引用者所講的公眾話語。倘若是公眾話語,書寫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何必引用他人的說法呢?書寫者引用他人的說法,有時不是在為自己的立論找旁證,而是批評對方的說法,通過駁論的手法樹立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要尊重對方,注意引文意思的完整性,切不可斷章取義。
四、觀點與結論
學術論著強調一個“論”字。研究者在論著中必須樹立自己的觀點,不樹立自己的觀點,不能稱之為論著。所謂論著,其實就是運用材料對自己所樹立的觀點作出充分論證,力求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成為一家之言。書寫者的觀點,應當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形成,這叫做“論從史出”。沒用足夠的史料積累,觀點便無從談起;即便有了足夠的史料積累,也未必能夠形成獨到的觀點,因為能否提出觀點,還同書寫者的理論思維能力有關。不可否認,中國古代哲學家具有實質的系統;如果他不具有實質的系統,就不配稱為哲學家。不過,中國古代哲學家并不用形式上的系統表達其實質上的系統,這正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如何從哲學家非形式的系統中提煉出實質的系統?這需要書寫者獨具慧眼,善生慧解,提出獨到的觀點。所謂觀點,就是書寫者運用自己的理論思維能力,對哲學家實質的系統所作出的概括、理解和解釋。哲學史的書寫,未必要充分反映哲學家實質系統,但一定是書寫者觀點的匯集。如果說觀點的形成取決于史料,猶如地球圍繞太陽轉的話,那么,觀點的表述則是用史料證明觀點,猶如月亮圍繞地球轉。哲學史的書寫,應當是觀點與史料的完美結合。
論著的結構,其實就是觀點之間的邏輯聯系。觀點同標題有區別。二者可以一致,構成直接的關系,標題就是觀點的直接表述;二者也可以不一致,觀點同標題構成間接的關系。有的標題只表明論域,如“某某人某某思想研究”,僅從標題看不出作者的觀點,但絕不意味著作者沒有觀點。作者觀點,通常在開篇即明確提出。修改定稿時,特別要注意審查論著結構,也就是審查觀點之間的邏輯關系。各級觀點應當構成嚴謹的邏輯系統。全書應當由一個總觀點,各章圍繞總觀點展開,任務在于以次級觀點為總觀點提供證明,說明總觀點何以成立的理由。每章下設的各節,應圍繞次級觀點展開,以第三級觀點為次級觀點提供證明,說明次級觀點何以成立的理由。節下所說各級專題,以此類推。總之,無論哪一級觀點,都必須得到論證,一環套一環。如果只有觀點,沒有理由,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在學術論著中不容許出現這種情形。書寫者對自己提出的每一個觀點,都應考問自己:我為什么如此看?我的理由是什么?我的理由是否充分?論著通過章、節、專題逐級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后,還要對全書做一總結,形成本書的結論。結論是對開篇所立總觀點的回應,使之更加明確、更加深刻。結論是從各章歸納出來的,應該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盡量做到條理化,把全書駕馭起來,使全書渾然一體。結論也可以做適度的發揮,適度地展現文采,給全書畫上一個精彩的句號。
五、立意與命題
(一)立意所謂“立意”,就是書寫者覺得自己有東西可寫,對某個問題或某個人物有所“見”,有了研究心得,有了寫作的欲望。“意”從何處來呢?不能來自他人的授意。按照他人的授意寫文章,可以寫出應景之作,但算不得真正的研究成果。“意”要自己去摸索,應主要從兩個方面下手:一是用心閱讀原著,琢磨作者的“意”,形成自己的“意”。中國哲學家的表意方式與西方人不同。西方哲學家采用系統的、邏輯的表意方式,捕捉他的“意”比較容易,把他的大前提、小前提乃至結論都搞清楚了,“意”自然就出來了。西方哲學家寫的哲學專著雖然都是大部頭,且數量比較多,但不難讀。中國哲學家不采用系統的、邏輯的表意方式,捕捉他的“意”比較困難。中國古代哲學家基本上不寫哲學專著,他的哲學思想是通過談話、書札、筆記、詩文、注釋等形式表達出來的,沒有形式上的系統可循。書寫者要想“立意”,必須通過哲學家非形式的系統,把其實質的系統找出來。這就要求書寫者有很強的思考能力、聯想能力和概括能力,從古人的說法中琢磨出古人的想法。借用司馬遷的話說,叫做“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同西方哲學專著相比,中國古人的書比較難讀。不讀書,當然無法立意;死讀書,也無法立意。二是了解最新的研究情況,掌握二手資料。書寫者有了“意”,還要判斷此“意”是否值得“立”:如果有“新意”,當然值得“立”;如果沒有“新意”,別人早已談過,那就只好放棄。要想作出如此判斷,前提在于了解別人關于此問題或人物的研究情況,做到心中有數。立意大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人無我有型。選題屬于全新的性質,填補空白,有開拓性,值得去做。這叫做新題新作。一種是人有我優型。雖有人做過關于此專題的研究,但并不到位。研究者找到了新的視角,找到了向深處推進的路徑,確信可以發人所未發,也值得一做。這叫做老題新作。如果情況不明,自以為有新意,其實是炒剩飯,那么,在立意這個環節就已經失敗了。如果硬寫下去,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立意是從事研究的第一個環節,也是最困難的環節。一方面要有學術積累,另一方面還要有靈感。只有積累沒有靈感,無法立意;沒有積累,靈感也無從產生。積累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料積累,認真讀書,摘錄研究對象最具代表性的觀點;二是思想積累,把自己的研究過程中點點滴滴心得都記錄下來,并且時常回味一下。在這兩種積累的基礎上,還要苦思冥想,融會貫通,力求進入“豁然開朗”的境界。這就是靈感。有了靈感再動筆,自然文思泉涌,猶如陸游所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靈感的出現有突然性,著急也沒有用;有了靈感如果不及時抓住,瞬間便會消失。書寫者有了立意,便可以進入寫作過程了。立意只是初步的想法,不必糾纏于細節。在寫作過程中,所立之意,便會一點一點地清晰起來。
(二)命題命題是立意最濃縮的表達。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學術專著,都應該有一個得當的題目,這就是命題。為論文或專著找到一個醒目的題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反復推敲琢磨。修辭學家把題目比作“文章的眼睛”,是很貼切的。題目過于平庸,就好像眼睛沒有光澤,不會有吸引力。題目吸引不了編輯的眼球,恐怕得不到發表的機會;吸引不了讀者的眼球,恐怕就不會形成社會影響。舉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論蛤蟆四條腿》,這篇文章誰也不會去讀,因為那是常識,誰也不會覺得有“論”的必要;倘若改為《蛤蟆為什么四條腿》,把陳述句改為用疑問句,或許有人就會感興趣,覺得你會講出一番道理來。學術論著的命題原則,講究消極的修辭方式。題目要求簡潔明了,富有創意,富有吸引力,但不能過度花哨。學術論著的命題原則與文學作品不同,后者講究積極修辭。學術論著的題目通常是的短句,不用單詞,不用模糊性吸引讀者;文學作品可以用單詞,可以用模糊性吸引讀者。比如,可以用《孔子》為題,寫小說或電視劇。寫學術論著不能這么辦,題目一定要用《孔子評傳》或者《論孔子》。題目也可以采用正副標題相配合的形式,正標題可以籠統一點兒,副標題則必須明確。例如,正標題是“理學的開山”,而副標題則是“周敦頤思想研究”。書寫者在立意的基礎上,可以多想幾個題目,等到定稿時,最后敲定其中自己最滿意的一個。
(三)寫作進入論著寫作階段就是把所立之意進一步具體化。寫作離不開兩大基本要素,一是遣詞,二是造句。學術論著用詞以消極修辭為主,即要使用哲學術語、專用語匯和抽象的范疇,但適當運用一點積極修辭的手法,也未嘗不可,這能避免行文過于晦澀,但不能過分,否則就不像學術論著了。有些哲學術語沒有統一的定義,各種說法會有分歧,可以采用自定義的方式處理。例如,“本體”一詞在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中的用法不同。在西方哲學中,本體與現象相對而言,本體真而不實,現象實而不真;本體在現象之上或者現象之后。在中國哲學中,本體與本然同義,與虛假相對而言,不與現象相對而言,不認為本體在現象之上或者現象之后。研究者選取哪種說法,一定要申明選擇的理由,界定清楚。一旦選定,就得遵循同一律,全書都是一種用法,不能再變了。如果變來變去,會把人弄糊涂。學術論著一般具有創新性,當現有的語匯不足以表達新意的時候,可以創造新的語匯。有些學術論著的新意,主要體現在書寫者創立的新詞匯上。例如,張立文教授創立“和合學”一詞,“和合學”便成為他的思想標志。在創立新語匯的時候,一定要界定清楚,力求使之得到讀者的廣泛認同。創立新語匯或許不算太難,而使大家接受你所創立的新語匯則并非易事。
總之,在書寫中國哲學史中,應當注意上述幾個方面方法。哲學在途中,作為家族成員之一的中國哲學也在途中,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自然也在途中。筆者希望從業者在研究中國哲學史的路途上,探索到更新、更好、更科學、更有效的方法,推動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百年”或許太久,一代學人有一代學人做學問的方法,恐怕理當如此。
作者:宋志明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 上一篇:文學家的哲學思考范文
- 下一篇:方東美哲學的理論研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