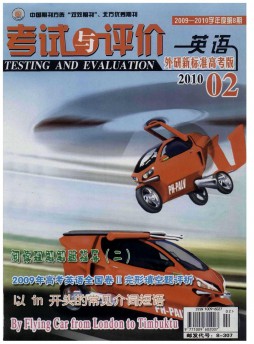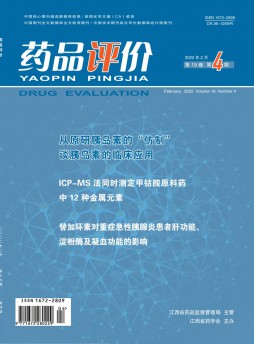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作用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作用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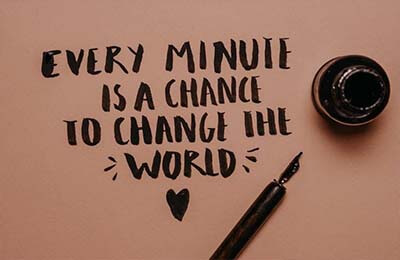
一、現有文獻概述與批評
現有的研究文獻絕大多數遵循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們接受這樣的假定,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意義,是代表了接受體的資金和技術資源的一種“凈增加”。這種分析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將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總量的主要指標的比率簡單標示出來,然后“讀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由此得出判斷,按照國際標準,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對較小,進入1990年代以后就開始大幅度上升。這些研究同時發現,在日益擴張的中國外貿出口中,外資企業所占份額也在急劇上升。這兩項指標,對于迅猛發展的沿海地區省市表現得尤為顯著(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種方法,可以說是第一種方法的補充,主要專注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各項指標之間關系的回歸分析。這種分析意在檢測外商直接投資對可觀測的指標,如GDP增長等的間接影響,這種影響在在第一種分析中不能夠顯示出來。另外也試圖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那些不可觀測的指標,如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影響。這些分析發現對于各種不同的回歸模型結果各異,但總體結論是,相關性都表現為正,而且在統計上顯著。其中最樂觀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年增長達2.5%,加上外商直接投資通過資本形成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總貢獻在1990年代年平均達3%,也就是占整體經濟增長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類研究還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量與國內總投資增長也是顯著的正相關。他們將這個結果視作是投資“擠入效應”的證據(Kueh1992;Zhan1993)。
在較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種方法的應用較為普遍,主要應用于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即進行個別區域分析或跨區域比較。很明顯,吸引較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現出較快的經濟增長。這些分析的典型結論,都是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影響,包括地方資本形成、地方投資的“擠入效應”、地方生產技術或知識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由此得出的推論是,外商直接投資解釋了不同地區或省份的不同經濟增長表現,對總體中國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現存這些文獻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顯的,在它們的分析中,因果關系和相關關系很難區分開來(Lietal.2002)。這個問題可以說貫穿所有的現存文獻,但在區域和跨區域回歸分析中尤其嚴重,因為所分析的這些區域與其他區域畢竟屬于同一國家、同一種體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環境),使用同一貨幣。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存在著眾多的機會,可以透過創造租金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尤其是在各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別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增長確實存在正相關,也難于判斷地方經濟增長到底是來自生產率的改進還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租金轉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極端情形是,租金創造效果如果超過生產率的改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對中國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就有可能為負而非正。
從上文的討論可以得出一個普遍論斷,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現有的文獻中,有關外資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具體機制,究竟主要是透過促進生產率進步抑或是創造租金的問題,往往會在回歸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聯立方程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測也是如此,問題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資引起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問題是,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創造租金還是通過生產率改進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因此,關鍵是要將有關兩者的相關性的分析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定路徑相聯系,在這個特定路徑中,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影響的機制必須要能夠準確地識別和評估。
要將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分析與中國特定發展路徑聯系起來,邏輯上就必須超越純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唯一指引的視野,訴諸更寬泛的理論框架。在相關理論文獻中,與新古典傳統相對,還有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它們并不否認外商直接投資可以體現為額外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然而它們更加強調外資的其他特性,這包括外商進入國內市場的模式、技術轉移的類型、塑造國內市場競爭模式的制度和結構環境,等等,認為這才是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后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且其影響往往是負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關的中國研究文獻中,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結論不盡全面、合理。
二、宏觀指標的直觀判斷
從宏觀指標的直接觀測結果看,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總體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觀點,并沒有得到經驗支持。作為固定資本形成的一個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在1979-1991年期間的年流入量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相比還是極其微小的,只有從1992年開始才大幅度增加。從1992年至2006年,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之比年均約為12%,從國際背景來看,大約是同期所有發展中國家平均值的兩倍。盡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所占的份額同樣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斷言,從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來促進GDP增長,其貢獻每年應該不超過一個百分點。
概念上,上述指標存在著三方面的局限性,從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第一,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并不反映資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因為對資本形成的貢獻除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外,還有來自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利潤再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與資本形成的比率這個指標,本身并沒有涵蓋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投資“擠入效應”。第三,這個比率并沒有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無法觀測的影響。
對第一點來說,要加以確證必須進行企業層面的調查,但這是不可行的,因為這樣的數據根本無法獲取。直觀判斷,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規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資企業在全部企業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僅達11%,因而,凈利潤再投資即使確實是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只能是近年來的事。同樣地,就第二點來說,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各種微觀經濟主體的一個典型化特征,是表現出過度沖動的投資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任何可能的“擠入效應”也僅在近年內才有意義。就第三點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這是現有文獻關注的焦點。部分研究是從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能夠帶來外匯的角度來考慮,而外匯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為技術進口提供資金來源,這些技術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機械設備或工業投入品中。還有部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改進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行業或區域的效率來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其作用機制包括技術轉移、促進經濟制度和結構的轉變、等等。
即使將因果關系問題、可出口品的競爭問題擱置一邊,從現有數據推斷出外資企業為中國外匯收入的增長起主要作用,這仍是頗為夸大失實。事實是,外資企業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過40%,2001年超過50%;然而,觀察各年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外資企業的進口份額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資企業每一年都存在相當規模的外貿赤字,形成對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國貿易表現順差。盡管外資企業從1998年以來一直享有順差,但這些順差僅占國家總順差很小的一部分。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的部分進口是隨同投資一起進來的生產設備,在這一點上,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可能貢獻可歸結為兩種形式:一是對使用進口設備的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的技術轉移,另一是,在長期上促使外資企業成為凈出口者,只是,這種前景迄今為止始終還只是潛在可能性。與此相關的話題是,外資企業以什么形式來實現外貿擴展?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占主導的外貿出口是加工貿易,這主要是由于外資企業的進出口活動所從事的主要是加工貿易。從加工貿易的生產特性看,加工貿易的增加值率(這里定義為凈出口對出口總額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勢頭,1998年以后則停止上升,基本維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國對外貿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貿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這么低的水平,這與中國追求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不相符的。
現在我們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透過改進經濟效率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主流理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以下列幾種形式發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資接受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對同行業或相關聯行業的其它企業產生溢出效應,根據“稟賦”比較優勢原則實現經濟結構轉變,按市場原則實現制度轉變,等等。這些理論觀點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實現,這些凈效果主要表現在與中國其他行業相關的整個外資企業部門的績效上。圖1標示出外資企業相對于工業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可以注意到相對勞動生產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間表現出長期的下滑趨勢。從表面判斷,這種趨勢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中國按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結構轉變的論題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國現有的“廉價勞動力”(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優勢進行產業轉變。這種趨勢也與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傾向于使勞動非技能化的理論相一致。換句話說,這種傾向的結果很有可能是改進了資源配置效率而同時削弱了生產效率。這就有必要去考察總的效率指標,這個總效率指標一般用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比率的演化來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和外資企業的大幅度增加這個長時期內,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序列也表現出相同的下降傾向。這就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損失已超過了資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書率的所得,由此,這就很難給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作一個正面的評價。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外資企業的相對效率確實是在下降,那為什么中國工業中外資企業部門所占的份額卻在不斷的擴大?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對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決策機制作進一步的考察。但這個答案有可能與勞動補償有關。眾所周知,由于進入該部門的產業工人無限的供給,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部分勞動密集、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的工資水平基本維持在一個低水平上不發生變化。圖1顯示,外資企業相對整個工業企業的相對平均工資率一直表現為下降傾向。這種狀況說明,盡管相對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為惡化趨勢,外資企業仍是有利可圖。這種傾向自身就意味著,對整個中國經濟來說,與外資企業部門膨脹相關的發展是不能作為效率判斷的依據。首先,我們對1991-2005年期間中國35個工業行業的相對生產率作一比較。觀察外資企業所占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那些行業的數據,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涉及外資企業的行業分布與有關行業的技術特征。理論上,主流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激進學派的“勞動的新國際分工”理論都認為,外資企業既然是市場導向的,那么它們應傾向于集中在中國的勞動密集工業行業。這與現實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貿易分析文獻中,通常將勞動生產率低于0.9的行業列為勞動密集行業。按照這個標準,在2005年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1個行業可以列為勞動密集行業,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點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主流理論一般傾向認為,外資企業占主導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這反映出它們采用了更多的勞動密集性生產技術。這一點與現實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討論的17個工業部門,在1991-2005年期間,有13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出現了負增長。這種績效與資源配載效率改進的預期是一致的。然而,這種績效與激進理論的勞動非技能化假說也是相符的;激進理論認為,外資企業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一般傾向于延緩勞動生產率的改進。
第三點是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工業效率的總體影響。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數值的表現上。可以觀察到,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這個指標對應的是整個中國工業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體經濟因素效應,而強化了行業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業因素的效應。這個指標大體上能捕捉到一些有關技術轉移、行業間和行業內的溢出效應、市場制度的改進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結果可以與主流文獻形成較好的對照:在外資企業占主導的17個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在1991-2005年間全要素生產率相對值出現了負增長。很明顯,正如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說,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對中國工業效率存在正的影響,但是,現實情況同樣符合結構主義和激進理論所判斷的負面影響,綜合而言,占主導的是負面影響。
我們還可以對1991-2005年期間30個省區的工業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資企業在空間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僅有6個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廣東、福建)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在這個背景中,所涉及的這6個省市的績效與行業分析結果略有不同。從相對勞動率標準判斷,1991年這6個省區的工業都不能視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到2005年,6個中有2個(廣東和福建)轉變成為勞動密集型。因為這兩個省的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比重確實遠比其他省區高,或許可以說,在空間分布上,外資企業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與此同時,從空間分布看,外資企業也確實表現出有利于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六個省市中有4個在1991-2005年間相對勞動生產率都出現負增長,僅有天津和江蘇例外。恰恰是這兩個省市在1991-2005年期間出現相對全要素生產率為正增長,而其余4個省則出現負增長。顯然,這些區域數據分析結果,大致上與行業分析結果相同。
行業-區域分析結果顯示,中國的實際情況,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理論預期,但是,由此就認為整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強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這卻是不符合事實。上文的分析結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論斷,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以及外資企業的運作有助于工業行業和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這些結果同樣符合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導致勞動生產率進步停滯、以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關于外資企業有可能扭曲行業或區域的經濟結構的批判性論斷。上文的分析結果,是大部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的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出現負增長,這意味著,總體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始終還是偏向于負面的。
最后,作為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行業-區域分析的結束部分,下文試圖對行業-區域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上文的分析僅僅考察了外資企業占主導的行業和區域,而不是全部數據,這對于總體上分析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表現來說,關注面可能顯得過于狹小。從另一個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顯得過于一般化,因為分析其實只是考察了有關行業-區域的特有因素對它們的相對生產率表現的影響,卻并沒有從各種特有因素中特別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資企業增加值比重這個因素。對總體數據的統計分析有可能彌補這兩方面的不足。特別地,可以假定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工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A)由行業或省區的總規模(由總增加值V表示)和行業或省區外資企業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決定,即:
lnA=a+blnV+c(Vf/V)
從兩方面來看,這個分析框架應該是可取的。其一,將V作為A的解釋變量,意味著該分析考慮到了行業或省區的特定增長路徑,即考慮到可能存在著規模經濟或集聚經濟;其二,在進行跨區域的比較中,這種分析將有助于檢驗由外商直接投資所產生的部門內溢出效應、以及外資促進結構和制度變動的效果。這是因為,這種溢出效應和變動一般應該是主要在同一個省區之內發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變量Vf/V反映的是外資企業在一個特定行業或省區滲透的累積效應,對2005年一年數據的分析,將能為判斷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工業中的累積影響提供一個推斷依據。結論
現有主流研究文獻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它們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資的性質是代表了對接受經濟體而言是一種“凈增加”的資金、技術或制度資源,相應地,它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評價只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純粹依系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觀點顯得關注面過于狹小,由此衍生的判斷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實上,相關的理論文獻中,同樣存在著其他理論傳統,它們并不將外商直接投資僅僅視為可以利用的新資源,而是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還承載著其他特性,有可能對后進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本文試圖超越狹窄的純粹新古典經濟學框架,訴諸于更為寬廣的理論文獻,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我們的主要分析發現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的的確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卻又惡化了生產性效率,而兩者綜合起來的作用應該是傾向于負面的。
上文談及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整個外資企業部門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進而分析那些外資企業所占比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工業行業和省份的相對經濟績效表現。在某個行業或省份中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比重這個指標,所顯示的,是從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資在該個行業或省份的累積滲透,因此,分析這個指標與這些行業或省份的績效之間的關系,將有助于測試主流經濟學關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技術轉移、溢出效應、制度和結構變遷等等改進效率論述的假說,也有助于考察結構主義關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扭曲或扼殺國內產業發展的假說,以及激進主義的勞動非技能化假說的現實解釋力。
內容摘要:近年來,在世界范圍上,中國被廣泛地認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主流文獻應用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得出結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透過資本形成、出口擴張、技術轉移和推動經濟結構和制度轉變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本文則從涵蓋結構主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等學派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和后進發展研究的一個多方位視角,來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通過比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確實促進了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卻妨礙了生產性效率的提升、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消極影響,綜合而言,總的效應卻應該是偏向于負面的。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相對生產率,比較優勢,經濟發展
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