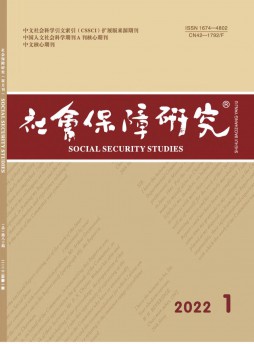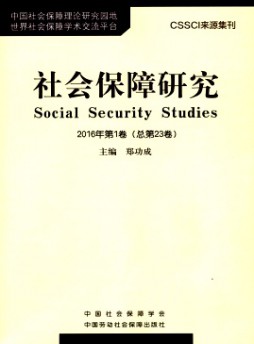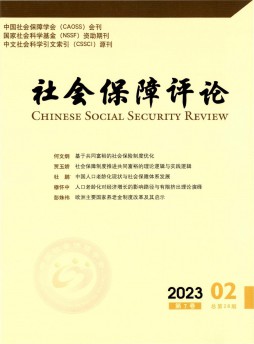社會保障對國內養老保險革新的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保障對國內養老保險革新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由于生活中總是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確定的風險,工業社會、特別是現代化的機器大生產時代更加劇了這種風險的侵害性。由于很少有人能夠對抵御這種不確定的風險做好充分的準備,或者由于個體稟賦等方面的差異更增加了歷受這種風險的可能性,政府施予“能夠減輕個人既無法防范、又不能對其后果預作準備的災禍的公共行動”是應當并可行的。但是意在避免收入減少的保障,或者說給予一切人或一部分人以一定收入的保障,則對自由具有潛在的危險,因為“在任何一種人們在各種不同行業之間的分配依靠這些人自己來選擇的制度下,都必須使這些行業的報酬符合于它們對社會其他成員的有用性”。
這是常態,但可能并非總是如此,也可能有一些意外情況發生。“盡管一個人努力工作,盡管他有特殊的技能,但他卻會受到不是他自己的過失造成的收入的急劇減低和痛苦的失望,這無疑是有傷我們的正義感的”。這些遭受不幸的人會要求國家進行干預,以維護他們的合法愿望。國家干預的結果是,不但保護受到這種威脅的人們免受嚴重的困苦和貧乏,而且還會使他們繼續獲得與從前一樣的收入和保護他們不受市場變遷的影響。這樣發展的結果是這部分群體享受的保障慢慢地成為一種特權,這種特權的存在是以犧牲他人利益為條件的,因而就必然會減少別人的保障,甚至危害到自由。此時,“報酬就不再和實際用處必然相關,報酬的差別就不能成為一種有效的誘導,使人們做出社會所需要的變動”。國家把有保障的特權給與某一個集團時,集團外人們的不安全感就必然增加,這樣就很快造成一種對保障的追求比對自由的熱愛更日趨強烈的局面。
“保障越具有特權的性質,而沒有特權的人所面臨的危險就越大,保障就越為人們所珍視。隨著有特權的人數的增加,在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無保障之間差別的增加,就逐漸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會價值標準。給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個青年人擁有領得年薪的確定權利比對他懷有飛黃騰達的信心更是其結婚的資格,而無保障則成為賤民的可怕處境,那些在青年時就被拒絕于受庇護的領薪階層之外的人,要在這種處境下終其一生”。
因此,政府選擇適當的社會保障的政策目標是十分重要的。政府應當提供的是那種“獨立于市場的、能讓競爭自然地進行而不受到阻撓的、不損害自由保障”。“為了保存自由,某種保障也是不可少的,因為大多數人只有在自由所不可避免地帶來的那種風險不是太大的條件下,才愿意承擔那種風險”。哈耶克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并不是一個偏激主義者。相反,他看到了福利國家的過度保障對自由的侵害,對經濟秩序的破壞。他的預言在歐洲國家相繼得到了應驗。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這些國家開始反思其實施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并陸續進行改革調整。我國的社會保障計劃起步晚,自然不存在西方國家意義的“過度福利”問題。但是如果仔細剖析的話,我國現在的社會保障政策問題則更為復雜和嚴重。
一、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審視
從經濟學角度講,養老保險是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外部性和非競爭性,市場無法有效解決其資源配置問題,所以,對于養老保險產品的提供政府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政府也存在“失靈”,并帶來配置無效率問題,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又對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解析了市場提供公共產品的效率問題。“對于養老金制度,現代公共品理論普遍認為,政府應提供公共養老金制度以致力于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實現收入再分配;而非政府提供的私營養老金制度能更好地增進制度供給效率,即提高管理效率。因此,通過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既能實現再分配效率,又能提高管理效率,促進養老保障資源的合理配制,增進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因此,世界銀行提出了建立包括公共養老金(國家財政)、強制性私人養老金(企業)、自愿性私人養老金(個人)在內的三支柱養老保障模式;國際勞工組織提出了包括公共養老金(政府財政,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公共養老金(政府財政,主要是再分配)、強制性私人養老金(企業)、自愿性私人養老金(個人)的四層次養老保障模式。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因國民身份的不同被人為地區隔為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和農民等板塊。目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基金由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以及政府補貼組成;城鎮居民主要由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組成;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由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組成,資金來源相對多元化。國家機關中公務員的養老金完全來自于各級財政,單位和個人均不繳費。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保險制度一直以來參照公務員的養老保險模式,資金全部來源于各級財政,單位和個人不負繳費義務。2008年,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開始試點改革,資金的籌集方式與待遇發放標準試圖與企業看齊,但改革受到阻滯。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險現狀,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是,以身份為標準的養老保險區隔導致了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呈“碎片化”管理狀態,嚴重地阻礙了我國統一的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不利于社會成員的合理流動。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1951年,頒布了我國第一個社會保險法規———《勞動保險條例》,初步確立了企業的社會保險制度。自20世紀90年代起,國家開始因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求對傳統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通過。《社會保險法》依據戶籍和身份把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劃分為幾個獨立的系統: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每種類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機制和待遇水平各不相同。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則因“職員”的“干部”身份不同于企業致其繳費機制和待遇水平完全不同。國家在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系統改革的同時,開始了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不斷探索。
但從實踐來看,改革舉步維艱。這種因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對養老保險體系的人為區隔固化了社會成員的身份差別,強化了身份差異對養老保險待遇水平的影響。不同系統的養老保險制度運營機制不同,各系統間接洽的平滑機制欠缺,造成社會成員間的流動渠道不暢、流動成本過高。同時,保險待遇水平的差異致使體制內的人因“放不下”而錯失個人價值的更大實現,而體制外的人因“攀不上”只能望洋興嘆。二是,國家機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保險長期以來實行單一支柱型的繳費機制,養老保險待遇大大高于企業職工,不但加劇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還進一步固化了國民的身份與社會的不公。而且,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采取與企業并同的改革模式,不但違背了福利剛性原則,而且沒有體現人力資本投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適度誘導作用。身份不同,社會成員的養老保險繳費義務也不同。城鎮職工、城鎮居民、農村村民分別負有程度不同的繳費義務,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長期以來以“干部”身份存在,不負有繳費義務,其養老保險由國家財政統一負擔。這種單一支柱型的繳費機制隨著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能的擴大和編制的增多以及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帶來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與繳費負擔輕重相反,公務員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金替代率遠遠高于企業。“到2004年,中國企業、事業和機關單位養老金替代率分別為52%、90%和93%”。
2008年啟動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試點改革無論從繳費機制還是保險待遇水平方面都有與企業看齊的跡象,因此被廣泛質疑并遭受抵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待遇比上(公務員)不足,比下(低收入企業)有余,而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卻沒有明顯預期,自然會成為攀比對象;況且,“與企業相比,企業可以搞活,工資上不封頂,工效掛鉤,尤其壟斷性行業和企業的退休金要遠遠高于事業單位,而事業單位退休金只是一個能‘過得去’的平均數,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業看齊,退休后卻要向低收入企業看齊”。這是事業單位倍感不公平的原因。因此,遭受抵制是必然的。“人力資本是勞動者所擁有的、未來某時刻參與社會生產時、預期‘勞動生產率’的折現值”。
種類繁多、門類齊全的事業單位是專業技術人員的主要集中地。為了能夠承擔起相應的專業技術職責,這些人員前期往往進行了大量的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接受更多的專業技能培訓,獲取更高的學歷。依人力資本理論,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成本和厚實的人力資本存量一般應該獲得較高的社會回報(包括勞動報酬),這樣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優化成員的價值追求。然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改革向企業看齊的做法,沒有很好地體現人力資本投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適度誘導作用,是有違常理的。
二、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路徑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應當既能提供哈耶克社會保障思想中的“最低保障”,又要避免某些領域的“過度保障”,從而使得養老保險體系變得更加和諧起來。
首先,應當建立起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國家財政應當充分發揮財政普惠作用,適當提高政府財政收入對養老保險事業的支持力度,為國民提供最基本的養老保障,不應把社會保障責任都加在企業身上。在調動個人儲蓄在養老保障中的積極性的同時,要充分展開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制度,充分發展商業保險,以提高有具備條件的主體能夠通過自己的投入享受到較高的養老保險待遇。當然職業年金和商業保險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還需要以居民收入作為參數,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才有保證對養老保險資金的投入,否則,養老保險待遇的提升只能是“無米之炊”。
其次,盡量整合養老保險制度的“碎片化”現狀,逐步建立起能平穩、有效銜接的系統化的養老保險體制。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公平的制度環境。如果說因身份不同造成的養老保險適用區隔是由種種歷史原因造成的話,那么,除因特別需要外(如國家公務員的特殊性),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就應該逐步縮小這種制度設計的人為因素影響的待遇差距,確立一種相對公平的標準,以營造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再次,要尊重歷史,充分考慮事業單位養老金對于人力資本投入與個人工作周期的收益補償。我國養老保險背負著巨額的隱性債務,這筆隱性債務的產生歸根到底是由于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對養老金進行儲蓄而造成的。
建國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財政稅收主要用于工業建設,發展國民經濟,忽略了對未來也就是今天人口老齡化的資金儲備。而在那個時期,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普遍較低,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逐步告別低工資時代。所以國家在建設時期的資金來源,可以認為其主要部分來源于“老人”和“中人”在幾十年的工作生涯里以低工資為代價向國家預付的養老金的積累。既然如此,我們又有何理由要求這些隱性債務的實際債權人“二次支付”呢?
哈耶克并不是一個偏激主義者,他看到了國家的過度保障對自由經濟的破壞,從而展開了對“福利國家”的批判。在他看來,適度的保障是可行和必要的,但過度的保障會固化社會結構,催生利益保守群體,并引起社會的不公。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既要普化養老保險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同時,又要恢復養老保險的共濟本性,改變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現狀,提高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系統性。
作者:李秀鳳單位:濟南大學法學院
- 上一篇:電視新聞導語情節化寫作方式解析范文
- 下一篇:當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體系的探新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