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古典時(shí)代的蠻族觀念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希臘古典時(shí)代的蠻族觀念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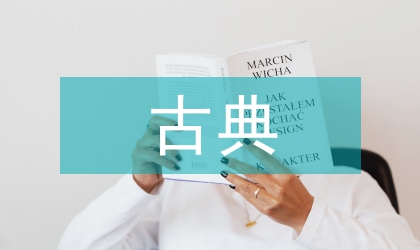
血緣在希羅多德提到的標(biāo)準(zhǔn)中居于首位。不過,排列順序并不能證明血緣一定是最重要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希羅多德所提到的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的重要性依次遞增,血緣反處于較弱地位③。然而,早在古風(fēng)時(shí)代血緣對希臘人認(rèn)同就有重要意義,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jì)左右,希臘人內(nèi)部已構(gòu)建起以希倫為共同祖先的譜系①,將所有希臘人都視為希倫的子孫,這一點(diǎn)在古典時(shí)代也常被人提及②。它是希臘人內(nèi)部團(tuán)結(jié)的基礎(chǔ),也是希臘人與異族區(qū)分的標(biāo)志。希羅多德自然了解這一點(diǎn)。作為關(guān)注各民族歷史的學(xué)者,希羅多德重視民族的起源。但無論是對希臘人還是對異族血緣的探討方面,希羅多德都表現(xiàn)出了某些與希臘傳統(tǒng)不同之處。他曾提到希臘人的族群起源:“在多里安人中的主要人群是拉凱代孟人,而伊奧尼亞人中的主要人群是雅典人,在古代伊奧尼亞人的祖先是皮拉斯基人,而多里安人是希臘人。”③希臘人內(nèi)部存在多里安、伊奧尼亞等次一級群體,這是希臘人的共識(shí),也與希倫譜系相一致,由此希臘人認(rèn)為多里安、伊奧尼亞等次一級群體之間具有共同血緣,這也是前述“全體希臘人在血緣方面有親屬關(guān)系”的原因。而希羅多德認(rèn)為伊奧尼亞人和多里安人有不同的起源,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雅典人和斯巴達(dá)人的血緣關(guān)系。更重要的是,作為皮拉斯基人的雅典人原先并非希臘人,但卻可以轉(zhuǎn)化為希臘人。這說明希臘人和其他民族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界限。因此,以血緣判定是否屬于希臘人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效力。由此,希羅多德在血緣問題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在觀念中仍然承認(rèn)希臘人之間的虛擬血緣對自身認(rèn)同以及與蠻族的區(qū)別有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作為歷史學(xué)之父,他又在不斷探求希臘人和蠻族真實(shí)的血緣演變,并在此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以血緣為標(biāo)準(zhǔn)識(shí)別民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作為希臘人與蠻族的界限。此時(shí)他只能將目光轉(zhuǎn)向其他方面。
希羅多德在書中不止一次提到語言在民族識(shí)別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提到:一只從埃及飛來的鴿子口吐人言,命令希臘人建立一座宙斯神諭所。他本人對這個(gè)傳說不以為然,因?yàn)轼澴硬豢赡苷f話,真實(shí)情況應(yīng)是埃及人來到了希臘人當(dāng)中學(xué)會(huì)了希臘語④。不過,這暗含了希臘人對外族語言的認(rèn)識(shí):蠻族語言與希臘語的區(qū)別等同于鳥語與人類語言的差異,語言差異中已蘊(yùn)含著希臘人對異族的歧視。語言作為民族區(qū)分標(biāo)志和證明希臘人優(yōu)越性的證據(jù),此觀念與“蠻族”(bar-baros)一詞的希臘語起源密切聯(lián)系,它最早就是指那些說不好希臘語的人⑤,至古典時(shí)代它的含義雖然有擴(kuò)大,但并未徹底擺脫源始含義,因此希羅多德持有這種觀點(diǎn)并不足為奇。他在《歷史》中還提到,其他民族中也有稱使用外族語言的人為蠻族的現(xiàn)象,埃及人就將使用包括希臘語在內(nèi)其他語言的人稱為蠻族⑥,說明希羅多德認(rèn)為以語言區(qū)分異族不僅是希臘人的意識(shí),而且是人類社會(huì)的普遍觀念,語言標(biāo)準(zhǔn)的作用由此擴(kuò)大到了全人類。不過,語言是阻礙民族交流的障礙,也具有后天可學(xué)習(xí)的特性,因此可以成為民族身份轉(zhuǎn)變的因素。希羅多德提到,皮拉斯基人轉(zhuǎn)化為雅典人的標(biāo)志就是學(xué)會(huì)了雅典語言⑦。因此,語言對于民族識(shí)別也就具有了兩面性:一方面,它仍然是區(qū)別不同民族的標(biāo)志;另一方面,它又成為實(shí)現(xiàn)民族身份轉(zhuǎn)換,特別是蠻族人向希臘人轉(zhuǎn)變的重要手段。由此,語言作為決定是希臘人還是蠻族身份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可能還高于血緣。
宗教與祭祀是希羅多德在民族問題上確立的另一標(biāo)準(zhǔn)。他在《歷史》中也確實(shí)對宗教信仰予以關(guān)注,特別對波斯、埃及等國的宗教詳加介紹。他認(rèn)為,宗教活動(dòng)對希臘人與蠻族的區(qū)別有重要作用。《歷史》中提到:“波斯人所遵守的習(xí)慣,據(jù)我所知是這樣的:他們沒有設(shè)立神像、神廟和祭壇的習(xí)慣,而認(rèn)為作這些東西的人們是愚蠢的。在我看來,這是因?yàn)樗麄儾幌裣ED人那樣相信神和人是相似的。他們將整個(gè)天空稱為宙斯,到群山的最高峰上向其獻(xiàn)祭。他們同樣地向太陽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風(fēng)奉獻(xiàn)犧牲。這些神是他們僅有的那些從最初就開始獻(xiàn)祭的諸神。后來他們又向亞述人和阿拉伯人學(xué)習(xí),又崇拜‘神圣的’阿弗洛狄忒。她被亞述人稱為米利塔,被阿拉伯人稱為阿利拉特,被波斯人稱為米特拉。”⑧希羅多德認(rèn)為,在宗教信仰領(lǐng)域,波斯人與希臘人存在著很大差異。他指出,在某些細(xì)節(jié)上,如神像、神殿、祭壇等是希臘人宗教崇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卻都被波斯人視為愚蠢行為,這就表現(xiàn)出二者在宗教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希羅多德雖然未明確地以宗教區(qū)分波斯人和希臘人,但在描述中他總是有意識(shí)地以希臘人的宗教活動(dòng)為參照物,與波斯人的宗教作對比,從而構(gòu)建出二者的對立。可見,希羅多德對以宗教區(qū)分希臘人和蠻族的重要性有一定認(rèn)識(shí)。除了祭祀之外,從古風(fēng)時(shí)代開始運(yùn)動(dòng)會(huì)就對區(qū)別希臘人和異族有重要作用,而運(yùn)動(dòng)會(huì)往往與宗教圣地相聯(lián)系。《歷史》中的運(yùn)動(dòng)會(huì)也可以反映出民族觀念,馬其頓人亞歷山大試圖參加奧林匹亞運(yùn)動(dòng)會(huì),但被希臘人拒之門外,理由是該項(xiàng)活動(dòng)只對希臘人開放,而亞歷山大只有在證明了希臘血統(tǒng)之后才得以參加運(yùn)動(dòng)會(huì)①。盡管希羅多德記載此事可以證明血緣的重要性,但也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出此類運(yùn)動(dòng)會(huì)與血緣相結(jié)合,帶有明顯的排外性質(zhì),將蠻族人與希臘人區(qū)別開,而這種作用也被希羅多德所認(rèn)可。運(yùn)動(dòng)會(huì)也同祭祀活動(dòng)一樣,成為了希臘人同蠻族之間的界限。
不過,希羅多德認(rèn)識(shí)到希臘人和蠻族在宗教上的差異并非絕對。在考察中,他不得不承認(rèn)東方文化,特別是埃及的宗教對希臘人有重要影響,二者之間有很強(qiáng)的一致性。例如,埃及人創(chuàng)造了十二神祇,修筑祭壇等行為都被希臘人模仿,甚至古希臘神靈名稱也有很多輾轉(zhuǎn)來自于埃及②。這些都對以宗教劃分希臘人和蠻族的觀念提出了挑戰(zhàn),但希羅多德還是如實(shí)地將其記錄在《歷史》中。
在希羅多德的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中,生活習(xí)俗最受其重視。有學(xué)者稱,希羅多德就是一位人類學(xué)家,總是在不斷觀察著其他民族的生活習(xí)慣,并用希臘人的眼光將其描述出來③。比如他曾描述埃及人的生活習(xí)慣:“他們中間,婦女從事買賣,男子則坐在家里紡織,其他人紡織時(shí)把緯線拉到上面去,而埃及人則拉到下面來,男子用頭頂著東西,婦女則用肩膀挑東西,婦女小便時(shí)站著,男子小便時(shí)卻蹲著———婦女不能擔(dān)任男神或者女神的祭祀,而男人則能擔(dān)任男神或女神的祭祀,兒子不被強(qiáng)迫贍養(yǎng)老人,而女兒即使不愿意,也必須贍養(yǎng)雙親。”④在希羅多德看來,埃及人此類習(xí)慣非常值得注意,它們恰恰與希臘人相反,對希臘人而言屬于陌生的事物。類似現(xiàn)象在其他人群中也存在。盡管他在介紹完這些人的習(xí)慣之后,總是用關(guān)于埃及人或者其他民族的習(xí)慣,“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來結(jié)尾,但作為經(jīng)歷豐富的歷史學(xué)家,希羅多德所了解的信息不止于此,而他常常挑選這些內(nèi)容進(jìn)行記載,說明他的關(guān)注點(diǎn)并非是所有的蠻族文化,而僅僅是蠻族習(xí)俗中與希臘人明顯不同的現(xiàn)象。因此,這類記載就擺脫了單純的歷史學(xué)研究,而具有了更深刻的含義:以希臘人的習(xí)慣為參照考量其他民族的習(xí)慣,對其中的差異予以重點(diǎn)關(guān)注。生活習(xí)慣成為了希羅多德區(qū)別希臘人和蠻族人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很多。雖然希羅多德很少直接提到某種或某類習(xí)慣是希臘人所特有的,可以作為希臘人和蠻族之間區(qū)分的標(biāo)志,但他對蠻族習(xí)慣的介紹方式中就體現(xiàn)了希臘人和蠻族對立的觀念。因此,生活習(xí)慣同其他成分一樣,就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希臘人的形象⑤;同時(shí)又是一種手段,有助于構(gòu)建蠻族觀念。
不過,希羅多德雖然將生活習(xí)慣看作希臘人和異族的區(qū)別之一,但很少直接批評其他人群的生活習(xí)慣,而是以包容態(tài)度去看待他們。這與希羅多德對習(xí)俗本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密不可分。學(xué)者們習(xí)慣于提到《歷史》中的一個(gè)例子:波斯國王大流士曾經(jīng)考察過各地風(fēng)俗,發(fā)現(xiàn)對印度人而言,吃掉親人的尸體是正常現(xiàn)象,而火葬則是極端可怕的行徑;而對希臘人而言,情況則恰恰相反⑥。希羅多德并未評價(jià)二者的優(yōu)劣。他提到每個(gè)民族都認(rèn)為自己的習(xí)慣高于其他民族,這是人類的本性,用詩人品達(dá)的話來說,“習(xí)慣是萬物的主宰”。可見,他認(rèn)為,各民族的習(xí)俗應(yīng)該是平等的,對本民族而言都值得尊重,不存在高下之分。因此,當(dāng)他提到印度人吃逝去親人的尸體,也只是為了用新奇的材料證明自身觀點(diǎn),而并未作出明確的價(jià)值判斷。正因?yàn)橄A_多德對蠻族的習(xí)慣相對開明,并不帶有太多的歧視心態(tài),所以在某些希臘人看來顯得對蠻族過于寬容,以至于他被一些人稱為“熱愛蠻族”的人①。
埃斯庫羅斯《波斯人》中的蠻族觀念
埃斯庫羅斯是古典時(shí)代最有名的悲劇作家之一。在其代表作《波斯人》中,他塑造了以“波斯人”為代表的蠻族形象,也由此成為古典時(shí)代最早描述蠻族與希臘對立的作家之一。盡管時(shí)至今日仍然有人懷疑他的作品是否具有丑化異族的主題②,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波斯等蠻族在悲劇中表現(xiàn)出某些完全不同于希臘人的特征,這也與古典時(shí)代之前的異族形象有顯著區(qū)別③。埃斯庫羅斯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塑造著蠻族的形象。在悲劇中,埃斯庫羅斯并沒有過多強(qiáng)調(diào)不同民族在血緣上的差異。相反,他似乎有意消弭希臘人和蠻族人的血緣區(qū)別。《波斯人》中,波斯國王大流士的遺孀阿托薩夢到了兩位性格迥異的女性,她們分別代表著希臘人和波斯人,兩人的個(gè)性沖突也代表了希臘人和蠻族的差異,但她們反而被塑造為同胞姐妹④。其實(shí),希臘人和波斯人同源的傳說有悠久的歷史,也曾作為拉攏希臘人的手段而為波斯人所利用⑤。即使埃斯庫羅斯不接受希臘人和波斯人同源的傳說,但在希波戰(zhàn)爭后雙方尖銳對立的背景下,他在悲劇中加入這一情節(jié),也說明他并不強(qiáng)調(diào)血緣對區(qū)別希臘人和蠻族的作用。
宗教等因素在《波斯人》中出現(xiàn)得不多。在《波斯人》中,埃斯庫羅斯提到了波斯國王大流士的鬼魂,這種鬼魂不僅具有人的意識(shí),而且能夠“與神明同尊”,同時(shí)能夠享有人的祭品。這似乎與希臘人對待逝者的傳統(tǒng)觀念不同。不過,對這個(gè)問題還需要進(jìn)一步分析。首先,希臘人、神界限并不是那么明顯,在《伊利亞特》等史詩中,神靈同人一樣具有好惡和情感,而一些人也認(rèn)識(shí)到,希臘人也并非絕對拒絕祖先崇拜,在希臘人中也有向死者獻(xiàn)祭等活動(dòng),這一點(diǎn)與波斯并無太大區(qū)別⑥。其次,埃斯庫羅斯對東方宗教的了解程度也值得思考。盡管古典時(shí)代希臘大陸的人們對波斯等東方民族的宗教了解有限,但波斯人和希臘人之間宗教的某些相似性在古典時(shí)代已經(jīng)為某些希臘人所掌握,埃斯庫羅斯可能就是其中之一⑦。因此,他對波斯人信仰的描述可能僅是根據(jù)劇情需要,而未必包含特殊含義。特別是在《波斯人》中,他并未刻意地突出希臘宗教的特征,因此也未必有意要將希臘人和波斯人的宗教作對比。即使埃斯庫羅斯在《波斯人》中表現(xiàn)出波斯人異于希臘宗教的特色,也不能由此斷言他一定在悲劇中強(qiáng)調(diào)宗教作為區(qū)分希臘人和蠻族的手段。
應(yīng)當(dāng)說,埃斯庫羅斯對波斯人與希臘人的語言沖突有所描述。在《波斯人》中,阿托薩稱自己的聲音是“用蠻族語言”發(fā)出的⑧。值得注意的是,“蠻族”一詞在《波斯人》中出現(xiàn)了不下十次,遠(yuǎn)遠(yuǎn)超過古風(fēng)時(shí)代的總和⑨,并且已經(jīng)突破描述異族語言的意義,而成為希臘人對異族的統(tǒng)稱。因此,“蠻族語言”可能同時(shí)具有語言和民族歧視的雙重意味。不僅如此,在《波斯人》中希臘人所發(fā)出的聲音莊嚴(yán)洪亮,而緊接著出現(xiàn)波斯人的聲音則是嘈雜混亂的瑏瑠。埃斯庫羅斯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直接比較二者,從而體現(xiàn)它們的差異;而其所表現(xiàn)的不僅僅在于不同民族之間的語言和聲音的區(qū)別,更具有鮮明的價(jià)值判斷,因?yàn)榍f嚴(yán)的聲音要比嘈雜的聲音更為高尚。因此,聲音的差異所表現(xiàn)出來的是波斯人比希臘人更為混亂和無序的特征。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在對比中展開,希臘人占據(jù)較高的地位。
埃斯庫羅斯更關(guān)注希臘人與蠻族之間的習(xí)俗差異。在悲劇中,埃斯庫羅斯不止一次提到波斯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箭①,而希臘人則以長矛、盾牌等為主②。其實(shí),希波戰(zhàn)爭雙方在武器上并無太大區(qū)別,這點(diǎn)在希羅多德的《歷史》等諸多作品中已有描述,弓箭對波斯人雖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武器。無論是波斯國王還是士兵都同時(shí)使用弓箭和長矛,這在其錢幣等物品上已經(jīng)有所體現(xiàn)③。同時(shí),這種描述也不符合《伊利亞特》等早期希臘文學(xué)作品中對希臘人與東方敵人(特洛伊人)武器的描述,因此更像是悲劇的虛構(gòu)。埃斯庫羅斯構(gòu)建出來的武器上的對立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在希波戰(zhàn)爭中希臘人以少勝多,使得希臘人認(rèn)為自身比蠻族更加勇敢④。為了突出這一特征,在文學(xué)作品中,希臘人往往使用長矛等近戰(zhàn)工具,而波斯人由于膽怯,則只會(huì)使用弓箭,它背后體現(xiàn)出的是希臘人對蠻族人的鄙視和不屑。與此類似的還有悲劇中對二者生活方式的描寫。波斯人的最大特點(diǎn)是生活奢侈,服裝華麗,并且喜歡使用黃金⑤。在埃斯庫羅斯看來,這并非波斯人的特權(quán),東方的其他民族,如呂底亞、巴比倫等,都有類似的習(xí)慣⑥,因此,它是蠻族的共同特征。與之相比,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則較為樸素。雖然雅典人擁有銀礦,但是銀子為他們共同享有,成為反抗波斯暴政的工具,而非滿足貴族的個(gè)人需求⑦。從表面上看,這體現(xiàn)出希臘人與蠻族兩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但希波戰(zhàn)爭后,波斯人奢侈的生活方式難以被希臘人接受,向波斯學(xué)習(xí)被認(rèn)為是嚴(yán)重罪行,那些向異邦學(xué)習(xí)的希臘貴族也經(jīng)常被冠之勾結(jié)波斯人的罪名⑧。在埃斯庫羅斯的作品中,有意夸大希臘人和波斯人在生活習(xí)慣上的區(qū)別,是因?yàn)闃闼氐纳钪档觅澝溃U族奢侈的生活方式則必須鄙視,這不僅與傳統(tǒng)的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的道德觀念有關(guān),而且也與希臘人同波斯人的對立觀念有密切聯(lián)系。
在埃斯庫羅斯的觀念中,雙方政治的差異最為重要。在《波斯人》中,這種觀念通過阿托薩的夢境表現(xiàn)出來。夢中的兩位婦女性格相反,薛西斯將她們束縛于車軛之下,代表波斯人的婦女以被統(tǒng)治為榮耀,溫順地服從韁繩的約束;而代表希臘人的婦女則折斷了車轅,拖著車猛跑⑨。顯然,埃斯庫羅斯是希望用桀驁不馴的希臘人與馴服的蠻族作對比,表現(xiàn)二者在面臨專制統(tǒng)治時(shí)的不同選擇。在另一處地方,阿托薩和歌隊(duì)之間的對話,則進(jìn)一步將對立具體化。阿托薩問道:“誰像牧者那樣位于他們(希臘人)之上,誰是他們的統(tǒng)治者?”歌隊(duì)則回答:“他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也不聽命于任何人。”瑏瑠阿托薩對此極為困惑,因?yàn)槿狈黝I(lǐng)導(dǎo)的體制在波斯人看來難以理解。希臘人與蠻族之間自由和專制的矛盾在此得以凸顯。它已經(jīng)超越了希羅多德的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但在《波斯人》中卻應(yīng)當(dāng)最為重要,因?yàn)楸瘎≌菄@希臘人反抗波斯入侵的主題展開的,希臘人和波斯人的沖突也建立在此基礎(chǔ)之上。不僅如此,在整個(gè)古典時(shí)代,以波斯為代表的蠻族專制制度是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極其反感的事情瑏瑡,成為希臘人與異族對立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埃斯庫羅斯經(jīng)歷過希波戰(zhàn)爭,與波斯人有直接接觸;而雅典人在希波戰(zhàn)爭中付出的犧牲最大瑏瑢,雅典的民主制度又是專制制度最有力的對立面,因此作家與觀眾之間對此問題都有極深的印象。不難想象當(dāng)埃斯庫羅斯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會(huì)很自然地以民主和專制的沖突作為希臘人與波斯之間的界限。
希羅多德與埃斯庫羅斯蠻族觀念蘊(yùn)含的時(shí)代特征
在希羅多德和埃斯庫羅斯的作品中,對希臘人和蠻族人之間區(qū)別有不同認(rèn)識(shí)。希羅多德在《歷史》中對自己所提到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都有具體例證,但是他更傾向于以語言、宗教和生活習(xí)慣等作為劃分希臘人和蠻族的標(biāo)準(zhǔn),并且只是相對客觀地?cái)⑹鲂U族和希臘人的差別,對蠻族的特征較少直接作負(fù)面判斷。而埃斯庫羅斯最看重希臘人與蠻族之間自由與專制的沖突①,也關(guān)注生活習(xí)慣等差異。與希羅多德相比,他筆下的蠻族形象帶有更多的負(fù)面特征,蠻族被塑造成為無序、奢侈、懦弱的人群。此外,希羅多德在書中表現(xiàn)出了矛盾性的一面。他既認(rèn)識(shí)到蠻族的特征是區(qū)別希臘人與蠻族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卻又在寫作中提出不少相反的例子,以證明蠻族在某些方面也具有與希臘人一致的特性,并不比希臘人低級。這些例子都可能動(dòng)搖他對區(qū)別民族的四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的認(rèn)識(shí)。而埃斯庫羅斯的觀點(diǎn)則較為一致,《波斯人》中通篇表現(xiàn)出希臘人和波斯人整體對立的觀念。
這些差異與二人的職業(yè)特征密不可分。希羅多德不僅是歷史學(xué)家,也是最早的人類學(xué)家之一。他在《歷史》中提到的四種標(biāo)準(zhǔn)是希臘人對民族識(shí)別的概括性認(rèn)識(shí),因此有必要將其記錄下來。而人類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決定了劃分人類群體的各種標(biāo)準(zhǔn)都有其局限性,很難全面覆蓋各種情形。他在游歷和寫作的過程中常注意到不同民族習(xí)俗的差異,因此能夠描述出希臘人和其他民族的區(qū)別;而他不斷接觸到新的情況,一再突破了其原有思維框架。作為歷史學(xué)家,他既需要廣泛搜羅材料,也需要如實(shí)地記錄。這并非希羅多德思想前后矛盾,而恰恰反映了歷史學(xué)家的嚴(yán)謹(jǐn)與誠實(shí)。與此同時(shí),希波戰(zhàn)爭后雅典人形成了對波斯人相對固定的負(fù)面看法。埃斯庫羅斯在悲劇創(chuàng)作中,把政治上與希臘人敵對的蠻族形象作為創(chuàng)作主題并不足為奇。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又依據(jù)作者的主題展開,這就使《波斯人》中以波斯為代表的蠻族形象能夠保持一致性,并圍繞雙方政治沖突展開,形成了希臘人與蠻族的鮮明對立。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他們兩人對區(qū)分希臘人和蠻族的標(biāo)準(zhǔn)的認(rèn)識(shí)有重大差異。
不過,在差異背后也能看到兩人之間一致性的地方。首先,盡管希羅多德被認(rèn)為是“熱愛蠻族”的人,而埃斯庫羅斯則對蠻族具有歧視心理,但這并不妨礙他們都將希臘人和蠻族人看作對立面。他們所描述的希臘人與蠻族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很大程度上服務(wù)于此觀念。這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希臘人在希波戰(zhàn)爭獲勝后仍面臨著波斯的威脅,因此,構(gòu)建以波斯為原型的蠻族形象是希臘人凝聚自身、抵抗外敵的需要,作為希臘人,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受此觀念影響。同時(shí),蠻族觀念也與某些城邦的利益有密切關(guān)系。蠻族觀念在雅典最具生命力,這種現(xiàn)象并非只因?yàn)檠诺湓谙2☉?zhàn)爭中受波斯人危害最大,也與它的政治需要有關(guān):它需要強(qiáng)化所謂的蠻族威脅,以便鞏固其領(lǐng)導(dǎo)下的、以對付波斯為目標(biāo)的提洛同盟,從而實(shí)現(xiàn)“帝國主義”政策②。希羅多德雖然成長于希臘人與波斯人交往密切的小亞地區(qū),在多數(shù)時(shí)候能夠以較寬容的心態(tài)去看待其他民族,但他曾長時(shí)間在雅典生活,其作品也為雅典人所熟知③,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雅典人觀念的影響,具有濃厚的蠻族觀念。希羅多德明確提到,《歷史》就是為了記載希臘人和蠻族沖突的歷史,并將雙方的功績記錄下來④。而埃斯庫羅斯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臘人民族意識(shí)覺醒的時(shí)代,也正是提洛同盟勢力擴(kuò)張的時(shí)代,除了《波斯人》之外,《乞援女》等其他作品也體現(xiàn)出他所具有的蠻族觀念。
在描述希臘人和蠻族之間差異時(shí),兩人都關(guān)注希臘人與蠻族間的文化差異。同時(shí),他們不約而同地弱化血緣因素的重要性。希羅多德雖然認(rèn)為血緣可以作為民族區(qū)分的標(biāo)準(zhǔn),但在歷史現(xiàn)實(shí)中卻發(fā)現(xiàn)這一標(biāo)準(zhǔn)很難完全實(shí)現(xiàn),而埃斯庫羅斯在悲劇中則很少提到這一標(biāo)準(zhǔn)。當(dāng)然,這并非意味著血緣已經(jīng)無足輕重,而是說在埃斯庫羅斯和希羅多德觀念中,民族區(qū)分中文化標(biāo)準(zhǔn)變得更加重要。這種變化與整個(gè)希臘民族對自我認(rèn)同的變化發(fā)展軌跡相一致。美國學(xué)者埃迪森•豪爾認(rèn)為,從希波戰(zhàn)爭之后,由于民族矛盾凸顯,希臘人的自我認(rèn)同方式經(jīng)歷了一次重大轉(zhuǎn)變,由原來的從內(nèi)部凝聚的“內(nèi)聚型”認(rèn)同模式轉(zhuǎn)變?yōu)閺耐獠拷?gòu)敵對民族,通過尋求與其他民族對立來強(qiáng)化希臘民族認(rèn)同的“對立型”認(rèn)同模式①。在“對立型”認(rèn)同模式下,文化因素比血緣因素具有更高的地位。
在希羅多德和埃斯庫羅斯著作中,文化重要性的上升絕非偶然。這與兩人構(gòu)建以波斯為主的蠻族形象這一目的密切相關(guān),只要這種需要存在,就必然需要某種最有效的手段維持希臘人和蠻族之間的區(qū)別。血緣標(biāo)準(zhǔn)自身具有一定的缺陷,在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被某些希臘人所認(rèn)識(shí):希臘人宣稱自己都是希倫人子孫,并認(rèn)為希倫的四個(gè)子孫形成了希臘人內(nèi)部的幾個(gè)次一級群體,它實(shí)際上反映出希臘人內(nèi)部次一級群體的融合。這種設(shè)想次一級群體的共同祖先是同胞兄弟的現(xiàn)象在人類歷史上很普遍,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現(xiàn)象②。因此,它本身就是歷史建構(gòu)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建構(gòu)已經(jīng)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并不同于所謂“客觀的”族群血緣,因此它并非穩(wěn)定的,會(huì)隨著時(shí)間而變化。希羅多德已經(jīng)注意到,希臘人的形成就是不斷有其他民族加入“希臘人”大家庭的過程,這些異族在此之后都以“希臘人”自居,反而忘記了自己源初的起源。由于血緣是建構(gòu)的,不同的人為了各自目的可能對血緣會(huì)有不同的表述,如古典時(shí)代希臘人內(nèi)部對馬其頓人與希臘人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就存在爭議,前述亞歷山大的血緣爭議就是一個(gè)很好的例子。在此背景下,血緣就很難有效地劃分希臘人和蠻族的界限,其重要性下降也是必然之勢。
而在此方面,文化標(biāo)準(zhǔn)的有效性要優(yōu)于血緣,它不僅能夠體現(xiàn)出希臘人與蠻族之間的差異性,而且更容易發(fā)掘與調(diào)整,甚至更容易建構(gòu),因而更適合希臘人與蠻族對峙的復(fù)雜局面的需要。與此同時(shí),盡管希臘人和以波斯為代表的東方民族長期處于對立之中,但二者的交流并沒有中斷,無論是戰(zhàn)爭還是和平交往,都為二者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機(jī)會(huì)。在此過程中,不少希臘人對自己與異族之間的文化區(qū)分非常清楚,無論是宗教特征還是生活習(xí)慣,抑或是政治制度,都比血緣更容易引人注意,因此較之于血緣,文化因素更容易將希臘人和蠻族區(qū)別開來。這就是希羅多德和埃斯庫羅斯都以文化區(qū)別與塑造蠻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羅多德和埃斯庫羅斯以文化因素構(gòu)建蠻族人形象的努力極具代表性,但這在古典時(shí)代決非個(gè)別現(xiàn)象,當(dāng)時(shí)其他的希臘作家如色諾芬等人都有類似的行為③。盡管他們對蠻族的認(rèn)識(shí),特別是對蠻族特征的描述有所不同,其中有的人可能對于蠻族未必有明顯歧視,而有的人則對蠻族具有很深的偏見。但這并不影響大多數(shù)希臘人對蠻族存有共識(shí),他們至少都認(rèn)為蠻族是處于希臘人的對立面,與希臘人有明顯的區(qū)別,而區(qū)別主要集中于政治觀念、生活習(xí)慣、語言等廣義的文化方面。這也帶來了另一方面的影響。由于文化可以后天學(xué)習(xí),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不少蠻族人學(xué)習(xí)了希臘人的文化,從而被納入了希臘人;而一些希臘人在接觸了蠻族文化之后就被看作蠻族人。在此過程中,民族認(rèn)同中的文化標(biāo)準(zhǔn)不斷侵襲著血緣標(biāo)準(zhǔn)的領(lǐng)地。到古典時(shí)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就宣稱:“由于雅典文化的影響,希臘人這個(gè)名字不再表現(xiàn)為一個(gè)種族的名稱,而是一種智力的名稱;與其把與我們出身相同的人叫作希臘人,不如把擁有我們文化的人叫作希臘人。”④盡管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種觀念并非完全否定血緣的重要意義,而是在血緣之外為希臘人的自我認(rèn)同以及與蠻族的區(qū)分又套上了文化的標(biāo)準(zhǔn)⑤,但它毫無疑問說明了此時(shí)文化已經(jīng)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在這種背景下,希臘人和蠻族的對立雖然并未被打破,但是二者的界限與古典初期相比已經(jīng)有了極大的變化,也預(yù)示了希臘化時(shí)代希臘人的民族觀念即將發(fā)生變革。(本文作者:李淵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