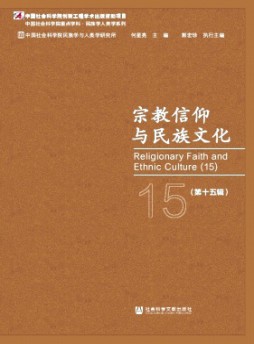民族文化制高點形成的原因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文化制高點形成的原因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石門坎文化運動的成就與該地區已有的民族融合基礎與西方文明及基督教文化的傳入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1千年來石門坎及周邊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已有的融合基礎。
首先,石門坎及周邊地區的漢族與苗彝等少數民族經過千年的融合,在生活習慣與行為方式上有了許多共同之處,比如居住在揚子江南岸漢人地區的彝族上層喜歡修建漢族式的深宅大院,而獨立深居在揚子江北岸山區的彝族人則保留了傳統低矮的建筑風格。在服飾方面,云南的漢人向少數民族學會了制作及穿著毛氈斗篷,以便在陰冷的冬季或雨天御寒。在宗教信仰方面,少數民族雖較少受到儒、釋、道等正統宗教的影響,卻與當時的漢人一同信奉招魂降神術,這類迷信思想對當時當地的居民皆有著驚人的支配力。由于迷信思想廣泛存在,當時的漢族與少數民族都喜好采用詛咒與發誓的方式來裁決一些難以解決的爭端,心虛的一方由于畏懼鬼神往往會退卻。此外,當時也有少數民族崇尚依照漢人法式傳下來的拳術。因此在衣食住行等習俗方面,漢族與少數民族互有影響。其次,在制度文化方面,當地少數民族上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漢人的社會制度。比如清朝的彝族土目們學會了與官府衙門官員打交道,知道如何將土地登記造冊及上交賦稅,并借此在自己彝族同胞中漁利。滿清時期川滇黔地區也有部分少數民族適應了科舉制度,積極參與應試。另外,長久以來當地漢族與少數民族也通過貨物貿易的方式發生經濟往來。比如漢族人喜好吃鹽,我國西部地區的自流井生產黑鹽,而彝族區域沒有地方出產鹽巴,漢人運用食用鹽與彝族人打交道,因此鹽巴成為當地廣泛使用的交易媒介物。又如近現代以前漢族的喪葬文化偏愛使用厚重的棺材,而千百年來漢人已經把廣布于自己山上的樹林濫伐殆盡,于是開始向揚子江北岸的彝族購買木材。由此漢族與少數民族間也建立了一定的經濟聯系。
2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與當地少數民族融合的可能性。
少數民族與漢族雖近在咫尺,但由于受儒家文化影響相對較弱,在民族風俗上,保留了許多自然天性,使得他們在某些方面反而與遠隔萬里的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表現出相似性。比如當時的漢族女性保留著纏小腳的習慣,而少數民族女性卻保持天足,當時的彝族人由于聽說柏格理的妻子長著一雙“大”腳,就認定柏格理是他們的同族人,無形中增加了許多親近感。當地少數民族中男尊女卑的概念十分淡化,男性比較尊重女性,少數民族女性可以直視男性的面孔,與男性們一起談笑風生,而漢族的女性卻只能笑不露齒、回避男人的視線。少數民族的“天然去雕飾”與漢族的“閨房”制度、“含蓄”文化形成鮮明的對照,但卻與倡導男女平等的基督教文化具有天然的親近性。此外,在其它生活習慣方面,柏格理還挖掘出不少少數民族與西方人之間的近似之處,比如二者在騎馬時都將腳尖部放入馬鐙,而當時的大多數漢人卻將腳后跟蹬在馬鐙里。在宗教信仰方面,少數民族因為反對偶像崇拜而與基督教文化產生了共鳴。比如在苗族社會中沒有廟宇,也不見木或石雕的偶像,他們認為漢族人的偶像崇拜是可笑的。他們沒有陰曹地府的概念,卻有著宗教泛靈論的基礎,他們認為萬物有靈,每一個村寨都拜一些當地的大樹,這種原始的有神論為他們進一步接受基督教一神論奠定了心理基礎。此外,當地少數民族中奉行巫術,它雖然是一種落后文化的象征,但巫師們承擔著與靈界溝通的職責,這與基督教文化中祭司的職能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彝族神話中,也有著情節十分類似于《圣經》中“伊甸園”、“諾亞方舟”等的經典故事,客觀上減少了少數民族人民理解基督教文化的障礙。在制度文化方面,由于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體制與當時彝族人中的封建體制頗為相似,使得當時遠赴石門坎的西方人迅速理解了少數民族文化。柏格理認為,在當時彝族地區朝廷官員的統治與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之上國王的作用相當,少數民族區域名義上為國家所有實則自治的狀況使得私人所有存在于國家所有之中,這與英美國家的狀況類似。因此,當時基督教與西方文明雖是一種“異質”文化,但卻具備融入石門坎及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心理基礎。
3基督教文化及西方物質文明對石門坎及周邊地區建設的促進作用。
從西方物質文明對石門坎及周邊地區的建設角度來看,當首推西方醫學的積極作用。清末民初,在中國的西南地區麻風病及傷寒等熱病流行,這里還是罌粟的主要產區,因此鴉片等肆虐,清政府根本無力管轄,許多人因為求醫無路而選擇相信落后的巫術。柏格理的書中記述了不少由于患麻風病而遭到遺棄或因毒癮發作無法自抑而選擇自殺的各族群眾,以柏格理為代表的一批英國傳教士雖是以傳播基督教信仰為目的,卻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醫學文明,他們創辦了數所醫院,利用當時先進的技術,對患病群眾細心呵護,許多人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石門坎及周邊地區。在云南昭通的鳳凰山上至今還保留著五位長眠于此的英籍醫護人員的合葬公墓,其中包括柏格理忠實的好友薩溫醫生,由于清末民初當地艱苦的生存環境,他們五人的壽命均在33~54歲之間,但由于他們的到來,石門坎及周邊地區踏上了現代文明之路。從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明對當地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看,除了創制苗文,還當推西式教育,西式學堂教授天文、地理、算術、外語等綜合學科,使當地群眾獲得了較為完備的知識結構。最后,基督教文化的介入客觀上對于緩解地區矛盾及民族矛盾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千百年來由于對土地的爭奪,漢彝之間以及彝族內部各部落之間矛盾重重,漢人的理念是越少介入少數民族內部事務越好,而傳教士們為了傳播基督教文化,甘愿深入少數民族內部,在取得當地群眾信任后,他們往往成為地區沖突的調停人,盡管并非出于本意,但由于沒有歷史瓜葛和利益沖突,傳教士們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各方勢力,客觀上有利于民族和諧與穩定。
4儒家文化、少數民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共同造就了石門坎民族文化制高點。
石門坎民族文化的形成是文明交流與互鑒的結果,儒家文化、少數民族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等均為之做出了貢獻與適應性調整。比如在柏格理深入苗疆、創立苗文的過程中,若無儒家文化出身的漢族傳教士李約翰、李斯提反等人的幫助,是無法想象的。柏格理1904年開始進入苗疆,就將在云南昭通漢族地區的事務交由李約翰負責。李約翰還向來華的外籍人士教授中文,他的工作為柏格理減少了后顧之憂。李斯提反乃李約翰之胞弟,他不僅為苗文的創制貢獻了不少智慧,且放棄了在昭通城市相對優越的生活,追隨柏格理深入石門坎地區,多次出生入死,且最終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柏格理認為中國舊式學校培養出的紳士,固守著古代傳統,同時又能相當明智地友善對待外來思想與觀念。以苗族為代表的石門坎及周邊少數民族出于對文化的渴求,主動找到黨居仁、柏格理等英籍人士,要求改變落后的現狀,接受西方文明,他們為此也做出了許多跨越式的改變,比如接受了一夫一妻制、男女分泳、注意清潔衛生等先進理念,同時也為當時基督教文化的在苗族地區的傳播貢獻了智慧,如柏格理曾經提到,少數民族群眾在成為基督徒后,常采用舊時戰前召集男子作戰的號角來召集會眾做禮拜,由于聲音能夠傳出很遠,這對于交通尚不發達的少數民族地區群眾來說是十分有幫助的,這也成為特色文化的一部分。最后,作為基督教文化化身的柏格理本人具有卓越的個人能力,且懂得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去感化當地各族人民、贏得信任,因此形成一股文明交融的凝聚力。柏格理精通漢語,后來又學會了苗語,還有“日日不改的微笑及精彩的幽默”也使他多次化險為夷。為適應儒家文化,柏格理全家在漢族地區經常穿著長衫,主動拉近了與當地漢族人民的距離。柏格理作為一位深入探索東方文明達到一定程度的西方人得出了一條重要結論:關于所謂存在于東方和西方之間不可思議的鴻溝其實并不存在。比起將東方和西方粗魯地分別置于絕對不同的分隔間的臆造來,中國的圣賢所言存在于天地間“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倒更接近于實際。這條出自西方人內部的結論既是對亨廷頓所謂“文明沖突”的有力駁斥,也道出了文明交流與互鑒的可能性。在新世紀回頭望向“石門坎”,將提醒我們在保持文明多樣性的同時以文明交流互鑒為動力,推動文化建設走向更高的臺階。
作者:王珊 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
- 上一篇: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范文
- 下一篇:諺語中反映出的民族文化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