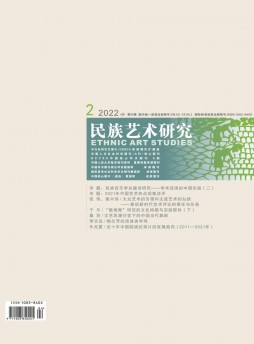民族藝術(shù)在文明沖突下的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民族藝術(shù)在文明沖突下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從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看
民族藝術(shù)的內(nèi)在矛盾民歌是前工業(yè)化時代人民群眾的文化創(chuàng)造,是最為大眾化的、也最具本土化特征的藝術(shù)形式,在經(jīng)濟(jì)和文化全球化的條件下,民歌這種古樸而且穩(wěn)定性較強的藝術(shù)形式也發(fā)生了許多變化,其中的意義變遷是值得哲學(xué)和美學(xué)研究認(rèn)真對待的。在全球化的影響和壓力下,民族藝術(shù)發(fā)生著什么樣的變化,怎樣分析和評價這種變化?這種變化對新文化建設(shè)有什么意義?這不僅是一個美學(xué)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哲學(xué)問題。我想先討論一個身邊的例子: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廣西的民歌節(jié)原來是一個以交流和展示民歌,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民歌節(jié)為主要目的的民間性藝術(shù)活動,由各縣輪流主辦,在其發(fā)展和演變過程中,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色彩逐漸增加。
在20世紀(jì)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對中國南方民歌的興趣主要是學(xué)術(shù)興趣,民歌節(jié)作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傳承的典型機制受到西方學(xué)術(shù)界的重視。1986年農(nóng)歷三月初三,我曾參加在廣西侗族自治縣舉辦的國際民歌節(jié),當(dāng)時的演出和參賽者全都是來自各縣的民歌手,民歌節(jié)的主會場在一塊收割了水稻的農(nóng)田上,歌手的服飾和民歌節(jié)的組織形式都是與傳統(tǒng)的的歌墟活動相一致的,在民歌節(jié)的開幕式上,除了唱民歌外,還有帶宗教色彩的搶花炮和場面宏大的蘆笙舞。到了傍晚,漫山遍野是自發(fā)的對歌情愛活動,讓人感受到民歌的深厚文化基礎(chǔ)和社會底層勞動者強健的生命力。自1999年起,廣西的民歌節(jié)改由南寧政府主辦,舉辦的時間也從每年春季的三月初三改到了涼爽而干燥的11月中旬。南寧市人民政府把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作為打造城市新形象的一個舉措,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請來國內(nèi)著名的導(dǎo)演、國內(nèi)外一流歌唱家,燈光和音響也從香港運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按照明星化和流行文化的形式重新演繹和闡釋了國內(nèi)外的眾多民歌,開幕式由中央電視臺現(xiàn)場直播,使民歌演唱這種傳統(tǒng)的文化形式具有了全新的意義,或說具有了現(xiàn)代意義。南寧市人民政府顯然不是在純粹藝術(shù)活動和民俗學(xué)活動意義上投入巨資來舉辦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其直接的動機還是政治上和經(jīng)濟(jì)上的考慮。值得注意的是,民歌這種樸實而原始的文化形式,在激光射燈、焰火、濃烈的民族化服飾和現(xiàn)代化舞美設(shè)計的烘托下,脫離了民歌原生態(tài)的文化語境,成為對于少數(shù)民族群眾來說高度“陌生化”了的“他者”,因而其意義和作用也發(fā)生了某種形式的變化。
民歌或山歌從民間娛樂的文化形式轉(zhuǎn)變成社會發(fā)展的一種力量,從與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相抵觸的力量轉(zhuǎn)變?yōu)榇龠M(jìn)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一種力量。另一方面,對于西方學(xué)者和旅游者來說,這種具有濃烈異國情調(diào)的藝術(shù)最大程度滿足了他們對異在他者的渴望,在激活其想象力的同時,暗含著對其自身民族和文化優(yōu)越感的肯定。在我看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舉辦,把張藝謀、陳凱歌電影所提及的“東方情調(diào)”的審美意義問題再次提出來了。“東方情調(diào)”的審美意義事實上是不確定的,在不同的語境條件下,“東方情調(diào)”風(fēng)格的藝術(shù)作品呈現(xiàn)出不同的意義,因此,理解“東方情調(diào)”藝術(shù)作品或者說民族藝術(shù)審美意義的關(guān)鍵,還在于對這類作品生產(chǎn)方式、存在特征以及內(nèi)在矛盾的研究和分析。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特點,是把前現(xiàn)代社會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民歌直接置于文化全球化的機制中,在這樣的機制和條件下,以前工業(yè)化社會為基礎(chǔ)的民歌呈現(xiàn)出的意義是很值得分析的。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采納和挪用西方現(xiàn)代大眾藝術(shù)的機制和手段是十分明顯的。2001年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開幕式晚會上,專程從美國來的空氣供應(yīng)站樂隊演唱了奧斯卡電影《人鬼情未了》主題曲《不變的旋律》和《沒有愛在身邊》,引起了歌迷們的熱烈歡迎。在演出后,空氣供應(yīng)站歌手這樣評論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開幕式:“參加這次民歌節(jié)就像參加‘葛來美’,中國式的‘葛來美’!這么大型的晚會辦得這么好,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舉行,都會受到同樣的歡迎”。
在組織形式和技術(shù)手段的運用方面,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確做到了國內(nèi)一流并且與西方類似的藝術(shù)節(jié)接軌,也因此帶動了經(jīng)濟(jì)和旅游業(yè)發(fā)展的正面效益。然而,在文化和審美效果方面,事實上情況要復(fù)雜得多。一方面,我們看到,在現(xiàn)代大眾文化的形式和背景下,民歌和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得以用新的形式表達(dá),從而呈現(xiàn)出新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更新和發(fā)展;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以及類似的文化活動,破壞和沖擊了民歌以及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原生態(tài)基礎(chǔ)。現(xiàn)代大眾文化形式和技術(shù)媒介裹攜著西方后殖民主義文化的泡沫和泥沙,對接受者的價值規(guī)范和文化信仰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沖擊和擠壓,以技術(shù)中心論、經(jīng)濟(jì)中心論和明星崇拜為基礎(chǔ)的審美文化對當(dāng)代中國社會和文化建設(shè)所產(chǎn)生的不良影響不容忽視。在我看來,經(jīng)過三年的發(fā)展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已經(jīng)成為西南地區(qū)民族文化展示的一個盛會,也正成為探索和推動少數(shù)民族文化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種強有力的動因和機制。在當(dāng)代社會發(fā)展中,文化的力量正在顯示其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跨國經(jīng)濟(jì)合作日趨普遍、網(wǎng)絡(luò)經(jīng)濟(jì)不斷發(fā)展的社會條件下,具有個性的文化是當(dāng)代人立足的根基,也是發(fā)展多樣化文化的基礎(chǔ)。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長期積淀凝結(jié)而成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根。沒有文化之根的個體,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技術(shù)工作者,但是決不會在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上有所貢獻(xiàn),不會成為優(yōu)秀的作家、藝術(shù)家、建筑設(shè)計大師,以及優(yōu)秀的企業(yè)家。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強大的延續(xù)能力和表達(dá)能力,是當(dāng)代人進(jìn)行文化創(chuàng)造的基礎(chǔ)之一。在保護(hù)和闡發(fā)少數(shù)民族文化中具有現(xiàn)代意義和現(xiàn)代美這一方面,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在我看來,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價值和意義在于:它通過一系列手段和機制,成功地凸現(xiàn)出民族文化的現(xiàn)代美:通過民歌新唱等形式,激活了民族文化傳統(tǒng)中積極強健的基因,使民歌顯現(xiàn)出現(xiàn)代美。從田野調(diào)查的情況我們看到,在南寧國際民歌節(jié)的舞臺上,民歌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等前工業(yè)社會的文化形式與現(xiàn)代流行音樂和大眾文化之間有一種復(fù)雜的互動關(guān)系,現(xiàn)代音樂和現(xiàn)代大眾文化與民歌等傳統(tǒng)文化既有矛盾和對立的一面,也有互補和共鳴的一面。這種作用還通過各種媒體的作用傳播到少數(shù)民族的日常生活活動中。在民間的歌墟和歌場中,伴隨著收音機、音響等現(xiàn)代技術(shù)的出現(xiàn),迪斯科和搖滾音樂的節(jié)奏等現(xiàn)代流行音樂的形式進(jìn)入民歌的傳唱中,使民歌的內(nèi)容和形式都出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和變化。而且因為民歌與旅游的密切關(guān)系,全球化的進(jìn)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少年一代傳唱和學(xué)唱民歌的熱情,事實上也有利于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hù)和傳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文化形式包括傳媒以及現(xiàn)代音像技術(shù)并不是純粹的形式,而是包含著價值觀念和政治代碼的形式,這種價值觀念和政治密碼事實上是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體現(xiàn),即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體現(xiàn)。“審美制度”和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等概念也許有助于研究和說明審美和藝術(shù)背后的“power”。
在現(xiàn)實的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并不是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的,而是在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一定制度的基礎(chǔ)上發(fā)生聯(lián)系和互相作用的。對于審美活動而言也是如此。這種共同的東西也許就是“power”,它也支配著審美和藝術(shù),也正因為如此,審美本身也存在著內(nèi)在矛盾和沖突。審美和藝術(shù)的異化現(xiàn)象最直接的體現(xiàn)就是在當(dāng)代大眾文化中存在著強烈的肉體化、肉欲化的單向度發(fā)展趨勢。它恰恰說明了一個悲劇,那就是人的工作、人的精神活動與他的感性活動和肉體存在相分離甚至對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動與理性活動相脫節(jié),這恰恰是審美現(xiàn)代性的表現(xiàn)。在馬克思看來,伴隨著資本主義商品化大生產(chǎn),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的弊端,那就是精神與物質(zhì)的分離,這種分離有其合理性,可以在一定歷史階段使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精神生產(chǎn)都更有活力,但最終會造成社會與人性的分裂。大眾文化雖然給人們帶來了數(shù)量上無比豐富的感性享受,但卻并非真正的審美滿足,比如,在流行音樂中,大多有極端化的愛情情節(jié),這種極端化的、不現(xiàn)實的對人類情感和激情的表現(xiàn)甚至可以達(dá)到一種宗教狂熱的程度。我認(rèn)為,藝術(shù)后面的“power”是一種以情感話語為形式的意識形態(tài),事實上是包含著價值立場和評價傾向的。西方現(xiàn)代流行藝術(shù)本身及其機制包含著西方某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傾向,因此,在與中國少數(shù)民族民歌這樣的藝術(shù)形式相結(jié)合時,必然產(chǎn)生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沖突。這種沖突大體上可以歸結(jié)為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種是外在的,一種是內(nèi)在的,所謂外在的是指藝術(shù)與其它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所謂內(nèi)在的則是指藝術(shù)內(nèi)部情感話語的對立和沖突。前者我們可以舉張藝謀的獲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為例,后者我們可以以在2001年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開幕式上由壯族歌手演唱的挪坡縣黑衣壯族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為例。《山歌年年唱春光》是一首由廣西挪坡縣原生態(tài)的山歌加工整理成的歌曲,由挪坡縣壯族歌手用壯語演唱。在南寧民歌節(jié)的開幕式上,以無伴奏合唱形式表演,其中的領(lǐng)唱者黃春燕是廣西歌舞團(tuán)的專業(yè)演員,是一名在挪坡長大的黑衣壯后代。
這首歌以層次豐富、旋律優(yōu)美和濃重的大石山氣息打動了時髦的歌迷和廣大聽眾。歌手們身著自己織布制成的民族服裝,用黑衣壯的方言演唱,使歌聲充滿了神奇的魅力,從音樂學(xué)的角度講,《山歌年年唱春光》并不符合現(xiàn)有的音樂規(guī)程,但卻表現(xiàn)出新奇的美。這首歌的純粹地方性使它不可摹仿也不可能流行,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它的唯一性和豐富的審美魅力使它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支小合唱隊在南寧民歌節(jié)獲得成功后被邀請到中央電視臺和美國演出。從美學(xué)的角度看,《山歌年年唱春光》表達(dá)了在極端惡劣和嚴(yán)酷的自然條件下,黑衣壯人民健康奮發(fā)的心態(tài)和對現(xiàn)實不公正現(xiàn)象的大膽抗?fàn)帯_@種不借助燈光、焰火,不借助伴奏和伴舞的演唱,有效地解構(gòu)了南寧民歌節(jié)開幕式上的后現(xiàn)代主義奢華,成為一種內(nèi)在而又是最有力的文化反抗和文化表達(dá)。民歌,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的民歌,作為社會底層人民對強大的壓迫性力量的反抗和超越的文化形式,在南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十分盛行,用唱山歌的形式罵人是一種常見的表達(dá)方式。對不合理現(xiàn)象的憤怒可以因為歌唱這樣一種非現(xiàn)實性因素而轉(zhuǎn)換,成為一種曲折表達(dá)反抗情緒的形式。在中國南方,劉三姐唱山歌罵地主的模式其實具有普遍的意義。如果說對于工業(yè)化社會的個體而言,夢和幻想是表達(dá)對現(xiàn)實的反抗和超越的一種形式的話,那么在中國西南地區(qū),民歌演唱也是如此。在民間的歌墟和歌場上,在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表演舞臺上,民歌的全球化魅力和現(xiàn)代化機制的本土化運用事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它的矛盾性也是它充滿活力的根源。
二、民族藝術(shù)的生產(chǎn)方式
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chǎn)論,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曾經(jīng)進(jìn)行過廣泛的討論,在當(dāng)時的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生產(chǎn)論表述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文藝生產(chǎn)作為精神生產(chǎn)同物質(zhì)生產(chǎn)的關(guān)系,其中包含著物質(zhì)生產(chǎn)與精神生產(chǎn)(包括藝術(shù)生產(chǎn))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文藝生產(chǎn)等某些精神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發(fā)展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之間的不平衡關(guān)系、精神生產(chǎn)與物質(zhì)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歷史地、具體地而不能抽象地去把握等內(nèi)容;二、文藝生產(chǎn)在精神生產(chǎn)領(lǐng)域內(nèi)部同其他精神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相互關(guān)系,包括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既有相同的規(guī)律又有各自不同的規(guī)律,等等;三、文藝生產(chǎn)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zhì)規(guī)定,對此,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家們著重強調(diào)了藝術(shù)想象和幻想對自然和社會生活進(jìn)行加工、運用美的規(guī)律來創(chuàng)造、富有激情等獨具的特征。[1]現(xiàn)在看來,這種表述仍然停留在較為表層的歸納階段,沒有在學(xué)理的層面上抓住根本的問題并展開系統(tǒng)的分析。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概念事實上就是日常生活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變?yōu)閷徝酪庾R形態(tài)的文化機制。如果說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生產(chǎn)方式是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統(tǒng)一,那么可以說,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文藝生產(chǎn)方式是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與審美關(guān)系的統(tǒng)一。在藝術(shù)的表現(xiàn)能力這個范疇中,有一個技術(shù)的問題和媒介的問題,這是藝術(shù)形象和文學(xué)修辭的基礎(chǔ)。藝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的區(qū)別,就在于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和藝術(shù)表達(dá)媒介對審美關(guān)系的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陌生化或者類同化。前者以藝術(shù)生產(chǎn)力與審美關(guān)系的矛盾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后者則傾向于彌合這樣一種矛盾。在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概念系統(tǒng)中,審美關(guān)系與審美的意識形態(tài)在概念內(nèi)涵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從理論上說,審美意識形態(tài)概念不應(yīng)該等同于藝術(shù)的概念。藝術(shù)是用審美的方式對意識形態(tài)進(jìn)行質(zhì)疑,或拉開一定距離審視,而審美意識形態(tài)則是用審美的形式和話語表達(dá)主流意識形態(tài)或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或者說,是現(xiàn)實生活關(guān)系在審美維度上的存在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說,審美意識形態(tài)就是現(xiàn)實的審美關(guān)系。在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中,現(xiàn)實的審美關(guān)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規(guī)定著審美意義的價值指向和價值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把藝術(shù)媒介、主體的內(nèi)在要求,以及來自現(xiàn)實生活的要求,或者說新的價值等等諸因素統(tǒng)一的框架。沒有審美,一切審美活動都無從談起。因此,把藝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簡單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與某些藝術(shù)生產(chǎn)部門相敵對,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與古典社會的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相敵對;另一方面,則指資本主義社會中物質(zhì)資料的生產(chǎn)方式與精神生產(chǎn)方式,特別是文學(xué)藝術(shù)的生產(chǎn)方式相敵對。馬克思并沒有簡單地作出結(jié)論說藝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相敵對。藝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藝術(shù)與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復(fù)雜關(guān)系,是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藝術(shù)與意識形態(tài)的關(guān)系,包括藝術(shù)與審美關(guān)系的辯證關(guān)系,無疑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要變化,這是理論研究應(yīng)該作出解答的。關(guān)于社會主義的文化,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文學(xué)藝術(shù),維護(hù)和促進(jìn)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發(fā)展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在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經(jīng)過浪漫主義文學(xué)運動和現(xiàn)代派文學(xué)階段,文學(xué)形象和現(xiàn)實生活體驗之間的聯(lián)系斷裂了,形成了保守主義和激進(jìn)主義二元對立的格局,文學(xué)的世界也分裂為古典的、符號化了的過去與激進(jìn)的、情感化的當(dāng)下體驗之間的對立。如果說伽達(dá)默爾、列維-斯特勞斯、海德格爾等美學(xué)家已經(jīng)明確意識到藝術(shù)形象與現(xiàn)代生活體驗直接聯(lián)系起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不僅提出了這種要求,而且實踐了這種要求。通過審美轉(zhuǎn)換這個范疇,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把形式和現(xiàn)實內(nèi)容、符號與現(xiàn)實生活體驗結(jié)合起來了。
審美轉(zhuǎn)換不僅只有從現(xiàn)實內(nèi)容升華或提升到藝術(shù)形式這樣一種通常的方式,而且還包括從藝術(shù)象征、藝術(shù)形式怎樣與現(xiàn)實的、生動的審美體驗建立起有機聯(lián)系這樣一種方式。對于當(dāng)代中國民族藝術(shù)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而言,傳統(tǒng)民族藝術(shù)的符號系統(tǒng)和文化表達(dá)機制與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符號系統(tǒng)和文化表達(dá)機制的碰撞和磨擦過程中實際上正在產(chǎn)生出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能夠使在全球化條件下發(fā)展中國家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體驗得到一種表達(dá)。多種文化符號系統(tǒng)和藝術(shù)形式彼此沖突與交融,其意義最終還是決定于這些文化符號和藝術(shù)形式怎樣與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相聯(lián)系。因此,對于當(dāng)代中國民族藝術(shù)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而言,日常生活的概念以及具體的審美經(jīng)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的實際情況來看,在全球化的影響和文化表達(dá)機制的作用下,少數(shù)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形式和藝術(shù)形式要與當(dāng)代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相結(jié)合,成功地表達(dá)當(dāng)代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生存困境和文化要求實際上是一個十分困難的任務(wù),對文化組織機構(gòu)以及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表演人員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種要求,實際上也就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民族藝術(shù)的生產(chǎn)方式的基本要求,其理論內(nèi)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要有一種把西方現(xiàn)代化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與當(dāng)代生活經(jīng)驗結(jié)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形式,例如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日常生活是藝術(shù)生產(chǎn)資料、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guān)系協(xié)調(diào)和統(tǒng)一的基礎(chǔ)。其次,在全球化的語境和條件下,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不同層面與中國當(dāng)代文化、少數(shù)民族文化形成多層面多維度的矛盾關(guān)系,在這種關(guān)系中,矛盾的主導(dǎo)方面和主導(dǎo)傾向決定于藝術(shù)生產(chǎn)者價值立場和文化傾向。
從目前的藝術(shù)生產(chǎn)實踐看,真正把握住當(dāng)代社會生活中少數(shù)民族個體的現(xiàn)實境遇和對未來要求的藝術(shù)作品并不多見。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需要尋找到一個超越文化霸權(quán)和民族主義立場的文化支點,這種支點顯然不可能直接來自現(xiàn)實的各種文化形式,而必須建立在新文化形式創(chuàng)造的基礎(chǔ)上。我認(rèn)為,黑衣壯的演員在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上演唱的歌曲《山歌年年唱春光》可以看作是這種新文化創(chuàng)造的一個例證。在這種新文化形式中,文明的沖突成為新文化創(chuàng)造的動力和契機。最后,文化生產(chǎn)者在現(xiàn)實強大壓力下激發(fā)出來的巨大創(chuàng)造力和激情是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形式或者說新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動力,這種激情只有與現(xiàn)代文化媒介、現(xiàn)代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相一致的時候,才能發(fā)揮出積極的效力和影響,簡單的民族主義情緒并不能實現(xiàn)對現(xiàn)實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超越。
三、審美意識形態(tài):重新思考
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在理論上,有關(guān)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復(fù)雜性和特殊性問題,事實上已成為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理論的中心問題。經(jīng)過布拉格學(xué)派、法蘭克福學(xué)派、阿爾都塞學(xué)派以及英國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學(xué)派的發(fā)展,經(jīng)過眾多學(xué)者和思想家從不同角度對問題的思考,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多層次性及其與現(xiàn)實生活的多重關(guān)系等理論問題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論證和說明。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各流派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研究,主要側(cè)重于審美意識形態(tài)與占統(tǒng)治地位的支配性意識形態(tài)的共謀關(guān)系,強調(diào)了審美意識形態(tài)與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內(nèi)在一致性。它雖然也深入研究了審美啟蒙意識在異化的社會生活條件下產(chǎn)生的條件和可能性等十分重要的問題,從美學(xué)角度批判了現(xiàn)代性與資本主義的文化制度,但在嚴(yán)格的意義上,對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積極作用及其中所包含的創(chuàng)造未來的可能性還研究不夠。在這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是有所貢獻(xiàn)的。社會主義文學(xué)生產(chǎn)方式的出現(xiàn),是20世紀(jì)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和文藝?yán)碚撌飞暇哂兄匾饬x的現(xiàn)象。社會主義文學(xué)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著與此相應(yīng)的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性質(zhì)和特征。弗•詹姆遜在《時間的種子》一書中以前蘇聯(lián)文學(xué)現(xiàn)象為例證,說明社會主義文學(xué)生產(chǎn)方式的特征在于對未來性的把握和表現(xiàn)。
相比之下,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秧歌、二人轉(zhuǎn)、民歌等下里巴人的藝術(shù)形式,呈現(xiàn)出一種直接表達(dá)情感、代表作性的審美體驗?zāi)J健T谶@些藝術(shù)形式中,當(dāng)下的藝術(shù)體驗就直接體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新型關(guān)系。這種新型關(guān)系經(jīng)過藝術(shù)提煉,成為人們現(xiàn)實生活關(guān)系更理想、更強烈的表達(dá),成為未來生活的“原型”。在這里,藝術(shù)與生活的關(guān)系不再是分裂和對立的,藝術(shù)和審美體驗成了未來生活的“預(yù)演”;審美和藝術(shù)的核心機制不是將個體從日常生活中“震驚”和“斷裂”出來的“陌生化”,而是把情感和朦朧的理想放大、顯影的“典型化”。從學(xué)理上說,這種“典型化”與亞里士多德式“典型化”存在著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就在于,后者是以歷史的或然性為基礎(chǔ)的,而前者卻是以歷史必然性為基礎(chǔ)的。在社會主義文學(xué)生產(chǎn)方式的基礎(chǔ)上,現(xiàn)實美以及對現(xiàn)實美的體驗從可能變成了現(xiàn)實。中國的美學(xué)問題在兩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首先,當(dāng)代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結(jié)構(gòu)非常特殊,不僅多種生產(chǎn)方式相互碰撞或彼此重疊,而且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似乎匯集了所有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和形象話語,構(gòu)成了一個巨大的反應(yīng)堆和試驗場。在現(xiàn)代傳播媒介的幫助下,西方藝術(shù)舞臺上剛剛出現(xiàn)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溶入到中國的藝術(shù)生產(chǎn)過程中去。而其他的藝術(shù)話語因為仍然具有現(xiàn)實基礎(chǔ)而保持著生命力。這種多話語共存以及不同形象體系彼此疊合的狀態(tài),極大地刺激了20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力,也向美學(xué)理論提出了尋求內(nèi)在統(tǒng)一性的要求。其次,中國藝術(shù)表達(dá)機制的特殊性,在多重話語疊合與碰撞的狀態(tài)中顯示了它的特殊優(yōu)勢,即以碎片表征整體、以虛靜表征生活的本質(zhì)、以余音繞梁的纏綿托起歷史的沉重和生命的悲劇性。
從理論上說,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以交感為特征的審美模式、以韻為內(nèi)核的藝術(shù)表達(dá)機制,有可能改變沉陷在肉體化感知模式中的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價值導(dǎo)向。對于文學(xué)藝術(shù)來說,表征社會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要求,表征先進(jìn)文化的前進(jìn)方向,積極促進(jìn)人的全面發(fā)展,既是社會的現(xiàn)實要求,也是“美的規(guī)律”的要求。因為在全球化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對“未來”的感受和思考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把審美與現(xiàn)實生活對立起來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中,審美的烏托邦不具有現(xiàn)實的必然性,現(xiàn)實的審美文化又不具有倫理的合理性。而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因其來自于現(xiàn)實的要求,正如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說,是對現(xiàn)實生活的“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豐富,更理想,因此,更帶普遍性”的表達(dá),是一種來自于現(xiàn)實又高于現(xiàn)實的表達(dá),因而是一種可以實現(xiàn)的未來。由于社會主義文學(xué)生產(chǎn)方式的這種特點,對于這類文學(xué)藝術(shù)現(xiàn)象的審美接受便具有更大的激情,而且可以轉(zhuǎn)化為改造社會、創(chuàng)造未來的現(xiàn)實行動。在這種條件下,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和意義問題就需要進(jìn)一步研究和思考了。路易•阿爾都塞曾經(jīng)用“多元決定”和“半自律性”等概念分析和論述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分析了上層建筑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復(fù)雜的辯證關(guān)系。阿爾都塞認(rèn)為,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藝術(shù)等意識形態(tài)現(xiàn)象之間,存在一個十分廣闊也十分復(fù)雜的領(lǐng)域,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的任務(wù)是對這種復(fù)雜機制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說明。
特里•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tài)》和《再論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等著作和論文中則討論了文化與人性的關(guān)系,他以身體作為文化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基礎(chǔ),分析了審美和倫理的人類學(xué)基礎(chǔ)。他指出,只有超越直接功利需要創(chuàng)造的文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由于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內(nèi)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特殊情形所迫,十分重視和強調(diào)審美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發(fā)展和新文化建設(shè)中的積極作用,文藝思想和美學(xué)思想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來說,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文化方面不僅是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問題,事實還是一個壓迫和被壓迫的關(guān)系問題,這種多重壓力的情況在經(jīng)濟(jì)落后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更為突出和尖銳。近年來我和課題組的同志們對廣西少數(shù)民族文化發(fā)展和審美活動的狀況做了初步的田野調(diào)查,我們發(fā)現(xiàn),對于中國南方少數(shù)民族而言,現(xiàn)實的巨大壓力不是簡單轉(zhuǎn)化為生存的焦慮,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人民并沒有陷入簡單的二元對立性思維方式中,反對社會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的進(jìn)步,相反他們渴望盡快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隨著旅游產(chǎn)業(yè)的開發(fā)和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文化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恰恰因為其本土化屬性和唯一性的特點而具有了重要的意義。南寧國際民歌藝術(shù)節(jié)和云南麗江的社會和文化發(fā)展就是突出的例證。這其中有許多值得在理論上認(rèn)真總結(jié)和概括的東西。根據(jù)我們初步的研究,我們認(rèn)為,在全球化的條件和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明顯存在著沖突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相互依賴的共生性一面。從美學(xué)的角度看,在文明的沖突和全球化的巨大壓力下,民族藝術(shù)的特殊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以農(nóng)耕文明為基礎(chǔ),這是一種藝術(shù)與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密切聯(lián)系的文化模式,審美價值還未從政治價值、經(jīng)濟(jì)價值中分裂出來,其藝術(shù)符號和象征體系的基礎(chǔ)與藝術(shù)生產(chǎn)過程和使用過程都是有機聯(lián)系的,其價值意義和審美意義也是復(fù)雜的和多義的。
雖然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包括文化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是歷史必然趨勢,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民族藝術(shù)的文化基礎(chǔ)中消極和落后的因素會受到?jīng)_擊和破壞,但是,前工業(yè)化社會的文化模式中不乏對于后現(xiàn)代困境中的當(dāng)代文化具有重要啟發(fā)的文化模式,例如中國南方多種少數(shù)民族文化和諧共存的模式,再例如廣西壯族用對歌的調(diào)侃來消解文化或政治方面的壓迫性力量的文化機制,就是富于啟發(fā)性和建設(shè)性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不是一個簡單的“他者”,而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和社會資源,是新文化建設(shè)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具有重要實用價值的民族藝術(shù),把藝術(shù)作為抵御現(xiàn)實壓力、改造社會包括改造主體自身的一種方式和手段,而且由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一般經(jīng)濟(jì)相對落后,生產(chǎn)和科學(xué)技術(shù)的水平不高,因此與經(jīng)濟(jì)全球化并不構(gòu)成簡單的對立和沖突的關(guān)系。在文明沖突的條件下,民族藝術(shù)可以起到新文化建設(shè)的“母胎”一樣的作用。其次,民族藝術(shù)作為一種個性鮮明的藝術(shù)形式,同時又是大眾化的文化形式,在保護(hù)文化的多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藝術(shù)是文化中一種十分特殊的形式,藝術(shù)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不是簡單受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決定和支配,藝術(shù)的形式有其人類學(xué)的基礎(chǔ),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外來的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的壓力,事實上會刺激民族藝術(shù)朝著更加個性鮮明的方向發(fā)展,因此,在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民族藝術(shù)可以起到實現(xiàn)民族文化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作用。民族文化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是通過民族個體來實現(xiàn)的,在全球化的語境和條件下,民族個體既要避免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困境,又要盡可能弱化全球化壓力所帶來的社會傷害和文化傷害,其行為模式是具有選擇性的。在我看來,民族藝術(shù)由于藝術(shù)自身的特殊性,有可能作為一種價值中立的非功利文化形式發(fā)展和傳播,通過民族藝術(shù)的隱密機制來實現(xiàn)民族個體的文化認(rèn)同和文化創(chuàng)造事實上是有效的。
民族藝術(shù)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其意義是兩重性的:一方面,藝術(shù)語言是人類交流的基本語言,它具有比語言文字、法律、宗教更為內(nèi)在和普遍的傳達(dá)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藝術(shù)語言是全球化的,民族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富于個性美的藝術(shù)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另一方面,民族藝術(shù)又是某一民族專有的文化財富,其中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民族個體難以完全感受和掌握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民族藝術(shù)得以在一種新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最后,民族藝術(shù)是一種大眾化的文化形式,與特定區(qū)域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具有天然的聯(lián)系,這種文化模式對于抵御全球化的強大壓力和消極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藝術(shù)是所有意識形態(tài)形式中最敏感的形式。藝術(shù)的幻想性和情感性使藝術(shù)具有超越現(xiàn)實的能力,成為將現(xiàn)在與未來聯(lián)系起來的一個中介。在社會主義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基礎(chǔ)上,民族藝術(shù)作為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的意識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是少數(shù)民族群眾生存斗爭的一種方式和一種武器。民族藝術(shù)這種大眾文化無論在社會基礎(chǔ)、美學(xué)性質(zhì)、表達(dá)機制方面,還是其社會效果和社會意義方面都不同于以都市文化和現(xiàn)代傳媒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現(xiàn)代大眾文化。
應(yīng)該承認(rèn),到目前為止對于民族藝術(shù)這種大眾文化形式的美學(xué)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在全球化的條件下,西方大眾文化機制與民族藝術(shù)的碰撞,既有矛盾和對立的一面,也有互補和相互結(jié)合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站在平民化而不是貴族化的立場上看問題,西方的大眾文化是一種包含著未來文化可能性的新的文化形式,它以現(xiàn)代技術(shù)為條件,以普通勞動者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chǔ),對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具較強的解構(gòu)能力。民族藝術(shù)與西方現(xiàn)代大眾文化機制的結(jié)合,在不同的生產(chǎn)方式基礎(chǔ)上是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在我看來,在社會主義藝術(shù)生產(chǎn)方式的條件下,民族藝術(shù)有可能發(fā)揮審美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轉(zhuǎn)型和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成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發(fā)展的一種牽引性的力量,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先導(dǎo)或者說是一種預(yù)演,如果事實證明確實如此的話,我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為廣西的社會發(fā)展,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貢獻(xiàn)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