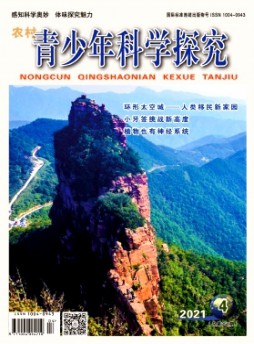探究內容創業背后的勞動關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探究內容創業背后的勞動關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文獻綜述
加拿大傳播學學者文森特•莫斯可①認為,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主要方面,故傳播政治經濟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努力地把研究對象放在具體的社會歷史進程和歷史變遷之中,借此來探討社會的結構性力量是怎樣影響傳播過程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雖然不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流,但其以宏觀的視角揭示出了很多關于傳播的本質現象。如丹•席勒②就對數字資本主義下過定義,即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
近些年突然興起的內容創業,便是丹•席勒所描述的數字資本主義環境中的一種典型現象。所謂內容創業,從廣義上講包括所有以創造高質量內容為方式的創業形式,具體操作不僅包括公眾號文章的創作,還包括網絡小說創作、網上直播、軟件編寫等諸多形式。而內容創業者,指的就是以內容創業為手段,從而進行自主創業的人。在很多人看來,內容創業可以讓自己在不需要投入太多成本的前提下,進行自主創業,所以內容創業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但事實并非真的像想象的那樣美好。雖看似有羅振宇、papi醬等成功創業者的先例,但實際上大多數內容創業者在創業的勞動關系中,都因受制于資方而處于不公平的地位,且難以獲得一個較高的收入。如吳鼎銘③發現,為網絡小說網站撰寫小說的們,名義上是自由工作者,實際上必須服從網站制定的分成規則,最終他們被迫淪為廉價甚至無償的數字勞工。又有統計數據顯示,雖然截至2017年9月,我國內容創業者人數已達260萬人,比2014年增長114萬人,但其中大多數人的收入并不高,2016年我國內容創業者從事內容工作的月營收在5000元以下的約占總人數的71.2%,月營收在1~2萬元的僅占6.7%,僅0.1%的內容創業者月營收能達100萬元以上④。姚建華與徐婧⑤認為,較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知識勞工們被剝削的本質,給了他們一種“我是中產階級”的虛假意識,但說到底,他們被剝削的階級本質并沒有改變。而對于相當一部分收入遠遠達不到中產水平的內容創業者來說,他們的境遇更加惡劣。
而且內容創業者的成功,往往極大程度地依賴于其本身的工作履歷和社會資源背景⑥。比如較知名的內容創業者羅振宇,其曾經在央視工作多年,有著專業的內容制作經驗和業界人脈資源,其本身先是一個資深媒體人和傳播專家,后才是一個內容創業者。除此還有“少年商學院”“潘幸知”“行動派”等知名內容創業自媒體,它們的成功都離不開主創者的知識和資源背景。而且隨著這批早期成功的內容創業者實力的逐漸積累,他們不斷占據內容使用者的眼球和閑暇時間,對用戶實施精準的營銷和把控,結果就是留給后來的和邊緣的內容創業者的創業空間越來越小,大多數內容創業者只會日益邊緣化,甚至被淘汰出局。
除了內容創業者以外,受眾實際上也在內容創業的勞動關系中處于不公平的地位。傳播學者斯邁茲曾開創性地闡述了“受眾商品”理論,他認為觀看電視的活動就是觀眾促進媒介產業資本積累的一個過程,本來是進行個人生活的家庭,也一躍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廠⑦。而在當今時代,受眾促進資本積累的活動已經遠不止觀看電視了,本質上觀看所有內容創業者所生產出的內容,都是促進媒介產業資本積累的過程。在內容創業者制作出大量優質內容的協助下,在受眾促進產業資本積累的勞動的協助下,資本不斷地壯大著自己的勢力⑧。所以不難看出,看似前途光明的內容創業,實際上背后隱藏的勞動關系相當的不公平。目前的國內外文獻中,研究內容創業的不少,但研究內容創業背后勞動關系的卻很少。故本文將從此角度入手,力圖展現出內容創業背后真正的勞動關系形式,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有所突破。
二、內容創業者和資方的勞動關系
在內容創業的環節中,一共有三個方面的人群:第一是資方,主要包括各內容平臺的平臺方和對內容創業者投資的投資方;第二是內容創業者,包括在各種平臺上以各種形式進行內容生產,且把這種內容生產活動作為創業手段的人群;第三是受眾,即使用各內容平臺消費內容生產者所生產出的內容的人群。這三者之間存在的勞動關系為本文所論述的重點。
(一)內容創業者和資方的常見收入分配模式
在內容創業者和資方的勞動關系中,內容創業者本身的利益和資方緊緊捆綁在一起。而且由于內容創業者數量龐大,而發展和待遇較好的內容創業網絡平臺相對較少,因此在雙方博弈的過程中,內容創業者往往處于劣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內容創業者不僅難以獲得較公平的收入,而且在工作穩定性、福利保障、勞動強度等方面均受到不同形式的不公平對待。
以內容創業者獲得的收入為例。在內容創業的流程中,內容創業者和資方的收入分配形式主要分為三種,分別是簽約工資、績效分成和股權投資。除此之外,內容創業者也可以通過廣告和經營網商等形式獲取利潤。在與資方進行收入分配時,簽約工資指的是平臺方和內容創業者簽約,給后者一個固定收益以保證其在自家平臺進行穩定的內容生產活動,比如直播平臺與主播動輒上千萬的簽約金即為典型例子。績效分成形式較為多樣,包括根據點擊量獲得收益、廣告分得收益、打賞獲得收益等,如今日頭條給其頭條號作者的薪酬即與點擊量掛鉤,在直播和網絡文學領域的打賞機制中,作者一般也會獲得一個固定比例的收益。股權投資的情況較少,一般出現在較為成功的內容創業者身上,如papi醬獲得羅振宇等人的1200萬投資,同道大叔獲投資套現2億等均為此方面的案例。至于內容創業者的廣告收入和網商收入,也要看平臺方的規定來決定如何分成。如微信公眾平臺中可以申請開通廣告權限,內容創業者就能根據廣告的點擊次數來獲得相應分成;而如果內容創業者在自己的文章等作品中軟性植入廣告,則多數不需和平臺分成。網商不是所有內容創業者都能開辦的,更多地取決于內容創業的形式和定位,以及個人精力。以起點中文網為例,網站簽約必須與起點中文網簽約才會獲得基本的收入,而收入的多少又和每日更新的文字數量、讀者訂閱量等因素掛鉤。為了獲得一個較高的收入,網絡們往往不得不每日更新數萬字的篇幅,極大地耗費個人精力。作為國內最大的網絡文學平臺之一的起點中文網,僅其不斷更新的小說數量就已達到數百萬本;而其簽約中年收入能達到百萬元以上的,也只不過數十人,大多數即使勤奮寫作,平均收入也不過小幾千元,而無收入的數量極為龐大。正是在大量貢獻大量勞動,而僅收獲微薄收入的前提下,起點中文網這個平臺才有了今天的體量。
(二)內容創業者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劣勢地位起點
中文網作為資方的網絡文學平臺,雖然在打造自身平臺的過程中投入了相當多的成本,但相對于數量遠大于平臺自身員工數的們,平臺投入的勞動量顯然要少得多。所以在平臺方強勢而們弱勢的前提下,以創作文學作品為方式進行內容創業的們,在與平臺的勞動關系中常處于劣勢地位。名義上網絡是為簽約平臺提供內容作品的“自主創業者”,但其收入實際上強烈依賴于網站,網站自然會從身上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最終結果就是網絡們成為廉價甚至是無償的數字勞工⑨。同理,如果資方以風險投資人等形式出現,雖然他們也會在投資的過程中仔細考察、詳細規劃、努力幫助被投資方提升自身價值,付出相當多的勞動,但其收益終歸要建立在被投資的內容創業者的勞動之上。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應屬于內容創業者們的剩余價值依然會被資方拿走相當一部分。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內容創業者甚至不能獲得任何收益。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所生產的內容過于冷門,達不到平臺方規定的分配收入的門檻;也或許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適當的經營技巧,導致自己生產的內容無人問津,等等。但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所生產的內容,在宏觀層面對平臺來說都很重要。比如微信公眾平臺中的冷門文章,其可能只有幾百或幾十的閱讀量,但無數冷門文章也是構成內容平臺龐大內容庫的元素,是一個成功的平臺所不可或缺的。平臺無成本地獲取了這些內容,本質上相當于無成本地占取了內容創作者在生產這部分內容時創造的所有價值。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內容的版權不歸屬于創作者而歸屬于平臺,這對內容生產者來說就更不公平了。內容創業者在與資方的勞動關系中處于劣勢地位的事實,還體現在工作的穩定性上。在全球傳媒產業里,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臨時工”越來越多,而且媒介知識分子也越來越“無產階級化”⑩,這種現象造就了“靈活勞工”概念的出現。比如唱片公司和音樂勞工之間的關系原本是穩定的,但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他們之間的關系開始變得不穩定,一張唱片制作完,一份勞動合同就自動結束。這種“靈活勞工”和內容創業者有很大的相似點,即他們和資方之間的關系都是“靈活而脆弱”的,資方通過讓內容創業者變成“靈活勞工”,減免了很多義務上的負擔,但后者的工作卻失去了穩定的保障。再加上不少內容創業者的收入要通過平臺方來發放,所以平臺一旦出現財務危機,就會直接影響到內容創業者的收入。所以實際上內容創業者的工作穩定性是較差的。除了工作穩定性,內容創業者的福利保障也無從談起。因為相當一部分內容創業者的辦公地點在自己的家中,所以他們自然就承擔起了更多的生產成本,比如購房、維修、房貸利息等,但是傳統上由雇主支付的一般管理費用,如暖氣費、電費、物業費,還有帶薪休假、帶薪病假、養老金等費用,在家中工作的人是無法享受到的。也就是說,內容創業者在為平臺生產內容、創造價值的同時,無法像平臺公司的員工那樣享受到任何形式的其他福利保障。
(三)少數成功者無法改變普遍的劣勢地位
當然,內容創業領域有不少成功者,他們能抓住機遇取得事業上的成功。但正如絕大多數行業一樣,成功的人總是少數,如上文提到71.2%的內容創業者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而僅有0.1%的能月入百萬以上。較為成功的內容創業者們,往往能憑借已有資源實現強者愈強。如網絡文學領域的明星作家和直播領域的明星主播們,往往能夠為平臺帶來相當大的網絡流量,因此可以獲得較大的談判籌碼,他們在得到相當優惠的收入分配方案的同時,能獲得平臺的重點合作,比如讓自己的內容優先展示在平臺的較高曝光位置。其他類型的表現較為優秀的內容創業者,同樣也可以通過類似的方式,憑借自己逐漸積累的人氣分得越來越豐厚的收入。這樣一來,這些成功的內容生產者在勞動關系中就不再單純處于劣勢地位了,而能獲得一個較公平甚至占優勢的地位。但正如剛才提到的,這部分成功的內容創業者,實際上僅占內容創業者總數的一小部分,他們的存在不能扭轉大多數內容創業者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劣勢地位的事實。
三、受眾和資方的勞動關系
如果說內容創業者和資方的勞動關系,還類似于傳統意義上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勞動關系的話,那受眾本身作為消費者也和資方產生勞動關系,則屬于一種較新的不公平現象。1974年傳播學者斯邁茲開創性地闡述了“受眾商品”理論,他提出,觀看電視的活動就是觀眾促進媒介產業資本積累的一個過程,本來是進行個人生活的家庭,也一躍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廠。進入互聯網時代,“受眾商品”現象愈發明顯,如果說原來人們收看電視只是在家中的客廳或者臥室里的話,那么因為現代人的零散時間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互聯網占據,所以受眾扮演的“商品”角色也越發突出。對于受眾來說,他們雖然本意上是在消費內容,但是卻不知不覺地被當作商品一樣有針對性地被利用,最后他們使用內容平臺的時間變成了為內容平臺勞動的時間。對于平臺來說,它們提供的內容只是“免費午餐”,其目的是引誘受眾。最終結果是,雖然受眾并沒有在傳統意義上為資方勞動,但卻又實實在在地用自己相當一部分的時間為資方創造了價值。他們不自知地成了勞動力,不自知地和資方形成了實際意義上的勞動關系,而且還沒有任何回報。這樣,受眾在傳播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就喪失了,他們和內容創業者一樣,在與資方的勞動關系中同樣處于劣勢地位。而且,隨著大數據等技術的逐步使用,資方越來越有能力預測和引導市場消費,受眾也越來越精準地“被”營銷。正如文森特•莫斯可曾指出的,“媒介服務通過把越來越具體的節目類型和界定得越來越清晰的受眾相聯系,強化了商品化的過程”。受眾不僅毫不知情,得不到任何報酬,而且還面臨著個人信息泄露、個人利益受損的風險。Corner認為,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創造的價值,帶來的不是人的異化的終結,而是數字資本主義新的剩余價值來源的增長點;與此同時,他們不斷淪為無能為力的資本的工具。
四、總結
內容創業在近幾年興起,著實造就了一批成功的內容創業者,讓不少人看到了內容創業這條路通向自我事業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光明坦途的背后,內容創業并沒有在實質上給絕大多數內容創業者一個主宰自己命運、自己創業當老板的機會。由于生產資料的稀缺性,內容創業者要想獲得較好的收益,還是不得不依附于以平臺方和投資方為代表的資方,因此,內容創業者在與資方的勞動關系中幾乎總是處于劣勢地位。而作為受眾的群體,也沒有逃過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束縛,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商品”,間接地為資方貢獻了自己的勞動,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回報。所以在整個內容創業的過程中,資方才是真正的贏家。內容創業還可能會加重某些社會問題的程度,如降低社會就業的穩定性,拉大貧富差距等。對于內容創業者和受眾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處境,目前還缺乏足夠的社會關注,但這些確實值得我們投以更多的目光。
作者:田正賡
- 上一篇:建筑企業勞動關系管理的重要性范文
- 下一篇:后人口紅利時代的新型發展戰略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