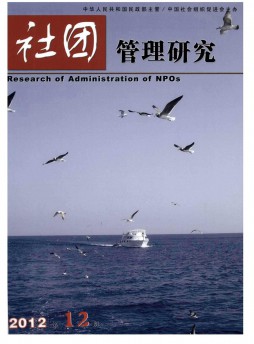社團企事業組織及個人的憲法解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團企事業組織及個人的憲法解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一期
摘要: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只能推論出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提出法律解釋的建議權不同,有關專家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解釋程序法(專家建議稿)》明確規定這些組織及個人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其第十一條規定了個人請求的條件,即憲法訴愿制度;但這并非賦予他們在具體審查性解釋和抽象審查性解釋中的提請權。準司法化應是我國目前憲法解釋的發展方向,通過司法途徑將民間的活力納入國家機關體系,是克服官僚主義的根本之道,也是激活憲法實施制度最簡便、最有效的措施。
關鍵詞:
社團企業事業組織及個人;憲法解釋;抽象審查性解釋;具體審查性解釋;憲法訴愿
我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關于人民行使權力的途徑,該條第二款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憲法解釋權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一種方式,但人民并非授權于國家機關后就萬事大吉,更不能從此就被排除在國家事務之外,因此《憲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為此憲法還規定公民對國家機關的工作有“批評、建議權”(第四十一條)。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重要社會力量,是“人民”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憲法由國家某個機關來解釋是必要的,但同時應賦予人民中的團體、個人依法享有參與權,如當某個憲法條文直接涉及他(她)或他(她)們的自身利益時,當他(她)或他(她)們“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時,他們應該享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在韓大元教授等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解釋程序法(專家建議稿)》(以下簡稱《專家建議稿》)中,明確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這一規定為公民提供了一條新的權利救濟途徑,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①。憲法和執政黨文件中的一系列保障人權的原則性規定應當具體化,應當落實到現實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不能僅僅停留在指導方針的層面。
一、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及個人應享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第四十六條在規定法律解釋的提起者時,沒有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權提出法律解釋的權利,甚至連建議權也沒有,但《立法法》第九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①。由于違憲審查、違法審查與憲法解釋、法律解釋緊密相連,“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既然有審查規范性文件的“建議權”,也就應該有法律解釋和憲法解釋的“建議權”。因此我們可以從《立法法》第九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中“推論”出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提出法律解釋的“建議權”。與《立法法》第九十九條第二款只能“推論”出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提出法律解釋的“建議權”不同,在《專家建議稿》第三章“憲法解釋請求的提起”中,第七條(請求解釋的主體)明確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和個人,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解釋憲法的要求。”但在隨后的第九條第一款“抽象審查性解釋的請求主體”中,只有“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60人以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或者一個代表團”,沒有“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和個人”;在第九條第二款中,“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只有規范性文件審查的“建議”權;在第十條“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主體”中,第二款規定:“當事人認為所適用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同憲法相抵觸,向人民法院書面提出的,而人民法院(或法官)認為確實存在抵觸的,應裁定中止訴訟程序,提請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是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解釋憲法的要求。”“當事人”可能是有關國家機關,如行政機關、軍事機關,也可能是公民個人、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但當事人在此享有的也是一種建議性質的請求權———“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書面提出解釋請求時,只能向在審人民法院(或法官)提出,在審法院(或法官)“認為確實存在抵觸的”,由他們向最高法院提出,最高法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請求才是正式的憲法解釋提起權,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作為當事人在此過程中提出的解釋請求只具有建議的性質。因此《專家建議稿》第七條(請求解釋的主體)規定的“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組織和個人”的憲法解釋提起權在隨后的第九條和第十條中都沒有落實,這兩條落實的都只是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的“建議權”②。真正落實了“個人”憲法解釋“提起權”的,是《專家建議稿》第十一條(個人請求的條件):“任何人認為自己的基本權利受到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侵害,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時,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解釋憲法的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受理。”這才是真正的憲法解釋提起權。但這一條只落實了“個人”而沒有包括第七條規定的“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組織”。第十一條為個人請求的條件,但條文中使用的是“任何人”這一概念,因此這個“任何人”似乎不能包括“法人”,而僅僅是指自然人。筆者建議將“個人請求的條件”改為“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請求的條件”③。
如果第十一條只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意味著不包括國家機關,這是否違反平等原則呢?的確,訴訟中的當事人權利應當具有平等性,賦予國家機關當事人以特權進而歧視社團或個人當事人是違反平等原則的,反之進行反歧視也是不平等的。但這里只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的提起權并不構成歧視,因為國家機關擁有“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個人”所沒有的抽象審查性解釋的請求權———當一個國家機關受到另一個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侵害,通過具體的法律訴訟途徑仍得不到救濟時,它們可以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抽象審查性解釋”的途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解釋憲法的請求,如“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直接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其他國家機關也可以通過上述機關間接地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如地方各級法院可以通過最高法院、地方各級檢察院可以通過最高檢察院、地方各級政府可以通過國務院、軍隊系統可以通過中央軍委,市轄區、縣、州、設區的市和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通過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憲法解釋的要求①。依據《專家建議稿》第十一條的規定,這種提起權以“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為前提,即個人(還應包括“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作為“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書面提出解釋請求后,如果在審法院(或法官)不認可其提起內容,而不向最高法院提出,或提出了但最高法院認為沒有必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在窮盡這些法律途徑后仍得不到救濟,才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解釋憲法的請求。這種提起權實際上是在判決后才能行使的權利,即走不通“在審法院———最高法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途徑,且訴訟結束之后,他們才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起憲法解釋的請求。如果是判決前(案件還在審理中),即使走不通“在審法院———最高法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途徑(如申請被法官駁回),但只要判決尚未作出,案件仍然在審理過程中,就不能說“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通過訴訟對權利進行救濟就還有可能。如果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走不通“在審法院———最高法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途徑,也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解釋(走“當事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途徑),那么規定“在審法院———最高法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程序就成為多余,同時還可能造成對法官獨立判案的干擾。也就是說,當當事人的憲法解釋申請被法官駁回時,當事人的權利有兩種可能,一是權利得到救濟,如法官認為當事人的權利不需要啟動憲法解釋機制也可以被救濟,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勝訴后不能(一般也不會)再提起憲法解釋,因為當事人的權利已經通過法律途徑得到了救濟②;二是權利未得到救濟,此時當事人只能在案件結束后提起憲法解釋,在此對“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是否得到救濟”的理解可能因人而異,但只要當事人認為自己的權利未得到救濟,包括法院認為當事人的權利已經得到救濟,但當事人自己認為沒有得到救濟或只得到部分救濟,當事人都應有提起憲法救濟的權利,總之權利是否得到救濟,在此應以當事人的理解為準③。《專家建議稿》第十條為“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主體”,第十一條為個人請求的條件,二者應是并列關系,至少應排除包容關系,即第十條的“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主體”不包括第十一條的“個人請求的條件”,這與德國模式頗為相似。正如韓大元教授指出的,第十一條(個人請求的條件)“類似于有些國家實行的憲法訴愿制度”[1]。那么,“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和“憲法訴愿”有何區別呢?筆者認為,首先,“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是在司法的一般性權利救濟中求助于憲法,“憲法訴愿”是在“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之后求助于憲法④;其次,“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發生在訴訟過程中,“憲法訴愿”發生在訴訟結束后⑤;再次,“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是在審法官提出的(當事人在其中只有建議權),“憲法訴愿”是“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個人”提出的⑥。
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提請權的限制
“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不論是作為“具體審查性解釋的請求主體”所擁有的建議權,還是在憲法訴愿中所享有的提起權,當他們行使這些權利時,是否會過于積極而產生副作用?筆者認為,只要將“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提出的憲法解釋限于具體訴訟的相關性,其副作用就會大大降低①。不論是憲法解釋還是法律解釋,大多屬于被動解釋,表面上看主動權在提起人手里,只要有人依法提起解釋,解釋機關就要納入法律程序,但“納入”法律程序包括“接收請求書、受理請求書、決定解釋”等多種情形[2],當有權提出憲法解釋的組織或個人提出憲法解釋的請求時,解釋機關固然必須納入程序,但仍然可以作出不予受理、無須解釋的決定,在此解釋機關有權不認可解釋的必要性而拒絕解釋,如《專家建議稿》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法律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解釋憲法的,應予駁回,并將駁回理由書面告知提請解釋的請求人。”②第十五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審查后認為確有必要解釋憲法的,應當提出書面意見,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會議討論決定。委員長會議認為需要解釋憲法的,應啟動解釋程序。”“委員長會議作出解釋或不解釋憲法的決定后,法律委員會應書面告知提請解釋的請求人。”③實踐中也有過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面對解釋請求而不予解釋的例子,如1985年山西省人大常委會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第九條第一款中“灘涂”的定義作出解釋④,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回復是:“河灘地定義,由于情況各不相同,可以具體情況具體解決,以不用援引和解釋憲法條文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為好。”⑤有時候全國人大法工委將有關權力下放給地方,由地方自己解決,如1988年湖北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曾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我省制定省人大議事規則,可否規定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檢察院有向省人大提出議案權?”這實際上是要求對《地方組織法》第十八條作擴大性解釋⑥,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回復是:“省人大議事規則是否可以規定省高級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本級人大提出議案,法律沒有規定,可由省人大決定。”
[3]只有在有關提起人提起、常委會也認為需要解釋時,才會對有關憲法條文作出解釋,因此,賦予“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憲法解釋的提起權,僅僅是可能啟動憲法解釋,這只是憲法解釋制度中的一個環節,至于憲法是否需要解釋、怎么解釋,這些權力仍然是由國家機關掌握的(不論是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或專門機關,都是國家機關)。將“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的憲法解釋提起權限制在具體案件方面,當事人對憲法解釋的要求只有在訴訟中或訴訟后針對該案件才能提出,這是對憲法解釋提起條件的合理限制,可以避免政治力量對憲法問題的過分侵擾,有利于防止憲法解釋的泛化⑦。“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除了在憲法訴愿制度中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之外,是否還應有具體審查性解釋,甚至有抽象審查性解釋的提請權?《專家建議稿》對此是否定的,筆者也認為不必。具體審查性解釋的提起權屬于在審法官,作為當事人的“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在訴訟中只有建議權,這樣的設計可以防止當事人過于頻繁地提出憲法解釋請求。德國《基本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法院如認為某一法律違憲,而該法律之效力與其審判有關者,應停止審判程序。如系違反邦憲法,應請有權受理憲法爭議之邦法院審判之;如系違反本基本法,應請聯邦憲法法院審判之。各邦法律違反本基本法或各邦法律抵觸聯邦法律時,亦同。”該條規定強調的是“法院如認為”,即中止訴訟程序、移送案件至有關憲法法院的權力屬于在審法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80條也規定“具備基本法第100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法院應直接請求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即直接請求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的也是法院。如在“無期徒刑與人的尊嚴”一案中,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違憲審查的是“弗奧廷地方法院第九刑事法院”;在“公務員忠誠案”中,將《公務員忠誠法令》提交到聯邦憲法法院審查的是州行政法院。韓國也是如此,其《憲法》第111條規定憲法裁判所審判的事項中,排列第一的就是“法院提交的某項法律是否違憲的事項”;在“刑罰標準不統一的違憲問題”一案中,就《韓國刑事訴訟法》第331條但書的合憲性向憲法法院提出違憲審判請求的是“審理該案件的法院”;在“《韓國律師法》第15條的違憲決定”一案中,被告人提出《律師法》第15條的合憲審查申請,“受理該案的法院接受其申請”后,進而向憲法法院提起違憲審查請求[4]。
至于抽象審查性解釋,可能更多地涉及政治問題,如我國憲法序言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否可以擴大解釋為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后者應是前者的延續和組成部分),憲法序言第10自然段中的“勞動者”是否可以包括“建設者”(二者是包容而不是并列關系),等等,筆者曾撰文指出這類“修憲”是多余的,只需對其做擴大解釋即可,今天看來對其進行憲法解釋也是不必要的,它們是政治理論問題而不是憲法問題。德國的抽象解釋大多也涉及政治問題或主權問題,如在“政黨公共資助案”中,黑森州政府對聯邦國會以法律形式通過的1965年度《預算案》第1條(對不同政黨的財政援助)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抽象性審查,其中涉及政黨與國家財政、政黨國家化等政治問題;在“聯邦軍隊核武器裝備民意測驗案”中,聯邦政府對兩個州制定的《與核武器相關的住民調查法》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抽象性審查,以阻止在社會指導下推進的住民調查計劃的實施[5]。
如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抽象的憲法解釋提起權,往往不太可能是一個社會團體、一個企業或事業組織,更不可能是一個公民提起,而是需要若干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聯合或一定數量的公民聯合。鑒于我國長期以來缺乏公民運動的實踐積累,倒是有群眾運動、農民暴動、義和團起事的傳統,目前又處于改革的艱難時期,社會矛盾加劇,因此這一模式可能是弊大于利的,條件不成熟的,至少是可以暫緩的①。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通過憲法訴愿提起的解釋請求,實際上把憲法解釋限制在了法律問題、具體問題、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限制在了非常具體的憲法秩序中,其對體制的變革是一點一滴地展開的,避免了對政治問題、對宏觀框架等國家體制問題大手筆的一次性解決。風卷殘云的社會變革是極有魄力,極其痛快,也非常激動人心的,但我們習慣的這種傳統政治思維及其模式代價太大,效果也不好(往往“成果”不穩固),新時代要求我們學習一種新的政治思維———用法律解決糾紛、構建制度,有些問題可以用司法而不一定用政治的手段解決,它是緩慢的、溫和的、理性的、蠶食的。它特別需要的是耐心(可惜我們現在最缺乏的就是耐心),急躁的改革往往不利于改革,甚至會最終葬送改革,不論是權力人還是普通民眾都需要節制自己的欲望,政治上的任性代價往往十分慘重。
三、我國憲法解釋的方向
由立法機關做出的立法解釋比較符合立法原意,但與實踐有一定距離,不如法官的司法解釋及時、有針對性,立法機關的立法解釋和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并存的體制有著內在的矛盾性,二者之間的界限很難劃清,在我們有限的法律解釋實踐中其弊端已經有所顯現。如1985年最高檢察院研究室曾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期間有違法行為,但又構不成犯罪,不能撤銷緩刑,可否對其實行勞動教養?”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回復一方面肯定了最高檢察院研究室的意見:“對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期間有違法行為又構不成犯罪,需要勞動教養的,可以實行勞動教養。在勞動教養期間,繼續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對犯罪分子執行緩刑。”同時承認這類問題不屬于自己解釋的范疇:“這一問題屬于司法解釋問題,以上意見提供最高人民檢察院參考。”又如1987年最高法院研究室請示全國人大常委會:“被告人(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是否視同懷孕婦女,不適用死刑?”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回復同樣將解釋權推給了最高法院:“刑法規定,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對于被告人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的是否適用這一規定,屬于適用法律問題,請最高人民法院定。”①
現行體制下立法解釋與司法解釋的界限不清,可能是制度設計本身造成的,因為解釋(不論法律解釋還是憲法解釋)都應是與具體案件或事件相結合的,而立法機關的解釋恰恰與具體案件結合得不夠緊密。在目前體制不做大調整的情況下,我們所應當做的是,在立法機關解釋體制中盡量多參入司法因子,不僅加強法院在憲法解釋中的作用,而且賦予“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有具體審查性解釋的建議權,在憲法訴愿中有憲法解釋的提起權,準司法化應該是我國目前憲法解釋的發展方向。有學者認為,憲法解釋權和立法權“兩者的屬性有著根本的區別”,如果混同二者,有溯及既往、違反中立之嫌,同時還會導致職權配置的混亂[6]。我們確實應該正視解釋權和立法權(包括制定和修改法律)在權力屬性上的區別:立法權是制定抽象規范之權,是為“今后”定規則,解釋權是解決具體條文的應用問題,是對已經發生的“當下”的糾紛如何裁決的判斷;立法權是主動行使之權,何時立法、怎么立法、立什么法,都由立法機關自己掌控,解釋權是被動之權,一般由解釋者之外的組織或個人提出解釋請求后,解釋者才做解釋,一般不宜主動解釋。而具體性、被動性都是司法權(而非立法權)的特征,司法權具有具體性,一事一議,一案一判,就事論事,不易導致大范圍的變革(不像立法權是針對某“類”行為而言的);司法權具有被動性,不告不理,如果憲法解釋是準司法化的,就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之外的組織或人員提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受理后進行解釋,一般不宜由解釋機關內部的成員主動提起②。
司法的不告不理原則,還意味著不告不理的“告”也應具有廣泛性、平等性,即對原告的資格不做身份限制,不論是國家機關,還是“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只要涉及自身利益,符合有關程序規定,就應當賦予其憲法解釋的“提起權”(只是提起的形式有所不同)。在我國、在當下,規定“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在“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仍得不到救濟”后有權提出憲法解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可能實際上成為我國憲法實施制度最有力的推動者。憲法解釋應具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性,體現出開放性、包容性,而不應僅僅局限于純粹的公權力范疇(如《立法法》規定的法律解釋那樣),它應當是公權力、私權利對憲法實施的共同參與。憲法解釋不僅與國家干部有關,而且與廣大群眾有關,讓人民群眾參與國家事務,體現了人民民主的憲法原則,也是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的途徑之一③。當憲法解釋與“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個人”的權利和利益息息相關時,他們維護自身的正當權利和利益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天經地義,具有天然合理性和正義性。利益是調動人們積極性的最有效方式,是推動人們改進制度的最大動力,將這股來自社會的活生生的極具生命力的能量引入憲法實施、憲法解釋機制,才能更好地啟動憲法保障制度,才可能使憲法具有鮮活的生命力量④。如果憲法解釋的提起權被國家機關壟斷,由于公職人員在其中沒有利害關系,就很可能只是按部就班地履行職責,缺乏生氣與活力,缺少民間那種為自身權利而斗爭的強烈訴求,以及由此而激發出的勇氣、韌性和智慧。立法機關可能在法律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釋、憲法解釋的自由裁量權中打轉轉,自娛自樂,甚至只圖自我方便⑤;其他國家機關也不一定積極行使法律解釋或憲法解釋提起權,權力的本性使我們不能過多地寄希望于他們有維護公民權利的道義自覺。如我國《選舉法》中的“預選”程序,1979年《選舉法》是有規定的,1986年修改《選舉法》時卻刪去了這一內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些地方提出,將選民集中起來比較困難,預選增加了工作量”[7]。地方人大把“增加工作量”作為刪減選舉中民主程序的理由,很具有中國特色,許許多多的國家機構(不限于政府)都是因為“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量”、給他們帶來麻煩和困難而要求減少或實際上已經自行減少其工作程序的①;當然這其中也可能包括中央國家機關對直接選舉中的“預選”易出亂子、難以控制的擔心。受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許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權力時只圖自己省事、上級滿意,為此不惜損害公民權利,悖逆民主,可見推動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基本動力在民間,而不在官方(開明的官方表現為能夠及時回應民間的訴求)。將民間的活力納入國家機關體系,是克服官僚主義的根本之道(讓人民監督政府),也是激活憲法實施制度最簡便、最有效的措施②。
參考文獻:
[1][2]韓大元.憲法解釋程序法的意義、思路與框架[J].浙江社會科學,2009,(9).
[3]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320.
[4][5]韓大元,莫紀宏.外國憲法判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69-71、201-204、329-333,442-445、477-481.
[6]蔣惠嶺.中國憲法解釋制度的三個基礎理論問題[N].人民法院報,2014-12-04.
[7]《選舉法》歷次修改回顧[J].復興論壇,2010-03-08.
作者:馬嶺 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法學院
- 上一篇:黏土斷裂韌度影響因素試驗范文
- 下一篇: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立法透析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