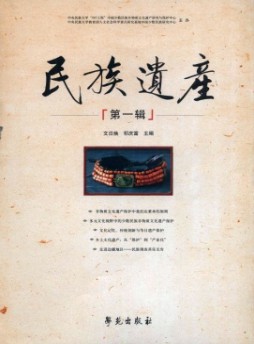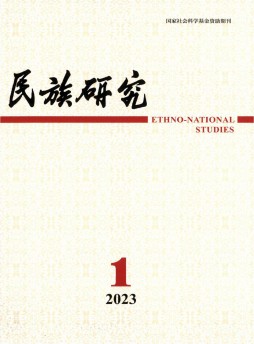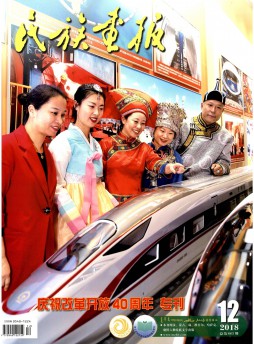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維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維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民族生態旅游是實現民族地區生態脫貧和經濟增長的“強勁引擎”,發展民族生態旅游是新時代下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然而,理應與法治充分耦合的民族生態旅游,卻處于外部法治環境失調、內在理性失范的法治困境中。基于此,實施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化是首要舉措,建構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維度勢在必行。統籌兼顧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宏觀維度和法治微觀維度,基于多維視域下透視分析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以期助推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的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維度
黨的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寫入黨章,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具體部署了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科學內涵是構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時代美麗鄉村[1]。新時代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應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實踐,堅持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根據不同民族的現實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一刀切”。當前我國民族區域發展極不平衡,長期以來,民族地區①**一直處于衰落、貧困、落后的境地。如何將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戰略變成現實可行的政策,落實在實際工作中,必須要進行科學地分析和論證。鄉村振興重在產業興旺,鄉村振興的順利推進,必須激活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如何從民族地區的客觀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破解產業發展瓶頸,培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重構鄉土文化生態的內在資源,實現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民族地區往往是經濟落后、資源匱乏、偏遠封閉的山區,正是由于如此,保存的原生態民族文化也相對豐富而完整。原生態民族文化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也是重要的旅游資源[2]。民族生態旅游作為保護性開發民族旅游的有效模式,民族生態旅游模式更是民族地區培育內生動力、實現精準扶貧的重要舉措,它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五大”發展理念和“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民族生態旅游作為我國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經濟新的增長點,發展民族生態旅游有助于優化民族地區農業經濟結構,增加民族地區居民的收入,轉移剩余農村勞動力,是實現民族地區生態脫貧的重要方式,也是振興民族地區生態經濟,促進民族地區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戰略步驟,更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選擇。新時代下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在于提升民族鄉村的內生能力,即以民族生態旅游,引領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旅游法治環境和旅游市場秩序作為衡量地區旅游發展水平的首要標準,決定地方旅游業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民族生態旅游業需要法治保駕護航,旅游法治化是民族生態旅游建設的有效保障。構建民族生態旅游業離不開法治話語權建設,法治作為民族生態旅游實踐發展的有力保障,必須要為民族生態旅游注入法治能量,依法治旅興旅,構建旅游法治良序,助力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民族生態旅游法治是推進法治中國下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更是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共同夙愿。但是,如何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建設,是一個值得學界思考的問題。目前學界對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問題缺乏深入的研究,亟待我們加強該方面的理論研究,為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提供智識引導。
一、意蘊:民族生態旅游的內涵
(一)民族生態旅游的涵義民族生態旅游是新時代下現代旅游發展的深度模式,它建構在“生態旅游”和“民族旅游”概念內涵以及理論實踐的基礎之上,提出的新概念。我國的民族生態旅游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貴州朗德苗族生態博物館的設立,之后陸續成立了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鎮山布依族生態博物館,它們還曾掀起學界研究民族生態旅游的短暫熱潮。目前關于民族生態旅游的概念,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知。比如在概念術語上,“民族生態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少數民族風情旅游”等都有學者使用,這也反映了學者對“民族生態旅游”的稱謂存在一定的分歧。民族生態旅游是以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孕育的倫理—文化生態精神為根基的旅游形態,它構造著生動的“倫理—文化、生態—經濟、旅游—文化”互促共榮的民族生態文化旅游圖景,并在民族生態旅游中毋庸置疑地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3]。筆者認為,民族生態旅游是一種具有弘揚民族生態文化傳統、保護地區生態環境、推動生態經濟繁榮發展的現代責任旅游模式,它融民族文化、生態經濟、文化生態旅游于一體,它根植于民族原生態的文化之中,在生態文化旅游學理論指導下具有教育、引導、規范等功能的旅游活動。
(二)民族生態旅游的品性民族生態旅游主要包含以下5個方面的品性:第一,民族生態旅游是一種生態責任的旅游活動形式,以旅游的方式來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第二,民族生態旅游是一種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傳承,以生態旅游為媒介,傳承和弘揚優秀的民族生態文化傳統;第三,民族生態旅游是推動生態扶貧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活動,通過旅游反哺社會,實現經濟效益,助力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第四,民族生態旅游是一種寓教于娛、寓學于樂的生態教育旅游模式,它立足于鄉土文化,以民族生態旅游的方式警示生態困境,探索人類生態文明的出路;第五,民族生態旅游是保護性開發民族旅游的最有效模式,其旅游活動具有原始自然性、民族民俗的原生態性、生態旅游文化的專業性,它在滿足游客“放松自我、回歸自然”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的同時,弘揚民族優秀的原生態文化、普及民族優秀的傳統生態價值觀,實現民族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旅游者、旅游地居民、旅游管理人員共同參與到由該民族生態倫理文化構建的場域,實現了生態經濟發展、民族文化傳承、民族生態旅游等科學有機的統一。
(三)民族生態旅游的價值民族生態旅游的多維價值建構在民族生態旅游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生態價值、時代價值的基礎之上,民族生態旅游兼顧生態環境保護、民族文化傳承與社會經濟發展,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下生態環境保護、民族文化傳承、生態脫貧三者科學有機地統一,更是實現新時代鄉村振興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旅游模式。第一,民族生態旅游的經濟價值。民族生態旅游,不僅是“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橋梁和紐帶,更是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保障,還逐漸以其強大的市場優勢、新興的產業活力、強勁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帶動作用,在精準扶貧開發中發揮著生力軍的作用。目前,民族生態旅游已成為我國民族地區的重要經濟增長點,也是我國貧困民族地區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選擇。第二,民族生態旅游的生態價值。秦遠好等學者從實證分析的視角,構建民族生態旅游與生態保護耦合態勢綜合評估體系,數據結果表明兩者交互耦合狀態緊密[4]。民族地區優質的自然生態環境為民族生態旅游的生存發展提供生態基礎,民族生態旅游為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注入活力,二者結合形成優勢互補。第三,民族生態旅游的文化價值。民族生態文化是民族生態旅游的靈魂,民族生態旅游為保護、傳承和弘揚、傳播民族生態文化提供載體,二者結合形成良性互動。民族生態文化和民族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共同構成民族生態旅游業發展的基礎資源,民族生態旅游發展促進民族生態文化和民族地區自然資源的保護與利用[5]。第四,民族生態旅游的時代價值。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是一場艱苦而漫長的跋涉,需要生態、旅游、文化、法治的有機結合。當民族生態旅游回歸并為鄉村振興提供動力,當法治成為民族生態旅游的底色,鄉村就會永遠充滿生機和活力。
二、耦合: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需求
(一)理論:民族生態旅游與法治的多維互動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和手段,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表征,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6]。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走向現代化,必須走向法治化。指出:“旅游是體現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質量的重要指標,旅游同樣需要法治來保駕護航。”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法興旅、依法治旅的戰略目標,即重構以游客滿意為導向的旅游行業微觀監管體系和以產業健康發展導向的旅游經濟宏觀調控體系[7]。因此,民族生態旅游法治化更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Ritchie學者構建Calgary模型,以政治穩定性為主的安全威懾因素作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之一[8];Chao等學者提出改善國內旅游法治環境能促進旅游業的繁榮發展[9];由亞男等學者提出法治文化意識是影響旅游經濟的重要變量[10];許陳生學者基于面板數據隨機效應Tobit模型的實證結果顯示,旅游法治環境等宏觀因素是決定地方旅游業效率的重要因素[11]。綜上所述可知,民族生態旅游作為旅游的一種模式,理論上民族生態旅游與法治是緊密耦合的、多維互動的,民族生態旅游需要法治為其保駕護航。構建民族生態旅游法治良序,實現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化是民族生態旅游發展繁榮的必然要求。
(二)實踐:民族生態旅游的外在法治環境失調旅游法治經濟學提出,營造良好旅游法治環境,可規范旅游經濟活動,推動旅游經濟健康而有序地發展。民族生態旅游作為民族地區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策略。然而,近年隨著我國民族生態旅游業的迅速發展,旅游的發展需求與法治供給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民族生態旅游資源的公共性與旅游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愈加明顯,旅游亂象和旅游糾紛也愈演愈烈。比如在云貴地區民族生態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各類旅游糾紛數量也呈現逐年上升態勢,旅游市場亂象不斷成為焦點話題。僅以貴州省12301旅游服務熱線的話務統計顯示為例,其中2014年貴州省共受理有效旅游投訴162件,2015年貴州省共受理有效旅游投訴540件。①*人民網旅游3•15投訴平臺2016和2017年旅游投訴數據顯示,云南民族生態旅游的投訴數量更是居全國首列,民族地區的民族生態旅游“宰客門”事件更是此起彼伏,接連不斷地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強烈反響。我國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有效供給不足、旅游市場秩序不規范、旅游監管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日益凸顯,旅游矛盾糾紛日益多樣化,旅游投訴問題逐漸尖銳化。究其根源,是我國民族生態旅游的外在法治環境失調,法治在民族生態旅游的發展中失范,旅游法治的缺失成為我國民族生態旅游健康快速發展的現實困境[12]。(三)運作:民族生態旅游的內在理性失范首先,民族生態旅游的過度商業化導致民族生態文化多樣性危機。民族生態旅游實踐運行中存在過度商業化的現象,它盲目發展經濟導致民族生態文化多樣性的削弱,改變鄉土社會的人文生態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進而毀滅鄉土社會的脆弱的文化基礎和基本秩序。可悲的是,許多地方政府、NGO、學者、當地居民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參與這一過程[13]。其次,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內在法律困境。一是生態游覽權與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矛盾;二是生存權與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矛盾;三是經濟發展權與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矛盾;四是民族生態旅游資源的公共性與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矛盾。再次,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外在法律困境。近年來,民族生態旅游的發展方興未艾,并日益成為民族地區旅游業的核心生態品牌。然而與此極不協調的是,目前,我國規范民族生態旅游的法律法規極不完善,缺乏相關法律法規來滿足民族生態旅游發展的法治需求。
三、出路: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維度
(一)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宏觀維度1.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原則。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與法治保障是辯證統一的、多維互動的。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是促進法治進步與發展的動力與措施,法治則是實現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的穩定基礎,民族生態旅游離不開法治的護航。首先,健全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法律制度,緩解民族生態旅游與法治供給的矛盾。筆者建議,盡快制定《自然生態保護區法》、《民族生態旅游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民族生態旅游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法律制度應當包括以下內容:民族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基本原則與規劃制度;民族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申請、審批與生態風險評估制度;民族生態旅游參與者的主要權利與義務以及生態損害的法律責任等。其次,創新民族生態旅游市場監管機制,落實旅游法律法規、政策。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也是如此。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要堅持跨區域的綜合治理,建構旅游市場監管體制的多中心模式,推進政府-市場-消費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共筑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基石。再次,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要根植于民族的法文化傳統。民族傳統法文化中蘊涵優秀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倫理規范、理想人格、審美情趣等文化基因,所傳承的習慣法文化是鄉村旅游法治的引導性資源,更是新時代下鄉村振興下建構一元主導、多元共生、創新生長的各具特色的鄉村文化生態,夯實鄉村民眾文化自信的歷史根基。2.民族生態保護優先原則。生態利益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出現的具有普遍需求和廣泛沖突的新型利益,需要法律的全面保護和調整,并進而成為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的實定法益。民族生態保護優先原則是作為一個事前的法律保護原則,協調民族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二者之間關系,在指導民族生態旅游關系中,更加注重對民族生態的法律保護,使其成為調整民族生態旅游關系的法律準則。民族生態旅游運作實踐是建構在“民族倫理—文化生態”的特定場域,必須以保護民族生態系統為前提。開發利用民族生態旅游資源時必須堅持民族生態保護優先的原則,堅決抵制過度商業化。民族生態保護優先原則應當包括以下內容:一是民族生態旅游在開發利用時,要堅守其根與魂———民族生態文化傳統,避免民族生態旅游過度商業化,從而破壞民族文化生態系統,引起民族文化的荒漠化,導致民族地區深層的文化貧困現象發生;二是民族生態旅游要堅持保護性開發,構建科學的旅游生態足跡[14]分析模型來評估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調控游客總量,預防生態環境的破壞;三是民族生態旅游開發要堅持適度性和科學性的理念,堅持保護性開發,配置生態化的旅游服務設施,科學規劃旅游景點的布局,合理協調旅游者、當地居民、政府之間的關系,建立健全旅游生態預警制度;四是旅游行為要堅持生態化,旅游參與者要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理念,踐行生態法治理念于旅游行為實踐中。3.旅游生態補償原則。生態利益衡平是民族生態旅游的應然法治功能之一,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宏觀維度理應處理好生態利益與經濟利益、資源利益的衡平,生態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的衡平。同時,要以生態利益衡平為出發點和基本方法,著力構建旅游生態利益有效供給制度、旅游生態利益合理補償制度、旅游生態損害賠償制度等保障制度,實現旅游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統一[15]。一方面,民族生態環境(包括人文生態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作為民族旅游地重要的吸引要素,是民族生態旅游發展的核心競爭品牌和重要生態資本;另一方面,旅游活動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會影響民族生態旅游整體生態服務價值的增值和持續發展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因此,在民族生態旅游的實踐運作中要堅持旅游生態補償原則。建立針對民族生態旅游資源所在地原住民的旅游生態補償制度,要遵循“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賠償”的理念指導,要明確旅游生態補償的原則、旅游生態補償的對象、旅游生態補償的標準、旅游生態補償程序與機制等問題。構建現實可行的機制判別旅游生態補償的利益主體,明確旅游生態補償的區域以及產權界定情景,科學建構旅游生態足跡分析模型,建立旅游生態補償標準的共識。探索基于旅游生態足跡研究范式對當地居民進行旅游生態補償的機制與標準,以期為民族生態旅游的生態開發與管理提供借鑒,推動其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微觀維度第一,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社會維度,健全民族鄉村旅游綜合治理體系,營造良好的旅游法治環境。首先,構建法治、德治、自治的鄉村良性互動治理體系。法治是從根本上保障和引領民族鄉村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確保良好鄉村秩序的建立和維護,以法治為保障,實現鄉村旅游治理有序;自治是從根本上保證和支持民族地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實行,貫徹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宗旨,以自治為核心,實現鄉村旅游治理有力;德治是從根本上凝聚社會人心和引導社會風氣,推行仁愛治天下的理念,以德治為引領,實現鄉村旅游治理有愛。其次,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綜合治理必須根植于民族的歷史傳統。新時代下民族地區鄉村旅游治理秩序的建構,其關鍵要以法治與德行為平準,構建以村民自治制度為平臺與框架,以公正開放的自治規則為準繩,允許鼓勵各權威要素按規則相互競爭,充分調動民族地區鄉賢寨老、鄉土法杰參與鄉村旅游法治[16],比如苗族的“榔頭”、侗族的“款首”、瑤族的“頭人”、水族的“水書先生”、布依族的“布摩”、彝族的“畢摩”等。新時代背景下的鄉村振興戰略必須依靠這些鄉賢寨老,他們在村寨治理和民族文化傳承中擔任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再次,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綜合治理必須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堅持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獨立性、自主性,特別是民族地區鄉村旅游基層治理,要維護、承認規則,約束、引導、整合諸種權威,據此以共建一種協商共治的格局,運用民族地區鄉賢力量重建、增進民眾與政治體制的親和關系助推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法治,而勿以權力扭曲規則。健全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綜合治理體系,要堅持黨的領導,完善以“三治”為核心的治理體系,根植于民族地區的文化沃土,立足于我國的鄉土人情。此外,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綜合治理體系的建構可以激發民族鄉村組織活力,促進社會有序運行,推動旅游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從而為民族地區生態旅游奠定法治基石。第二,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文化維度,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法文化,營造良好的旅游法治環境。發展民族生態旅游是實施新時代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旅游法治化是民族生態旅游建設的法治保障,旅游法治作為鄉村振興下民族生態旅游發展的核心踐行路徑,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石。在新時代背景下民族地區的民族生態旅游法治進程中,從理念到制度,我們并不缺乏可利用的本土資源,我們理應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充滿信心。比如,清水江流域的糾紛化解習俗等。結合民族地區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民族傳統生態法文化資源,不僅有利于探索適合民族地區的生態法治體系建構,更利于推動民族地區由“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的返本開新,促進民族優秀生態法文化的弘揚和傳承,從而構建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生態環境,推動民族地區生態經濟的繁榮發展,助推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民族地區傳統矛盾糾紛的化解機制作為民族地區民間法范式的內部行為規則,寓于民族經濟社會生活之中,并在維護民族社會秩序中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
民族傳統生態法文化與我國現代的公共治理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法文化傳統因素和自然現實因素,決定了以法治多元化互動合作模式發展以生態倫理文化為靈魂的民族生態旅游業是民族地區新時期跨越式發展的歷史必然和現實選擇。民族傳統生態法文化的當代轉型與價值重塑是時代主題,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下民族生態旅游的應有之義,無論主流文化策略還是本土文化策略的選擇,都應當增進邊界意識的理論自覺與行動自覺,應當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夯實鄉村民眾文化自信的歷史根基[17]。以奮斗精神為統領,堅持黨的領導,立足于民族的風土人情,發揮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淬煉新時代法治信念,凝聚新時代振興力量。以的治國理政方略涵養新時代下民族地區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理念,傳承中華民族多元優秀文化傳統,充分調動民族地區的積極因素,構建民族地區鄉村旅游治理體系,助推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第三,民族生態旅游的法治制度維度,健全旅游法治的制度體制機制,為民族生態旅游保駕護航。從法理上講,每一項制度都承載著一定的價值與功能,法律作為社會制度最重要的載體,發揮著社會關系調整器與社會利益分配器的功能,旅游法治亦不例外。落實旅游綜合監管協調機制是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的基礎,構建旅游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是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的關鍵,旅游政策法律化是民族生態旅游法治的核心。首先,落實旅游綜合監管協調機制。坐實旅游綜合監管協調機制,要強化不同政府部門機構間的資源信息共享,加強對旅游市場信息的溝通,形成綜合監管體制,創新旅游執法形式和管理體制。整合社會資源和行業力量,構建旅游警察、旅游管理、工商管理、交通管理、城市管理、旅游景區、行業協會等部門組織聯動的監管機制,實現全天候、全覆蓋、多元化的旅游綜合監管協調機制,快速高效調處旅游矛盾糾紛,從而構建旅游司法跨區域聯防聯控機制。其次,構建旅游糾紛的多元化解機制。構建旅游糾紛的多元化解機制,旅游司法要構建以旅游法庭為主導的,提高旅游糾紛司法審判的專門性、專業化,要強化旅游法庭訴訟服務功能和審判管理職能,完善訴訟便民利民機制。完善旅游法庭與旅游糾紛ADR網絡機制多維互動,充分發揮非訴解決糾紛機制的優勢,實現司法服務前置,讓旅游矛盾糾紛訴前化解,同時積極預防旅游糾紛發生,從而維護旅游參與者的合法權益,提升旅游法治滿意度,實現以旅游促進生態經濟繁榮,推動鄉村振興。再次,加強對既有旅游法律體系的完善和規范,比如加快修改《導游人員管理條例》、《旅行社條例》等相關法規、規章。旅游糾紛非訴制度在設計上必須考慮經濟原則和合法性問題,規避制度缺陷影響非訴公正。因此,要完善我國旅游糾紛ADR機制的法律法規,明確旅游糾紛ADR機構及相關人員的職業行為規范。唯有如此,才能逐漸地構建良好的旅游法治環境,以適應方興未艾的民族生態旅游的發展需求。
參考文獻:
[1]韓俊.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政策藍圖[N].人民日報,2018-02-05(004).
[2]羅永常.旅游開發視角下的黔東南原生態民族文化[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2):57.
[3]馮慶旭.民族旅游的倫理文化生態建構———以中華回鄉文化園為例[J].回族研究,2015(3):102-107.
[4]秦遠好,劉德秀,秦翰,黃曉楠,王志章.連片特困地區旅游扶貧與生態保護耦合態勢研究———以重慶市武隆縣仙女山鎮為例[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70-77.
[5]艾菊紅.文化生態旅游的社會參與和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J].民族研究,2007(4):50-58.
[6]張文顯.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中國法學,2014(4):5-6.
[10]由亞男,盧小靜,李東.多民族地區旅游目的地文化變遷量表開發[J].新疆社會科學,2014(2):110-115.
[11]許陳生.財政分權、法治環境與地方旅游業效率[J].旅游學刊,2012(5):80.
[12]宋強.我國構建旅游法治環境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分析[J].法治研究,2013(6):79-83.
[13]張曉松,張小軍.過度商業化與民族文化多樣性危機[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4(4):142.
[14]楊桂華,李鵬.旅游生態足跡:測度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新方法[J].生態學報,2005(6):1475-1480.
[15]史玉成.生態利益橫平:原理、進路與展開[J].政法論壇,2014(2):28.
[16]潘建雷,李海榮,王曉娜.權威的構成:鄉村治理秩序的古與今[J].社會建設,2015(4):26-36.
[17]徐燕飛,余貴忠.生態法治視域下貴州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法治理念及其當代價值[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45-50.
作者:徐燕飛;余貴忠 單位:貴州大學法學院
- 上一篇: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制度保障范文
- 下一篇:淺談依法治國下的網絡法治化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