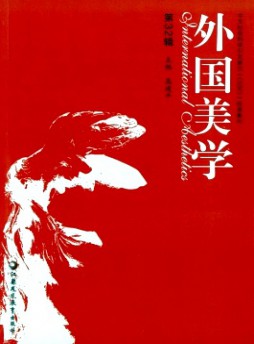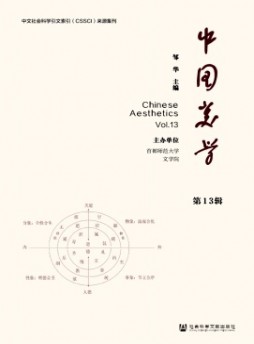美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美學研究的內在邏輯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作者:周軍偉單位:河南教育學院學報編輯部
一、問題與緣起:自相矛盾的康德美學
康德把美分為兩種,他說“:有兩種美:自由的美[pulchritudovaga(飄移的美)],或者純然依附的美[pulchritudoadhaerens(附著的美)]。前者不以任何對象應當是什么的概念為前提條件,后者則以這樣一個概念以及對象依照這個概念的完善性為前提條件。前一種美的諸般種類叫做這個事物或那個事物的(獨立存在的)美,后一種則作為依附于一個概念的美(有條件的美),被賦予隸屬于一個特殊目的的概念的那些客體。”[1]
對于這個區分,宗白華評價說,“自相矛盾地提出了自由(自在)的美和掛上的(系屬著的)美的區分”,“在這里又見到康德美學的矛盾和復雜,和他的形式主義傾向”[2]。蔡儀說:“這兩種美論,正集中表現他思想上的矛盾。而承認純粹美之外的依存美,等于承認他思想的矛盾,也可見康德作為大思想家既按照觀點立論,卻也還有按照事物說話的一方面,也許這有事他的二元論的一種表現吧。”[3]朱光潛認為:“在《美的分析》部分,表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在《崇高的分析》部分,卻從‘美在形式’轉到‘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現’,又走到道德主義。這也就是純粹美與依存美的矛盾”[4]。李澤厚認為,康德美學的真正矛盾在“‘純粹美’與‘依存美’、美與崇高、審美與藝術、趣味與天才實即形式與表現的對峙中更深刻地呈露出來……康德的美學就終結在統一這個形式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尖銳矛盾而未能真正作到的企圖中”[5]。康德美學中純粹美與依附美之間存在矛盾是諸位先生的共識,相對而言,宗白華、蔡儀更加激進,而朱光潛、李澤厚則較為辯證。形成這種區別的原因是,宗白華、蔡儀以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價值判斷對康德美學進行批判,而朱光潛、李澤厚則把更多的筆墨放在康德美學的結構和邏輯上。
20世紀90年代之后,對于純粹美與依附美之間關系的看法出現分化,多數人承接諸位先生的“矛盾論”觀點,也有少數人認為二者之間并無矛盾。馬新國認為,純粹美與依附美的區分是康德為了補救“美的分析”脫離實際生活中豐富多彩的具體美提出來的,并進一步說,附庸美(即依附美)動搖了“美的分析”(即純粹美)的理論基石,康德之所以在對美的關系范疇中提出這個問題是由于這樣做危險要小一些[6]。這是對“矛盾論”的進一步推演。蔣巒認為,“在康德的美學思辨中也就始終交織著純粹美與依存美的矛盾和斗爭”。盡管如此,蔣巒也認為康德美學也蘊含了解決這個矛盾的萌芽,“事實上,康德美學并未安心在自己對立的困境中逗留多久,而是一開始就隱含了純粹美同依存美關聯與辯證轉化的思想。……公正地說,要不是康德美學正確地處理了純粹美與依存美二者間的關系,‘美學就不可能以其現代形式而存在’”[7]。蔡艷山認為,“純粹美與依存美是康德美學中的一對矛盾,這是不爭的事實,純粹美與依存美有互相區別對立的一面,也有互相聯系的一面,二者能共存于同一對象并且存在著共同的規定根據”[8]。與之前的“矛盾論”者相比,90年代以后的“矛盾論”者,更加重視如何在康德美學中消解這個矛盾。總體來看,在美學研究中,對于康德的“純粹美”與“依附美”的劃分,大多數研究者認為二者是康德美學矛盾性的體現,只有少數研究者認為二者之間沒有矛盾①。從人數比例和歷史影響來看,“矛盾論”者的觀點在康德美學研究領域仍舊有強大的學術影響力,因此,對此問題進行研究,梳理康德美學的內在邏輯對于康德美學研究來說有重要意義。
二、矛盾的來源
康德美學兩大部分是否自相矛盾,兩種美是否矛盾,需要從“矛盾論”者所指明的矛盾來源中求解。宗白華認為康德產生這種“錯誤”的原因在于他采用的科學分析方法,“他的這種洗刷干凈的方法,追求真理的純潔性,像十七世紀里的物理學家、數學家的分析學(數學是他們的,也是康德的科學理想),但卻把有血有肉,生在社會關系里的人的豐富多彩的意識抽空了(抽象化了);更是把思想富饒、意趣多方的藝術創作、文學結構抽空了”[2]。相對于其他研究者總是糾纏于先驗方法論,宗先生的看法切入到方法論的具體層面上來,是極有見地的,但時代的局限使他從科學分析轉到了形式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讀。馬新國前承宗白華的“提純”說,提出“補救”說[6],徘徊在寫作技術的取舍上,未能觸及方法論層面。朱光潛也認識到科學方法在康德思考中的地位,但遺憾的是他把自然科學對康德的影響局限在康德的物理學研究中(“也受到當時自然科學的影響,關于天體形成的星云說是他的重要貢獻”[4])。具體到兩種美這個問題,從方法論角度探究時,朱先生說,“從思想方法的淵源看,他的許多矛盾都起于他的主觀意圖雖然傾向辯證,而實際上他沿用了理性派側重分析理性概念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他經常把本來統一的東西拆開,抽象地去考慮從它的對立面,把矛盾絕對化,然后又在弄得無法調和的基礎上設法調和。但就美學來說,在純粹美與依存美、美與崇高、自然美與藝術美、審美趣味與天才(即欣賞與創造)、美與善這一系列的對立面問題上,康德的方法程序都是如此”[4]。論及兩種美之間矛盾的來源時,朱光潛先生說:“在《美的分析》部分,表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而在《崇高的分析》部分,卻從‘美在形式’轉到‘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現’,又走到道德主義。這也就是純粹美與依存美的矛盾。這個矛盾的根源也還是在形式與內容的割裂。”[4]很明顯,相對于宗白華從科學方法的理解,朱光潛更加關注康德哲學的先驗批判方法(“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立場對康德美學的影響。李澤厚也同樣如此,他所說的“康德的美學就終結在統一這個形式主義與表現主義的尖銳矛盾而未能真正做到的企圖中”,仍舊是在指認康德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本身的失敗導致了其美學的內在矛盾。蔣巒也在此范圍內看待康德美學的“矛盾”,他說,“作為其哲學體系有機組成部分的康德美學毫無疑問繼續著他的哲學思辨中的矛盾。因而矛盾與對立就不可避免地構成了純粹美與依存美二者相互關系的第一層涵義”[7]。
對兩種美的區分,矛盾論者認為其源于康德的先驗方法(研究者多用“形式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等術語來替代康德自己的術語)和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立場。問題在于:首先,從立場角度看,康德認為哲學是一門科學。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追溯過邏輯學、數學和自然科學走上“科學的康莊大道”的歷史與條件之后,說“盡管形而上學比其余一切科學都更為古老,而且即使其余的科學統統在一場毀滅一切的野蠻之深淵中被完全吞噬,它也會留存下來,但迄今為止命運還不曾如此惠顧它,使它能夠選取一門科學的可靠道路”[9],并認為就自然科學“作為理性知識與形而上學的類似鎖允許,至少嘗試效仿它們”[9]。因此說,從立場角度而言,康德堅持純粹的科學立場。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不過在科學立場之下綜合哲學知識的具體領域的具體做法,哲學史上對康德調和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立場判斷沒有回溯到康德哲學的根本立場上來,是誤讀。其次,從方法角度看,康德堅持的是科學方法。他說:“如今,純粹思辨理性的這一批判的工作就在于那種嘗試,即通過我們按照幾何學家和自然研究者的范例對形而上學進行一場完全的革命,來變革形而上學迄今為止的做法。這項批判是一部關于方法的書,而不是一個科學體系自身。”[9]
具體說,康德的方法是“按照幾何學家和自然研究者的范例”構建的,這也與康德哲學的根本立場相適應。康德在為幫助讀者理解《純粹理性批判》而撰寫的《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以更加清晰和扼要的方式重述了康德的科學立場和方法。
通過重新認識康德方法論和立場,我們看到,多數矛盾論者對康德的方法判斷比較空疏,沒有看到在先驗方法背后隱藏的是科學方法;對康德立場的判斷也囿于一般哲學史的結論而不能夠回溯到康德的基本立場。如此,矛盾論者對康德兩種美之間存在矛盾的論證前提便是錯誤的,其結論的正確性自然難以保證。宗白華先生對康德方法的判斷是準確的,但對康德哲學“主觀唯心主義”立場的判斷使他難以看到康德純粹美與依附美在科學意義上的內在關聯[2],因此,他對康德美學的評判便不能不陷入窘境。
依照矛盾論者的觀點,我們追溯到“矛盾論”的方法論根源;依據康德對自己方法和立場的陳述,多數矛盾論者對康德的方法和立場的理解并未切中康德的意圖,也距康德的具體論證中采用的方法甚遠,因此,兩種美之間存在矛盾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兩種美之間矛盾的認識是錯誤的,那么由此而來的對康德美學邏輯結構的認識也就不合乎康德美學的實情,矛盾論者從各種角度把康德美學“辯證地”聯系為一個整體便成為無的放矢之舉。那么按照康德的科學方法區分的兩種美在其美學邏輯中起什么作用?康德美學的內在邏輯是什么?
三、康德美學的邏輯結構
對康德美學的邏輯結構的把握,朱光潛先生說:“就康德在全書發揮的總的觀點來看,他的意思是:從分析的角度看,純粹美是只關形式的,有獨立性的;但從綜合的角度看,美畢竟要涉及整個的對象和整個的人(主體)。所以緊接著純粹美與依存美的嚴格區分之后,他就著重地討論到理想美的問題,明確地指出理想美要以理性為基礎,所以只有依存美才是理想美。”[4]“他也認識到(純粹美的)這種獨立性、超然性和純粹性畢竟是假想的,或者說,為分析方便而設立的;事實上人是有機整體,審美功能不但不能脫離其他功能,取抽象的純粹的形式而獨立存在,而且必然要結合其他功能才好發揮它的作用;考慮到這個事實時,理想美就不能是‘純粹的’,就必然是‘依存的’,必然是在于能表現道德精神的外在形體,這也必然就是人的形體。康德的思想線索大致如此,所以表現上雖似前后矛盾,實際上還是說得通的。”[4]
對此宛小平評論說:“朱先生的這一看法是非常深刻的,他仿佛說康德的形式主義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問題。任何研究都需要抽象,把原來整體分解開來,然后再還原為一個可理解的新整體,不過康德加強了抽象分解的這一環節,但并不意味著康德不知道或忽視還原一個新的有機整體的這一環節。”如果,揚棄朱光潛先生關于矛盾及其來源較為僵化的論證,僅就學科架構角度看,他的論述是合乎事實的,并與宗白華“提純”說一道成為新一代學人理解康德美學邏輯結構的基礎。《西方美學通史》中對康德美學理解對此體現得最為典型,該書關于康德美學的論述從學科建構的角度,擺脫了對美學家首先進行價值判斷的做法,以科學的方式分析康德美學,認識到康德美學的科學性[10]。但遺憾的是,《西方美學通史》到此止步,既未能明確地意識到兩種美區分的方法論意義,又未能由此理解“純粹美”與“依存美”在康德美學內在邏輯中的價值。他們說:“關于美與形式的關系,康德的觀點是:純粹美在純形式,依存美包含其他因素。如果有人發現對象的美與內容有關,那難不倒康德,他會把它歸入依存美。如果有人說世上純粹美很罕見或根本不存在,這也難不倒康德,他會讓你在想象中吧其他因素排出,剩下的就是純粹美,況且在他看來,純粹美是存在的,如蔟葉飾、阿拉伯花紋之類就是。”[10]這就把把康德的做法變成了一種充滿巧智的詭辯游戲。事實上,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純粹美和依附美是“支撐這座大橋(康德美學)的兩根支柱”[7]。這兩根支柱勾勒出與康德美學清晰、連貫的內在邏輯。試闡述如下:
1.康德美學從方法上講是科學的,在邏輯上可以分為純粹美與依附美兩大部分。純粹美與依附美之間是原理與運用的關系。
2.純粹美在康德的科學的美學中處于核心地位,康德美學的其他內容建立在純粹美的基礎之上。從章節上講,純粹美涵蓋的是“美者的分析論”。純粹美構成了康德美學的原理部分,美的本質特征和疆界以及判定標準由純粹美決定。純粹美在現實中極難找到對應物,這從康德所舉的極少數常遭人詬病的例子即可看出。實際上,依照科學分析方法確定的純粹美,理論上講是沒有現實對應物的。宗白華先生于此有精到的分析,“按照康德的意見,在純粹美感里,不應滲進任何的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動”[2],“損之又損,純潔又純潔,……剩下來的只是抽空了一切內容和意義的純形式”[2]。宗先生引了老子的話,“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11],明確指示出了純粹美“以至于無為”,但截斷了老子邏輯中的“無為而無不為”。以此而論,康德美學的邏輯結構與老子的“無為”、“無不為”論十分契合。既然“損之又損”,便意味著純粹美并非是自在的、自然的,是范導性質的。
3.依附美是康德美學的現實部分,構成了康德美學的應用部分,是康德哲學的實踐論。“在實踐中,他不僅承認審美與其他因素經常混合在一起,并且還認為認識的愉快和善的愉快會增強審美愉快。一個鑒賞的對象,常常包含者感官刺激、認識和倫理因素在內”[10]。康德是在充分認識現實中審美活動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基礎上,理出其構成要素,以純粹美為核心闡明依附美的結構、范疇與特性。從章節上講,依附美涵蓋除“美者的分析論”之外的所有部分,其中“審美判斷力的辯證論”可以視為對康德美學總的說明和對其他美學理論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