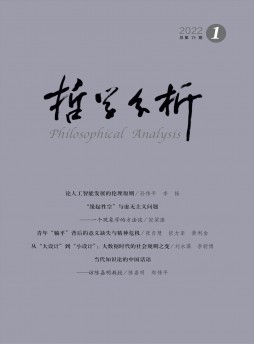哲學視野下的春秋社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哲學視野下的春秋社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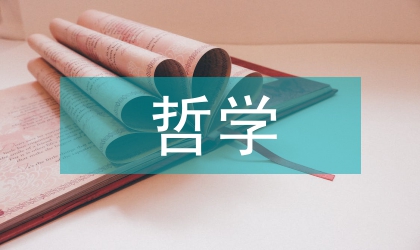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第一,僭禮現象的發生,使人們對傳統禮制進行了反思,促使了禮治思潮的產生。西周時期的禮制表現為禮義、禮儀、禮器的三位一體,其主要功能在于通過一定的禮儀、相應的禮器表達禮義,以此辨別貴族內部的親疏貴賤,確立貴族之間等級名分,鮮明昭示尊卑貴賤的不可逾越。春秋以降,僭禮行為不斷發生,禮制規定下的原有階級結構因之遭到沖擊和破壞,通過禮儀、禮器來體現禮義已名不副實,原來辨貴賤、明等級的禮義也失去了實際意義,傳統禮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對諸侯相爭,大國肆意僭越禮制的現實,春秋時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開始對禮的本質進行反思,主張減弱原先禮制中禮儀、禮器的重要性,并通過以禮治理國家和教化人民來實現禮義的新突破,由此孕育出了禮治思想。他們要求“以禮治世,認為禮治的實行是重建社會秩序的根本,也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安危存亡。當時一大批思想家活躍于各個國家,宣揚禮對政治的作用,或影響當權者的決策,或直接參與政治,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潮流”。可見,“禮制”向“禮治”的轉變,本質上是“禮從原來標志和捍衛貴族統治集團利益的工具,演變為一種能治國安邦的政治學范疇的概念”的過程。春秋時代禮治思潮的產生,與其時思想家、政治家對傳統禮制的反思,將儀從禮中區分出來,突出其作為政治秩序核心作用的做法密不可分。《左傳•昭公五年》記載魯昭公和晉平公會盟,昭公“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平公評價其知曉禮制,但晉大夫女叔齊卻認為昭公只是知儀而并非真正知禮。因為禮是國家治國安民的手段和個人安身立命的方式,而這些會盟場合的繁瑣程式,只能稱之為“儀”。此時魯國政權被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把持,三桓通過經濟手段籠絡了民心,魯君不僅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和支配,經濟上也需依仗三桓的進貢。魯君淪落到如此地步,仍不思索如何治國保民,卻熱衷于這些繁文禮節,實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故不能說是真正的知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黃父盟會,子太叔會見趙簡子,趙簡子借機詢問會盟時諸如揖讓周旋等禮制,子太叔認為“揖讓周旋”乃儀非禮,真正的禮應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由此可見,春秋時代的一些思想家已不再過分追求禮外在的表現形式,而更重視蘊藏其中的精神和內涵。隨著儀從禮中被剝離出來,禮外在的禮節程式漸為人們所淡忘,而蘊藏其中的政治功用經思想家的挖掘日益為人們所重視,禮從而成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禮治思潮由此形成。鄒昌林指出:“古禮是形式與內容緊密結合的統一體。在春秋以前,這二者幾乎是不分的。春秋以后,人們為了探索古禮的意義,才逐漸把其形式與內容加以區分,這就是儀與義的分離。但是,這種分離并非不要形式,而是為了讓形式更好地表現內容。”認為“儀”是禮的表現形式,“義”是禮的本質與精髓;禮治就是要體現“禮義”,使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價值功能得以全面發揮,孔子曾感慨:“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實是對禮治的強烈呼吁。
第二,僭禮行為背后隱藏著對民眾的重視,孕育了古代樸素的民本思想。僭禮和重民之間看似并無關聯,但在僭禮行為背后,卻隱藏了重民思想。春秋時期,僭禮最終目的是為了攫取更多的政治、經濟權力。僭越者知道,如果忽視民眾的力量和作用,他們的努力將付諸東流,不僅得不到實惠,還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因而,重民就成了僭越者用以鞏固既得利益的一項重要法寶。如魯國三桓雖以僭越者身份出現,卻取代了國君而掌控著本國權力,并最終獲得了社會認可,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重民、惠民政策使民心歸附。三桓掌握國家軍政大權之后,魯昭公不甘心失去權柄,聯合與季氏積怨的貴族攻打季氏,結果“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季氏、叔氏、孟氏三家齊心協力將昭公驅逐出國。昭公在外流亡長達八年之久,在此期間由季氏代行君權,昭公雖也曾多次策劃回國奪權,均未能實現,最終客死他鄉。此事發生后,在當時居然并未引起多大震動。晉國執政卿趙簡子就此事問及史墨,史墨答曰:“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也,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認為魯君因不重視民眾而為民眾所拋棄,季氏雖為僭越者,卻懂得重民、惠民,從而在魯國僭居國君之位而行使君權。當時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民眾的重要性,為了防止權力被僭奪,或以實際行動樹立重民形象,或以諍言進諫國君,力陳重民的意義。如邾文公曾占卜遷都于繹,史臣謂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答曰:“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也。”邾文公的舉動,必將得到民眾的擁護,從而使別有用心者難以實現非分之想,充分展現了邾文公的高明之處。《論語•顏淵》篇所載有若和哀公的對話也頗能說明問題:“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如果說,這種重民思想是統治者被迫的非自覺意識,那么春秋時代思想家“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的呼吁,則可視為自覺重民意識的覺醒。這種重人事、輕鬼神的思潮,奠定了后世君主治民的基調。
第三,僭禮使春秋各國宗室貴族之間權力之爭愈演愈烈,宗族勢力在這些勾心斗角的奪權中或遭受重創,或直接消亡,宗族統治難以為繼,新官僚制度的推行勢在必行。按照西周宗法制嫡長子繼承、余子分封的規定,嫡長子與分封諸子之間形成了雙重關系,從血緣關系上來講,他們是同姓兄弟;從政治關系上來講,他們又是尊卑分明的君臣,正如《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說:“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這種統治格局以宗族為各級政權的核心勢力,并且各級宗主職位可以世襲,使得國家與宗族合二為一。經過春秋社會的禮制動蕩,人們的宗法觀念逐漸淡漠,宗室貴族之間為一己之權力私欲結黨營私,全然不顧同宗骨肉血緣之情,宗派與宗派之間形成對抗與殘殺,往往導致兩敗俱傷,大批宗族消亡,各國宗族統治名存實亡,新官僚制度呼之欲出。晉國公室內斗就是最好的例證。公元前745年,晉昭侯將叔父成師分封于曲沃,時人稱其曲沃桓叔。曲沃桓叔的封邑規模甚至超過了晉國國都,這在當時是不合乎禮制的,《左傳•隱公元年》記祭仲言:“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晉國一些賢者憂心忡忡:“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后來事實證明,這樣的分封確實為晉國埋下了禍亂的根源。公元前739年,晉大臣潘父弒殺昭侯,迎立曲沃桓叔,桓叔入晉受阻,與國君之間的矛盾公開化、尖銳化。后曲沃一系在莊伯、武公時代完全把持了晉國政權,晉國國君由他們任意廢立甚至殺戮,如莊伯弒殺了晉孝侯,武公弒殺了晉哀侯、晉小子和晉侯緡。僅經過三代人努力,曲沃便取晉而代之,周釐王封武公為晉君,位于諸侯之列,最終完成了代晉的全過程,曲沃也從晉之小宗搖身一變而成晉之大宗。在這場長達67年的權力爭奪戰中,晉國舊公族遭受到沉重打擊。晉武公之后,其子獻公即位。獻公為鞏固君位,采納士蒍之計,對桓叔、莊伯之族展開了大清洗,最終誅殺了桓、莊之族群公子,晉國公族勢力再一次遭受打擊。然晉國公族的厄運仍未結束,時隔不久發生驪姬之亂,太子申生受驪姬陷害被迫自殺,重耳、夷吾等群公子也受到驪姬誣告而失去信任,被迫流亡國外,“自是晉無公族”。公元前636年,公子重耳回國執掌政權,是為晉文公。鑒于晉國公室內亂的慘烈教訓,文公不再分封同姓子弟,政治上亦不再倚重公族而起用一批能干的異姓貴族。晉國宗族從此逐漸被排斥在權力中心之外。不惟晉國如此,春秋其他國家的宗族也基本上經歷了類似的衰落過程。由于各國國君多有提防同姓篡權奪位的心理,使得同姓貴族出仕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卻大力提拔異姓貴族出仕,導致這一時期的君臣關系出現了新變化。由于“臣與君未必屬于一族或一‘家’,異國、異族之君臣關系逐漸代替同國、同族間之君臣關系,于是所謂‘忠’遂不得不與‘孝’分離”。這樣,宗法制下君臣之間的血緣關系不復存在,臣對君也就不可能盲目地絕對服從。從政治角度分析這一時期的君臣關系可以看出,“忠”的觀念依然得以保留,但這種“忠”是有條件的,即以臣子的人格受尊重作為前提。如臧文仲教育兒子要“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論語•八佾》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都強調臣子對國君盡忠的同時,國君也要尊重臣子的人格,對他們以禮相待。春秋末期,孔子興辦私學,弟子中“學而優則仕”者不在少數,他們無論仕于國君參與國政,還是仕于卿大夫為其家臣,都是憑借才干謀得職位;他們和國君及卿大夫之間沒有血緣關系,不存在依附性,合則留任,不合則去職,職位亦非世襲。這些都與宗法制官僚體系下的情形有別。第四,僭禮使得諸侯國之間攻伐戰爭不已,部分小國為大國吞并,直接淪為大國屬縣,加速了國家行政建制的改變。周滅商后,為有效控制被征服地區,派遣王室子弟或異姓勛戚建立諸侯國,同時賜予他們土地和人民,代表周天子行使對地方的管理。諸侯在其封國內,將部分土地分封給卿大夫作為“采邑”,卿大夫再將采邑內的部分土地分封給士作為“食地”。經過周初大分封,形成了“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統治格局。在眾多的封國之中,姬姓封國獨占鰲頭:“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反映出周初以血緣關系為重點的分封特點。同時,由于周人實行同姓百世不婚的習俗,又與異姓貴族結成了婚姻聯盟,這樣,整個國家被一張龐大的血緣網所籠罩,各級貴族的封邑構成了國家行政建制的主體。至春秋時期,禮壞樂崩,同姓諸侯國之間不再顧及骨肉之情而大動干戈,企圖侵奪對方土地和人民以壯大自己的地盤和勢力,晉國就曾先后滅掉了同姓的虢、虞等國。同姓的諸侯國之間尚且如此,無血緣關系的諸侯國之間攻伐更加殘酷和激烈。隨著大國所屬區域的擴大和人口的增加,各國普遍設縣以便于統治和管理。在諸侯國的混戰中,小國被滅成為大國的屬縣,縣名也多以原國名稱之。如晉獻公滅掉耿、魏后,“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晉文公滅原,以“趙衰為原大夫”;楚莊王滅陳,“因縣陳”;楚文王曾“實縣申、息”。故顧炎武謂“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此外,一些諸侯國內失去權柄的宗室貴族,其封邑被新興權貴倚仗軍事實力和政治特權瓜分而設為縣。如晉國大批宗族失去封邑后,以六卿為代表的新興貴族就將其封邑改稱為縣,“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公族祁氏、羊舌氏的封邑被六卿分為了十縣。縣的設置與運行,揭開了由宗族政治體制下的封邑制向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轉變的序幕。
第五,僭禮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趨向開放和自由。春秋時期魯國的僭禮現象非常多,但并不能完全改變魯國保守的思想觀念,畢竟魯國為周公后裔,得周禮之嫡傳,號稱“周禮盡在魯矣”,是當時各國恪守周禮的模范,因而發生像宋伯姬為等待保姆而寧可葬身火海的悲劇就不足為奇了。但這件事并未得到其時“君子”的肯定,“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顯然,在“君子”看來,宋伯姬固守禮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似乎有些迂腐,因而并不值得稱道。《國語•魯語》篇記載季康子拜見他的叔祖母時,“皆不逾閾”,孔子“以為別于男女之禮矣”。這種男女有別的禮制規定,使人們的思想僵化、保守。與魯國相比,其他國家的人們精神面貌相對開放一些。齊晉鞍之戰,齊國大敗,齊頃公率兵倉惶逃歸途中,銳司徒的女兒攔路打探消息,詢問國君和她的父親是否免于戰爭死傷,在得知“君與父免矣”的確切消息后才離去,態度落落大方,毫無羞澀之意。齊大夫杞梁隨莊公出征戰死,杞梁妻迎喪于郊,齊莊公欲在郊外行吊唁之禮,杞梁妻據理爭辯說:“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結果齊莊公不得不“吊諸其室”。這位齊國女子直面國君亦無忸怩之態。此二女做法顯然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的規定相背離。除此之外,齊國還經常組織社祭之類的群眾性活動,使男女一起玩樂,魯莊公就曾欲“如齊觀社”,“以是為尸女也”,即以“觀社”為由頭,想趁機去看女人,蓋因齊國舉行社祭時,男女可以同時參加,禮制方面沒有性別忌諱,這種男女混同參與的公眾活動,成為吸引莊公前去觀看的主要動因。第六,僭禮導致的名實失調為先秦名家提供了豐富的思考素材,為中國古代思想領域注入了一股新鮮活力。春秋時期僭禮之所以層出不窮,原因在于僭越者不斷追求禮所象征的等級名分,以致本應天子才有資格享受的禮制,卻被諸侯甚至大夫僭用,魯國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禮的名與實嚴重不符,同時,君不君、父不父的名實失調現象,使得子弒父、臣弒君的社會事件也屢屢發生,整個社會呈現出紊亂狀態。孔子從政治角度對名實關系進行了思考,呼吁通過“正名”重整社會秩序。但這樣的呼聲,最終被淹沒在社會巨變的浪潮之中。戰國中期惠施、公孫龍等名辯家的出現和名辯思潮的興起,使名實觀念從哲學思辯角度得到了大討論,為名實的理性回歸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國名辯思潮的出現,和名辯家對春秋僭禮現象所引發社會問題的思考有一定關系。
作者:任曉鋒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寶雞文理學院歷史系
- 上一篇:哲學視野中的音樂本性的文化性范文
- 下一篇:哲學視野的文化評價標準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