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式哲學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柏拉圖式哲學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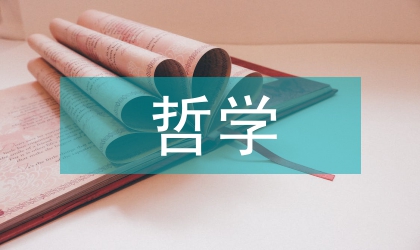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一、哲學之為“習作死態”
如果說作為愛智慧的哲學的使命就在于求真的話,那么我們也就同樣可以認為,在柏拉圖這里,哲學的重要性,也是它的無可替代性,就在于它可以讓人還在世時就開始凈化自身的心靈,從而使之有朝一日能夠擺脫流變的現象領域而進入永恒的真理領域。反過來說,如果哲學不能凈化人的心靈,無法使心靈獨立于肉體而存在,從而無法達于真理之域,那么,哲學也就不配稱之為“愛智慧”,因為智慧就是對真理的把握。因此,在柏拉圖這里,“習作死態”與“愛智慧”也就是同一件事。同時,我們應當注意,在柏拉圖這里,要使“哲學即以習作死態為職志者”這一命題變得有意義,僅僅強調心靈獨立于肉體存在還遠遠不夠,它還必須以真理存在,即以永恒事物存在為條件。哲學之所以要承擔起凈化心靈這一使命,原因就在于真理本身是一個絕對的、永恒的領域,而我們的肉體作為一個有限的存在物根本無法對之進行把握,因而,要對之進行把握就必須依靠我們的心靈。凈化心靈的目的也就在于使我們的心靈獲得同真理之領域同樣的本質,以便對其進行把握,“在生時吾意以為若能絕少顧念肉體,始能于智識有所趨近且勿沉淪物欲,而常自保純皎,以迨神命解脫之時。既能脫免于肉體之愚妄,則吾自即純皎,且必能與純皎者同處,遂于凡純皎者無所不知,如此即可謂有得于真際矣”,這即是說,如果真理本身或者說永恒事物是不存在的,那么,心靈的獨立也就失去了意義。
實際上,在柏拉圖這里,真理之為真理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永恒的、自在的領域,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們感性世界的根據。感性世界的具體事物變動不居,但是,真理作為感性世界的根據,也就是使感性世界成為感性世界的最后原因,或者說,是使一物成其為該物的原因,是事物的本質,是一切可變之物的絕對標準,是概念,具體事物只有“分沾”了此一絕對標準方能存在,而絕對標準之為絕對,就在于其絕對真實性、永恒性。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柏拉圖所說的真理并非是科學真理中所說的真假判斷,也就是說,這種真理并非是一種可用定義來把握的知識,因為當我們在用定義去把握一物時,我們首先必須有將該物判定為該物的知識,也就是那個使該物成其為該物的絕對標準,換言之,這種知識并非是一種“對象性”知識,而首先是“存在性”知識,也就是說,在柏拉圖這里,“存在性知識”實際上是一切“對象性知識”的前提,這也就是哲學所要追求的真理,換言之,哲學所追求的是那種使具體事物成為可能的知識。在此,我們可以說,就柏拉圖將哲學規定為“以習作死態為職志者”來說,他首先要向我們揭示的就不是“真理是什么”的問題,而是要使人的心靈得以獨立以便可以進入絕對存在者之領域而與之共在,其本意就是要讓我們覺悟到心靈作為人的本質的絕對性與獨立性以及真理的絕對性與永恒性,也即是說,讓人作為自身存在的同時,也意識到絕對事物的存在。
二、哲學之為“成己”與“濟世”
由上,我們可以認為,在柏拉圖這里,就哲學要讓人意識到心靈的獨立存在這一方面來看,哲學是為“成己”之學。因為在柏拉圖看來,人之為人的本質即在于人的心靈,心靈是“致肉體于生者”,對于人來說,心靈是永恒者,肉體則轉瞬即逝,心靈可以獨立于肉體而獨存,而肉體離開心靈,卻轉眼間便化為腐朽,“心靈近于神,近于不滅,近于常,近于不散不變,具有智;而肉體則屬于凡,屬于可滅,屬于雜多,屬于易散與善變而不具有智”,換言之,心靈是人的本質存在方式,是人的本相身份、本源形態。實際上,在《斐多篇》中,肉體之所以召到否定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其是心靈的牢籠,或者說,是肉體使心靈陷入受奴役狀態。墮入肉體的心靈耽于物欲,沉迷于聲舍犬馬之中,從而忘卻自身的來歷、失去其之為人的本位,這遠離自身本源的心靈也就不可避免的迷戀于那可見的感官世界而忘卻了不可見的理智世界,正因如此,在柏拉圖這里,對真理的學習才成為“回憶”。反過來說,柏拉圖說哲學是“習作死態”,其本意就在于要讓人去回憶自身的本源,讓人追問自身的來歷,讓人意識到自身的超越性(神圣性)存在。這種對自身本源的追問,也就是發現自身的努力,也就是要使自身成其為自身的努力。而使心靈獨立于肉體而存在,也就意味著人“趨赴于與其本相相近者之所”[12]P103,從而作為自身的本質而存在。這也就是說,一個使自己的心靈獲得獨立存在的人,也就是一個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從而作為“人自身”而存在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哲學乃是“成己”之學,其所成者就不是別的,而正是要成那“本真之己”、“本源之己”。就哲學不僅要人意識到自身的獨立存在,同時也應意識到“絕對事物”的存在而言,它同時又是“濟世”之學。因為絕對事物的存在,也就意味著人并非僅僅處于與世間萬物的世俗性功利關系之中,而且還處于與絕對者的絕對關系之中。也就是說,人在此世間的行動并非是一種可以隨心所欲的行動,相反,他的行動應該成為一種有所規定、有所擔當的行動;他所應當考慮的也就并非僅僅只是當下的世俗性事物與功利性事物,否者,當死后之審判來臨之時,他將無以立身①。這同時也就說明,人在世間的活動不僅要具有世俗的合理性,而且必須具有神圣的真理性。因此,人世間的一切倫理規范與法律律令就不能只是涉及人世間的世俗利益關系,同時還要涉及與神圣事物之間的絕對關系,人必須根據絕對者的絕對律令來規范其在世間的生存活動。就此意義上來說,哲學實為“經天緯地”、“安身立命”之學,是追求與維護真理而明明德于天下之“大學”,哲學的使命也就不在于為某一個集團利益而服務,而在于示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從而安天下人之身心。
三、哲學之為自由之學
就哲學使我們覺悟到自身的本源來說,它乃是“成己”之學;而就意識到自身的本源,同時也就意味著對絕對事物、絕對法則的覺悟來說,哲學又是“濟世”之學。所謂“成己”,亦即指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作為一個獨立自在的人而存在,因此,“成己”就意味著“解放”,即將我們自己從世俗的耽于聲舍犬馬的功能性角色中“解放”出來、從受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成己”也就是“成自由之己”,或者說,成為一個自由的存在者而獨立自在,也就是說,自由在這里成為了自我的本質,本真(本源)的自我也就是自由的自我。同樣,所謂“濟世”,也即意味著將他人從那些世俗角色中“解放”出來,使他人同樣作為一個自由存在者而存在。因此,在柏拉圖這里,無論是“成己之學”還是“濟世之學”,其基礎都在于自由,“成己”就是成為自由的“自我”,而“濟世”也就無非意味著將他人同樣作為一個“自由存在者”來看待。因此,無論是“成己”抑或“濟世”,其根本都在于去承擔起一個“自由存在者”的絕對責任。因為他人是自由的,所以“自我”對“他人”負有絕對責任,“他人”因此而擁有其絕對尊嚴與價值;因為“自我”是自由的,所以“自我”可以承擔起對“他人”的絕對責任,并且,“他人”也因此對“自我”負有絕對責任,而“自我”也因此擁有了在與他人關系中的不可替代的絕對身份。正是在這種責任的相互承擔與尊嚴的相互給予中,柏拉圖構想了一個理想的國家,這個理想的國家也就是一個每個人都恪盡職守的履行自己的義務的國家,因而是一個絕對正義的國家,但這已經是他在《理想國》中進一步涉及的思想。就我們本文談論的《斐多篇》來說,柏拉圖是通過對蘇格拉底之死的描寫來述說著他對人類之自由本性的確認。蘇格拉底的從容就義是柏拉圖對于人類自由本性的最直接和最有震撼力的證明,雖然這是通過對蘇格拉底之死的直觀展示而非邏輯演繹而得到證明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心靈的獨立性這個主題在《斐多篇》中才被賦予了當頭棒喝、直指人心的力量。在這里,心靈的絕對獨立存在,或者說,我們本質上作為一個自由的存在者而獨立自在,對于蘇格拉底來說絕非只是其死前的理論探討,恰恰相反,這實際上是其生活的基本信念,因為對心靈的絕對獨立性的確信,蘇格拉底選擇了慷慨赴死,而蘇格拉底的視死如歸反過來又強有力地證明了其信念的真理性,而柏拉圖也在此完成了其對哲學之本質的探討:哲學是“習作死態”,其目的在于追求真理,真理的本質是自由,哲學因自由而生,也應追問與維護自由為自己的使命,哲學乃自由之學。這就是柏拉圖對哲學之本質的基本洞見。
作者:馬哲辰單位:貴陽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 上一篇:幼教視域下的兒童哲學論文范文
- 下一篇:傳統養生的哲學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