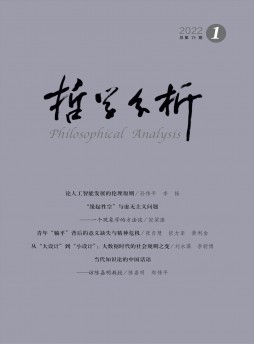哲學角度看翻譯本質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哲學角度看翻譯本質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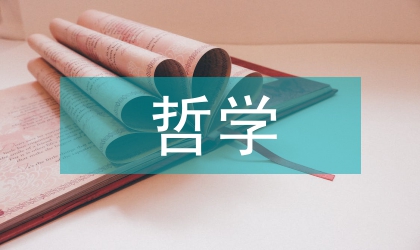
柏拉圖強調意義具有普遍性,且在經過語言傳遞前后都具有安全性。即一個事實(實際意義)在跨過語言邊界后,其本身意義依舊可以保持“原汁原味”,并未因為受到語言的影響而產生絲毫的扭曲。柏拉圖在闡述這一哲學思想時并未從翻譯層面加以考慮,更沒預料到它對翻譯研究的深遠影響。依據他的觀點,人們亦步亦趨地認為原文和譯文、作者和譯者形成了一種隸屬關系,原文和作者總是占據統治地位。這種哲學觀點盛行了幾千年,譯者不但要隱身,而且被看不見的鐐銬捆綁了幾千年。
本質傳統中“本意不變”“靈魂不變”是柏拉圖思想的精髓,他所倡導的二元對立思想即內容和形式、語言和思想、能指和所指、語言和意義等不僅可以分開,而且還可以獨立存在。語言被視為提供原來意義傳輸和交流的穩定載體,這樣意義就可以通過這樣的載體安全地被運送至別處。既然事物本質不受我們影響,它們的名稱又可以代表其永久不變的本質屬性,那么這種屬性必能超越任何語言障礙,又可以在任何時空條件下得到重復和延續。依據這樣的觀點,已在一種語言中存在的事實可以完全在另一種語言中體現出來,而且意義可以超越歷史、語言、文化,作為意義傳遞的翻譯過程亦被認為是簡單的復制過程。德里達認為,黑格爾、康德、索緒爾、海德格爾都是以此為理論基礎,并把它稱為具有穩定、真實、純粹性質的真理。這樣看來,語言的作用被嚴重低估了,語言本身對概念或意義的形成或構建沒有起到絲毫的作用。
同樣,作為復制者,翻譯者的作用是簡單機械地模仿原著。翻譯者被認為應該和事物分開,意義可以和語言分開,翻譯在語際傳輸時應遠離人為痕跡,譯者本身的能動性亦會受到壓抑。這樣一來,譯文對原文的從屬地位得到了安全的保障。語言和意義的關系被形象地比喻成衣服和身體的關系,語言像衣服一樣被精心設計來保護身體。不管衣服(語言)如何精心變換,身體(意義)一直保持不變。由于受到衣服的保護,譯者永遠不能接觸到身體(意義)本身,譯者的工作就是換衣服。譯者只是從事中立的、服務的、機械的傳輸性(更換衣服)勞動,譯者的主體性被徹底否定。譯作因此看成原作的派生,譯者和身體(意義)因為衣服的阻隔而被彼此孤立起來,譯者的隱身成為了翻譯界的約定俗成。翻譯的過程正如一個透明的過濾器,譯者的干預是不允許的。譯者、語言、翻譯的內容都獨立存在,而且互不干擾。譯者機械地把一件衣服(原語)從身體(內容)脫下,換上了另一件衣服(譯入語),身體卻毫發無損,并且身體與譯者不許有半點接觸。這樣,譯者的創意和構建能力便被剝奪了,即使輕微的接觸也將被視為觸犯了“清規戒律”。
事實上,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和衣服的接觸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如許多人將英語“unlessyouhaveanaceupinyoursleeve,wearedished”譯成“除非你有錦囊妙計,否則我們輸定了”。但英語中“haveanaceupinyoursleeve”是西方賭博時的“王牌”,這種說法在英語中已成為一種約定俗成。而“錦囊妙計”是中國戰場上的巧妙計策,這樣的成語在漢語中傳遞了幾千年,兩者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內涵。“錦囊妙計”的翻譯說明了,譯者在進行雙語轉換時具有主體性,翻譯內容必定受到翻譯者的“觸碰”和變通。因此,本質主義本身的缺陷為反本質主義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尼采作為反叛柏拉圖思想的旗幟性人物,對語言做出了新的定義。他辯稱,語言是人類創造的產物,如果意義或概念脫離了語言環境便不復存在,更談不上從一種語言傳遞到另一種語言。語言作為約定俗成的一個體系,通過它產生的每個概念都會留下人為的痕跡,甚至它會把不等同的東西通過語言符號人為地等同起來。RosemaryArrojo教授通過樹葉來說明等同的不可實現性。我們所說的概念上的“葉子”只是理想化的葉子,我們通過概念原型來判定所有的葉子都是展開的、脈絡分明的、尺寸合適的、有些卷曲的、帶有顏色的。正是這個約定俗成的概念使我們忘掉了不同葉子之間的區別,并產生了“相同的東西可以復制”這一虛幻。人們是為了形成概念而故意忘掉葉子間的不同,不過正是“葉子的概念化”使語言體系能夠成功地運行。人們往往忽視概念或意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構建的,甚至是人們創造的。由于構建它們的時代和環境不可能相同,概念或意義也就不能復制。文本在用另一種語言表達時便不可能體現出完整的原有含義,因為它承載了其形成過程中歷史和環境的痕跡。正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Davis所說“構建的東西易于改變”。
當人們在尼采對柏拉圖思想的批判過程中醒來時,翻譯已經不再被認為是把意義從一種語言傳輸到另一種語言的過程,由此翻譯的理念發生了轉變:在一種語言中的文本經過規范的梳理和轉變后用另一種語言表現出來。作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曾經被數次翻譯成英文。其中,賽珍珠的譯文既體現了原汁原味的“中國元素”,又使西方讀者易于接受。而沙博理的譯文更適合美國口味,原因在于他是生長在西方的學者。兩者的翻譯難說優劣,它們都是譯者基于自己的文化歷史背景,從自己的角度對譯文進行解讀。Borges認為雖然譯者們表明翻譯要忠實于原文,但他們的翻譯作品皆帶有他們自己的痕跡,譯者注定要在譯文中顯身。這種痕跡既有歸化又有異化,因此,譯品某種程度上是重新構建了原著。《水滸傳》的翻譯是反映譯者興趣和其所處環境的一面鏡子。我們不應該批評這部著作翻譯的不忠實性,而是認定原文和譯文之間的不同是譯者的構建成分,這種認定內容成為當今翻譯研究的中心。例如,翻譯對文化及身份構建的作用、歸化和異化的關系等。原文和譯文的差異性研究是直接或間接用后尼采時代的哲學來研究的,這種差異同時是探討原文和譯文之間關系的最具創意的成分。譯者接受這一事實的好處是譯者可以在選擇歸化和異化時自己做出決定,并由此不再隱身。譯者可以從2000多年來被禁錮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恢復其“自由身”,并逐步恢復其處理翻譯的權威性。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寫道:“翻譯不依靠本意而生存,是本意依靠翻譯而生存。”如果說原文在精神層面、歷史層面延長了作者的生命,那么譯文使作者在異域文化中獲得新生。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能夠傳播至今,就是因為它們被不斷地翻譯和闡釋(通過語內翻譯或語際翻譯),而讀者讀到的往往是更新的譯文。德曼在評價《譯者的任務》時說,翻譯不是文學的附庸,翻譯是一個文本的“來世”。
文本因翻譯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并獲得了生命。正如莫言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一樣,翻譯不但為其作品注入了新鮮血液,而且為其贏得了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讀者的青睞,從而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解構主義認為,譯者是創造的主體,由翻譯所產生的文本是創造性語言。譯文不僅和原文地位相等,而且原文還得靠譯文才能生存下去。尼采在意義傳遞過程中對語言作用的重新評估以及對事實與習慣、事實與權力關系的重新定位和梳理不但對哲學而且對翻譯學、人類學都意義深遠。人們對語言的興趣及語言的作用使許多以文化和主體性為核心的學科界限模糊起來。在這種前提下,翻譯被理解成“規范的意義重組”,文化對翻譯方式的影響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性,被理解成一種翻譯。同樣翻譯研究不但成為跨學科研究的關鍵,而且對語言殖民、性別翻譯意義深遠。語言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使人們對異域文化的處理方式得到重新定位。當代哲學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界面,這個界面超越實質主義者的束縛而使翻譯學科活力四射。譯者由原來的機械性的模仿者變成了調節兩種文化的“外交家”,因為他在表面處理文字的同時,必須留下文化空間,這樣譯者變成了“作者”———專門為異域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的作者。憑借譯者個人的翻譯策略和技巧,人為地創造類似原文的譯文,因此他在處理文化之間的關系、政治、文學、讀者接受程度等方面成了權威,從而凸顯了譯者的政治特點。在翻譯層面上,從柏拉圖的“意義可以翻譯”到尼采的“意義是翻譯的結果”絕對是質的飛躍,因為它意味著原文和譯文不存在對稱式的對等。從這一角度來看,翻譯不再是從一個語言容器轉移到另一個語言容器,因為譯者選擇的每一個詞匯都揭示了他所處的歷史、政治、社會環境,譯文無論怎樣都烙上了譯者的“印記”。正如Lefevere指出的:翻譯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無論哪一位譯者,都會受到各種主觀或客觀條件的限制,絕對“信”的譯文不可能存在。
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深刻探討了語言哲學問題,尤其是“純語言問題”。正如維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所有的哲學都是語言哲學。”本雅明的翻譯研究是在語言哲學的框架下展開的,他認為,盡管存在不同的意指方式,但依然可以指稱同一事物,從而想證明“純語言”的存在。雖然語言之間或大或小地存在差異,但它們之間具有可譯性。德里達的《通天塔之旅》借用了“純語言”的觀點,通過《圣經•創世紀》中的故事來說明專有名詞的多義性打亂了“純語言”的建設,并使其成為不同的語言。猶如本雅明的比喻,“純語言”好像一個花瓶,各種語言猶如這個花瓶的碎片。我們見到的只是這個花瓶的碎片,即各種具體的語言。翻譯的任務是把各種語言碎片接合起來,最大程度的恢復花瓶的原貌。
哲學對翻譯本質研究的啟示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從實質主義到反實質主義。人們逐步了解了語言本質和意義傳遞問題,其內在規律可以通過翻譯的深層次研究揭示出來。實質主義認為,語言具有安全性,它可以把意義安全地送達到目的語。而反實質主義認為,語言和概念都是人類發明和構建的,而發明和構建的東西都易于改變。這一轉變不僅使傳統的對等理論得到比較徹底的顛覆而且使我們以更通達的態度來對待可譯性和不可譯性。其次,重新審視譯者的地位和作用。翻譯不再是原文的機械性模仿,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改寫。因為原文要靠譯文來生存,所以譯者和譯文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例如,本雅明在1920年左右完成的《譯者的任務》幾乎被遺忘了,但是由于解構主義的風起云涌,各個國家的哲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才重新意識到其文章的含金量,《譯者的任務》因此被譯成多種文字,文章的生命得以延續。由此可見,原文和譯文、作者和譯者多年形成的上下級關系、隸屬關系被徹底打破,而譯者也從被看不見的鐐銬捆綁了幾千年的桎梏中得以解脫。再次,譯者的痕跡在譯文中得以彰顯,譯文會顯現譯者所處的歷史、政治、社會環境,譯者對原文的解讀無論如何都逃脫不了他所處的環境對他的限制,譯文無論怎樣都會烙上譯者的“足跡”。從哲學的高度來理解翻譯,起始于研究意義傳遞的可能性,但它卻能夠把文化、譯者、語言、翻譯巧妙地結合起來,使翻譯研究拓展到比較文學、人類學等領域,為翻譯本質的研究開辟了新天地。
作者:蔣鳳霞蔣繼春關玲永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長春理工大學科技翻譯中心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院北京建筑大學文法學院
- 上一篇:傳統文化在市場的價值探討范文
- 下一篇:傳統文化與設計基因的探討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