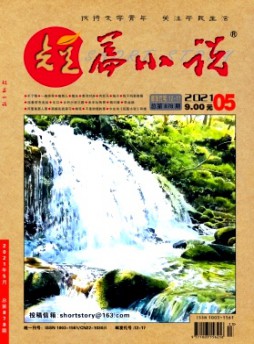“新小說”的美學新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小說”的美學新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文藝理論研究雜志》2015年第三期
晚清“小說界革命”以政治小說的勃興為起點,“舊制度”與“大革命”顯然是近代小說變革的基本論域。正因如此,此類小說往往會立足于“資政體、助名教”,有“中體西用”之局限。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新小說”中革命的破壞美學經過新儒學的轉化,從救亡與破壞的互資利用,轉化為救亡與啟蒙的相互促進。這與五四以后“救亡壓倒啟蒙”形成對照。以康門激變為線索可見,梁啟超等人所欲構筑的儒家視域下的革命美學,創生性交融于破壞性,成為儒家道德救世美學新的表達。晚清儒學激變與革命烏托邦的轉化生成關系,是我們重新理解“新小說”的重要出發點,也是把握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革命內在演進理路的重要切入點。
一、革命的破壞美學
20世紀初,逃亡日本前后的康門弟子受到盧梭民約思想和俄國虛無黨、無政府革命思潮共同沖擊,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以“十三太保”為代表的康門激進弟子群體倡言革命,與孫文為代表的共和革命派漸有合流趨勢,與老師康有為的分歧則達到了頂峰。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以及革命小說始倡于國。隨著康門激變,“革命”一詞隨之廣為流傳于中土,其中無政府主義和虛無黨思潮又是破壞主義中最激烈者。“三界革命”實為康門激變的產物,梁啟超所言“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革命”之意涵蓋上述“歐洲真精神真思想”,這與19世紀末黃遵憲“新詩派”存在根本不同(陳建華183-96)。換言之,梁啟超等康門弟子20世紀初展開的“三界革命”才是真革命,所謂“詩從革新命,書號自由篇”(聘庵《贈別復庵》)中的“自由篇”即《飲冰室自由書》,“破壞主義”是其核心觀念之一。梁啟超說道,“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梁啟超全集》1:349)。“凡一國國民,當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時,不挾猛烈之勢行破壞之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劇,則國民難得而蘇。此變革腐敗之政體,喚醒全國之民氣,所以重破壞主義。”①盡管從儒家美學傳統的角度看,我們并不能夸大革命中血腥的一面,但是至少在1902年“小說界革命”前后,康門弟子破壞之心最熾,其創作實績也較大。這一時期,康門弟子除梁啟超外、韓文舉(捫虱談虎客)、羅普(披發生、嶺南羽衣女士)、麥孟華(蛻庵)、麥仲華(玉瑟齋、玉瑟齋主人)、梁啟勛(曼殊、曼殊室主人)、馬君武等人也都集中發表了影響深遠的作品。自康有為首倡“小說學”以降,《新小說》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半數出自康門弟子,其思想與技巧的顛覆意義早已為文學史論者所肯定。其中,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是“新小說”的開山之作,而《東歐女豪杰》則是近代女權小說、虛無黨小說的代表作品,五四“革命加戀愛”敘事模式在此可見端倪。如果我們再考慮到康門的辦報辦學活動對吳趼人、李伯元等等通俗小說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康門思想觸發了晚清小說的繁榮更是不爭的事實。近年來,不少研究者業已指出,晚清作家對社會理想和生活理想的追求,只有大致的傾向,而沒有清晰明確的理論表述。一來連作家自己都把握不準,隨時可能修正甚至改弦易轍;二來矛盾對立的各方觀點相互滲透,呈現錯綜復雜狀態。因此,陳平原認為將晚清小說界劃分為革命派、維新派和保守派毫無必要(199)。事實上,晚清小說劃界之難緣于“革命”本身的曖昧性。無論是作為維新派和保守派,其思想、行動和創作中都有革命的要求和傾向。從思潮上說,民主立憲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科學主義等等都是革命潮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革命派、維新派和保守派的區分只能代表一種政治光譜上的區分,在文化的光譜上,如果完全套用這種區分則暗含著一種“真理的暴力”。即真理將自身化約為主義,成為一種獨斷的意識形態。
《人肉樓》是這一時期韓文舉思想激烈交鋒的作品,也是康門弟子群體激進思想的體現。《人肉樓》作為破壞主義的代表作,它既是一部歷史的寓言,也暗含著巨大的破壞沖動。在形而下的層面是排滿,在形而上的層面是否就是新興的革命意識以及無政府主義呢?或者我們更進一步問,康門的新儒學傳統及其內部分歧是否為破壞美學提供了支持呢?這是有待考辨的問題。《人肉樓》的故事最核心的主題是排滿。“人肉樓”上坐一少年,后坐一老嫗。前者顯然是光緒,后者指慈禧,“其老嫗啖人肉最多,十余年間,啖‘須陀人’數百萬,其旁坐著數十人。專執剖割之役”(韓文舉98)。其中對老嫗的痛恨之情顯然是康門弟子失敗后流亡日本時的心跡。文章的末尾那位吃人最多的老嫗“走于村野,后為村夫執殺之”,顯然指涉排滿獲得成功,慈禧以及后黨窮途末路。康門這一立場的轉變在時務學堂時期就已經看出端倪。梁啟超和韓文舉共同主辦時務學堂時,便秘密印刷數千冊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節本,并且附上他們的評注。這無疑對19世紀最后幾年的思想與文學啟蒙起到了巨大的影響。②1899年的江之島結義,康門弟子中激進分子與康有為的分歧逐漸公開化,梁啟超、韓文舉、歐榘甲等13人上書直云,康有為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由梁啟超等人繼往開來。這些康門歷史上著名的“十三太保”,排滿“言革”之心已經非常堅定。③1899年還堅持“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為本”的歐榘甲,1902年以“太平洋客”為筆名的詩文中滿紙都是“滿賊”和“清賊”。④其轟動一時的《中國歷代革命說略》疾呼“將獨夫民賊之血,灑地球而皆紅,則民安矣!”⑤換言之,20世紀初排滿風潮的激蕩與保皇會中康門弟子的激進轉向密不可分。
從《人肉樓》情節看,小說已經超越了傳統康門弟子的帝黨后黨之爭的模式,而是注入了現代民族主義思想。這也是康門弟子與老師康有為之間的重要分歧點。康門弟子從最初追隨乃師參加保皇活動到“惡滿洲之心更熱”,從保皇到排滿,與興中會孫中山合縱連橫,一段時間內充當了激進革命的急先鋒。梁啟超1902年《與夫子大人書》為樹園(韓文舉)和自己辯解稱,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梁啟超還以日本討幕作比,認為討滿是當下最適宜之主義(丁文江趙豐田144)。阿英《晚清小說史》將“種族革命小說”看作最被忽略但最不應忽略的題材(90),顯然是看到了此類小說巨大的歷史影響。阿英列舉的《自由結婚》《洗恥記》《獅子吼》《盧梭魂》《東歐女豪杰》等等幾部作品正是1902年前后的作品,并且與《人肉樓》的情節有許多雷同之處,可以想見,這與梁啟超韓文舉等人對民族主義的極力鼓吹有關。20世紀最初幾年,梁啟超本人創作了一系列種族革命題材的小說戲曲,韓文舉則在相關的作品點評中與之遙相呼應。對《新羅馬》的點評中,“捫虱談虎客”云: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眾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康門梁啟超、韓文舉、馬君武、羅普等人竭力譯介并鼓吹下,虛無黨小說風靡一時,并且成為激進革命的最高代表。虛無黨小說宣揚死亡之美,傳達了一種命運抉擇的巔峰體驗,一種全新的包容崇高、悲愴、恐懼、震驚、神圣、哀憐、怪誕以及嫵媚的復雜美學體驗。相比《水滸傳》等傳統俠義小說,虛無黨小說所呈現的革命精神顯然更為決絕。以陳景韓“冷血體”為代表,虛無黨小說以“奇”“勇”為特色。在“奇”的方面,《爆裂彈》有著精心設計的圈套、巧妙排布的炸彈,也有誘惑敵人的種種手段,不輸三打祝家莊的曲折。在“勇”的層面,虛無黨人都是與當權者酣斗的勇士,即便涉險蹈死甘之如飴。與一百單八將不同是,革命黨人、“虛無美人”身上更有著一種屬于新時代的美的“無功利性”。因此,《水滸傳》在晚清文人的重估風潮中往往會附會到虛無黨和無政府主義精神上去。經典的附會如天繆生言,“觀其平等級,均財產,則社會主義小說也;其復仇怨,賊污吏,則虛無黨小說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治小說也。”⑥平等級、均財產、復仇怨、賊污吏都只是手段,這是一種包容一切反強權訴求的小說文類,其終極歸屬在于一種革命的虛無主義,它恰恰是無功利的。
無功利的虛無主義賦予虛無黨小說一種獨特的崇高感,這一崇高感是無形式的,是打破等級、財產、組織、仇怨的破壞主義,是康德所言的心靈受到巨大震撼的消極的快樂。正是因為生存與幸福不可得,才有了虛無黨這一“擾亂平和的種子”,其實“平和幸福,奚誰不愛?殺人流血的事,誰不驚心動魄?平和之法茍能救我國家,虛無黨人不愿?”正因為“我們虛無黨人無所逃避,只得出此激烈的手段。”⑦在這種“無依據可循”的崇高美中,《虛無黨奇話》《女偵探》《東歐女豪杰》等等將主人公置于“生”與“死”、“個人”與“集體”、“社會正義”與“私人感情”的二難處境中,以此展現出人性的復雜性。相比同時期海派狹邪小說、林譯小說和鴛鴦蝴蝶小說,“虛無美人”形象體現出一種“形而上”的性質。溫柔仁愛的蘇菲亞、倚劍美人華明卿、風流俠女夏雅麗都是哀憐與嫵媚的結合。在蘇菲亞就義瞬間,其母唱曰“兒耶!兒耶!大志乎!偉事乎!今生不成,來身繼之。魂兮有靈,速攜爆裂丸而歸來!”⑧這是詩人向著不朽的觀望,向著隱秘著的神圣精神的觀望。在一種烏托邦式的召喚中,逍遙與拯救統合在了一起,“美人之死”的豪邁光芒穿透并照亮了黑暗世界。“美人之死”是最富于詩意的文學題材。如艾倫?坡《創作哲學》所言,當憂郁最靠近美的時候最富于詩意。如果是一個美麗女性的死亡,毫無疑問,它是世上最富有詩意的題材。這種美是一種“效果”,而非“性質”,所以先打動靈魂,而不是理智(陸揚55)。“虛無美人”形象所體現的破壞美學的價值在于,此類小說著眼于打動讀者的靈魂,而非理智。理智與“打動靈魂”的破壞恰恰是一對矛盾,也是一對悖論。“新小說”的破壞美學正是一種悖論的體現。這一悖論不僅是儒家和平主義與革命破壞主義之間矛盾的體現,更隱藏著20世紀初革命思潮傳入之初革命美學內部難以化解的沖突。
二、儒學新變與革命悖論的化解
破壞主義關鍵性的內在悖論當要理清。以西洋無政府主義思想觀之,排滿無疑是符合以反抗一切壓迫為宗旨的無政府精神的,但民族主義的情感恰恰又與無政府主義反對民族壓迫的理念相悖。事實上,正是這一內在理智與情感的悖論,塑造了“新小說”美學一些獨特的特質,并且這些美學特質多與新儒學在晚清的深刻轉型有關。首先,排滿的現實訴求與民族主義思想的塑造存在著某種張力,這導致康門小說將不同訴求都簡化為對破壞美學的追求。正是在排滿的背景下,虛無黨精神通過日本被保皇會引入中國,由此引發了虛無黨小說以及各類暗殺小說、俠客小說、會黨小說的流行。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并沒有明確的區分,并且如梁啟超所言,他們只想引入的是虛無黨的暗殺手段,并非其主義,⑨這也客觀造成理論上的理清變得沒有必要。結果是各種革命思想都歸結為破壞主義。吳樾形象地說這一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鄒魯12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言:“以當時情勢言,非革命排滿,無以變法,復生見之甚透,論之甚切。又復生以暗殺伸民氣,亦為此后革命黨人成功一因”(742-43)。從現有史料看,梁啟超在《無政府黨之兇暴》與《難乎為民上者》中首先使用“無政府”一詞。其后的《致康有為書》《新民說———論進步》《擬討專制政體檄》《論俄羅斯虛無黨》更是直接宣揚破壞主義。另一康門弟子馬君武則第一個系統介紹了虛無黨精神和無政府主義學說。1902年,他以“獨立之個人”之名翻譯了英國克喀伯《俄羅斯大風潮》,極力宣揚這一“新主義”。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中記載,讀畢這一“新主義”后,讓人感嘆其意欲獲得完全無限制之自由,不僅專制的君吏當去除,即便是民選的政府亦當去除,此學派創于俄羅斯最高貴族巴枯寧,可見破壞之烈。以至于孫寶瑄嘆道“余謂創此派之人,其心為救世,非不可嘉也,病其識不足。若從其說,反為害于世”(713)。對破壞美學的崇尚是這一時期康門弟子小說創作和評點的重要特點。例如針對梁啟超《新羅馬》中的“女燒炭黨”,“捫虱談虎客”將之比附為虛無黨人,他批注說:“俄羅斯之虛無黨,閨秀最多,其行荊聶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
《東歐女豪杰》第二回批語中,蘇菲亞等虛無黨人也被“捫虱談虎客”評為“至誠義俠”。這些虛無美人與荊軻、聶政一樣,將死亡與燃燒化作昂揚激勵的情意生命之表現。1902年前后,保皇會會員特別是萬木草堂的康門弟子以《文興報》《新中國報》《新民叢報》等為陣地倡言破壞主義。梁啟超《與夫子大人書》為韓文舉、歐榘甲、徐君勉向康有為辯解稱,“亦未始不懼,然以為破壞終不可得免,愈遲則愈慘,毋寧早耳”(丁文江趙豐田144)。破壞主義倡行,已經是時代潮流,梁啟超自辯說即使自己不說,他們也會說,并且康門弟子中猖狂言此者,有過弟子十倍者。這些比梁啟超強十倍的人之中,韓文舉是年齡最長的領軍人物,其創作的《人肉樓》則是破壞美學的巔峰之作。作品中,無論是康有為念念不忘的儒家黃金時代,還是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中對仁君名臣的脈脈溫情,都被徹底地質疑與解構。歷史像一部作品的廢墟,其中不再有永恒的生命,而是不可抵抗的腐朽與死亡。其次,康門小說的破壞主義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虛無黨破壞美學,而是儒家美學與革命美學的混合物。換言之,破壞只是儒家意向結構中的一個環節,它并非是終點,而是創造性循環的一部分。施蒂納和巴枯寧的虛無主義美學通過懸隔一切權威達到“真正的利己主義”,而康門的破壞美學是要以破壞為手段“回到人本身”。成中英在談及儒家人本美學思想時如是說,“儒家的超越重視人的發揮、人的美德經驗的發揮,導向善、導向真;同時在人的經驗里發展一些價值,也能夠導向美”(98)。在韓文舉看來,虛無黨人的精神就是菩薩的救世精神。《東歐女豪杰》第一回華明卿吟誦盧梭《民約論》一節,“捫虱談虎客”批云“救苦救難觀世音經”。第四回云,蘇姑娘是個救苦救難的菩薩特來普渡我們的,批云:我愿我國降此菩薩。第四回中還有一個細節,子連欲聚眾劫獄,蘇菲亞卻說,“這位子連那么義俠,真真令人敬服,只是劫獄這件事,是斷斷使不得的。為什么呢?第一件,為著我一個人,燒了民房,反叫許多人受苦,我心里卻是不安;第二件,萬一事弄不成,害了子連各位的性命,即不然,亦必至失了職業”(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一卷》上冊140);第三件是警察有了防備,劫獄不容易,再者,獄中雖然沒有自由卻可以讀書研究大道理。韓文舉對此的批語說,“果然是菩薩心腸”。如此種種菩薩心腸與巴枯寧的狂暴、虛無黨的破壞其實并不合拍,但是在羅普和韓文舉的筆下,卻有著另一種東方式的“打動靈魂”的力量。梁啟超因此感慨,“夫樹園、君勉,豈肯背師之人哉,然皆若此,實則受先生救國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時勢,實不得不然也”(丁文江趙豐田144)。韓文舉梁啟超等康門弟子以破壞主義作為康有為救國救民之教的實踐,豪俠之情回歸了仁者之心,這才是這一革命時代最值得珍視的儒家人格美學。再次,康有為所傳承發揚的救國救民之教深刻影響了梁啟超、韓文舉、羅普等人的小說創作,以救世主義化解破壞主義成為一種內生的、自覺的美學追求。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雖是宣揚革命之作,但其中對革命破壞的反思也頗費筆墨。文中多處點到法國大革命讓人毛骨悚然,玉石俱焚的災禍讓人民反受其害。借黃在田之口,梁啟超反思道:“我也知道你這破壞的心思是要歸結到建設一路,只是已經破壞未能建設的時候,這些悲風慘雨,豈是語言筆墨能形容出來?”(第三回)羅普《東歐女豪杰》作為革命小說的代表作,其中虛無黨員的形象已經發生了異化。《自由血》中記載,蘇菲亞原是“十步之內,劍花彈雨,浴血相望,八駒萬乘,殺之有如屠狗,斷頭抉目,一瞑不視,追捕之命,蹈死如飴”的死士形象。女性暗殺者蘇菲亞形象成為晚清小說最為靚麗的風景,深深影響了魯迅、巴金和蔣光慈等等一代五四知識人。蘇菲亞“有著天真爛漫的容貌和溫柔仁愛的性情”,“卻又是恐怖主義團體中最可怕的黨員”,以至于蔣光慈發出“此生不遇蘇維亞,死到黃泉也獨身”瑏瑡的感嘆,一時傳為美談,而魯迅也曾談到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都忘不掉蘇菲亞,她是暗殺的好手,更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魯迅4:459)。不過,在羅普筆下,蘇菲亞雖是暗殺的好手,卻“現在總要到處游說,提倡風氣,別要急激從事的話”。第二回中,蘇菲亞在演講中也認為,籍沒貴族,沒收土地的方法便是“太過激烈”,并且企圖從政府一面找到辦法。同樣,革命黨人晏德烈在學堂里也主要從事啟蒙工作,洋洋灑灑的宏論也主張溫和立憲,和虛無黨所奉行的暗殺主義大相徑庭。這一口吻與其說是俄國虛無黨人的主張,不如說是康門弟子的政治理念。在第二回的總評中,最打動“捫虱客”的“虛無黨之精神”在于,“蘇菲亞以千金之軀,雜伍傭作,所至演說,唇焦舌敝,百折不磨”的救世精神。綜上可見,破壞主義在康門弟子的轉化下,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即從救亡與破壞的互資利用,轉化為救亡與啟蒙的相互促進。創造性因此超越了破壞性,烏托邦小說、虛無黨小說的終極理想最終都歸附于天下大同的想象。革命黨“向死而生”以及其代表的康門破壞美學,居于破壞的終點,是高貴人性凝結成的生命理想的一次精神大凱旋。
三、超越的救世美學
在新小說家的創作中,借助對破壞美學的宣揚到反思,儒家救世美學的超越性獲得了一種另類的展示。新儒學作為重要的革命路徑,是在錯綜復雜的西學思潮之外觀察文學變革和社會變革的重要視角,但是這一重要的方法論長期遺落于被忽視的角落之中。以《人肉樓》為例,我們甚至可以超越目前學界通行的滿漢之爭的解讀,將“們焦人”對“須陀人”的殺戮看作列強對中土的蹂躪,列強不僅是統治者,具有吃人的癖好,他們更是力本論的信徒,經歷了社會進化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扭曲,他們比東方信仰儒家和平主義的滿人更加嗜血成性。如海德格爾等西哲的反思,現代歐洲人在現代性的歧路上過早地先行冒險,他們才是現代文明世界真正的“們焦人”。這讓人不禁想起梁啟超、吳趼人的質問,“今日世界上哪有什么文明野蠻,不過是有強權的便算文明罷了。你看英國待波亞,美國待菲律賓,算得個文明舉動么?”(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63-64)。深受梁啟超影響的吳趼人也在《新石頭記》第二十八回說,“看著人家國度的弱點,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入政權,還說是保護他呢[……]照這樣說來,強盜是人類中最文明的了”(220)。當華胥帝在《人肉樓》文末發出“豈有野蠻烹文明者乎?”的質問,《新石頭記》“東方文明”發出紅棕黑黃諸種族“何一種非天所賦”,更是像對人類文明史反詰。張全之認為,“新小說”指出了一種理想的存在,映照出了現實的黑暗及一切人類文明史的罪惡。但在歸結原因時,他認為,如果沒有無政府主義的介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設想作者能夠獲得這樣一種批判眼光和具有現代色彩的視域(17-18)。此論斷恰如其分地解釋了問題的一面。康門對西方文明的輸入功莫大焉,但康門同樣有著對西方文明反思的傳統。康門作為最為重要的文化保守主義陣營之一,儒家天下大同的烏托邦與文明中心論的意象刻印在思想的深處。這是比無政府思潮更為重要的康門破壞美學的思想來源。特別在康有為、梁啟超游歷歐美之后,以東方“文明論”度量西方文明的沖動更為強烈。瓊樓玉宇、神仙才賢的文明,其實放僻邪侈、詐盜遍野,康有為感嘆百聞不如一見。而梁啟超先后寫作《新大陸游記》和《歐游心影錄》,在目睹科學的墮落和戰爭的殘酷,他更加強化了《新中國未來記》中對西方文明殘酷性的質疑,轉而認同“爭民施奪,末日將至,西洋文明破產矣”,而未來的道路在于“輸入中國文明以相救拔爾”(錢基博312,357)。耿傳明認為,從《人肉樓》中可以看到,清末“新文明派”已開始超出民族、國家的立場,而以“文明世界”的“普世公理”來批判現實、評判歷史(144)。
儒家文明傾向于以天下大同的普世立場看待世界,“民族國家”本來便是晚清時代的舶來品。與其說《人肉樓》中的“新文明派”是一種進化,不如說是對儒家文明的回歸。事實上,韓文舉的破壞美學更為接近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歷史觀,即以唐虞三想批判秦以后墮落的惡時代,只是儒家的理想國被表述為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華胥國。錢穆如此定義所謂的“三代”:“三代”是天理流行,一片光明潔凈,而歷史的現實過程,所謂三代以后,即使是漢唐盛世,也多半是人欲泛濫,一片黑暗(《朱子新學案》1:415-18)。《列子》所記黃帝華胥夢中的“自然國”,也即《人肉樓》中的“自然極樂國”。考慮到《列子》系偽書幾成定論,華胥夢想象應該被認為是先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后世佛家世界雜糅的烏托邦。黃帝神游于道家自然之境,在夢境中見到了真理,這一自然之國、自由之國、生命之國的真理,并不存在于一種封閉性的空想之中,而是有待實現的人間藍圖。黃帝返回人間,象征著大人、圣人與天地合德,將烏托邦的夢想轉化為改變現實的行動和生命的力量。大人的人格操守皆從儒家,神游華胥之國,從佛家哲學圓融廣大領悟中,透出對蒼生宇宙的無限同情。如余英時所言,中國知識人自始便以超世間的精神來過問世間的事。他們要用“道”來“改變世界”(4:11)。晚清諸多小說文本中,“華胥國”敘事與西方的“文明”甚至看不出有必然的關聯,反倒見出中國儒家救世美學的真精神。
進而言之,在終極的倫理道德的領域,康門諸人與晚明學人同樣都“志于道”。盡管康門弟子之間,特別是激進的十三太保與康有為在破壞主義上的分歧非常明顯,但在“道”的層面,都傾向于以儒家道德美學立場對破壞美學展開重構與反思。在談及與老師康有為的分歧時,梁啟超曾經做出一個總結性的反省。他說啟超之在思想界破壞力的確不小,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的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他借用佛家的說法“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反思自己誤人子弟,“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清代學術概論》106)。如果我們將這一反思之語置于晚清人禽之辨、夷夏之辨的歷史語境下,可見康門諸人對儒家所謂本質意義上的“性本善”依然保有虔誠的信仰。由此可見,新儒學中的仁、善、文明、天下一家的觀念才是《新中國未來記》《人肉樓》《東歐女豪杰》《新石頭記》等“新小說”批判性的主要源泉所在。至于陳獨秀認為無政府主義也是“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2:252),章太炎堅持無政府主義者“堅信性善之說”(4:435),這是一種對無政府主義東方式的轉譯。因為20世紀最初幾年,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諸多激進革命思潮輸入之時,往往淪為虛無黨暗殺主義、恐怖主義,并不能構成一個系統性的批判理論體系。晚清文人對人類文明史與現代性全面反思的沖動,各路革命思潮有促發之功,但“新小說”破壞美學的深處卻帶有明顯的儒家救世美學的內在理路。
綜上可見,如果簡單套用無政府主義革命理論來分析相關作品,難免會忽視這一時期無政府主義理論本身以及對于文學影響的復雜性和歧義性。“新小說”宣揚破壞美學主要是出于表達排滿與民族主義的訴求,無政府思潮只是其借力的激進思潮之一。并且,康有為及其弟子作為深受儒家救世傳統及和平主義文化影響的學術團體,對破壞美學的轉譯表現出相當深刻的反思精神。這場由梁啟超等人挑起的影響深遠的小說界的“大革命”,也因此帶有深刻的、烙印在精神深處的“舊制度”的痕跡。康門基于儒家思想對西方破壞美學的轉譯和改寫,同樣提供了觀察“現代性與大屠殺”一個超越性的視角。結語綜上所述,文學史論者不能簡單怪罪晚清作家以及“新小說”無力突破“中體西用”的思維格局,或者指責舊價值對于一個“覺世”的“新人”來說是致命的局限。晚清作家急切地以外來政治詞匯和藝術技巧更新傳承,腳力或許有些差跌,但最影響深遠的變化已經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現。在19世紀末西方“現代話語”霸權入侵之際,近代文人的文學演繹圍繞“舊制度/大革命(舊道德/新政制)”這一中心論域,層層擴大為對“文明/野蠻”、“自由/道德”、“科技/文明”、“專制/自由”、“東方/西方”、“宗教/俗世”、“進化/循環”、“天演論/再造天”等等一系列現代性核心悖論的探討。盡管囿于上述“體用”與“道德”的原因,他們曾經被五四新傳統歸入腐朽的舊傳統之內,但是這一“被壓抑的現代性”也因此隱藏了“一個文學傳統內生生不息的創造力”(王德威10)。“文學傳統內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未嘗不是西風東漸以來新儒家深層的憂患意識的反映,所謂的創造力正是這一憂患意識所激發出的超越意識。楊聯芬將其概括為“陌生而超越”(楊聯芬72),究其來源,這正是“新小說”“內在而超越”精神的體現。以政治小說、科學小說等域外小說的引入為發端,晚清文人借助陌生世界的民主科學激發“外在超越”,進而展開對于革命和西方文明最初的反思,最終企圖借道德理想主義與內心的良知喚醒“內在超越”。這一革命與超越的路徑,不僅表現為中國近現代政治文學主動地感召,也很大程度上沉淀為20世紀文學和政治展開的現實路徑。
作者:朱軍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
- 上一篇:“詩史”指向與晚近詩壇的李商隱接受范文
- 下一篇:低碳導向的城市規劃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