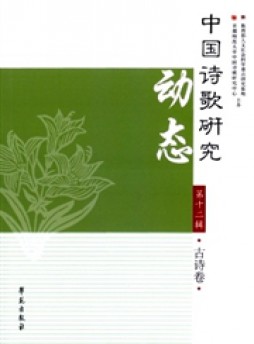詩歌的知識社會學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詩歌的知識社會學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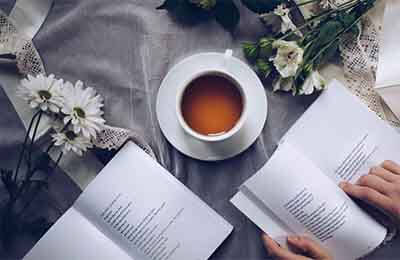
一、作為反知識的詩性知識
在以往的研究中,詩性知識并沒有被提及,所以我們先從以往對知識的評價中來獲得我們對知識的見解,以再次旁證詩性知識的特殊性。或者這樣解釋,詩歌自然是一種知識,我們可以從學者們無所不包的知識的討論中來獲得對詩性知識的辯證認識。社會學大體上探討了知識的四種視角:(1)詞語(;2)語言(;3)認知方式(;4)意識與思維。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方面來討論詩性知識。社會思想家福柯主張從詞語的角度來觀察語言的流變來管窺社會現(xiàn)實的變異,他甚至創(chuàng)立了“知識考古”一詞專門指代他的話語實踐研究。福柯認為知識是世界觀的反映,他從詞語與物的關系中闡述了他的知識型理論。知識型理論中他區(qū)分了四種知識型,分別是文藝復興時期詞與物統(tǒng)一的知識型、17到18世紀的用詞的秩序表現(xiàn)物的知識型、19世紀的用詞的秩序再現(xiàn)人對物的秩序知識型和現(xiàn)代的詞與物的分離的知識型。[7]256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視野讓我們看到了詞語系統(tǒng)走向獨立的歷史。無獨有偶,法國社會學家在“模擬社會”的論述中同時指出,符號系統(tǒng)的獨立使得社會被擬象物控制,這難免有些悲觀。不過我們需要承認詞語已經(jīng)走向某種獨立,或者脫離事實、脫離客觀,但是它仍然來自于現(xiàn)實。就像鬼神之說,仍然在人類的掌控之中。詩歌以詞語的形式表現(xiàn),詞語開始獨立為一個系統(tǒng),它仍然是詩人的創(chuàng)造物,或者某種意義上是出版的創(chuàng)造物而已。以詞語表現(xiàn)的詩性知識只是一種呈現(xiàn),而這種特殊的呈現(xiàn)或許驚世駭俗,這恰是詩歌作為自由表達的體現(xiàn)。當代的詩歌詞語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挑戰(zhàn)詞語秩序的傾向,詩歌內(nèi)容里大談、死亡、存在的邏輯等等,而這都是人們在生活中極力想要避免的話題。詞語同時作為一種語言,它與社會現(xiàn)實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語言社會學就是以此為出發(fā)點來探討語言的知識是如何反應社會現(xiàn)實的。語言社會學從不同社會群體使用不同語言的角度來開展的社會學研究,而詩性知識之間體現(xiàn)的語言的差異,即使有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甚至成長歷程都會影響到詩人的詩歌寫作,但是這些差異往往是無規(guī)律地隨意的,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就是一種隨意的創(chuàng)作,而且來自于外部的借鑒對詩歌語言的獲取也有重要的影響。雖然沒有確證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證明詩歌語言的自由性,但是我們?nèi)匀幌嘈牛驗槿绻姼枵Z言是一個公式或者規(guī)律的話,那么詩歌創(chuàng)作早就走向了死亡。知識被看作是脫離于身體的話,自然就需要主動去獲取,這就是認知。現(xiàn)象學社會學等派別傾向把世界認為是一個分類系統(tǒng),這個分類系統(tǒng)使得知識獲得意義,那樣也可以說這個分類的系統(tǒng)就是知識,需要去內(nèi)化這個分類系統(tǒng)形成現(xiàn)實世界的真實感。可以說詩歌區(qū)別與小說、散文等其他文學形式,也是某種分類系統(tǒng)的內(nèi)容。這里借用哈貝馬斯關于共同知識的論述,詩人自然有一種自然知識,這來自于詩人對自己和對詩歌的界定和感受,當然也會存在相異的知識。這里的討論主要是知識是人的產(chǎn)物還是獨立于人存在的,而我認為是前者,因為幾乎所有的知識都體現(xiàn)為一種事后解釋,事后解釋源自于我們時間的一維性,這里就必須要提出,事后解釋的缺點——不確定性和多種解釋。而詩歌則是一種創(chuàng)作中的知識,恰和亞里士多德的解釋相符。詩性知識是一種正在被創(chuàng)造的知識,而不是在事物發(fā)生之后做出的解釋。當然基于人思維的穩(wěn)定性,知識的穩(wěn)定性與其同期的穩(wěn)定性被一部分人質(zhì)疑是否存在關聯(lián),而我以為這種關聯(lián)更像是一種虛假關系。卡爾•曼海姆承繼馬克思的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開展他的批判,他指出思想認識的發(fā)展并不遵循自身的邏輯規(guī)律。在詩歌方面這一點能夠得到更好的體現(xiàn)。很多時候詩人恰是正不斷嘗試著突破被別人稱之為思維慣性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的文字和思想來往于一個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國度,甚至沒有國家民族的界限。這是對現(xiàn)存分類系統(tǒng)的某種挑戰(zhàn)。但是這種挑戰(zhàn)又是遵循詩歌的原則和邏輯的,詩歌總是有一種模糊的創(chuàng)作邏輯,詩人總是不滿足于現(xiàn)實邏輯,因為那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完美的只存在詩歌的意向和詩人的腦子里。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反思,我們可以得到詩性知識的幾個特點:(1)詩性知識是一個詞語的自成系統(tǒng),它是詩人個人的創(chuàng)造物,是某種模糊的詩歌邏輯指導下的產(chǎn)品(;2)詩性知識是一種自由的象征,它們是用來表達情緒和體悟,這種表達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3)詩性知識的獲得不僅僅是詞語本身的意思,而是以詩歌為形式所體現(xiàn)出來的某種特殊語言體系,這種語言體系中包含一種內(nèi)在的價值(;4)詩性知識是一種正在創(chuàng)造的知識,而區(qū)別于一般的事后解釋,從而避免了事后解釋的人的價值型的扭曲(;5)正是因為與事后解釋的價值改造的其他知識的區(qū)別,使得詩性知識存在某種意義上的反知識,這種“反知識”是反對那些違背詩歌模糊邏輯的現(xiàn)實,詩歌在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流變中獲得了這種“反知識”的自我認同(;6)詩性知識是現(xiàn)實秩序的一種有益補充,這種“反知識”存在著某種正功能,即充實知識類型,豐富視野和傳遞思想等功能。
二、社會學視野下的詩性知識
1.詩性知識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雖然說詩性知識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但是仍然存在于人類社會,自然會受到社會的塑造,這些則可以從社會環(huán)境來討論。事實上,新詩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至少在中國是如此。所以為了區(qū)別于古體詩,取名為現(xiàn)代詩。這種現(xiàn)代性卻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中發(fā)生著悄無聲息的變化。美國社會學家貝爾較早地觀察到了一種區(qū)別與工業(yè)社會的現(xiàn)代性的新的類型,他稱之為后工業(yè)社會的現(xiàn)代性。他關于后工業(yè)社會的五個預測中已經(jīng)被證實或者正在被證實,除了一點——他所認為的社會的中軸:理論知識。他認為在后現(xiàn)代社會理論知識會處于中性地位,成為社會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這一論斷難免有些理想主義,畢竟社會還在人類的手里,但是他也開啟了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的先河。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關于第二現(xiàn)代性的研究對理解知識有一個較好的借鑒作用。他把區(qū)別于工業(yè)社會的現(xiàn)代性命名為自反現(xiàn)代性,意指一種自己反對自己的現(xiàn)代性。[7]284而中國的新詩也開始呈現(xiàn)出這一特點,傳統(tǒng)的知識秩序在造反。伊哈布•哈桑就在《走向后現(xiàn)代文學》中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做出了闡述,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強烈對比,我們不得不醒悟,原來文學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變化:從象征主義走向了怪誕,從形式的走向反形式的,從等級制的走向混亂的,從創(chuàng)造走向了結(jié)構等等。[8]174后現(xiàn)代主義似乎已經(jīng)打亂了我們對秩序井然的文學作品的印象,而中國詩壇梨花體、羊羔體、下半身等也無一不是一種嘗試。所幸的是,任何文學的嘗試都沒有對錯。
2.詩性知識的意義轉(zhuǎn)向和現(xiàn)實境遇古體詩所要求的平仄和對仗,在自由主義浪潮中被拋棄。如此詩性知識失去了自我確認的一個標尺。那么詩性知識是如何形成本身的個性,以保持對別的知識的界限的呢?而回答在于意義的深度挖掘。除了對詞語的廣泛引入,其意義外延也得到很好的拓展。中國新詩寫作越發(fā)傾向于一種實驗——破壞性實驗。破壞性實驗是常人方法學派創(chuàng)始人加芬克爾創(chuàng)立的一項獨具特色的研究方式,它的意涵在于通過打破生活秩序來觀察社會現(xiàn)實如何得以建構的。也正如魯迅曾經(jīng)提到的那樣,一流的文學作品在于毀滅美,從而獲得對美的認知,而這就是詩性知識對其意義的建構。一首詩總會有一些破壞秩序的句子,而那些破壞秩序的句子所呈現(xiàn)出來的秩序就是寫作的意義所在。古體詩和早期的朦朧詩中的詞語一定是人或者物,而現(xiàn)代詩中的詞語開始涵括一些社會事實。社會事實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克姆提出的用以指代那些外在于人的社會之物,例如制度、現(xiàn)象和結(jié)構。現(xiàn)代詩為表現(xiàn)的詩性知識則是一盤散沙式的表現(xiàn),任何只要能夠想到的、寫出來的詞匯都可以用來放進詩里,而且加諸一種社會意涵,使之成為新的意義的代名詞。按照馬克思對社會實踐的定義,詩性知識的生產(chǎn)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參與社會實踐的個體應當獲得相應的生產(chǎn)資料。但是,以破壞秩序為特色的詩性知識被稱為非主流,這種破壞在很多時候并不能夠被接受。這就使得詩性知識生產(chǎn)雖然成為了產(chǎn)業(yè),卻少有收入。詩性知識的生產(chǎn)者難以從生產(chǎn)中獲得與其付出對等的回報,詩人不再與詩性知識親近,而轉(zhuǎn)而生產(chǎn)一種近乎諂媚的偽詩性知識,這里的“偽”體現(xiàn)在情感的職業(yè)化上。一個詩人在觀潮時贊美大海,這是真實的感情,而他贊美一個觀潮景點的時候就顯得他感情失去了標的。資本的社會運作使得詩性知識的生產(chǎn)也不再那么純粹,政治資本、經(jīng)濟資本、社會資本所把控的詩歌出版使得詩性知識產(chǎn)出質(zhì)量降低。
三、詩性知識的走向
詩性知識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而現(xiàn)代性一直在變化。荷蘭學者賀麥曉就曾就中國早期新詩的現(xiàn)代性進行了研究,他指出了早期新詩在形式、內(nèi)容和和語言方面的變化的現(xiàn)代性表征。這是新詩從古體詩中走出的第一次裂變。林鐵在其對90年代現(xiàn)代詩的研究中指出,1990年代詩歌的轉(zhuǎn)向?qū)嶋H上就是詩歌內(nèi)部的自我反思。[9]從新詩出現(xiàn)到90年代,雖然社會變遷迅速,但事實上,詩歌仍然在追求自我解放,仍然是在形式、內(nèi)容和語言方面的革新。而新世紀以來,詩歌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現(xiàn)象,即所指詩性知識,其中既有自由和異化的世界,又有雜亂的詞語秩序。結(jié)合當代中國新詩寫作和發(fā)展不難看出,詩性知識正在形成并逐漸改變中國新詩寫作。如果說要給中國詩歌的發(fā)展定下一個脈絡,就不難得出格律詩、第一現(xiàn)代性下的新詩萌芽、第二現(xiàn)代性下的詩性知識三個發(fā)展形態(tài)。而當代詩性知識的走向則體現(xiàn)在以下幾點:第一、個體化。正如貝克指出的那樣,第二現(xiàn)代性作為一種自反現(xiàn)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個體化,這種個體化既非個人主義,也不是個性化,而是表現(xiàn)為個人生活的承諾和關系網(wǎng)的強迫性。詩性知識的個體化則是表明共同標準與個人標準的共存。詩的共同標準若稱為“詩理”的話,那么個人標準則是對“詩理”的個性化,個性化是這一整個時代的個性化,即后現(xiàn)代的任一表征都可能在這里體現(xiàn)出來。第二、脆弱性。詩性知識對傳統(tǒng)詞語秩序的破壞和重構讓讀者難以接受,這就使得詩性知識只能在少數(shù)“懂行”的人中間。一方面,面向市場的出版業(yè)無法承受傳播詩性知識的虧損,這又使得私人出版物開始流行。民間刊物、內(nèi)部刊物開始成為詩性知識的陣地。繼而詩性知識的生產(chǎn)者開始形成圈子,但是自身又投入到與詩性知識生產(chǎn)無關的行業(yè)中去,使得當代新詩的傳播變得相當脆弱。另一方面,資本開始運作到詩性知識的產(chǎn)出和傳播過程中來,經(jīng)濟資本和政治資本開始進入詩性知識產(chǎn)出領域,而使得詩性知識功利化。[10]社會資本主要是運用于詩性知識的傳播過程中。人際關系網(wǎng)絡開始成為詩性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途徑。第三、裂變式發(fā)展。詩性知識的傳播開始與各種媒體相結(jié)合。博客、網(wǎng)刊、微信等信息傳播方式都被用來作為詩性知識傳播。每一種傳播途徑又會引發(fā)相應的內(nèi)容、形式和語言本身的裂變。這種裂變式的發(fā)展是迅速的,悄無聲息之中完成的。通過這種方式,詩性知識必將走向一種更極端,這種極端是將會作為對意義表達的新探索而在文學史上閃耀。
作者:朱慧劼單位: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農(nóng)村發(fā)展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