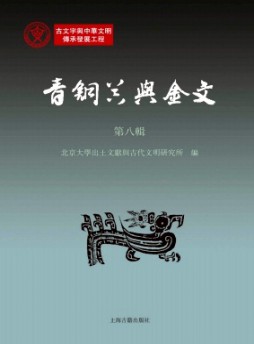青銅礦產資源與社會結構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青銅礦產資源與社會結構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華文化論壇雜志》2014年第七期
青銅時代西南夷各族的社會結構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各自保持了獨立發展狀態,每支民族都控制著一塊較為穩定的區域,并長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征。他們的分布態勢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其文化特征則可以通過考古材料(主要是青銅器)窺其全豹。每支民族都擁有明顯文化特征的青銅器群,這是西南夷文化呈現出豐富多彩面貌的時期,也是整個西南夷青銅文化的重要特點。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西南夷諸族文化與自然地理環境的關系。屬于“西南夷”地區的云貴高原、川西南和川西山地都是山脈縱橫的山區,但在叢山中分布有數量眾多的山間盆地和較為寬廣的河谷,還分布有不少高原湖泊及湖濱平原,形成了一個個自然地理單元,而這些地理單元因為適合人類生產和生活而被古人選擇為自己的家園。但是這些地理單元四周被高山環繞,客觀上也限制了各單元之間人群的相互交往。這種“叢山峻嶺中的‘綠洲’”式分布格局現象在大約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表現得十分明顯〔3〕。進入青銅時代后,西南夷諸族在分布區域上雖然比新石器時代文化有所擴大,但多民族聚居于西南夷一隅而又各據一方的格局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各民族各自控制著一塊基本穩定的區域,并持續保持著自己的文化特征,沒有出現由某一文化為主的文化整合現象,盡管相互間的文化影響一直存在。第二個原因是,由于西南夷地區青銅礦產在地理分布上的相對均衡性,使西南夷諸族分別控制著青銅礦產資源,再加上各族都掌握了相應的冶鑄技術,使西南夷諸族在整個青銅時代都保持了各自文化的獨立性,并擁有自己的活動區域。這一點,對于理解青銅時代西南夷分布格局的形成很重要。西南夷各族都控制有青銅礦產資源,使其在青銅原料上能夠自給自足。根據文獻記載、考古料和現已勘察到的礦產資源等三類資料,可大致判明西南夷各族所控制的青銅礦產資源的情況。
1、夜郎。目前大部分學者傾向于將夜郎的中心區域定在今天的黔西北、黔西南和滇東北的昭魯盆地一帶,這一區域銅礦資源豐富,見于歷史文獻的有《華陽國志•南中志》:“朱提郡,堂螂縣,出銀、鉛、白銅。”滇北區是云南銅礦最大的產區﹐包括東川﹑昭通兩地,其中又以巧家﹑大關﹑魯甸﹑永善等縣為盛。著名大廠湯丹﹑碌碌均在此區,產量曾占云南全省銅礦產量的70%,這幾個地方很可能是夜郎銅礦的主要來源地。大關、永善、鹽津、綏江還是產鉛之處。此外,貴州西北的威寧產銅,水城出鉛;赫章出銅、鉛,均有可能是夜郎青銅礦料的來源地。
2、勞浸、靡莫。《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其(夜郎)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傍東北有勞浸、靡莫之屬,皆同姓相扶。”說明夜郎之西和滇之東北是勞浸、靡莫族群的分布區。將夜郎與滇的地理位置作為參照系,再結合考古材料綜合分析,將勞浸、靡莫中心區域定在滇東的曲靖盆地一帶應該比較準確的。該區域內的曲靖、會澤、宣威、富源、尋甸都有銅礦分布,會澤、尋甸、宣威還發現了鉛礦。
3、滇。《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滇位于夜郎之西,勞浸、靡莫的西南,這只是記載了其大致的方位。根據滇文化墓葬的分布情況,可知滇的分布是以滇池湖濱平原為中心,北到金沙江南岸,南至通海,東抵路南,西迄安寧。《漢書•地理志》載益州郡有俞元縣,顏師古注“懷山出銅”,俞元即今之澄江,位于滇的分布區內。東川也屬于滇國的疆域,東川產銅量極大,其中湯丹鎮以產銅礦而聞名,有“天南銅都”之稱。滇人制造大量青銅器的銅料當主要來源于此。滇國境內有銅礦的地點還有澄江,該區域內的祿勸、易門和華寧出銅、鉛;嵩明、峨山、新平、武定出銅;晉寧出鉛。
4、句町。漢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漏臥、句町并屬牂牁郡。方國瑜先生考證句町地在盤龍江上游,童恩正先生認為廣西的西林也是句町地,劉琳先生認為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廣南、富寧,廣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縣亦當為句町轄境。又云南有濮水,方國瑜先生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一書中考證“此水(指濮水)自葉榆地區流至西隨,又至交趾入海,則為今之禮社江,下游稱紅河之水,即《漢志》之濮水”。濮水因沿岸多濮人而得名。根據沿濮水一線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點分析,沿濮水(禮社江、紅河)的元江、紅河、個舊一線,也是句町文化的影響區。《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梁水縣,(梁水郡)郡治。有振山,出銅。”劉琳考證,梁水縣即今之云南開遠。《華陽國志•南中志》又載:“賁古縣,山出銀、鉛、銅、(鐵)、[錫]。”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冊•兩漢時期》認為漢之賁古縣在今云南蒙自一帶。該區域內的個舊號稱“中國錫都”,是我國錫礦最為豐富的地方,個舊還出銅、鉛;元江、丘北出銅;紅河出銅、鉛;金平出銅、錫;文山出錫、鉛。
5、漏臥。《漢書•地理志》與《后漢書•郡國志》益州郡皆有漏臥縣,應劭注《漢書•地理志•漏臥縣》曰:“故漏臥侯國。”根據《漢書•西南夷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的記載,漏臥大致北與勞浸、靡莫相接,西與滇為鄰,南與句町相望,東與夜郎毗鄰。汪士鐸《漢志•釋地略》云“漏臥,師宗東南”。金兆豐《三國疆域志》云:“漏臥介于夜郎與句町之間。”方國瑜先生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中考證:“因其(漏臥)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結合考古材料推測,漏臥應在今云南曲靖市南部的師宗縣、羅平縣和紅河州北部的瀘西縣、彌勒縣一帶。該區域內的彌勒出錫,《華陽國志•南中志》載:“興古郡,律高縣,西有石空山,出錫;東南有町山,出(錫)、[銀]。”劉琳考證律高縣當在今彌勒縣南竹園鎮一帶。羅平出銅、鉛。
6、邛都。邛都又稱邛都夷,是西南夷中的大族。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邛都位于滇之北,這只是邛都的大致方位,其具體的分布范圍可以根據文獻和考古材料劃得更清楚一些。位于川西南安寧河中游的今西昌古稱邛都,其旁有邛海(古稱邛池澤),越西古稱闌縣,《華陽國志•蜀志》曰“闌,故邛人邑”,邛都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大石墓則主要分布在安寧河流域,故安寧河流域應該是邛都的分布中心區域。《漢書•地理志》“邛都”下顏師古注:“南山出銅。”西昌市南的黃聯關東坪就發現了一處面積達18萬平方米的漢代冶銅鑄幣遺址〔4〕。該區域還分布有錫、鉛礦。如西昌市東南部的安哈鎮就有鉛礦分布,安寧河河谷的銅礦產地還有西昌太和釩鈦磁鐵礦中的伴生銅、德昌興隆菱鐵礦(銅)。冕寧產銅、錫、鉛;越西出銅、鉛;其北鄰的甘洛出銅、鉛。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在德昌、喜德亦發現有錫礦的礦化點。唯一一處沒有在安寧河谷的大石墓分布地區普格也出銅、鉛。根據測試,在西昌發現的青銅器多為鉛青銅,如出土于西昌黃聯關石嘉鄉的漢代銅錠經光譜分析,含鉛量大于百分之十。
7、笮都。笮都又稱笮都夷,是與邛都相鄰的西南夷又一支大族。《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笮都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但因其在戰國至西漢期間發生過從北向南的大規模遷徙,所以其分布區域比較復雜。根據漢晉時期的文獻,笮都的活動區域有汶山郡、沈犁郡、越巂郡,根據考古發現,笮都的最后落足地應在金沙江和雅礱江兩江交匯的一片三角形的地帶,鹽源盆地是中心分布區,滇西北的寧蒗、華坪、永勝和麗江也是笮都的分布區。該區域內有鹽源平川代石溝銅礦,永勝縣大安鄉寶坪銅廠,寧蒗縣境內也有豐富的銅、鉛等金屬礦,鹽源的棉埡、梅雨、大地等地也有鉛鋅礦分布。麗江、華坪、永勝都出銅。玉龍出銅、鉛。
8、嶲、昆明。《史記•西南夷列傳》是將嶲與昆明并列起來敘述的,這兩族分布的區域很廣,《西南夷列傳》說:“其外(指滇與邛都),西自同師以東,北自楪榆,名為巂、昆明,皆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此處所指為西漢時期昆明的分布情況。楪榆的地望比較清楚,《漢書•地理志》云:“楪榆,楪榆澤在東。”《后漢書•郡國志•楪榆縣》注引《地道志》亦云:“有澤在縣東。”《水經•楪榆河注》又曰:“楪榆之東,有楪榆澤,楪榆水所鐘,而為此川藪也。”楪榆澤即今洱海,在今大理縣之東。同師(又作桐師)則應位于楪榆與巂唐(即今大理與保山)之間。結合考古材料分析嶲、昆明分布在以洱海為中心的滇西地區,北至劍川、鶴慶一線,東抵大姚、楚雄一線,西到云龍,南達南澗一帶。該區域面積廣大,有銅、錫、鉛分布的地方很多。其中祥云、漾濞、姚安出銅,彌渡、南澗、云龍、洱源、云縣、楚雄、雙柏、大姚出銅、鉛,鳳慶出銅、錫、鉛,永平出銅、錫,劍川、賓川、鶴慶出鉛。
9、滇越。滇越在巂、昆明以西千余里。方國瑜先生考證,滇越在今騰沖。尤中先生也認為滇越在今騰沖至德宏一帶。該區域內的昌寧和梁河出銅、錫、鉛,龍陵出錫,施甸出鉛。
10、徙。《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徙的分布方位是“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徙與笮都相鄰。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沈犁郡,所轄之縣可考者有青衣、嚴道、徙、牦牛四縣,徙為其中之一,《集解》云:“(徙)故城在今天全州東。”據任乃強先生考證,徙縣故址在今四川天全縣東30里之始陽鎮,故今四川天全一帶,應是徙人的分布區。結合考古資料分析,與天全相鄰的四川寶興一帶及屬于大渡河中游流域的石棉、漢源兩縣也應是徙人的分布區。漢源產銅、鉛,曾在大田鄉新中村寨子園發現漢代冶銅遺址,面積約6300平方米,文化層內發現有大量銅礦渣〔5〕;蘆山產銅,寶興產銅、鉛;而與漢源相隔大相嶺的滎經自古就是一個銅礦的富礦區。西南夷諸族中唯冉、駹較為特殊。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冉、駹在笮之東北。一般認為即今岷江上游地區。岷江上游地區不產銅、錫,僅理縣分布有鉛礦,故岷江上游戰國至西漢時期的墓葬(主要是石棺墓)出土的銅器小而少,唯牟托一號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但若仔細觀察,皆為蜀器,這一現象可能說明冉、駹的青銅器來源于蜀,冉、駹在地理上與蜀最近,關系也最密切,因此其青銅器來源于蜀是完全可能的。
三西南夷諸族不但各自控制著青銅礦產資源,而且都掌握了青銅器的冶煉和鑄造技術,這對于他們保持各自相對獨立發展和文化風格至關重要。在西南夷地區發現了不少鑄造青銅器的石范或陶范,這些范并非為某一支民族所獨有,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西南夷地區發現范的地點有:貴州省普安縣的銅鼓山遺址的石質的戈、斧、鑿、劍莖范〔6〕;四川省會理縣瓦石田的石質戈、矛、鏃范〔7〕;云南省的曲靖市八塔臺的石質彈丸范和簪范〔8〕;陸良縣薛官堡的陶鉞范〔9〕;嵩明縣鳳凰窩的石質鋤范和斧范〔10〕;彌渡縣合家山的石質戈、矛、劍、甲、鋤、鑿、斧、鈴范和陶器物范〔11〕;劍川縣海門口的石質鉞范〔12〕;鰲鳳山的石質斧范〔13〕;鹽源老龍頭的陶鉞范〔14〕。這些地點出土的范分別證明了夜郎、滇、勞浸、靡莫、昆明、笮等民族都擁有冶銅和鑄造銅器的技術。普安銅鼓山還發現了坩鍋。
西南夷諸族的青銅器都擁有獨具自身文化的風格特點,成為該民族的典型文化遺存。如:滇的貯貝器、一字格劍等,夜郎的鏤空云頭紋劍,邛都的發釵,笮都的杖及杖首、人馬紋枝形器、蛇蛙銅案,滇越的不對稱鉞、大彎刀,冉、駹的T字形劍等等。這些器物除了在本民族分布區內出現外,都不見于其它民族分布區,說明為該民族自己制造。西南夷諸族的青銅器還反映出各族所掌握的青銅鑄造工藝水平有高低。例如,滇青銅器的鑄造水平最高,制造的青銅器最為精美,而笮都的青銅器制造水平就明顯低于滇,青銅器上常發現在鑄造過程中因銅液流不到而出現的孔洞,冉、駹的青銅鑄造技術也低于滇。這種高低不一的技術水平,正是西南夷諸族獨立掌握了青銅冶煉鑄造技術的反映。以上說明,西南夷各個民族都控制有青銅礦資源,并掌握了冶銅鑄銅技術,加上自然地理環境形成的“藩籬”,不但使各民族的獨立性得以長期保存,而且也同時保存了西南夷青銅文化的多樣性。這種格局直到漢文化進入該地區后才被打破,從此西南夷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作者:劉弘胡婷婷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四川涼山州博物館助理館員
- 上一篇:朱仙鎮木版年畫的色彩研究范文
- 下一篇:饒雪漫圖書市場運作模式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