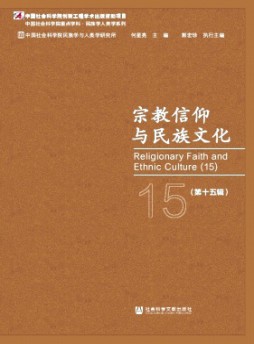民族文化意識及當代威爾士詩歌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文化意識及當代威爾士詩歌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威爾士詩歌在近年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兩位女詩人基蓮·克拉克和格溫妮絲·路易斯業已成為英國當代詩歌的重要代表人物,更有不少青年詩人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認可,但對威爾士民族文化推廣最為積極的是詩人羅伯特·明希尼克。明希尼克的詩歌創作,以務實的態度對待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建構,綜合業已成為威爾士民族精神的對北部山區意象的認同,和南部城市英格蘭化、全球化的現狀,力圖融合威爾士南北文化,構建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當代威爾士文化。
關鍵詞:
威爾士詩歌,民族性,文化
引言
威爾士20世紀最重要的兩位英語詩人之一,R.S.托瑪斯以威爾士為題材創作了大量的詩歌,為威爾士的英語詩歌創作確立了以威爾士北部山地風景為依托的精神家園。后輩詩人紛紛效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當代威爾士的“民族詩人”(NationalPoetofWales)基蓮·克拉克(GillianClarke)。克拉克通過一系列的長詩創作,為威爾士詩歌建構了“北部山地房屋”這一帶有強烈威爾士色彩的民族意象,從而成為當代最有影響的威爾士詩人之一。威爾士英語詩歌創作中對于北部威爾士風景的過度描寫受到不少評論家的詬病,詩人約翰·戴維斯曾寫詩加以嘲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個20世紀的威爾士英語詩歌創作中,對威爾士北部山地的描寫和抒情占據了主流,而對威爾士南部地區的文化則缺乏思考和呈現。20世紀威爾士英語詩歌的這種價值取向給不少向往威爾士民族復興,但同時也關切威爾士南部文化的詩人帶來了挑戰與困惑。作為克拉克的同時代人,羅伯特·明希尼克(RobertMinhinnick1952-)的詩歌創作正體現出威爾士詩人在平衡民族復興和地域文化之間的艱難選擇和復雜情感。
1.明希尼克與威爾士詩歌傳統
羅伯特·明希尼克出生于威爾士南部斯旺西附近的尼斯,先后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和卡迪夫的威爾士大學學習。1978年明希尼克出版詩集《迷宮中的線索》(AThreadintheMaze),之后陸續出版詩集《家園地》(NativeGround1979)、《無期徒刑》(LifeSentences1983)、《恐龍樂園》(TheDinosaurPark1985)、《劫掠者》(TheLooters1989)、《嗨,胖子》(HeyFatman1994)、《颶風之后》(AftertheHurricane2002)和《巴比倫的鑰匙》(TheKeysofBabylon2011)。明希尼克的詩歌作品多次獲得包括“前進詩歌獎”(ForwardPoetryPrize)在內的各類詩歌獎項,是當代威爾士詩壇上舉足輕重的代表詩人之一。在詩歌創作之外,明希尼克還從事小說創作,小說處女作《海冬青》(SeaHolly2007)曾入圍翁達杰獎(OndaatjePrize)的評選。他的散文創作也成果豐碩,散文集《觀看食火者》(WatchingtheFireEater1992)和《巴別塔往返》(ToBabelandBack2005)先后成為1993年和2006年的威爾士年度書籍,體現出他在威爾士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力。作為1997到2008年間《威爾士詩歌》(PoetryWales)雜志的主編,明希尼克更以自己對詩歌的熱忱推動了整個威爾士詩歌事業的發展,為威爾士培養出一批出色的中青年詩人。在明希尼克身上,充分體現了格林·瓊斯所說的,“盎格魯-威爾士作家惟一帶有英格蘭色彩的就是他們所用的語言”(Jones2001:196)。作為積極推動威爾士民族性的旗手之一,明希尼克像R.S.托馬斯、克拉克一樣充滿著對威爾士民族復興的期待,也同樣希望以自己的詩歌創作為當代威爾士民族建構精神家園。和前輩詩人一樣,他意識到詩歌在民族性建構過程中地位獨特,因為詩歌具有小說和戲劇所沒有的民族色彩,是可以“界定民族的靈魂的”(Mueller-Zettelmann2011:225)。明希尼克對于將威爾士生活的抒寫始終限定在工業化之前,以展現一種“生活在邊緣土地上的邊緣人”(Day2002:16)的威爾士民族文化不以為然。作為威爾士南部的本土詩人,明希尼克與R.S.托馬斯和克拉克不同的是,他力圖在詩歌中擺脫這種威爾士民族的刻板印象,為在現實生活中頗有影響的威爾士南部文化發聲,改變盎格魯-威爾士詩人那些千篇一律的書寫威爾士北部山地的創作。然而,對明希尼克來說,在威爾士山地書寫之外尋求威爾士民族精神的路途并不平坦。
2.《尋找亞瑟》:威爾士文化困境的歷史書寫
在詩歌《尋找亞瑟》中,明希尼克試圖擺脫R.S.托馬斯開創的北部山地風景傳統,而在更具歷史厚重感的不列顛傳說中探求威爾士民族精神的源頭。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前輩詩人都采用這一方法來挑戰帝國時期塑造的以英格蘭為圭臬的英國詩歌傳統,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以北方神話來重構當代愛爾蘭民族文化的希尼。明希尼克在拒絕R.S.托馬斯所引領的道路之后,希望仿效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成功路徑,以對歷史的書寫和思考來建構當代威爾士民族精神和文化,擺脫對北方山地的單一呈現,將人口眾多的威爾士南方和具有民族象征意義的北方融合起來,表征一種具有強烈威爾士特色又能為普羅大眾所接受的民族性。出于威爾士地理位置和歷史流變的考量,明希尼克選擇了亞瑟王這一在不列顛歷史中具有廣泛影響的威爾士傳奇人物。①亞瑟王的故事幾經流傳,成為中世紀的重要文本,之后又經浪漫主義詩人和現代作家的推廣,成為英國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不過,經過歷史洗禮的亞瑟王雖然成為英國的文化符號之一,卻甚少有人留意到他與威爾士的淵源。明希尼克希望通過對亞瑟王文化傳統的開掘,為當代威爾士的民族文化構建找到突破口。然而,由于威爾士的民族文化建設業已荒廢經年,詩人這種美好的愿望注定無法實現。在傳說中的亞瑟王谷地中,民間傳說里的神奇色彩無處尋覓,目光所及只有“一堆銹蝕的汽車”和“一汪漲溢在巖石間的/綠色氮水”(Minhinnick2012:79)。亞瑟王昔日的輝煌已經逝去無蹤,即使未曾改變的山峰也“戴著迷霧織就的圍巾”(ibid.:80)。雖然詩人以沉默來表達對民族歷史的敬意,但孩子們卻用一把把的石子“在莊嚴的冰湖上掀起了漣漪”(ibid.)。詩人意識到,“我們所探索的/不過是別人早已了然的”———對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尋求,由于缺乏歷史的積淀,是無法復制希尼在北愛爾蘭那樣的成功的。對亞瑟王的追尋最終沒能有所收獲,過去的一切只剩下“帝王的塵土”(ibid.),這就是當代威爾士民族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在威爾士的現實生活中,民族過去的歷史輝煌已經成為尋覓的遺跡,留給當代威爾士人的只有工業化的垃圾。雖然對亞瑟王歷史追尋的失敗,宣告了明希尼克未能突破托馬斯北部山地的傳統,沒能通過歷史回歸來為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建構奠定堅實基礎,但正如巴什拉指出的,“偉大的詩歌會對語言的靈魂產生巨大的影響”,將“喚醒已被磨滅的意象”(Bachelard1994:xxvii)。毫無疑問,明希尼克在這首詩歌中為威爾士民族喚醒了他們早已忘卻、被磨滅的民族英雄意象。然而,強大的英格蘭文化已經將威爾士的民族英雄亞瑟王貼上了鮮明的英格蘭標簽,遠不是山路上的“石子”可以改變的了。這不僅是明希尼克的困境所在,也幾乎是所有威爾士詩人無法解決的難題。正是因為英格蘭文化的強大以及在威爾士南部地區的巨大影響,托馬斯才不得不選擇了北部山地來作為突破性的意象和抗衡英格蘭文化侵襲的手段。
3.《家》和《劫掠者》:威爾士民族文化的雜糅性
在建構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努力中,明希尼克期望擺脫托馬斯引領的以北部山地描寫來凝聚民族精神的限制,力圖從威爾士的歷史傳說中探索當代威爾士民族性的建設,結果卻是“別人早已了然的”失敗。不過,詩人并沒有放棄在詩歌中對威爾士民族文化意象的追尋,不斷探索著其他的途徑來彰顯威爾士的民族性。在傳統的民族身份建構中,“家”一般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意象之一。克拉克的成功之處正在于她通過自己的長篇詩歌創作,為威爾士民族建構出北部山地的“房屋”這樣一個家園意象(參見何寧2013:56-58),并由此得到英國主流評論界的認可。明希尼克對這樣一種將位于威爾士邊緣的、北部山地的家園意象作為民族認同的思想頗為抗拒。正如在《尋找亞瑟》中所表現的,詩人并不拒絕歷史和北部山地,但他更加關注的是威爾士民族的當代生存狀態。明希尼克追求的是體現當代威爾士民族精神、與時展相契合、可以與強大的英格蘭文化并列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威爾士民族文化意象。在放棄對北部山地的家園意象的認同之后,詩人轉而探索在占威爾士人口多數的南部地區的家園意象,將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復雜性予以深刻的呈現。明希尼克在詩歌《家》(“TheHouse”)中,通過對自己位于南部威爾士住所的描寫,勾畫出構成當代威爾士民族身份的各種復雜因素,反思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與英格蘭文化之間的關系。詩人對家園的反思來源于一次在自己家中修理電器的經歷,在修理的過程中,他開始審視自己業已熟悉的房屋,并逐漸意識到自己與所住的房屋之間的關系并非他原本以為的那樣。家中的紅磚露臺所代表的歷史和蘊含的力量讓詩人踟躕,喻示著詩人不過是這房子里的過客,而房子才是真正的主人:“房子已經吞噬了我”。明希尼克在詩歌中暗示,這所位于威爾士南部現代化城市中的房子代表的是以英格蘭文化為主流的當代英國文化,并不是人們一直以為的威爾士傳統文化的傳承。雖然威爾士南部依然是威爾士的領地,但英格蘭文化的強勢已經使得這里的威爾士民族文化陷入了危機。正如詩人在詩歌中所寫到的:疆土不是買賣來的而是戰斗來的:它是第一本能,是我們生活中細小而平凡的戰事。(Minhinnick1999:35)明希尼克通過對個人居所的反思,喻指整個威爾士民族文化的現狀:在強勢的英格蘭文化的房屋中,威爾士民族已經幾乎喪失了對民族文化的掌控,完全為英帝國的文化所吞噬,成為英格蘭文化的過客和附庸。通過“戰斗”“戰事”等詞語的運用,詩人將兩種文化之間的較量和爭奪上升到頗為殘酷的層面,因為如果威爾士民族不再奮起建設自己的民族文化,那就將徹底失去民族文化的獨立,成為英格蘭文化這間屋子里的房客。盡管現狀堪憂,但對威爾士民族文化的未來,明希尼克并不悲觀:雖然他發出“房子已經吞噬了我”的吶喊,不過現實是黑暗與光明并存的,猶如詩歌中紅黑相間的電線,既有意味著死亡和歷史的黑色,也有代表著希望和未來的紅色。正如詩歌中主人公要修理好這電線,當代的威爾士人也需要解決好威爾士文化被英格蘭文化同化這一復雜的現實問題。英格蘭人在19世紀中后期開始大量移民威爾士地區,是英國工業化的結果,也意味著工業化文化對威爾士傳統農業文化的改造。在明希尼克看來,這一變化是不可逆的,也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當代的威爾士民族文化不可能脫離現實,重回工業化前的社會。要在當代英國構建威爾士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必須面對現實,在詩歌中對威爾士南部工業化城市的各個生活側面都加以描摹和思考,力求在占威爾士人口多數的南部城市中構建可以為當代威爾士人所用的現代威爾士民族文化,才能讓威爾士文化擺脫被英格蘭文化全然同化的命運。在批判英格蘭文化入侵,強調建立自己的家園的同時,明希尼克也對威爾士民族文化成為英格蘭文化附庸的原因予以反思,對威爾士民族性中的弱點加以批判。在詩歌《劫掠者》(“TheLooters”)中,明希尼克筆下的當代威爾士面對著惡劣的天氣所造成的外部困境,但更令人唏噓的是由此而來的對當地民眾人性的考驗。暴風雪造成了交通困難,司機們只好離開車輛,在學校里過夜。雖然如此,但他們依然微笑面對,孩子和寵物都照顧得安全溫暖。然而,室外的世界則是另一幅景象:丟棄在高速公路上貨柜卡車猶如移位的脊椎骨。嚴寒業已打斷我們商業的脊梁(Minhinnick2012:53)為冰雪和寒冷所困的人們不得已采取劫掠貨車的手段來繼續生活下去,而這些劫掠者從未被人看見,因為他們是“了解天氣的人”,在這風雪天里“制造了明天的新聞”。詩歌寫的雖然是暴風雪天氣下的一場小動亂,但隱喻和反思的卻是整個威爾士民族的現狀和未來。正如詩歌開頭所寫的:“智者有云,壞天氣,/讓一個群體更團結。”(ibid.)不過,令人沮喪的是,盡管詩中描寫了相互支持、遵守規矩的司機,但劫掠者的出現意味著威爾士民族這個群體的團結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些劫掠者似乎也情有可原,在風雪封門的農場中生活,應對天氣帶來的生活困境,從貨柜車里拿點肉似乎是他們不得不選擇的出路。明希尼克通過學校內安置的司機和劫掠者的對比,隱喻出威爾士南部城市與北部鄉村之間的距離和潛在的沖突:生活安定的南部威爾士人顯然愿意循規蹈矩,因此對威爾士民族文化的現狀并不在意,而在北部生活并不富足的鄉村威爾士人對英格蘭主導的威爾士秩序存在不滿,更希望通過改變現狀,復興威爾士民族文化來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每一個威爾士人在當下都需要認清自己的位置,并做出自己的決定,不能任由外界的力量打斷威爾士民族的脊梁。正如詩人在詩中所寫的:“今晚的電視屏幕就是鏡子/而新聞就是我們自己”(ibid.)。
4.《短波》:確立威爾士文化的環境與出路
通過對英格蘭文化侵襲的批判和對威爾士民族性弱點的反思,明希尼克指出了威爾士民族文化當下面臨的困境:在威爾士民族面前的文化傳統幾乎是一片荒原(Thurston2009:79)。由于威爾士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差距,在現實中將北部山區作為當代威爾士民族的精神基礎這一希冀帶有過于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難以凝聚南部的廣大威爾士人。因此,在詩歌《短波》(“ShortWave”)中,明希尼克面對當代世界紛紜變化的現實,提出了他心目中構建當代威爾士民族性的路徑。詩人以日常生活中收聽廣播的事件為切入點,通過短波中不同電臺和雜音來喻指威爾士民族在當今世界的各種不同選擇和可能性。威爾士自建立自己的議會以來,一直期望在歐洲群體中發出更強的聲音,不再作為英格蘭的附庸出現,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愿望顯得過于一廂情愿,并沒有得到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支持。不少歐洲大陸國家,如比利時和西班牙,都面臨國內的民族主義挑戰,因此對威爾士的想法并未予以支持。明希尼克在詩歌的開頭就將這一現狀通過敘述者選擇電臺的動作展示得非常清楚:我試圖調諧,但歐洲模糊的聲音隨著轉盤的撥動愈加陌生奇特。所有的電臺聽起來都像在播放演出的片斷,(Minhinnick2012:4)雖然“我”所代表的威爾士一心想投入歐洲的懷抱,但這種努力卻是讓歐洲與威爾士愈加漸行漸遠。在經歷一系列雜亂的調臺過程,聽過詩歌、弦樂等之后,詩人意識到:出于某種原因,各種語言的喧嘩和朦朧的音樂比任何既定的節目變得更為重要(ibid.)在明希尼克看來,按以往那種按部就班的模式來實現對傳統意義上的民族身份的追尋和實現在當下日新月異的世界中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幾乎“所有的電臺”播放的都是片斷。在全球化文化的風潮和英格蘭的強勢文化之下,威爾士文化必須一方面堅持對民族文化獨立性的探求和追尋,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接受多種文化的融合,擺脫威爾士語純粹主義的限制,通過英語來展示威爾士民族的聲音,讓威爾士文化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只有威爾士出現“各種語言的喧嘩”,才能讓歐洲和世界感受到威爾士文化的存在與價值。而詩歌中“朦朧的音樂”則暗指自20世紀以來作為威爾士民族精神象征的威爾士北部山區,雖然缺乏華麗的樂章和文化經典,但符合威爾士對民族傳統的認同,是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方面。
5.結語
羅伯特·明希尼克的詩歌創作,以批判和務實的態度對待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建構,綜合業已成為威爾士民族精神的對北部山區意象的認同,對南部城市英格蘭化、全球化現狀的思考,以及威爾士民族的歷史傳統,立足于威爾士的社會現實,著力反思并消弭威爾士南北之間在文化上的分歧,將充滿“喧嘩”的南部城市和具有“朦朧”色彩的北部山區兩相融合,以此作為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代表,在當代關于威爾士民族文化構建的討論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作為威爾士當代最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明希尼克的詩歌創作為威爾士雙語詩人格溫妮絲·路易斯(GwynethLewis)、以及具有全球化視野,融合英格蘭和歐洲元素的詩人奧利維爾·雷諾茲(OliverReynolds)和斯蒂芬·奈特(StephenKnight)成為當代威爾士英語詩歌的主流奠定了基礎,不愧是當代威爾士詩人中對民族身份最關注的詩人(Peach1996:382),對當代威爾士民族文化的發展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何寧.2013.論基蓮·克拉克和格溫妮絲·路易斯詩歌中的民族性書寫[J].外國文學評論(1):56-68.
作者:何寧 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 上一篇:民族學生就業中的民族文化影響范文
- 下一篇:秋頌中的生態女性主義構建研究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