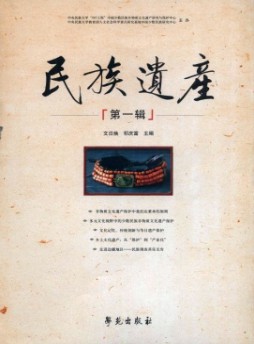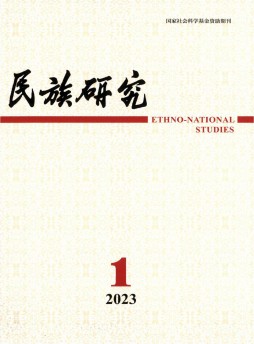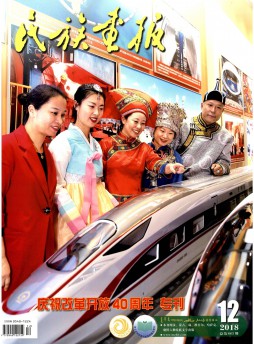民族法學的地方性知識研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民族法學的地方性知識研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作為對象的民族法學在邏輯中的現有存在觀照
民族法學既然是以民族法律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法律學科,那么,民族法學必然會隨著民族立法的開始而出現,隨著民族法律制度的實施而不斷成長進步,民族法學學科也必然會伴隨著民族法的正規教育而出現和逐步完善。對各個少數民族的習慣法文化進行整理,是對祖國大家庭各民族傳統和法律文化的保護。當下對民族法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對調整民族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研究;其次是對祖國大家庭中各個少數民族傳統法律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最后是對多民族聚居地區的法律實施狀況進行實證性研究。在當前的法學理論研究中,中國法學會、民族法學學會曾經對學者們提出,民族法學應以現行民族法律規范和民族法律制度為主要研究內容,重點關注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治理。通過對上述研究的梳理可以發現,現有的研究總體而言僅僅是對于民族法學存在狀況的描述,并沒有發現和指出支撐民族法學這一知識性存在集合體的內在觀照。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在其名著《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中指出,法律只是自發性地生長于一個民族的歷史之中,無論如何不能奢望通過規范理性的方式來創建,只是一個民族歷代民族精神的再現,因此,只有民族精神才是一個國家所有實在法規范的真正創造者。在他另一部法學名著《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他進一步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緊密相連,法律的特征和民族的特征密切相關。在人類社會的早期,法律就已有了自身獨特的屬性,和人類社會中的語言、風俗和建筑一樣,一定是具有自身的民族性特質。因此,在每一個共同體中,在每個人心中活動著的現實性民族精神才是產生實在法體系的堅實土壤和根基。薩維尼將“民族精神”視為法律的內在觀照,這種進路啟示意義重大,在對民族法學的研究與審視中,也必須探索發現其背后存在的內在觀照。
美國學者吉爾茲曾在其著作中向世人指出,從本質上來講,法律不過也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他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溝通法學與人類學之間關聯的方法論,因此,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理論就很難演變為本土資源論的理論論據,因為本土資源理論并非聚焦于方法論,而是聚焦于知識論。在地方性知識理論中與本土資源理論的相關論斷中,吉爾茲承認法律不過就是地方性知識,并且他同時還解釋了他所理解的地方性,指出地方性并非是指某一個具體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指一種特殊性,是一種能夠把對所發生事件的地方性經驗和對可能發生本土資源想象連接在一起的一種狀態。由此可知,地方性知識能夠作為民族法學的內在理論觀照。
從更深層次來看,“地方性知識”還并不僅僅是指一種特殊的地方性知識,更大程度上還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地方性也不能僅僅被簡單理解為某一個特殊的地區,在這種描述的場域中,更大程度上涉及到在知識的產生與發展中所面對的特殊存在環境,特別涵蓋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展現的文化人群之間的價值差異和觀念區別以及決定這種表面區別背后的由特定利益所決定的立場和態度。“地方性知識”向我們展示,由于知識總是在某一種特殊的條件下生成并得以向人們展現其存在的,因此,人們對知識的觀察和考量也不能僅僅局限于絕對理念下普遍的準則,更重要的是要著眼于知識的具體情境條件是如何形成的這個重要問題。一般情況下,即便是主張地方性知識的視角,也并不意味著對普遍性科學知識體系的徹底和完全否定。在地方性知識的觀念體系和知識結構中,知識究竟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內能夠發揮效能,主要靠人們的實踐活動來驗證,絕對不能僅僅根據某種所謂的先天原則來設定,這只會產生一種有害的偏見。
在以吉爾茲為代表的人類學學者看來,地方性知識的特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地方性知識必須要和所謂的普適性知識做相互觀照,知識的一端是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知識,而另外的重要一端則是這個星球上除西方價值體系之外的其他地區的地方知識。其次,地方性知識被隱喻為一種現代性視野之下的非現代性知識。最后,地方性知識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權力結構中,必然與一個地區的權力者和知識權威相關聯。地方性知識之所以會產生所謂的存在地域極限與自己存在地的兩種命運差別,是因為地方性知識在自己的存在范圍內自主地表現出了一種內在邏輯自洽性,其自身存在的系統中存在著內在沖突性的張力,這種張力使得這個系統中不同結構之間具有一種互相矛盾的關聯性。與此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四處生長的地方性知識,本身也具有一種內生性自我修復性生長的功能,這使得在其各個組成部門之間的緊張性張力沖突突破外生性擴展的結構要求。
在這個時候,這種所謂的構建關聯性力量的方法并不是要知識分子和觀察者機械地轉述一個特殊地區的文化內應張力,地方性知識的本質要求知識分子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和所謂的他者交流溝通。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地方性知識是對于一種特殊文化的近距離感知與遠焦距觀察,是兩種觀察視角的水乳交融,更是一個闡述體系與另外一種意義系統的內容交流。這種嶄新理念的進步和增量就在于其設法實現在觀察過程中的視角對立,進而發現不同本體之間的交流互動。對于地方性知識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只有探尋其中的多樣性,才能實現對人類學知識的最佳深化性理解。推演理性的抽象性和文化表象展示的直觀性,只在有關民族的研究中很難相互理解:在理論的存在體中,對地方性知識的內在把握與真實深化之間存在著尖銳性的沖突,在理論中越完備,矛盾性張力就越大,地方性知識的穩固性和普世的抽象性知識之實現就越困難。由此可以得知,民族法學從內在觀照的維度審視,就是一種“地方性知識”。
三、民族法學在理論邏輯中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意義
隨著中國之崛起,中國在理論話語權方面也日益主動,西方的各種理論,在中國的歷史與實踐面前,越來越不具備普適性的說服力,在法學領域也是如此。中國的多民族法律史源遠流長,從炎黃二帝到春秋戰國,是中國各民族融合與多民族國家統一的開端。以地處中原的華夏族為主體,加上融入俗稱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部落集合體,初步形成了一個大致的民族共同體,后來,隨著民族融合的深入,形成了秦漢時代的若干強大封建帝國。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祖國大家庭中的各個民族之間的法律智慧開始有了初步的交流。
從中華民族的文明歷程伊始,包括漢族在內的各個少數民族就一直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因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個民族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但作為中華文明之智慧成果的中華法系是祖國大家庭中的各個少數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包含著祖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法律智慧,是祖國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法律文化與法律實踐相互融合的結果和結晶。中華法系是以漢民族為主體、各個民族共同締造的,凝聚著包括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和漢族文化的法律智慧,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中華法系還吸納了不同少數民族優秀的法文化成果。盡管不同的民族法律文化對中華法系在形成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有所不同,但其歷史作用是不能否認的,要注意從多方面的維度來考察中華法系,這也是中華法系之所以博大精深的根本原因。中國民族法律史的嬗變,也證明了民族法學的“地方性知識”屬性。
從根本上說,地方性知識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價值為擔當,但其結果是在這種邏輯開始在西方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全球同質化、普世價值、同構社會思想和語言挑戰的現實。但同樣應該指出的是,為了強調本地知識,很容易使一個國家的中心轉移到以他者為中心的另一個極端。地方性知識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和經驗相交,但不完全相同。因此,相比其他更強烈的“后殖民”的時代特征,這種思想相較于其他的思想觀念具有更強烈的“后殖民”時代特點,其興起與流行同樣有著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歐美人類學界的文化研究、新實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對科學的政治批判等思潮相互交織在一起,其結果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發起了一波強大的沖擊,與此相聯系的副產品---對作為傳統科學觀念核心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也進行了批判。
作者:汪沛單位:湖北省行政學院經濟學與經濟管理學教研部
- 上一篇:法學教育中素質教育的實踐范文
- 下一篇:計算機技術與應用研究論文4篇范文
擴展閱讀
- 1民族旅游與民族文化論文
- 2民族品牌戰略
- 3傳播民族志
- 4民族品牌戰略
- 5藝術民族性
- 6民族企業官商關系
- 7民族地區旅游
- 8民族主義情結
- 9民族科技提升近況評估
- 10民族文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