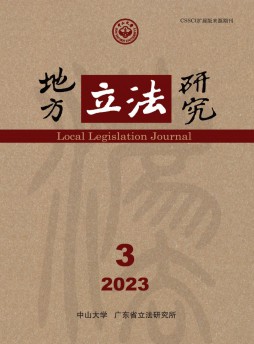立法表決前工作指導意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立法表決前工作指導意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對于多數民主,在立法工作中我們的理解基本限于法律案表決時的多數通過。但是,在不久前民辦教育促進法制定過程中出現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看待立法過程中,更準確地說是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從去年六月起連續四次審議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曾經因為對其中所謂“合理回報”問題的爭議而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在民辦教育促進法進入常委會三次審議中,對于草案三次審議稿中刪去了有關民辦學校舉辦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的規定,有的委員提出,要求法律規定民辦學校舉辦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是多數常委會委員的意見;多數常委會委員的意見,為什么聽不進去?是聽多數常委會委員的意見,還是聽行政部門的意見?委員的意見也許聽起來比較尖銳,但這些尖銳的意見表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暢所欲言的民主氣氛,更重要的是,它向我們提出了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是指什么范圍內的多數意見?立法活動是廣泛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過程。立法中的多數意見不僅僅是指表決時的多數意見,更重要的是指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而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不僅包括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發言時的多數意見,還應當包括常委會列席人員的多數意見,包括各個地方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多數意見,包括有關專家和學者的多數意見,包括立法中利益相關人的多數意見,以及普通公民和社會組織中的多數意見。所以,將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僅僅視為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多數意見,是不全面的。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多數意見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復雜眾多的意見單元中的一個方面,而并不代表立法活動中的多數意見。
第二,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意見與組成人員之外的意見有什么區別?立法過程既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過程,同時又應當是一個十分開放的過程。說立法過程的相對封閉,是指立法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活動,必須由法定的組成人員依照法定的程序進行;在這個程序中,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對法律案的意見具有重要作用,他們可以通過會議形式獨立完成一項法律案的審議和表決工作。而立法過程的開放性是指立法必須面向社會、面向地方、面向部門、面向公眾,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才能保證立法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保證立法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所以,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意見與立法機關組成人員之外的意見實際主要是會內會外意見的區別,前者更多地通過會議表現出來,后者更多地通過會場外的途徑表現出來,兩者在立法活動中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第三,立法機關組成人員是否具有意見特權?在表決之前的立法活動中,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意見和地方、部門以及普通公眾的意見,應當沒有優劣高低之分,只要是正確的意見,不管來自哪個方面,立法機關都應當認真聽取和吸收。那種認為立法機關組成人員享有意見特權,他們的意見高于其他方面意見,可以凌駕于其他方面意見之上的想法是失之偏頗的。作為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他們本身就來自于社會、來自于群眾,他們的意見本身就應當代表民意;由于了解民意的有限性,在具體的立法活動中,立法機關組成人員就更應當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和十分重視來自地方、部門、社會和群眾的意見。而實際上,在法律法規案征求意見的過程中,一個地方、一個部門反饋過來的意見本身就是經過多次座談會和調查研究而總結出的認識,這些認識常常更貼近實際,更能反映民意,反映事物的規律。所以不能說一個或者多個委員的意見就比一個地方或者一個部門的意見重要,關鍵要看意見的正確程度。只要意見正確,即使是普通公民的個人意見,立法機關也應當積極采納。當然,必須承認,立法機關的組成人員是有特權的,但這個特權僅限于其依法在參與表決中貫徹自己意見的特權,而不是表決前的特權。
在提出了上述三個問題后,就可以進一步討論立法表決前的多數意見。在筆者看來,在立法表決前即立法的審議和征求意見過程中,既存在一個多數意見,實際上又不存在什么多數意見。說存在一個多數意見,是指有不少人、不少單位或者說有一些人、一些單位對法律法規的某一條款、某一問題發表了意見。說不存在什么多數意見,是因為我們所說的不少人或者不少單位、一些人或者一些單位,在發言人數的總數和征求意見的總數中沒有超過半數或者幾乎不可能超過半數。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實踐中,通常所據以修改法律草案的意見,無論來自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意見,還是來自各地和有關部門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根本不是也幾乎不可能是多數意見,最多只能說是不少人的意見或者一些人、少數單位或者一些單位的意見。因為在常委會審議法律案或者各方面對法律案提出意見的過程中,存在這樣的情況:對法律案的某些或者某一條款,直接發表意見的常常只是有權發表意見人員或者單位中的極少數。就拿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說,在150多名常委會組成人員中,只要有10人以上對某一問題發表同樣的意見,即使其他140多名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該問題都保持沉默,這樣的意見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了,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其他工作機構就必須對這一意見進行慎重研究,考慮是否吸收。而這10多名組成人員的意見在常委會全體組成人員中實際只是極少的一部分,他們的意見無論如何是不能算多數意見的。再比如,一件法律案發往30多個省級地方和40多個省會市、較大市以及幾十個中央部門征求意見時,這些征求意見的地方和部門數量都是具體確定的,而對法律案中某一問題或者條款同時發表相同意見的地方和部門也極少能夠超過征求意見的地方和部門總數的半數以上。但即使是60個地方中有10個地方、40個部門中有10個部門對某一問題持相同的意見,這一意見也就必須引起重視了。而這些意見從數量上只能說是少數意見。
這里提出的問題是,立法過程中除表決之外的多數意見實際是一個虛擬的量詞,是達不到多數的“多數意見”。那么,這樣虛擬的多數意見和在征求意見的總數或者發表意見的總數中在實際數量上超過半數的多數意見,是否有區別以及有什么區別呢?筆者認為,在數量上沒有過半數的多數意見和在數量上超過半數的多數意見存在著重要的區別:一方面,兩者實際是少數民主和多數民主的分水嶺,前者本質上只是少數民主,而后者是名副其實的多數民主。另一方面,對于前者的認真考慮實際是對少數民主的認真考慮和應有尊重,同時這也意味著,對于前者可以考慮但并不必須接受,而對于后者就不一樣了,對于后者我們則沒有考慮和研究的余地,有的只能是服從了。所以,多數民主即使是錯了,我們也只能服從。沿著這樣的思路可以發現,在我國的立法活動中,對法律法規案中問題和條款的研究修改,實際存在和廣泛運用的就是對少數民主的尊重和研究,因為任何法律法規案在常委會的審議和征求意見過程中,對問題和條款提出的意見絕大多數都是少部分的意見。
上述多數意見和少數意見的論述在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立法活動中得到體現。關于在法律中規定“合理回報”的問題,草案二次審議稿沒有作出修改,但是它引起了常委會會議與會人員的熱烈討論。其中,明確反對民辦學校舉辦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的有8人,明確主張民辦學校舉辦者可以取得“合理回報”的14人,認為民辦學校舉辦者取得“合理回報”有一定道理,但同時提出“合理回報”與教育的公益性質有矛盾并要求對回報.新晨
予以嚴格限制的有5人,認為民辦學校舉辦者應當有“合理回報”,但對如何規定“合理回報”存在不同意見的有6人。在常委會一次審議后向各地和中央有關部門征求意見的過程中,贊成規定“合理回報”者沒有作為意見反饋,但反對規定“合理回報”的地方和有關部門有10多個。在法律委員會的幾次審議過程中,對“合理回報”的討論意見都比較分散,也沒有通過表決的方式予以確定。在此基礎上,法律委員會修改后的草案三次審議稿對所謂“合理回報”作出否定性的規定。在常委會的第三次審議中,反對規定“合理回報”者有9人,贊成恢復有關“合理回報”的規定者有19人。從上述列舉的具體數字來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發言人員(在常委會審議法律案中,有權發表意見的實際遠遠不止150多名常委會組成人員,還包括30多名省級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負責人、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以及10多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對有關“合理回報”問題發表意見的其實只是參加會議人數的極少部分,而在這極少部分人員中,有不少人還不是常委會委員。可見,對所謂“合理回報”這個關鍵問題,我們實際面對的是多數人的沉默。
這里需要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對于“合理回報”,在少數人的發言者中,也存在兩種相反的觀點,而在兩種相反的觀點中,支持“合理回報”者又占相對多數。那么,應當如何對待少數發言者的意見呢?如何對待少數發言者中的多數意見呢?正確的方法是高度重視,認真研究,反復權衡,將兩種意見都作為修改法律案的重要參考,但卻不能作為必然依據。而對少部分意見中的多數意見是否必須采納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這少部分意見中的多數意見情形十分復雜,在性質上與少數意見并沒有區別;只有當這少部分意見中的多數意見上升到常委會全體會議組成人員中過半數的多數意見時,不管這種意見是正確還是錯誤的,它才必須成為修改法律案的依據,因為這是多數民主的要求,也是多數民主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