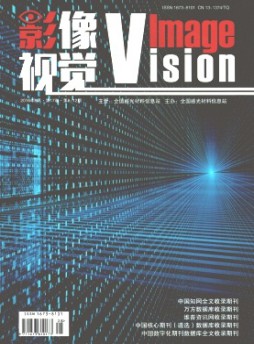論視覺審美現場感的意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視覺審美現場感的意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徐冰的《天書》、《煙草計劃》和蔡國強的《草船借箭》等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現場感的強調。這種現場感是不能單單被互聯網和多媒體的圖片影像所替代的,就像盧浮宮和世界各大美術館里的藏畫一樣,現場性是永遠不能被任何形式的展現所替代的。
經驗主義、意義論對審美現場直觀判斷的影響
18世紀哲學家克萊在《新視覺論》中指出,人之所以能通過面部表情感受到對象的情緒變化,是因為“這些變化是視覺直接把握的對象,我們之所以能夠從中看到情感,是因為它們在我們的經驗中總是伴隨著情感一起出現。如果預先沒有這樣一種經驗,我們就分不清楚臉紅究竟是羞愧的表現還是興奮的表現”。此理論被后世的社會學家改頭換面地提出“主觀推論說”。認為眾人之所以有共同的對待某事物一致的反映,是因為這些反映都是按照一種習俗和常規作出來的。此兩種解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認為事物的表現性質并非是事物本身的視覺式樣所擁有的,人所看到的僅僅是他們舊有的知識經驗所作用的。一旦這些知識經驗被喚醒,就即刻注入到了某種事物中。而運用這些理論去解釋藝術創造,結論便是:藝術家所創造的作品僅僅是視知覺對象的簡單復制。
阿恩海姆針對這種錯誤的聯想主義觀,提出藝術家對現實的知覺和把握具有創造性性質。他指出,知覺的整體性不是對元素簡單復制的結果,而是對元素的一種創造性再現,無論是藝術家的視覺和心靈都不是簡單復制著現實的裝置。藝術家的視覺形象永遠不是對于感性材料的機械復制,而是對現實的一種創造性把握。藝術家把握到的圖像是具有感染力、想象性的美的形象。阿恩海姆從格式塔心理學出發,認為知覺不是初級、零碎和無意義的,知覺本身就顯示出一種整體性、一種統一的結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如不能把握住事物的整體和統一的結構,就永遠都不能創造和欣賞藝術品。阿恩海姆還認為,欣賞偉大的視覺作品,是由作品本身的知覺特性直接傳達到眼中的。我們在觀看米開朗基羅在羅馬的西斯廷教堂的《亞當出世》時,通過繪畫本身的力的展示,一眼就能看出其深刻的象征意義。表現作品的能動式樣是由作品的構圖分割顯示出來,而故事的本質是由那些眼球前的事物———作品的主要樣式呈現出來。在觀看時,這個主要樣式并不是原本地復制在觀者的腦海中,而是在他的視覺神經系統中喚醒了一種與他的力的結構相同的力的樣式。這個用于表現力的樣式,在觀者大腦里活躍起來并使觀者處于一種激動的心理狀態,從而產生了相應的心理體驗的經驗。也就是說他認為繪畫作品或者靜止的視覺藝術作品并不是由聯想和經驗所致,而是由藝術創造的形象結構所喚起的視覺感染力。
一張畫就是一張畫,它告訴了你什么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傳達了什么感受,解讀應該是視覺感受的解讀,而不應該是文字的解讀,如果我們看了一張畫需要去用社會中某一件發生的事情去套進作品里,那不應該是視覺藝術的最終目的。筆者想在談論現場感這個問題時,應該首先明確視覺藝術作品所屬的范疇。在觀看方式上,我們很容易、很自然地會帶著舊有經驗去主觀切入,經驗主義影響觀看者的視覺感受。嘉泰諾•卡泥莎(GaetonoKanizse)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對所在環境中的事物已經很熟悉了,這正是因為這些事物已經通過視覺組織力構成了它們本身,而組織的過程是先于經驗且獨立于經驗的,這就使得我們可以憑借自己的經驗去體驗環境中的事物”。因為舊有的經驗影響看威尼斯雙年展、很多主題性的展覽(全國美展、體育展)等,觀看者往往會從尋找主題入手。當觀看作品的時候,會將自己對此主題的一個強烈愿望帶進觀看方式中。同樣,理解作品也會如此切入———此件藝術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說明了此位藝術家對待此主題的一個表達,以至于藝術評論家在主題鮮明的語境中尋找表達的文字。我們贊揚某位藝術家的作品有著某種情懷和觀看世界的方式,忽視的卻是最重要的作品美感。視覺藝術作品不是一篇文字說明文,它不同于寫作,視覺藝術作品永遠都是將視覺審美效果作為最終目的的,而不是以更恰當、更巧妙地說明某個問題、某個社會現象為目的。當觀看者懷有一種強烈的個人意愿來觀看給定物像的知覺性質時,舊有的記憶印象就會得到強化,往往會忽視了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貢布里希(Combrich)說:“一個物象對于我們的生物需要的相關性越大,我們就越容易與對它的認知協調一致,那么,我們對它所持有的形式上的對應標準也就越有寬松度”[貢布里希,范景中等譯.圖像與眼睛—圖畫再現心理學的再研究[J].浙江攝影出版社,1989.106.]。
藝術作品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在現場中的呈現
視覺藝術作品的審美方式并不取決于它的實體界限和它的形成過程,而在單一的“瞬間呈現”與通向過去與未來的多重維度的“現場”狀態中,由此得以讓觀者在面對千變萬化的作品時,體驗到一種超越日常生活本身的精神價值與意義。傳統的時空觀已不具備全面的表達世界的能力。取而代之,“現場”的概念延伸至藝術表達的各個領域,成為藝術品最終的審美效果。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在藝術與視知覺中談到:“視覺經驗具有動力性,一個人或一個動物所感知到的視覺經驗,絕不僅僅是物象有秩序的安排,也不僅僅是各種色彩與形狀的組合,或者物象的動勢和大小。我們的視覺感受往往首先受一種有方向感的張力的作用,這種觀看靜止的物體而體驗到的張力,并不是觀察者鑒于個人經歷,經由判斷而得出的。這種張力存在于對各種大小、位置、形狀、顏色等要素的一切感知過程內部。由于這些要素具有量和方向,因此這種張力被描述為‘心理力’”[史風華.阿恩海姆美學思想研究[M].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108.]。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畢加索看到大炮上的偽裝色竟然大吃一驚地喊道:“我們就是這樣畫的———這是立體主義繪畫的典型手法”。德國表現主義大師巴塞利茲曾在1983年的一次談話中說道:“我逐漸開始明白自己能夠從事繪畫。我想繪畫并不一定得畫有趣的題材。繪畫形象不在具備固有的重要性。所以我選擇沒有意義的東西……繪畫客體不表達任何東西。繪畫不是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相反,繪畫是自發的”[馬永建.后現代主義藝術20講[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從60年代開始,巴塞利茲發展了一種標志著他個人風格形成的創作方法———形象倒置。這種倒置的繪畫形象并不僅僅在展出的時候給觀眾看,他本人在創作的過程中也是倒著畫的。畫面中強烈的色彩和豪放的筆觸,看起來顯得粗魯而悲愴、厚重而充滿力量,他對于自己的這種創作方式是這樣說到的:“引發出迷惑和震撼,表現出一種挑戰的姿態”。通過這種表現方式,他讓觀眾的注意力瞬間就吸引到畫面本身,讓藝術作品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而不是讓觀眾專注與題材上。
藝術家在做作品之前,會有著某種想表達的東西,但很多作品并非如藝術家之前設想好的那樣,它自身具有生命力,會呼吸、會成長、會變得有自己的性格,就像是我們從小被父母寄予希望,將來長大會成為什么樣的一個人,該做什么,該怎么樣完成自己的人生。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像父母期待的那樣。可這也不代表不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就是失敗的人生。如果所有的作品都是之前設想好的,那么做作品的過程就是一個無創造性的、乏味的過程。藝術作品可能談不上創新,準確地說,是失去了它本身的自由性。藝術史的發展是具有承接性的,作品本身的成長也應該是具有創新過程的,藝術作品本身具有的生命力只有在現場才能得到完美的呈現。
結論
“現場感”是不同于“現場”這一概念的。一個完整意義上的“現場”的定義是指:藝術家的場所、藝術作品的場所、觀眾的場所。而“現場感”指的是觀眾在面對藝術家作品的時候視覺所感受到的作品的感染力。傳統的價值體系正在消逝,單向度的審美方式被淡化,互動對話式的討論成為更為普遍的交流形態,對藝術作品的審美標準更是到達了空前開放的程度。因為標準的不趨同性,為了滿足不同人群的審美需求,孕育而生了很多不同定義的展覽。那么我們在面對藝術品的同時,更多地把注意力引向藝術而不是藝術創作者的所謂的動機。闡述的對象應該是藝術品而非藝術家,我們想閱讀的對象永遠都是藝術品而不應該是創作它們的藝術家。這條原則將我們帶到我們對一個特定作品的反應方式上,如果我們將注意力放在藝術家的意圖上,那么我們勢必會錯過更好理解藝術品和我們對它的反應的機會。后現代主義語境下強調“現場感”的視覺觀來審視當代藝術,則必須拋開一切先入為主的預設法則,就藝術作品本身含有的符號系統(包括視覺和聽覺等所有的感知)來參悟其語義變化的進程。因此,循著“重要的是現場感”這一觀念,將使我們在欣賞視覺藝術作品時更純粹地去感受作品本身帶給我們的感染力。(本文作者:何藝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 上一篇:交通行業遠程教育的發展思路范文
- 下一篇:論視覺藝術的影像性思維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