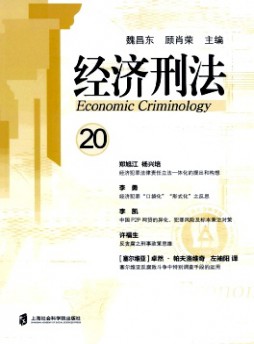刑法理論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刑法理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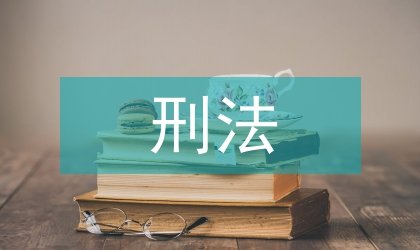
第1篇
在心理學中,意志是指人自覺地確定目的并支配其行動以實現預定目的的心理過程。人在反映現實世界的時候,不僅對現實世界有依據其主觀思維的認識,而且還會對它們形成一定的情感體驗,并且在自我認識和情感的支配下有意識地去改造客觀世界。這種最終表現為行動的,積極要求改變現實世界的心理過程就構成了心理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意志過程。 意志與行為有著不可忽視的密切關聯:意志引導行為。這種引導又體現在兩個方面:發動與制止。發動就是推動人去從事達到預定目的的所必需的行動;制止就是阻止不符合預定目的的行動。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一定的意志因素,行為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心理支持,那么這一行為就不成為我們刑法學上所談論的行為,因此也不會導致對此行為的刑事非難。
依照刑法學傳統,罪過通常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將引起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一種故意或過失的心理態度。它以故意和過失為內容,所以我們分別討論一下意志因素在故意與過失兩種心理狀態中的地位。
1.根據我國《刑法》第14條第1款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中規定的故意心理的意志因素具有兩方面特征:希望和放任,其表現為意志對行為的發動作用,在犯罪故意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一個人僅有對自己行為的危害結果的認識而沒有形成犯罪的意志,不希望或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便不可能自覺的確定行為的方向、步驟、方法,導致此種行為的事實。德國刑法學家克萊因指出:決意實施法律禁止的行為,或者決意不履行法律命令的行為,就表明積極的惡的意志,就是故意, 可見故意心理是在積極的惡的意志的推動下而轉化為現實中刑事非難的罪過心理的,它在犯罪的實施過程中具有決定的、主導的作用,是聯系犯罪意圖和犯罪行為的橋梁紐帶。總之,意志因素是在認識的基礎上,將人的心理外化到客觀世界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意志是故意成立不可缺少的因素。
2.過失心理狀態下是否存在意志因素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在刑法理論上一直爭論不休。我國《刑法》第15條第1款對過失犯罪作了規定,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是過失犯罪,由這一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上規定的過失有兩種:(1)疏忽大意的過失;(2)過于自信的過失。
大多數學者將疏忽大意看作是這一過失心理的意志因素,但是筆者認為,意志的存在是以認識為前提和基礎的,在疏忽大意的過失中,其認識因素是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也就是說行為人對于其行為的危害結果是沒有認識的,既然沒有認識有何來的意志呢?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疏忽大意的過失心理中既無意識又無意志呢?這顯然與過失犯罪應承擔刑事責任相矛盾。對此陳興良教授認為過失犯罪心理過程是有意志參加與意識和無意識交錯活動的過程,在司法實踐中除個別沖動行為外,找不到完全沒有意志的過失犯罪。 因此筆者認為,疏忽大意并不是這種過失心理的意志因素,而是行為人的一種潛意識的表現,這種潛意識導致了行為人的認識能力低于社會認可的正常標準,從而做出了與一般人的意志內容相反的決定,在這種決定(實際上也就是意志因素)的引導下實施了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
第2篇
我們可認為我國刑法中存在三級的行為概念:作為最基礎范疇的行為概念作為犯罪核心范疇的危害行為犯罪(即依法應受刑罰懲罰的行為)。危害行為是行為的一類,但卻是犯罪在評價前的狀態。也就是說,危害行為在我國刑法上實際是包含了侵犯一些社會主義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的對社會有害的行為,包括了一般違法行為、犯罪行為甚至一些違主義道德風尚的行為,而只有那些“依照法律應受刑罰處罰”的危害行為,才是犯罪。
二、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概念內涵檢討
對于危害行為的概念,我國權威教材認為學術界迄今并未達成一致意見。權威教材認為,危害行為“是指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識的支配下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認為它有三個特征:(1)有體性,即在客觀上是人的身體動靜。(2)有意性,即在主觀上是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識支配下的身體動靜。(3)有害性,是指在法律上看是對社會有危害的身體動靜。北京大學的教材認為,危害行為“是指表現人的犯罪心理態度,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將其特征概括為兩個:(1)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有危害性且為刑法所禁止;(2)表現人的犯罪心理和態度。而張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學教材中直接將刑法上的行為等同于危害行為:“刑法上的行為不是一般的行為,而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因此,刑法上的行為,是指基于人的意識實施的客觀上侵犯法意的身體活動。這一定義實際上是上述自然行為論、有意行為論與社會行為論的結合。據此,行為具有有體性、有益性、有害性三個特征。”馬克昌先生主編的《刑法學》定義是:“刑法中的危害行為,指由行為人的心理態度支配的危害社會的身體動靜”。同樣認為其具有有體性(行為人的身體動靜)、有意性(由行為人的心理態度支配的身體動靜)和有害性(對社會有危害性的身體動靜)。此外,陳興良教授把作為罪體構成要素的行為稱為“是指行為主體基于其意志自由而實施的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身體舉止。”盡管不同教材或學者關于危害行為概念有所不同,但從其實質內涵與特征來看,其實并沒有多大差別。它們都強調行為的有意性和有體性。有體性本文在此不必多說,有意性都是指在意志、意識或心理等支配下的活動,但都不指出其具體內容;都強調危害行為的有害性,而且都把這種有害性解釋為法律違反性。唯一不同的是有的稱之為法律違反性;有的稱之為法意侵害性;有的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侵犯性;有的指是刑法違反性等,但無論如何,都認為危害行為的危害是建立在違法的含義上的。
將危害行為視為對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侵害,被認為是統治階級以自己的價值標準對人類行為進行價值評價的結果;將危害行為視為對法益的侵害,是從大陸法系借鑒來的法益概念作為對危害行為的解讀,它實際上是將危害行為看作是一種違法行為;將危害行為視為刑法所禁止的行為,那么實際上是說危害行為具有刑事違法性的行為;自然,將危害行為視為具有法律違反性的行為,是將危害行為等同于違法行為,這種概念正確嗎?在筆者看來,從現有的刑法條文來看,我們不能得出危害行為是一種違法行為、特別是刑事違法行為的結論。如刑法第14條中,立法者只提到一種對社會危害的行為,也只要求行為人自己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認識,而不要求一種違法性認識或法益侵害性的認識,更沒有要求具有刑事違法性的行為。如果將危害行為視為具有刑事違法性的行為,那么這種危害行為幾乎無需進行犯罪構成的評價了,只要找到其行為人即可。如果將危害行為視為一種一般違法行為或者侵犯所謂法益的行為,那么也是不符合條文要求的。因為危害行為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不是一種違法判斷,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違法行為固然是一種對社會有害的行為,但是對社會有害的行為并非都是違法行為。一些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也不能不說對社會有害的行為,但未必是違法行為。立法也沒有要求行為人對行為的違法性具有認識,而是只要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認識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呢?其實,對現行統治關系的侵害,就是具有社會危害。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刑法中的危害行為應當是指體現人的意志或心理,對現行統治關系具有威脅或侵犯性的行為。它不僅包括違法行為,還包括違反道德倫理、一般規范的行為。在這里,我們看到危害行為根本不同于作為刑法基本范疇的行為,而是行為中體現人的意志或心理,對現行統治關系具有威脅或侵犯性的行為。
三、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危害行為功能檢討
在傳統刑法理論中,犯罪客觀方面被視為犯罪的核心地位。所謂的犯罪客觀方面,“是指刑法所規定的、說明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損害的客觀外在事實特征。”犯罪客觀方面之所以被傳統理論看作處于核心地位,是因為危害行為的存在。對此,權威教材指出:“因為犯罪畢竟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危害行為這個客觀方面的要件,是犯罪其他要件所依附的本體性要件,犯罪客體是危害行為所侵犯而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主體是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行為的自然人和單位,而犯罪主觀方面也必須由危害行為得到體現和說明。”在這里,危害行為被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這里的問題在于,作為被評價之前的危害行為與作為構成要件(或評價標準)的危害行為是否是一致的呢?如果二者是一致的,那么這種被評價的對象如何同時成為一種評價標準呢?而且,如果這種評價對象和評價標準是統一的,這種評價標準又有什么用處呢?在筆者看來,危害行為固然是成立犯罪的基礎范疇,但是它只有經過刑事違法性、刑罰可罰性評價才能成為犯罪行為,被評價為犯罪的危害行為仍是危害行為自身,只不過在法律上被評價為犯罪而已。
問題在于犯罪構成的理解,犯罪是一種行為,而不是包含了主體、客體、時間、地點、方式的聯合體,犯罪構成不是犯罪的分解和組合,而應是對危害行為進行評價的體系。所以,危害行為不應當成為犯罪構成的要件,所謂犯罪構成中的危害行為要件,實際是實行行為,或者說是構成要件符合。我們有必要把作為犯罪評價對象的危害行為同作為犯罪客觀構成要件的行為區分開來。這個問題還可以從以下角度看,這種危害行為的“危害”從何而來,如果一個行為已經被評價為危害行為,它一定是被認為已經具有了規范違反性,已經被考慮了正與不正,或者合法與不法之后的結果,而且在一些情況下已經考慮了其造成了具有危害性的結果,這種評價不是單純的依據行為本身,而是依據行為及其周圍環境做出的。換言之,已經根據犯罪的客觀方面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如果這樣的話,還有必要考察除行為之外的其他方面嗎?在這里,這樣一個危害行為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客觀要素,將其歸類到犯罪客觀方面也是不妥當的,而且存在重復評價之閑。所以,一種平面化的犯罪評價體系是不對的。傳統上的危害行為存在兩種方式:一種是作為,即行為人以身體活動實施的違反禁止性規范的危害行為;另一種是不作為,是指行為人負有實施某種行為的特定法律義務,能夠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為。這兩種方式都涉及到規范評價的問題,可以表達出其危害性的內涵。危害行為的劃分功能在這里是可取的.但是對于持有呢?持有是一種人對物的控制與支配關系。就持有本身而言,它不是行為,而是一個事實。如我擁有一支槍或一個國家工作人員擁有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財產,本身是一個事實,而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行為。它是中性,只有非法持有才能構成犯罪。如果說非法持有可以作為危害行為的話,那么持有也屬于危害行為嗎?這顯然是不對的。
持有本身是一個行為概念下的范疇,人們應當在行為的概念下討論持有是否是一種行為,是怎樣的一種行為,不應視其為危害行為下的范疇,與作為、不作為并列。這里必須首先注意這樣一個問題,即就持有本身而言,無論持有的是何物(不論是錢幣、還是槍支彈藥等),都是中性的,只有在無權或無合法根據持有的情況下,才是非法的。如一個警察持有槍支和一個公民持有槍支,就持有行為本身而言并無差別,但是警察持有槍支基于其職責或授權而持有,因而是合法持有,而公民持有槍支如果不是被核準才是非法持有,才存在成立盜竊槍支罪的問題。因此,危害行為的范疇存在盡管有其理論和立法功能,但是不能因此取代行為范疇,只有在行為范疇下才能將持有認識清楚,將持有在危害行為下進行討論,即討論其屬于作為、不作為或是一種獨立的行為形式,是理論的錯位。危害行為概念的理論結果還導致這樣的問題:既然是行為的一種,那么它有助于自始就將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排除在犯罪評價之外。因為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是正當的行為,就法律的立場上看,是沒有錯誤的行為。這樣一來,從邏輯上說,對于正當過當和緊急避險就不需要經過犯罪構成的評價,而只要進行危害行為的評價即可。可是,這種評價又與罪與非罪評價有什么區別呢?正如前文所述,這個概念可能導致重復評價的問題。
四、結語
第3篇
(一)解決“定罪難”問題
在刑事和解中涉及不到對加害人定罪量刑的問題,因為刑事和解理論弱化了犯罪是對國家統治秩序挑戰的概念,加害人承擔的責任只是對被害人的賠償責任,不再承擔國家對其犯罪行為做出的刑事懲罰責任,這樣一些很難認定的刑事案件就很好解決了。解決了定罪難問題也就解決了疑難案件的問題。
(二)有利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
刑事和解制度的第二個有益之處是有利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按照傳統的刑事司法理論認為,對犯罪人的刑法懲罰要有國家來進行,國家代表被害人來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被害人沒有權利去向對自己的合法權利造成損害的犯罪人進行懲罰,因為傳統刑事司法理論認為刑罰權只能由國家來行使,任何人不能懲罰犯罪人。這樣在國家社會利益的語境下,被害人要求懲罰犯罪人的權利被國家壟斷了,這樣在權利保護方面,刑事和解制度下,被害人同加害人直接商談,直接要求加害人對其加害人行為給自己帶來的損害進行賠償,被害人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表達了出來,這樣就更有利于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國家刑罰權的退讓給被害人保護自己的權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有利于加害人的社會回歸
刑事和解制度的第三個有益之處是有利于加害人的社會回歸。傳統的刑事司法理論中,國家代表被害人懲罰犯罪人,犯罪人要被處以刑罰處罰,首先犯罪人被處以刑罰處罰,在心理上就極其容易產生報復社會的思想,執行完了后的犯罪人很容易再次犯罪以報復社會;其次是刑罰的執行如果不脫離社會,比如監管、剝奪政治權利,會使得犯罪人在社會中很難生存,在心理上有一種恥辱感,在與人的正常交往中感覺自己低人一等抬不起頭來無顏面對被人,如果是脫離社會,刑罰的執行就在一個封閉的場所中進行.犯罪人完全與社會脫離與世隔絕.“汗水洗刷罪惡。勞動重新做人”。犯罪人的改造完成后復歸社會,但是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與世隔絕一段時間后的犯罪人無法適應社會的變化,陷入生存的困境之中。而刑事和解制度中,只要雙方的和解協議執行完畢。被害人的損失得以賠償,而加害人不會獲得刑1處罰,加害人得到了社會對他的尊重,這就會使加害人更加深刻的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性從此不再犯罪,這就有利于加害人的社會回歸,加害人可以在社會中繼續正常的生活,不脫離社會同時也不會再對社會產生危害。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負益分析
(一)弱化了刑罰的懲罰功能
所謂負益,就是指刑事和解制度的不利的一方面,稱之為負益。首先刑事和解理論弱化了刑罰的懲罰功能,由于刑事和解理論認為犯罪時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沖突,因此在加害人承擔刑罰時只承擔相當于原有刑罰特殊預防部分的責任,失去了一般預防的作用。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出發,刑罰的目的在于報應和預防,報應是國家代表社會對犯罪人的一種懲罰,是國家暴力強制犯罪人對自己的危害社會行為承擔的后果;預防是國家通過對犯罪人的懲罰,一是告誡犯罪人不要再次的犯罪,二是通過對犯罪人的懲罰,以威懾社會中的其他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犯罪,一旦犯罪要承擔嚴重的后果。而刑事和解理論弱化了這些概念,和解的方法失去了原有刑罰的作用,對犯罪人的告誡沒有了,對社會中其他人的威懾沒有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沒有了。犯罪的人沒有受到懲罰,就是對守法公民的打擊,刑法失去了應有的功能是對社會秩序的一種損害。
(二)可能導致權利濫用
同時還表現在,刑事和解有可能導致權利濫用。一旦有了權利,每個人都想利用權利為自己謀取盡可能多的利益,這就是權利濫用。刑事和解制度下,和解協議能否達成起到關鍵作用的是被害人,如果被害人利用其主動地優勢,謀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向加害人提出許多過分的無理的要求,利用機會盡可能多的索要賠償,而加害人基于急于擺脫危險境地的心理,無奈會同意被害人的要求,這樣的結果就是加害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并沒有降低,反而可能會因為被害人的要挾而產生報復的心理。另外一方面,加害人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比如金錢、社會關系等,迫使處在弱勢地位的被害人與其和解。并通過威脅、引誘來達成有利于自己的和解協議,這樣的結果就是被害人的利益不但沒有受到保護得以恢復,反而利用刑事和解協商解決問題的心理也受到了打擊,這比上一種情況更容易產生報復心理。由此可見,由于當事人雙方的地位和實力的不對等,達成的和解協議可能是不公平的,如果沒有嚴格法律監督,刑事和解中權利濫用是很容易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