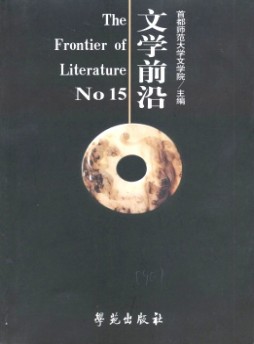論文學(xué)的生態(tài)想象構(gòu)建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論文學(xué)的生態(tài)想象構(gòu)建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加拿大文學(xué)中自然和荒野有著特殊的文化象征意義,加拿大的民族/國家身份構(gòu)建也和自然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荒野想象既包含了個(gè)體的經(jīng)歷,又是文化記憶和身份的隱喻。荒野文學(xué)體現(xiàn)了加拿大從殖民時(shí)期到后殖民主義時(shí)期轉(zhuǎn)變過程中的超民族想象,而荒野動(dòng)物想象更是構(gòu)建加拿大文化象征的一種獨(dú)特的文學(xué)體裁。荒野文學(xué)一方面呼應(yīng)了世界文學(xué)范圍內(nèi)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倫理思想、動(dòng)物倫理的興起,另一方面在文化寓言的深層內(nèi)涵上折射出加拿大人的地方、民族、國家和社會(huì)想象,可謂世界文學(xué)舞臺(tái)上的一枝奇葩。
[關(guān)鍵詞]加拿大文學(xué);荒野文學(xué);生態(tài)批評(píng)
自然或荒野往往被認(rèn)為是人跡罕至、意識(shí)形態(tài)缺席的客觀空間。然而,新興的空間哲學(xué)、文化地理學(xué)認(rèn)為,民族/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和自然密不可分,荒野常被當(dāng)作一個(gè)國家的標(biāo)志。哲學(xué)家哈維(DavidHarvey)指出:“民族身份往往是建立在某些環(huán)境特征之上的……如果沒有某種環(huán)境意象或身份的支撐,民族主義將是一種不可能的體系。”①事實(shí)上,“自然”這個(gè)詞就是人類話語的產(chǎn)物。自然是語言中的一個(gè)能指(signifier),總是被各種話語體系或意識(shí)形態(tài)利用,被賦予種種價(jià)值或?qū)傩浴W匀徊⒎枪铝⒌模俏幕漠a(chǎn)物,永遠(yuǎn)處在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歷史、話語的構(gòu)建過程中。齊澤克(SlavojZizek)認(rèn)為,自然就是意識(shí)形態(tài),“自然是不存在的”②。自然和荒野是“展示……民族/國家這個(gè)想象共同體的象征舞臺(tái),是地域的烏托邦,是荒野共和國”③。本文從自然的文化符號(hào)學(xué)視角出發(fā),論述加拿大文學(xué)中的荒野想象及其在民族/國家身份構(gòu)建過程中發(fā)揮的象征作用,探討“加拿大想象”和民族精神的文學(xué)表征。
一、荒野精神的民族文化和哲學(xué)
基礎(chǔ)自然對(duì)國家身份認(rèn)同具有精神象征意義。例如,美國荒野精神是美國精神的隱喻,荒野在美國歷史奠基之初就發(fā)揮了塑造性作用。在西進(jìn)運(yùn)動(dòng)中,美國邊界不斷向西部荒野擴(kuò)張,荒野作為伊甸園和烏托邦理想的象征,鑄就了美國的民族夢(mèng),成為美國精神的象征。特納(FrederickJacksonTurner)在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一文中指出:理解美國文化的“關(guān)鍵在于偉大的西部和邊疆———蠻荒和文明的交界”④。荒野精神成為美利堅(jiān)民族堅(jiān)韌不拔的精神寫照,上升為美國的主流文化價(jià)值取向,象征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反映出強(qiáng)烈的實(shí)用主義世界觀。正如美國文學(xué)對(duì)荒野的精神塑造一樣,荒野也成為加拿大文學(xué)象征中的重要元素,對(duì)其民族/國家身份構(gòu)建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弗萊(NorthropFrye)指出:加拿大文學(xué)“最具特色的成就就是對(duì)絕對(duì)恐懼的描繪……它直接來源于人們?cè)诿鎸?duì)加拿大廣袤而人煙稀少的土地時(shí)所感受的那種恐怖的孤獨(dú)感”①。荒野的嫵媚、狂暴、秀麗、雄奇,無不對(duì)人的精神世界產(chǎn)生直接影響,并作用于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rèn)同。如果說美國的荒野精神代表了國家擴(kuò)張過程中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的話,那么加拿大的荒野精神則代表了對(duì)人與自然共處的生態(tài)敬畏和精神認(rèn)同,而非征服意圖。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荒野想象的國家構(gòu)建是一個(gè)循序漸進(jìn)的過程,它是隨著加拿大文學(xué)體系的建構(gòu)和成熟,逐漸與國家想象合二為一的文化象征符號(hào)體系的一部分。如果從加拿大文學(xué)史的宏觀視角來看,荒野的形象和意義的形成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程。也就是說,荒野作為加拿大的文學(xué)形象只是在20世紀(jì)60年代之后逐漸成型的,而其內(nèi)涵和意義進(jìn)入21世紀(jì)以來也一直在發(fā)生著微妙的變化。在早期的加拿大文學(xué)中,文學(xué)的主題主要是圍繞殖民地開拓而展開的,記敘英國殖民者與加拿大荒野和叢林的初次接觸與對(duì)峙。此時(shí)的文學(xué)書寫中,荒野對(duì)人類的生存構(gòu)成極大的威脅,代表荒蠻和文明的邊緣。在蘇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的《叢林艱苦歲月》(RoughingItintheBush)中,作者把安大略北部的無人叢林描繪成險(xiǎn)象叢生的邊遠(yuǎn)地區(qū),作品中不時(shí)流露出對(duì)母國英格蘭的眷戀和懷念,荒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兇險(xiǎn)、野蠻的代名詞。正如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在《存活:加拿大文學(xué)主題指南》(Survival:AThematicGuidetoCana-dianLiterature)中所分析的那樣,加拿大文學(xué)中的鮮明主題就是:“在荒野中存活———荒野冷漠無情,甚至充滿邪惡,因而是不具備道德意識(shí)的。由此可見,早期文學(xué)想象中的荒野還沒有上升為一種國家文化象征符號(hào),只是作為人類社會(huì)的陪襯,凸顯加拿大人堅(jiān)韌不拔的品質(zhì)。”然而到了1867年加拿大聯(lián)邦成立前后,加拿大人愛國情緒高漲,支配殖民地居民的邊塞思維逐漸發(fā)生了改變,人們開始對(duì)土地有了認(rèn)同,從此展開了對(duì)荒野的文化文學(xué)想象與符號(hào)構(gòu)建。此時(shí)的文學(xué)作品中開始出現(xiàn)對(duì)荒野的謳歌,產(chǎn)生了諸如浪普曼(ArchibaldLampman)、司各特(D.C.Scott)、克勞福德(IsabellaValancyCrawford)等浪漫派詩人,他們以優(yōu)美的詩行謳歌荒野,把荒野轉(zhuǎn)變成沉思和靈感的源泉。格德斯密(OliverGoldsmith)在他的《新興的農(nóng)莊》(TheRisingVillage)中熱情謳歌人們的昂揚(yáng)斗志和欣欣向榮的景象。這首詩實(shí)際上和他的同名祖父、英國詩人格德斯密的《廢棄的農(nóng)莊》(TheDesertedVillage)形成鮮明的反差,荒野開始被賦予活力和生機(jī)。20世紀(jì)20—40年代之間的荒野小說[如格羅夫(F.P.Grove)的《沼澤地的定居者》(Set-tlersoftheMarsh)、奧斯坦索(MarthaOstenso)的《野鵝》(WildGeese)等]則刻意塑造出人類與荒野斗爭的英雄氣概和精神,荒野往往成為映射加拿大人性格的象征。20世紀(jì)60—70年代之間,加拿大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高漲,荒野的文化象征雛形逐漸成型,成為加拿大區(qū)別于美國的一種文化象征和精神符號(hào)。在阿特伍德的小說《浮現(xiàn)》(Surfacing)中,無名女主人公在深入北部荒野的途中見證了原始土地逐漸被美國商業(yè)和工業(yè)侵蝕的景象。小說中的北部荒野成為加拿大人的精神象征,并巧妙地結(jié)合了阿特伍德在《存活》中所提出的受害者形象。此時(shí)在文化界和思想界展開了一場(chǎng)深刻的荒野建構(gòu)工程。加拿大人開始借用荒野的狂暴、原始、純潔、寒冷來凸顯民族性格與特征,以示與美國西部精神的文化區(qū)別。
二、荒野精神的文學(xué)想象
在加拿大文學(xué)中,一方面,荒野氣候惡劣、險(xiǎn)象環(huán)生,極端的天氣給生存帶來威脅;另一方面,荒野散發(fā)出一種神秘的誘惑力,催生了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神秘主義、自然主義、生態(tài)主義作品,成為塑造民族文化符號(hào)的源泉。阿特伍德在《異象》(StrangeThings:TheMalevolentNorthinCanadianLiterature)中分析了荒野的文化內(nèi)涵和象征。例如,富蘭克林探險(xiǎn)故事①成為許多加拿大小說的主題[如魯?shù)?#8226;韋伯(RudyWiebe)的小說《發(fā)現(xiàn)陌生人》(ADiscoveryofStrangers)],故事被一遍遍重述,使寒冷的北極圈變成一種既散發(fā)出死亡氣息又充滿神秘魅力的地理和文化象征。她指出:“對(duì)美國人來說……富蘭克林這個(gè)詞意味著本杰明,或者是一臺(tái)爐灶,但對(duì)加拿大人來說,它意味著一場(chǎng)災(zāi)難。加拿大人對(duì)災(zāi)難情有獨(dú)鐘,尤其是對(duì)冰霜雪暴情有獨(dú)鐘。”②荒野和嚴(yán)寒象征著生命的荒蕪,生存因而成為加拿大人的首要需求,而在文學(xué)上則表現(xiàn)為對(duì)大自然的一種絕對(duì)敬畏,凸現(xiàn)出荒野的崇高美。加拿大作家“總是確保他們的主角要么死去,要么遭受失敗的挫折”,因?yàn)槭 笆俏ㄒ荒苤С种鹘怯钪嬗^的事物”③。對(duì)荒野存活主題的描寫比比皆是。例如格羅夫的小說《穿過草原的小徑》(OverPrairieTrails)描寫了一幅自然主義的生存畫面。一場(chǎng)暴風(fēng)雪過去之后,艾比決定去尋找失蹤的拉德克里夫,經(jīng)過艱難跋涉,終于在雪堆里找到了他的尸體。拉德克里夫蜷縮在雪洞中,表情安詳,仿佛墜入夢(mèng)鄉(xiāng)。顯然,他在突來的暴雪面前自知生還無望,因而坦然選擇在雪洞中死去;而妻子在得知丈夫的死訊之后也反應(yīng)平平,仿佛一切都沒有發(fā)生過。在辛克萊•羅斯(SinclairRoss)的《門上的漆》(“APaintedDoor”)中,性格倔強(qiáng)的約翰一心撲在農(nóng)活上而無心陪伴寂寞的妻子。在一個(gè)暴雪夜,妻子和鄰居斯蒂芬偷情,外出返回的約翰目睹了一切,卻選擇默默地離開,凍死在雪地中。此刻的雪成為主人公內(nèi)心的外在化表現(xiàn),深刻揭示了人的存在與自然的微妙的依存關(guān)系。可見,荒野和自然成為作品的主人公,是加拿大人集體思維的表征,它一方面影響并塑造了加拿大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又成為加拿大民族想象的文化構(gòu)建產(chǎn)物。這種荒野想象投射出加拿大人的集體意識(shí)、記憶和歷史,“被一代代相傳下去并加以改造,一代代的故事講述者重新用不同的視角講述,在每一次講述中都會(huì)發(fā)現(xiàn)不同的意義……并賦予它新的象征性”④。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荒野的象征化進(jìn)一步升華,超越了簡單意義上的地理和氣候描寫,被賦予新的屬性,即加拿大人性格的生態(tài)性,這種生態(tài)性格總是和地理空間緊密相關(guān),體現(xiàn)出一種生態(tài)的地方認(rèn)同。例如,加拿大人“總是把自己想象或構(gòu)建成一種‘加拿大即北方’的形象(Canada-as-North)”⑤。
加拿大北部具有文化地理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象征意義,成為民族精神的符號(hào)。批評(píng)界對(duì)加拿大北方的文化象征意義的研究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層出不窮,如巴里•洛佩茲(BarryLopez)的《北極之夢(mèng):北方風(fēng)景的夢(mèng)幻與欲望》(ArcticDreams:ImaginationandDesireinanNorthernLandscape,1986)、約翰•莫斯(JohnMoss)的《沉默的回聲:北極敘事選》(EchoingSilence:EssaysonArcticNarrative,1997)、勒內(nèi)•胡蘭(RenéHulan)的《北方經(jīng)歷與加拿大文化的神話》(NorthernExperienceandtheMythsofCanadianCulture,2002)、舍利爾•格雷斯(SherillE.Grace)的《加拿大和北方的觀念》(CanadaandtheIdeaofNorth,2002)等。由此可見,荒野已經(jīng)“不僅僅是一個(gè)地方……而是一個(gè)文化產(chǎn)物”①。荒野甚至超越了倫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價(jià)值意義,成為一種審美價(jià)值觀和精神建構(gòu),在文學(xué)上則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空間的生態(tài)倫理。在米切爾(W.O.Mitchell)的小說《杰克和小孩》(JakeandtheKid)中,古德弗萊太太感嘆道:大自然就“是一種心靈的凈化與滌蕩———就像希臘悲劇中的凈化(catharsis)一樣”②。這種精神的蕩滌發(fā)揮了美學(xué)意義上的壯麗和升華(sublimation)作用,超越了人們的文化歸屬,凸顯出人類主體對(duì)自然生態(tài)的崇敬和深度的大地認(rèn)同。在亨利•克萊里爾(HenryKreisel)的短篇小說《摔壞的地球儀》(”TheBrokenGlobe”)中,尼克的父親一輩子在薩斯喀徹溫的草原上生活,他固執(zhí)地認(rèn)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每天東升西落,永遠(yuǎn)圍繞著靜止的地球旋轉(zhuǎn)。上小學(xué)的尼克用地球儀向父親講解地理常識(shí),卻被憤怒的父親斥為異端邪說,并把地球儀摔毀。小說中開闊平坦、一望無際的荒野成為人們的心態(tài)和世界觀的投射。對(duì)祖父來說,加拿大荒野是獨(dú)特的、絕對(duì)的,不像英國和法國“到處可以看到被賦予人性意識(shí)的自然景觀”③。即便20多年后,父親仍然不能原諒已經(jīng)成為大學(xué)地球物理教授的兒子的“錯(cuò)誤”。故事結(jié)尾,父親指著空闊的大草原說道:“看……大地是平坦的,而且靜止不動(dòng)。”④又如,在肯•米切爾(KenMitchell)的《電力大革命》(“TheGreatElectricalRevolution”)中,敘事者的祖父從都柏林移民到加拿大,當(dāng)他看到連綿不絕的荒野時(shí)緊張不安,神經(jīng)幾乎崩潰。祖父“遠(yuǎn)涉重洋,從五千多英里遠(yuǎn)的地方來到這片開闊的土地上,卻最終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空間恐懼癥”⑤。荒野的遼闊和人類社區(qū)的隔絕形成鮮明反差,祖父割斷了政府架起來的電話線,選擇生活在自我封閉的空間之中。“橫躺的土地和直立的人”是加拿大西部文學(xué)中的一個(gè)鮮明主題。在史蒂芬•斯科比(StephenSco-bie)的《條紋馬賽克》(“StreakMosaic”)中,畫家女主人公來到了加拿大西海岸,卻不能適應(yīng)城市里狹小的空間,眼前的山峰阻擋了她的視線,影響了她的想象力。她希望“能夠推倒所有的墻壁,讓空氣一涌而進(jìn)”⑥,就連她的油畫也非常簡單抽象,只能在畫布的最底端看到一條水平的直線。的確,荒野想象對(duì)精神狀況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的作品俯拾皆是,例如凱瑟琳•帕爾•特雷爾(CatharineParrTraill)的《加拿大的叢林》(TheBackwoodsofCanada)、米切爾的《誰曾看見風(fēng)》(WhoHasSeentheWind)、約翰•霍華德(JohnHoward)的《泰•約翰》(TayJohn)和辛克萊•洛斯(SinclairRoss)的《關(guān)于我和我的房子》(AsforMeandMyHouse)等等,這些作品都成為反映加拿大民族性格的一面鏡子。
三、荒野的動(dòng)物想象
關(guān)于荒野的生態(tài)性,一個(gè)極其重要的體現(xiàn)就是動(dòng)物想象。動(dòng)物想象是一個(gè)和荒野意識(shí)密切相關(guān)的承載了民族想象和文學(xué)符號(hào)學(xué)建構(gòu)使命的元素。弗萊在1976年指出,荒野對(duì)加拿大人定義“我是誰”和“這是哪里”具有重要作用。人類和動(dòng)物一樣,是荒野中生存的物種。阿特伍德在題為“那個(gè)國家的動(dòng)物”(“TheAnimalsinthatCountry”)的一首詩中把“這個(gè)國家”和“那個(gè)國家”的動(dòng)物進(jìn)行了對(duì)照。“那個(gè)國家”或是美國,或是英國,這里的動(dòng)物“都長著人的臉……它們的眼睛像車燈一樣閃亮/又消失”①,它們被作為人類的構(gòu)建物納入社會(huì)價(jià)值體系。相反,在“這個(gè)國家”,即加拿大,動(dòng)物卻“長得誰也不象”②。大自然在詩中就是一片純粹的荒野,這里缺乏秩序,散發(fā)出恐怖的荒野氣息。實(shí)際上,用荒野動(dòng)物傳達(dá)文化意義是加拿大文學(xué)想象的一個(gè)獨(dú)特傳統(tǒng)。薩摩比-慕雷(R.Sum-merby-Murray)指出,在后聯(lián)邦時(shí)期,“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構(gòu)建同樣來自對(duì)自然世界的想象或魔幻般的描繪,尤其是對(duì)荒野動(dòng)物的擬人化想象,通過這種手段構(gòu)建出一個(gè)神秘的荒野世界”③。他認(rèn)為,“荒野生存和對(duì)加拿大自然的不可預(yù)測(cè)性的想象塑造了加拿大的民族身份”,自然不僅給人們提供能量和資源,而且是一種“復(fù)雜的生活經(jīng)歷,不能得到完全理性的解釋”④。加拿大荒野動(dòng)物文學(xué)在表現(xiàn)手法上主要分為三種:第一種方法是對(duì)加拿大獨(dú)有或常見動(dòng)物擬人化處理,借動(dòng)物映射民族性格,反映人類社會(huì)的品質(zhì),因此這些作品往往是現(xiàn)代形式的民族———?jiǎng)游镌⒀浴@纾幽么髣?dòng)物敘事中常常借用海貍⑤映射加拿大人的“海貍社會(huì)”,因?yàn)楹X偸且粋€(gè)辛勤勞作而秩序井然的動(dòng)物,它就是“殖民社區(qū)構(gòu)建者的完美形象”,這種表征是“帝國權(quán)力對(duì)殖民社會(huì)和土著民族施加影響的媒介”⑥,通過它構(gòu)建出勤勞、有序的民族性格。在阿里斯泰爾•麥克勞德(AlistairMacLeod)的《島》(Island)中,動(dòng)物具有鮮明的加拿大蘇格蘭后裔民族性格。他筆下的蘇格蘭邊境犬忠誠、重感情、防御性強(qiáng),和小說中濃郁的部族親情形成強(qiáng)烈陪襯。在《來年春天》(“SecondSpring”)中,卡普蘭的加拿大蘇格蘭人對(duì)牲畜的品種非常挑剔,決不讓“霍爾斯坦牛和艾爾夏牛雜交,因?yàn)檫@會(huì)讓其品種特色被搞亂”⑦。在《林間空地》(“Clearances”)中,敘事者的蘇格蘭犬成為守護(hù)加拿大小島土地的忠實(shí)衛(wèi)士,跟美國人的美洲囂犬形成對(duì)峙。因此,麥克勞德的動(dòng)物形象完美闡釋了文學(xué)想象與民族身份書寫之間的聯(lián)姻關(guān)系。第二種方法是借用加拿大荒野意象和動(dòng)物神話,在抽象意義上構(gòu)建加拿大的本土文化象征。荒野文學(xué)中最常見的一種動(dòng)物是加拿大叢林狼。希拉•沃特森(SheilaWatson)的小說《雙鉤》(TheDou-bleHook)講述了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內(nèi)陸加里布地區(qū)的一個(gè)與世隔絕的社區(qū)故事。小說充滿了神秘、魔幻和怪誕的描寫,叢林狼是一個(gè)無所不在的神的形象,控制著山村里所有居民的思想和行為。沃特森不僅將叢林狼設(shè)置成一個(gè)幽靈般的隱身主角,還利用了印第安土著部落傳說中詭計(jì)多端的叢林狼和創(chuàng)世者的雙重角色,小說被譽(yù)為加拿大的《荒原》。同樣,在肯•米切爾的小說《多尼•克尤提的英雄冒險(xiǎn)》(TheHeroicAdventuresofDonnyCoyote)中,克尤提(即叢林狼的讀音,英文為Coyote)如同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一樣,踏上了追求夢(mèng)想的旅途。在跨越邊境追求美國夢(mèng)失敗之后,克尤提回到加拿大,重返加拿大的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
小說利用現(xiàn)實(shí)與夢(mèng)想的反差,借用美國夢(mèng)的失敗凸顯了克尤提的加拿大身份。此外,阿特伍德在《異象》中還討論了荒野怪獸溫迪戈①和灰林鸮②的神話傳說。她認(rèn)為,這些荒野怪獸形象反映了加拿大人孤獨(dú)和與世隔絕的心理,進(jìn)而成為加拿大文學(xué)和民族神話構(gòu)建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對(duì)加拿大民族想象中的家庭、兩性關(guān)系、社區(qū)和民族身份等重要概念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第三種方法是模糊人性與荒野性(wilderness)/動(dòng)物性(animality)的界限,將荒野性/動(dòng)物性投射于人性身上,構(gòu)建人與自然的混合體或人獸同體形象,使加拿大民族身份披上一層神秘的色彩。此類著作有托馬斯•金(ThomasKing)的《綠草流水》(GreenGrass,RunningWater)和湯姆森•海威(TomsonHighway)的《毛女王的吻》(TheKissoftheFurQueen)等。在這些作品中,叢林狼常常在人類與動(dòng)物身份之間游離,并拒絕脫離自己的野性。《毛女王的吻》把世界看作一個(gè)共同社區(qū)而不是等級(jí)社會(huì)秩序,構(gòu)建出一個(gè)特殊的精神世界,其中的一切相互聯(lián)系,所有人的故事相互滲透,時(shí)間也是循環(huán)的,現(xiàn)在和過去相互交叉。小說中不僅人獸的界限被模糊化,而且不同物種的動(dòng)物能夠相互溝通。又如恩吉爾(MarianEngel)的《熊》(Bear)講述了女主人公與一只熊朝夕共處的故事,女主人公對(duì)熊的戀情超越了人類情感的范疇。她似乎忘記了人性,完全回歸了野性,她的“身體、頭發(fā)、牙齒和指甲到處散發(fā)出熊的氣味”③。她感到自由,覺得自己“獲得了新生”④。在阿特伍德的《浮現(xiàn)》中,無名女主人公踏上深入荒野的旅途,最終成為荒野的一員,開始像青蛙一樣吃土、排便,她忘記了人類的語言,甚至變成一棵樹,最終和自然融為一體。在這些作品中,人類和野獸有著一種不可言說的相似和聯(lián)系,加拿大性與野性之間建立起一種獨(dú)特的象征聯(lián)系,成為加拿大民族/國家形象的一個(gè)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加拿大荒野/動(dòng)物文學(xué)傳統(tǒng)中,一個(gè)不能不提的名字就是查爾斯•羅伯茨(C.G.D.Roberts)。羅伯茨的動(dòng)物小說集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于一身,是加拿大動(dòng)物文學(xué)的典范。在小說《古老森林的心臟》(TheHeartoftheAncientWood)中,彌漫著孤獨(dú)、荒野的氣氛,人類和動(dòng)物的遙遠(yuǎn)親情被喚醒。小女孩米蘭達(dá)對(duì)神秘的森林有一種莫名的歸屬感,在母親的記憶中,她是一個(gè)“怪異的嬰兒,更象一個(gè)仙子或者野生動(dòng)物,而不是人類”⑤。克魯芙和米蘭達(dá)的“親情”取消了人與野獸之間的界限,如果說克魯芙是一只具有人類靈魂的熊,那么米蘭達(dá)就是一個(gè)具有野獸靈魂的人。羅伯茨筆下的人和動(dòng)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和象征意味。米蘭達(dá)是加拿大移民者的后代,出生在加拿大的荒野,因此在小說中她就是荒野的化身,她和自然荒野以及荒野動(dòng)物的親情聯(lián)系代表了加拿大新生民族性格的一個(gè)重要方面。莫里森在《加拿大人不是美國人》(CanadiansareNotAmericans:MythsandLiteraryTraditions)一書中比較了加拿大文學(xué)和美國文學(xué)傳統(tǒng)中對(duì)荒野的態(tài)度。她指出,美國文學(xué)中展現(xiàn)了西部推進(jìn)運(yùn)動(dòng)中人類對(duì)自然的破壞,而加拿大文學(xué)中則充滿對(duì)文明進(jìn)程中“自然世界所承受的痛苦的不安感和負(fù)罪感”①。因此,對(duì)于自然來說,加拿大人比美國人更富有同情和認(rèn)同。的確,動(dòng)物文學(xué)被稱頌為“19世紀(jì)末興起的一個(gè)……嶄新的、獨(dú)具加拿大特色的文學(xué)體裁”②,并被民族主義文學(xué)批評(píng)家作為構(gòu)建加拿大想象的表達(dá)方式。
從歷史角度看,荒野和動(dòng)物文學(xué)的興起恰逢加拿大聯(lián)邦建立,呼應(yīng)了加拿大這個(gè)新生國家的身份構(gòu)建的需求。波爾克(JamesPolk)是第一個(gè)將動(dòng)物小說和加拿大民族身份危機(jī)相聯(lián)系的學(xué)者。他認(rèn)為,羅伯茨小說中被獵殺的動(dòng)物就是加拿大人作為“受害者”的化身。在潛意識(shí)中,加拿大的身份構(gòu)建總是和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面對(duì)英國的政治影響以及美國的文化威脅和經(jīng)濟(jì)吞并,加拿大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這促使文學(xué)和文化界開始努力尋找身份構(gòu)建的標(biāo)志。文化界對(duì)加拿大身份的不懈追求,總是和“藏匿在灌木叢中的那個(gè)青面獠牙的美國”有著無法擺脫的關(guān)系。美國被想象成一個(gè)捕獵者,因此,加拿大作家“對(duì)迫害癥和存活保持如此高的興趣,也就不足為怪了”③。例如,在行銷全球的西頓(ThompsonSeton)動(dòng)物故事中,動(dòng)物首先是英雄形象,它們“具有悲劇的氣質(zhì)”,這些故事反映了“我們的集體自我形象……展現(xiàn)了我們所說的被動(dòng)的角色模型”④。作為文化反美主義的斗士,阿特伍德認(rèn)為,荒野故事是對(duì)加拿大人“受害者”地位的文化解釋和反映:“英國的動(dòng)物故事寫的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美國的動(dòng)物故事寫的是人類對(duì)動(dòng)物的捕殺,而加拿大的動(dòng)物故事寫的則是被捕殺的動(dòng)物,是從動(dòng)物皮毛之下的軀體內(nèi)部的親身感受。”⑤正如她在小說《浮現(xiàn)》中所描繪的一樣,加拿大荒野受到來自美國工業(yè)化的侵略和污染。小說中借用女性/男性、自我/他者、加拿大/美國、自然/文明的二元對(duì)立講述了無名女主人公的“受害”經(jīng)歷,這使小說成為一個(gè)地地道道的民族和國家政治寓言,通過生態(tài)女性主義的文學(xué)訴說了加拿大的身份追求故事。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加拿大荒野文學(xué)進(jìn)一步把生態(tài)思想和超民族主義相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多元文化主義框架下的民族想象。馬特爾(YannMartel)的小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就是一部關(guān)于荒野和動(dòng)物的敘事。小說結(jié)合了成長小說和殖民/后殖民小說的特征,描述了少年主人公在同自然(大海)、野獸交往的過程中逐步在身體、精神和情感上走向成熟的故事。派接受了自然的洗禮,學(xué)會(huì)了和孟加拉虎理查•帕克的共存,最后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完成了進(jìn)入加拿大文化空間的旅程。派的移民過程和海上存活經(jīng)歷相互交織,是構(gòu)建加拿大民族性的一次精神洗禮和文化儀式。小說象征性地把背景設(shè)置在無國界的太平洋上,還突出描寫了派的多元宗教信仰,這暗示了多元文化主義語境下社會(huì)的多民族和超民族主義特征,展示了民族身份想象的居間性(in-betweenness)。當(dāng)民族的壁壘不再鮮明,與動(dòng)物性的認(rèn)同則成為人類社會(huì)不可否認(rèn)的共同根基。派分別在三個(gè)不同的時(shí)刻喊著“我愛神”“我愛你,理查•帕克”和“我愛加拿大”①,完美地響應(yīng)了派的身份構(gòu)建過程,使他個(gè)人的移民和返回自然的旅程成為一次跨民族的精神旅程,并最終實(shí)現(xiàn)生態(tài)的身份構(gòu)建。加拿大荒野文學(xué)近年來開始“回歸自然”,對(duì)人類主體和動(dòng)物主體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反思,號(hào)召人們“和動(dòng)物主體的認(rèn)同”②。
生態(tài)視野下的加拿大人類社區(qū)和動(dòng)物社區(qū)之間相互交融和重合,動(dòng)物關(guān)懷和動(dòng)物倫理成為加拿大文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表現(xiàn)。在克羅奇(RobertKroetsch)的后現(xiàn)代主義小說《烏鴉的話》(WhattheCrowSaid)中,作者描寫了一個(gè)沒有明確邊界的加拿大西部草原。在這里,動(dòng)物、自然和人相互轉(zhuǎn)換。小說中薇拉和一群蜜蜂交配而懷孕,她的身體被描寫成和世界一樣古老的處女的身體,“沒有任何凡夫俗子能夠滿足她”③,但她卻在蜜蜂的誘惑下產(chǎn)生。薇拉顯然就是加拿大荒野和身份的象征。在早期動(dòng)物文學(xué)中,動(dòng)物主要體現(xiàn)動(dòng)物作為人(animal-as-human)的形象,故事主角是動(dòng)物,他們具有人類行為特征和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這映射了弗萊所說的加拿大移民社會(huì)的“前哨心理”和荒野生存意識(shí)。當(dāng)代加拿大荒野和動(dòng)物文學(xué)主要表現(xiàn)的卻是人作為動(dòng)物(human-as-animal)或者人成為動(dòng)物(becoming-animal)的形象。例如,阿特伍德的生態(tài)小說《瘋狂亞當(dāng)三部曲》(TheMaddAddamTrilo-gy)、約翰•霍華德的《泰•約翰》等。迪恩認(rèn)為,這些故事中所體現(xiàn)的人獸相互認(rèn)可和認(rèn)同的思想構(gòu)建了“一個(gè)意識(shí)形態(tài)網(wǎng)絡(luò)”④。人與動(dòng)物的這種矛盾和并存,正是對(duì)加拿大現(xiàn)實(shí)和歷史的寫照,是加拿大身份想象的重要層面。綜上所述,自然、荒野和動(dòng)物意象在加拿大文學(xué)中具有深刻的文化蘊(yùn)意。荒野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具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表達(dá)了加拿大人和大自然作斗爭的存活經(jīng)歷和與自然共存的生態(tài)思想,也反映了加拿大人的殖民建國歷程以及多民族和超民族社會(huì)構(gòu)成。因此,荒野文學(xué)包含了自然、生態(tài)思想和加拿大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想象構(gòu)建,荒野文學(xué)的繁榮在表層上似乎呼應(yīng)了世界文學(xué)范圍內(nèi)的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倫理思想的興起,而在文化寓言的深層內(nèi)涵上則折射了加拿大人的地方、民族、國家和社會(huì)想象,可謂世界文學(xué)舞臺(tái)上的一枝奇葩。
作者:丁林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