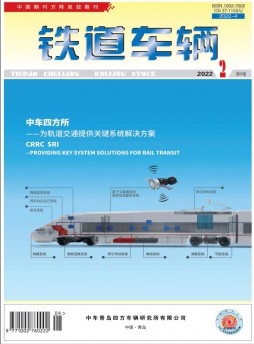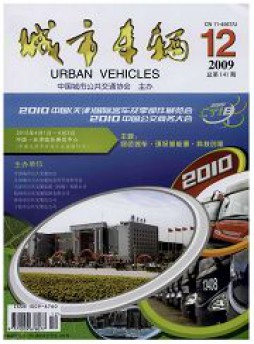車輛借用責任保險合同糾紛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車輛借用責任保險合同糾紛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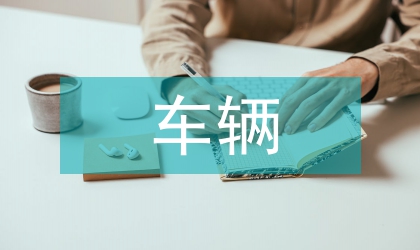
摘要:
合同相對性是合同制度的基石。在車輛借用引發(fā)的責任保險合同糾紛中,對于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的仲裁協(xié)議應堅持合同的相對性,其效力不能延及于車輛借用人,而保險車輛借用人盡管不是投保人,但是有資格突破合同相對性而成為原告。
關鍵詞:
車輛借用;責任保險合同;合同相對性;賠償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家庭機動車的保有量在我國正呈現持續(xù)上升的趨勢。事物的發(fā)展都是兩面的,機動車日益進入尋常百姓家,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堵車和環(huán)境的污染等問題。而頻發(fā)的道路交通事故給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帶來的損失和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威脅則更成為不可小覷的社會問題。對此,其實早有專家斷言:“交通事故已經成為今天國家最大的問題之一”。[1]304在交通事故引發(fā)的責任糾紛案件中,法官經常要面對第三人可否直接對強制責任保險的保險人行使請求權,以及第三人得否直接對保險人主張賠償追索權等涉及合同相對性的理解和處理的問題。例如,車主(投保人)A將投保了商業(yè)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保險車輛出借給C,借用人C在使用中發(fā)生交通事故致使他人死亡并且在本次事故中負全部民事侵權賠償責任。借用人C在對受害人賠償了損失后向保險人主張追償賠償保險金,由此與保險人產生爭議。對此爭議,借用人準備走訴訟的途徑解決,可是借用人與保險人不存在直接保險合同關系,而且車主和保險人之間的保險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在這樣的案件中,法官便面臨投保人A和保險人之間約定的仲裁條款對于車輛借用人C是否適用以及車輛借用人C能否直接對保險人主張賠償追索權兩個涉及合同相對性的問題。
一、關于合同相對性原則
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的法律。合同相對性原則,簡而言之,就是指合同只在簽約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fā)生法律拘束力,對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沒有約束力。特定合同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對合同當事人主張權利,合同當事人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合同債權人只能向合同債務人主張合同權利,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反之,合同債務人也只對合同債權人承擔合同義務,只有合同債權人能基于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合同的相對性最早起源于羅馬法的“債的相對性”理論。在羅馬法中,債被稱為“法鎖”,意指“當事人之間之羈束狀態(tài)而言”。[2]72無論在大陸法系還是在英美法系,合同相對性原則都被視為合同規(guī)則和制度的基石。合同相對性在英美法系中,主要通過兩個原則來體現:其一,只有受允諾人方可強制履行合同。舉例來說,比如甲對乙支付對價,乙向甲允諾,將對丙為一定行為,在乙未能履諾的情況下,由于丙不是受允諾人,其無權申請乙強制履行該允諾。其二,對價必須由受允諾人提供。同樣甲給付對價,乙對甲允諾,將對丙為一定行為,由于丙未提供對價,所以不能強制履行該允諾。
我國《合同法》對合同相對性原則也予以了直接的肯定。該法第八條規(guī)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作為合同規(guī)則和制度的基石,合同相對性原則在具體合同制度中得到廣泛體現,內容非常豐富而又復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主體的相對性,意即合同關系只能在特定的主體之間發(fā)生,只有合同當事人方可基于合同向合同另一方當事人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具體的說,由于合同關系是僅在特定人之間發(fā)生的法律關系,因此只有合同關系當事人之間才能相互提出請求,沒有發(fā)生合同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第三人屬于非合同關系當事人不能依據合同向合同當事人提出請求或提出訴訟。另外,合同一方當事人只能向另一方當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和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合同無關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及訴訟。二是內容的相對性,意即除非法律或合同有特別的規(guī)定,合同規(guī)定的權利只由合同當事享有,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也由合同當事人履行,當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張合同上的權利,更不負擔合同中規(guī)定的義務。在雙方合同中,還表現為一方的權利就是另一方的義務,權利義務相互對應,互為因果,呈現出“對流狀態(tài)”,權利人的權利須依賴于義務人履行義務的行為才能實現。合同內容的相對性又主要通過以下幾個具體規(guī)則來體現。(1)合同賦予當事人享有的權利,原則上并不及于第三人,合同規(guī)定由當事人承擔的義務,一般也不能對第三人產生拘束力。(2)合同當事人無權為他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3)合同權利與義務主要對合同當事人產生約束力,法律的特殊規(guī)定即為合同的相對性原則的例外。三是責任的相對性,即指違約責任只能在特定的合同關系當事人之間發(fā)生,合同關系以外的人不負違約責任,合同當事人也不對其承擔違約責任。
二、機動車責任保險合同的仲裁條款如何適用合同相對性原則
現在不少機動車責任保險合同中設立了仲裁條款。對這些訂有仲裁條款的責任保險合同,一旦在保險事故發(fā)生后引發(fā)糾紛,一個普遍性的但同時也是理論和實務上亟待回答的難題是,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已經存在的仲裁條款是否對第三人有約束力?若以車輛借用案例為例來說明,即是仲裁條款對車輛借用人是否適用?
1、肯定論對此問題,理論和實務界持肯定論者指出,現在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鼓勵和支持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因此,如果過于嚴格堅持合同相對性,認為仲裁條款只能約束合同當事人,對車輛借用人不發(fā)生效力,與現今各個國家度正不斷加大對仲裁的鼓勵和支持的力度的背景背道而馳。為適應仲裁條款的效力出現擴大化的趨勢,應該將仲裁條款的效力擴大到第三人。
2、視情論理論和實務界也有持視情論者。他們的觀點是,既不直接肯定,也不直接否定,而提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具體情況而定。有人以利益衡量為基本理據認為,“是否承認責任保險合同中仲裁條款對第三人的效力涉及到不同利益和不同政策的權衡與選擇,它既關系到第三人對仲裁的同意權,又關系到保險人對保險合同的正當預期;既關系到仲裁法中對仲裁擴大化的支持,又關系到保險法中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因此,只有對所有因素加以平衡才能得出一個較為合理的結果”。[3]128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仲裁協(xié)議的立場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堅持仲裁條款或說仲裁協(xié)議是仲裁得以開始的基石,進行仲裁必須具備書面的仲裁條款或仲裁協(xié)議。沒有通過仲裁條款或仲裁協(xié)議確定的仲裁合意,就沒有仲裁。另一方面,嚴格堅持仲裁協(xié)議相對性原則,認為仲裁協(xié)議只對直接的仲裁協(xié)議雙方當事人產生約束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和第九條規(guī)定,仲裁協(xié)議只在兩種情形下擴張適用到第三人:一是仲裁協(xié)議簽訂后,當事人發(fā)生合并和分立的事實,則原仲裁協(xié)議可擴張適用到該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繼受人;二是債權債務全部或部分轉讓的,仲裁協(xié)議對受讓人有效,除非仲裁協(xié)議當事人另有約定、受讓人在受讓債權債務時明確反對或者不知道有單獨仲裁協(xié)議。
(1)從仲裁協(xié)議的特質出發(fā)看肯定論觀點在各國對仲裁普遍持鼓勵和支持立場的背景下,肯定仲裁條款能擴展適用于車輛借用人的觀點得到較大程度的認同是不難理解的。肯定論者,面對我國現行立法,更是進一步指出解釋法律不僅要從法律的文義出發(fā),更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從法律精神的層面講,認可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延及于車輛借用人,符合保險人的合理期待,因為保險人在保險合同上寫明仲裁條款,一般是希望任何人,只要是依據保險合同向其主張保險賠償金請求權的,都應當受其約束;也符合“禁止反言”(英美法系)原則的要求,因為車輛借用人既然依據保險合同主張權利,那么同時也應當接受保險合同其他條款的約束。我們認為,肯定論者將仲裁協(xié)議與民事合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恰恰忽略了我國仲裁立法關于仲裁協(xié)議規(guī)定的基本精神。仲裁協(xié)議雖然是一種協(xié)議,但它規(guī)定的不是協(xié)議當事人的民事實體權利義務,仲裁協(xié)議是解決爭議的協(xié)議,仲裁協(xié)議與民事實體合同相比較,具有自己獨自的特質或說獨自的精神。仲裁協(xié)議的第一個特質或說精神是它的獨立性。保險合同是民事實體合同,而仲裁條款是有關民事爭議解決方式的協(xié)議。兩者雖然同寫在一張紙上,并通常取保險合同一個稱謂,但從精神來說,兩者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協(xié)議,而非同一合同的兩個組成部分。關于兩者之間的關系,肯定論者常常機械套用合同法,將兩者視為主合同和從合同的關系,在作為主合同的保險合同發(fā)生變更情形時,藉由諸如合理期待或者禁止反言之類的觀點為橋梁,認為,仲裁協(xié)議作為從合同也應當隨之產生相應變更。然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19條規(guī)定:“仲裁協(xié)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除、終止或者無效,不影響仲裁協(xié)議的效力”。解讀本條文的意思就是說,仲裁協(xié)議是獨立存在的,其與保險合同之間沒有主從關系。考慮仲裁協(xié)議時,原則上無需也不應當援引保險合同。就車輛借用引發(fā)的車輛借用人主張保險金追償案件而言,盡管保險合同發(fā)生了某種變化,可這只是保險合同的變化,但不可據此認為,這種變化使仲裁協(xié)議也隨之變化。因此,合理期待或者禁止反言在此是不適用的。仲裁協(xié)議的另一個特質或說精神是它的明示性。也就是說,必須通過仲裁協(xié)議明確表示仲裁的合意。我國現行立法堅持仲裁協(xié)議具有明示性的特征或者說默示從無的特征,要求當事人必須以明確的方式表達仲裁意愿,如果仲裁意愿表達不明,必須通過補充協(xié)議來予以明確,不通過補充協(xié)議予以明確的視為仲裁協(xié)議無效。①而合同法上的合同,則承認默示的成分,當事人沒有明確表述的內容,不能通過補充協(xié)議予以澄清的,合同并不因此而不成立,而是按照交易習慣或者一般原則等予以補充。由此可見,明示性(默示從無)是仲裁協(xié)議的特質和精神所在,除了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例外情形外,對于其不明確之處,不是應當根據一般原則加以補充,而是應當或者通過補充協(xié)議予以明確或者按仲裁協(xié)議無效處理。仲裁條款對車輛借用人是否適用的問題,肯定論者不去管有沒有補充協(xié)議的情形,試圖簡單通過合理期待或者禁止反言原則予以明確,顯然是有違我國立法精神的。當然,這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仲裁協(xié)議為何具有明示性的特征?我們不妨把訴訟和仲裁在糾紛解決中的地位粗略分為兩者模式。一種模式是仲裁和訴訟平等模式,另一種是訴訟優(yōu)先模式。前一種模式中,訴訟和仲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在界限模糊的管轄地帶,誰也不優(yōu)于誰,可以相互競爭,客觀上需要用一般原則使之明確下來。在后一種模式中,訴訟優(yōu)先,具有侵略性,凡是模糊的地方,不允許使用一般原則來判斷孰是孰非,而是排他的納入訴訟的領域之內。肯定論者所持的觀點,大致來自英美法系,而英美法系對于前一種模式似乎天然有家園之感。可是,我國仲裁法的法律文化土壤,卻是傾向于后一種模式的,在界限清晰的地方,固然是或裁或審,但是在模糊之處,國家司法管轄優(yōu)先而不是民間仲裁優(yōu)先,這在有強職權主義傳統(tǒng)的我國是天經地義的,大家都認可其正當性。這基本就是我國仲裁協(xié)議明示性特征的主要成因。從這種理解出發(fā),肯定論者張冠李戴,違背了我國法律規(guī)定的仲裁協(xié)議精神。
(2)從統(tǒng)一司法和提供可預見的合理期待角度看視情論觀點視情論的觀點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一概肯定或否定仲裁協(xié)議對車輛借用人是否適用確實是相對辯證合理的。本觀點試圖在堅持和突破傳統(tǒng)合同相對性原則方面尋求一種平衡,一方面回應了保險合同仲裁條款可在一定條件下擴張適用于第三人的潮流性共識,另一方面也固守傳統(tǒng)合同相對性原則,將保險合同仲裁條款最終對第三人是否適用的問題交由法官根據個案情況自由裁量。但我們認為,這種觀點的最大缺點在于其不利于司法的統(tǒng)一,也不能給當事人提供可預見的合理期待,因此也是似是而非,不宜采取。司法統(tǒng)一是現代法治國家法律適用的基本要求。司法權作為與立法權、行政權并列的重要國家權力,必須做到統(tǒng)一。做不到司法統(tǒng)一,便無司法的公正性可言。司法統(tǒng)一的內容除了行使司法權的主體的統(tǒng)一之外,最核心的內容便是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而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的必然邏輯要求就是要做到同樣的事情受到同樣的處理。簡而言之,就是要求在訴訟中要做到“同案同判”。能否做到“同案同判”已成為人們判斷司法是否公正默認的“試金石”。雖然有如哲學名言所示: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河流,此案和彼案總是可能難以完全相同,但“同案”在人們的觀念中總是相對存在的。面對這些“同案”,老百姓不能容忍同案不同判的結果。由此出發(fā),責任保險合同仲裁條款是否對車輛借用人有效的問題,如果允許法官根據個案情況自由裁量,視情而論的話,必然會出現差不多的"同案"情況,由于法官的視角不一,一些案件認定為有效,一些認定為無效,從而形成司法不統(tǒng)一的局面。與司法不統(tǒng)一的局面形成相伴而生的是,如果持照視情論的觀點,在車輛借用引發(fā)的保險合同糾紛中,無論是車輛借用人還是作為責任險的承保人的保險公司,對于彼此糾紛的解決路徑是不能有合理的預判的,具言之,對車輛借用人而言,其既不知是否要受原保險合同的仲裁條款的約束而不能選擇訴訟方式來解決其與保險公司的糾紛,也不知是否可援引原保險合同的仲裁條款針對保險公司提出仲裁申請。反之,對保險公司而言,情況亦是如此。這顯然不能給當事人提供可預見的合理期待。我們認為,在仲裁協(xié)議對車輛借用人是否適用的問題上宜堅持嚴格的合同相對性。其一,這種做法符合我國現行立法的文義規(guī)定。已如前述,我國現行立法只在兩種情形下認可仲裁協(xié)議可擴展適用于第三人。對于車輛借用人而言,當事人發(fā)生合并、分立的情形顯然是不適用的。仲裁協(xié)議對權利義務的受讓人有效的規(guī)定,初看起來似乎是適用的,因為車輛借用人取得的保險賠償金請求權給人的感覺是來源于車主(投保人)的轉讓。但細究一下,這種感覺似是而非,經不起邏輯的推敲。試想,如果是轉讓,必須以車主自己享有保險賠償金請求權為前提。我們無法想象他(她)能轉讓不存在的權利。而車主享有保險賠償金請求權,又以其對于受害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否則,沒有損害,何來索賠!在車輛借用引發(fā)的車輛借用人向保險人主張追償的案件中,實際情況是,車主(投保人)并不對受害人承擔民事侵權賠償責任,全部賠償責任都由車輛借用人獨自承擔。由此可見,借用人的保險賠償金請求權并非源于車主(投保人)的轉讓,它其實是一種同車主債權一樣原始的債權。綜合上述不難看出,仲裁條款對于車輛借用人沒有約束力的觀點是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其二,這種做法也符合仲裁立法精神。已如前述,仲裁協(xié)議具有獨立性和明示性,車輛借用人沒有在載有仲裁條款的保險合同或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單獨的仲裁協(xié)議上簽字,其和保險公司之間沒有明確的保險合意,堅持仲裁條款對于車輛借用人沒有約束力的觀點符合仲裁立法的精神。綜合上述,無論是從法律的文義理解出發(fā),還是基于從法律的精神,車輛借用人沒有在仲裁條款上面簽字,在車輛借用人沒有同保險人補充達成新的仲裁協(xié)議情況下,車主(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仲裁條款對車輛借用人是不適用的。
三、車輛借用人對保險公司主張賠償追索的合同相對性分析
車輛借用人并非責任保險合同的當事人,車輛借用人能否直接對保險公司主張賠償追索,換言之,車輛借用人是否具有原告資格是理論和實務上亟待回答的難題。對于這一問題,商業(yè)第三者責任保險第六條的規(guī)定是: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中發(fā)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等,對被保險人依法應當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依照保險合同的約定,給予賠償。關于本條款的理解,保險人一般會認為,保險人只對被保險人的第三者責任承擔賠償責任,對被保險人之外的車輛借用人不予賠償。因此車輛借用人沒有資格向保險人索賠。與此相反,車輛借用人認為,上述規(guī)定第六條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亦即條文的前一段規(guī)定,如果被保險人或者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對第三人侵權而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那么應當由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但不足之處在于,本條文的后一部分亦即條文的后一段僅規(guī)定對于被保險人的侵權賠償責任,保險人在保險責任范圍內予以賠償。前后段不對稱。前段肯定了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也承擔賠償責任,后段卻只規(guī)定對于被保險人的侵權賠償責任,保險人在保險責任范圍內予以賠償。前段引起了問題,正常的人都會期待后段給出答案。后段的答案和前段的問題之間明顯不對稱,不周延。前段提出的問題,除了針對被保險人的,還有針對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的。但是,后段給出的答案卻只有針對被保險人的,沒有針對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的,隱含了合同漏洞,需要通過解釋予以填補。填補內容適宜表述為:被保險人允許的合法駕駛人,按被保險人對待,保險人在保險責任范圍內予以賠償。由此填補內容出發(fā),車輛借用人作為被保險人允許的合法駕駛人無疑是有權直接要求保險人賠償的。
車輛借用人的直接索賠資格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朱永琪訴天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州吳中區(qū)支公司、第三人吳建偉保險合同糾紛案①中得到了明確肯定,該案的判決要旨在于:車輛所有人將投保商業(yè)三者險的車輛借給他人使用發(fā)生交通事故,借用人向第三者承擔賠償責任后,具有保險金請求權,保險公司應當向車輛借用人承擔保險責任。因此,肯定車輛借用人具有直接索賠資格的觀點是合理正當的。合理期待原則便是支持上述裁判要旨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理由。投保人為車輛投保第三者責任險之目的希望保險人承擔交通事故中不特定第三者損失,而不管這一損失的導致者究竟是投保人、被保險人、車輛所有權人還是其允許之合格駕駛員。這是社會的合理期待,對此合理期待,應當受到保護。合理期待原則無疑是能夠成立的,但是司法實務中,我們不能停留在原則的層次,需要予以具體化。投保人不但是為自己利益而投保,同時也是為自己允許合法駕駛人利益而投保,從合同法理的層面來看,其實就是說這種合同是為第三利益而訂立的合同,具有利他合同的性質。因此,合理期待原則可以轉化為利他合同的本然之理規(guī)則。對于利他合同,我國《合同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都有規(guī)定。在保險合同和信托合同中,由于法律的特別規(guī)定或者合同的特別約定,第三人(包括被保險人、受益人以及信托受益人)突破合同相對性的限制,成為了合同當事人,享有相應的請求權。責任保險合同也具有利他合同的性質,因此車輛借用人可以成為享有賠償保險金請求權的當事人,是具備原告資格的。需要提及的是,有的論述運用了另外一個支持理由。這個理由是:車輛借用人具備原告資格符合類推解釋的要求。因為保險法規(guī)定,保險標的轉讓的情況下,保險人對保險標的轉讓之后發(fā)生的事故原則上要承擔保險責任,既然轉讓了都要對受讓人承擔責任,舉重以明輕,那么對保險標的出借的情形,更應該承擔保險責任。我們認為這個類比難以成立,因為如前所述,車輛借用人取得賠償保險金請求權不是基于繼受,而是屬于原始取得,而類推的觀點似乎將其視為繼受取得了。總而言之,將合同漏洞加以填補之后,被保險人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也應當作為被保險人對待,惟有符合社會的這種合理期待,才能發(fā)揮三責險的應有功能。因此,車輛借用人就借用車輛發(fā)生交通事故所承擔的侵權賠償責任,有權要求三責險的保險人予以賠償,具備原告資格。
參考文獻:
[1][英]科林•史密斯.責任保險[M].陳彩芬譯.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
[2]李宣琛.日耳曼法概說[M].商務印書館,1944.
[3]朱嵬.論責任保險合同中仲裁條款對第三人的效力[J].法學評論,2009(5).
作者:周曉 匡青松 單位:中南大學 法學院
- 上一篇:注冊會計師審計風險控制分析范文
- 下一篇:保險合同會計核算體系研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