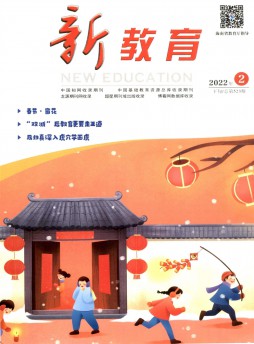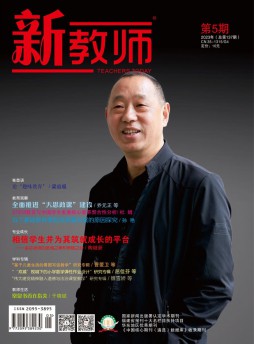《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述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述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一生著述頗豐,研究領域極廣,打破了各門學科之間的那種封閉狀態,往來馳騁于社會學、宗教、哲學,歷史等領域,以其開闊的思路為后人研究注入了新鮮的靈感,開啟了嶄新的理論眼光和研究視角。《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是這一代表之作,本書中韋伯試圖從意識形態、新教倫理的角度探究現性起源的內在動因以及其存在發展的合理性,并反思了現性膨脹所面臨的困境和應對之策。
一、現性在西方的崛起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導論部分,韋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問題:“那些僅在西方文明中顯現出來的典型文化———就像我所認為的那樣,產生于具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發展的現象,究竟是哪些時間的合力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實際上,韋伯就是在提出為什么會在西方出現現性,這應當歸諸于怎樣的環境背景因素。韋伯用一種求逆式的演繹推理,從科學、史學、藝術、建筑、國家政治制度等已經具備了理性形態的方式中對東西方進行了大致的比對研究。韋伯認為現性的擴張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韋伯所要探究的并不是現性概念本身,而是理性背后的精神原因,即從神秘的宗教入手,研究西方宗教改革之后,新教教派的教義所產生的人的精神和思想的轉變過程,包括這種精神所生產的理性思維和行為,及其相關理性形態的組織。韋伯認為:“理性主義實際上是一個歷史概念,它是一個由所有事物構成的完整的世界。我們的任務就是將理性思維這一特殊形態歸于某種精神產品。”
二、新教倫理精神對俗世生活的內滲
韋伯考察了自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以馬丁•路德和讓•加爾文為代表的新教教義,發現新教倫理與理性主義之間的親和性。韋伯認為,路德的“天職觀”和加爾文宗的“預定論”是孕育現性精神的溫床。“天職”一詞的現代意義源于馬丁•路德對《圣經》進行的重新翻譯,這個詞傳達了一種嶄新的宗教精神,馬丁•路德賦予這一概念以全新的意義,即把履行世俗事務的義務奉為個人的道德行為所應承擔的最高形式。出于這一新的意義,“天職”一說給生活在世俗中的人們的各種活動賦予了宗教意味。傳統的天主教注重天國與靈魂的凈化,厭惡和逃避世俗生活,認為熱心于塵世的人就是靈魂的墮落,然而,路德卻認為,修道士的生活作為在上帝面前進行證明的手段非但毫無價值,而且,他們放棄塵世義務,那是自私與逃避現世責任的產物。這一教義是對世俗活動的道德辯護。隨后,宗教理念,特別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入世苦行主義新教從修道院逐漸轉移滲透進塵民世俗生活中,路德的“天職觀”不僅得到宣揚,在加爾文宗教義中,以“天職觀念”為宗教基礎,發展成了占據世俗思想中心位置的“預定論”,即“命定說”。關于預定論,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引述了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綱,“通過他那完全不可思議的判決,永遠地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并控制了宇宙最細微的末節。由于上帝的判決不能改變,因此對于那些他賜予恩典的人來說,他的恩典是無法得到的一樣。”
這表明上帝在每一個人出生之前便決定了他的最終命運。“以為人類的美德或罪孽在決定這種命運時起了一定作用,就是認為上帝永久以前絕對自由地作出的判決,會由于人類的影響而改變,這是一個不可能存在的矛盾。”這些都清晰的解釋了預定論,塵民在世俗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并不會影響上帝的事先預定。這種冷酷無情、毫無人性的教義使信徒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無助感,如果不采取某種方式的轉移和寄托,這種可怕的無助之感便會擊垮人們的希望,吞噬他們的命運。于是,人們轉而在世俗生活中尋找是否被上帝選定的跡象,人們懷有對上帝期待性的信仰,將盲目的聽天由命和消極等待轉變為一種積極活躍的世俗創造活動。人們通過在世俗職業上獲得的成就來確定自己是否被上帝所選定,并以此來佐證上帝的恩寵是否存在。在這種精神倫理前提之下,人們開始了在世俗生活中的苦行主義之路。在修道院式的苦行主義介入世俗生活的這一入世過程同時,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和心理機制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這種苦行主義略帶強制的抑制了人們本能自發性的享樂欲望和浪漫主義情懷,讓人們時刻警醒,不可怠惰。這種新教倫理觀念督促并鼓勵著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的生活并創造自身價值,同時又約束著人們,要時刻自我克制,這套倫理在社會活動中的不斷泛化和滲透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社會氣質,即現性的精神。這一內在氣質變成一種自動的,世俗的力量,合理性的根存于西方社會中。
三、現性的困境與救贖
韋伯指出現代性乃至整個現代文化是由從基督教苦行主義衍生而來的,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所構成的。但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苦行性質的現代行為運作過程中,人們的信仰之花逐漸凋零枯萎。現代性初露機械的工具理性的端倪,它好似隱藏在世俗生活背后的無形之手,將人們局限在各自專業化的工作中,機械地完成任務,放棄了對人自身相關的知識和精神的廣泛追求。如同歌德在《浮士德》這個故事里所隱喻的。現性賦予人類主宰、支配世界和自然的力量,但這是以破壞人類對宇宙的理解和終極的意義為代價的,這是一種惡魔般的殘酷代價。理性以一種無所不在的,不偏不倚的光輝照亮了一切存在之物,文學、詩歌、信仰和神話便消失在這種光芒之中。當現性精神介入日常生活中的時候,它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制力量,控制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準則,助長了一系列現代化組織的龐大秩序的建立,曾經人們渴求從事職業性的工作,而如今我們卻被迫如此,因為我們一出生便在這一秩序之中。當這一理性滲透進文學活動中的時候,以往文學世界所散發的魅力之光卻黯淡了,在現性的約束下,來自心靈深處的那種自發的情感受到了壓抑甚至是禁止,這是與豐富人性的時代的背離,人們對外物的機械的依賴最終以一種無可更改的外在力量統治了人類的思考和行動。正如韋伯書中所言,“對外物所操的心思,應該像一件輕輕地披在圣徒的肩膀上的單薄外套,隨時可以脫下,但是造化弄人,竟然使這件外套變成了一間像鋼鐵一般堅硬的牢籠。”如何能逃出這一后知后覺的牢籠?韋伯援引了詩人席勒的一句話,德文翻譯后的意思即,消除事物的魔力。韋伯就像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合理性的灰暗天空下把自己的魔杖埋藏起來的魔法師,以他非專職化的視角,用一種“去魅”的方式為我們繼續尋找出路掀開了一角亮光。只有意識到現代性是如何根存于人們內心并驅使人們活動的,我們才有可能規避機械性的現代化。這種機械性質的心理機制和行為機制是摧殘人的,使人們在特定的社會分工中喪失了他們豐富多彩的天性,完全歸屬于規律性極強的工作和生活中。“個人職業責任的理念,如同已經死去的宗教信仰的鬼魅,在我們的生活中游蕩。”
人們所肩負的責任沒有由個體自身所控制,反之,猶如一股沖擊力強迫性的讓個體去實現,這不再和精神、文化的最高價值有什么直接聯系,似乎也根本不需要追求什么更高的精神文化價值,漸漸脫離信仰倫理的現代精神,轉而趨向于和純粹的塵俗欲望一脈。韋伯回溯式的去魅探究過程,最后拋給我們一個未成定論的難題,這是一次對現代性文明時代的預判和診斷,“社會上到處都充斥著沒有精神的專家,沒有信仰的聲色沉迷之徒;這樣的凡夫俗子,竟然自負自己,已經登上了人類未曾達到過的最高文明階段呢。”的確,我們需要一次個人情感的復歸,敲醒那些即將麻木的人群,以防止機械性的僵化現象在現代社會大行其道。我們也需要重新肯定自身存在的價值,審視審美價值的標準,而不是讓現性全權做主,成為神秘必然性的立法者。
作者:邵越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 文學院
- 上一篇:學術資本主義下大學生就業問題分析范文
- 下一篇:循環累積因果論與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