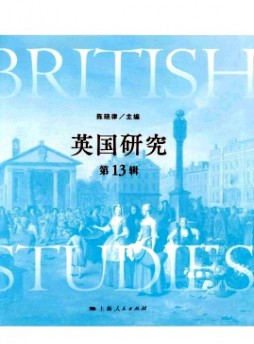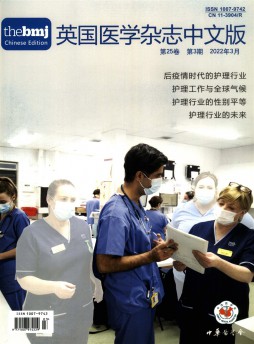英國工人階級的憲政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憲政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協會最主要的理論家和演說家瑟爾沃爾(JohnThelwell)認為:“英國的憲政可以被正確地定義為一個民主政體,同時在立法上容納了一些貴族制的混合,采納了一個世襲的首席執政官來負責法律的執行,這個人就被稱作國王。”⑤但當有人指責倫敦通訊會社無視君主和貴族所享有的傳統特權時,協會進行了堅決的回擊,“不管是誰,如果想將‘不要國王,不要議會’的口號歸罪于我們(我們只想恢復我們國家失去的自由),那都是故意的,無恥的和邪惡的謊言。”直到1795年,協會領導人阿希利(JohnAshley)繼續公開聲明倫敦通訊會社要“堅持不懈地努力,不是去推翻,而是去恢復和實現憲法。”⑥1837年爆發的憲章運動是近代英國工人激進主義運動的最高峰,被列寧稱為“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憲章運動從本質上看是頗具英國特色的運動,它在許多方面都與常規意義上的“傳統主義、立憲主義,甚至保皇主義的歷史有關。”雖然在運動中一些工人領袖和演說家發表了大量的演說,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反對政府的壓迫,但運動中主要的斗爭方式仍是群眾集會和向議會請愿:“憲章派實際上對合乎憲法和合乎法律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極為敏感的(法律是那些腐敗分子指定的),可是他們仍然做到不僅在別人看來不違憲(他們對憲法更廣泛的定義),而且盡可能合法。這樣做的部分目的就是想把道義的力量都集中在自己這一方。”
這不僅反映出憲章派希望在同統治階級斗爭時取得道義上的優勢,也說明了工人階級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憲章派的領導人之一、《憲章運動史》一書的作者甘米奇就指出:“今天,還有什么明智的人,會把君主制度看作是民間疾苦的根源呢?倘若明天廢除了君主政體,而讓勞資間的基本關系仍保持在現有的基礎上,那么,你實際上就是毫無所獲。”⑧2.訴諸傳統,而不是抽象的自然權利和法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形成鮮明對比,英國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是在恢復傳統憲法、堅持英國人自古就有的權利的旗幟下要求政治改革的,更多地是求助于傳統的先例,而不是抽象的自然權利理論。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和潘恩的《人權論》對早期英國工人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英國工人運動的歷史中,共和主義思想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當時的許多英國人來說,他們是從立憲主義文化中汲取思想養料,撒克遜人的先例為君主立憲制、以男子普選權為基礎的自由議會和法治提供了合法依據,因此如果將改革的要求放在所謂“不言而喻的真理”上去,這種做法不僅是令人震驚的,其含義也是危險的。正是在憲政思想上的分歧,使許多工人階級政治團體與潘恩的思想保持了一定的距離,當設菲爾德的改革派亨利•約克(HenryY-orke)在1795年受審時,他為自己辯護道:“在幾乎每一次演說中,我都竭盡全力反駁托馬斯•潘恩的信條,他否認我們憲政的存在。……我始終反其道而行之,我認為我們有完美的憲政……即從我們的撒克遜祖先和不朽的阿爾弗雷德那非凡的心靈中孕育而出的高尚的政府。”
倫敦通訊會社的領導人之一約翰•巴克斯特(JohnBaxter)在1796年還專門出版了一本長達830頁的《新編公正英國史》,他將撒克遜人的先例幾乎等同于自然狀態、高尚的蠻荒時代和原始社會契約,而且最初的政體肯定是自由的。如果說工人階級在尋求改革上與潘恩找到了共同點的話,那么在尊重傳統上,工人階級卻與自己的敵人—保守主義的鼻祖愛德蒙•柏克(Ed-mundBurke)殊途同歸。柏克曾這樣描述英國人的自由:“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我們憲法的一貫政策都是要申明并肯定,我們的自由乃是我們得自我們祖輩的一項遺產,而且是要傳給我們的后代的。那是一項專屬本網過人民的產業,不管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優先的權利都是些什么,我們的憲法就以這種辦法而在其各個部分之如此巨大的分歧性之中保持了一種統一性。我們有一個世襲的王位,一種世襲的貴族制,以及從一個漫長的祖先系列那里繼承特權,公民權和自由權的下院和人民。”⑩對比倫敦通訊會社將憲法稱之為“我們的先輩以生命的代價為我們爭取的憲法”,可以看到,尊重傳統不是哪一個特定階級的價值觀,而是英國整個民族的共識。尊重傳統本身其實就蘊含了對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消極否定,所以在英國歷史上,極端的激進主義歷來就沒有廣大的市場。對于廣大的英國勞動人民來說,自身的權利是自己的先輩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并不需要什么抽象的理性來證明。3.要求社會公正,但不謀求改變財產私有制度工人階級要求議會改革的目的是最終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但從未提出過平均財產,推翻私有制度的綱領。倫敦通訊會社剛成立就聲明:他們決不是平等派,絕不主張財產平等。設菲爾德知識會也曾宣布:“我們不講虛幻的財產平等,實行財產平等會使世界荒涼倒退,退回到最黑暗最野蠻的洪荒年代去。我們所要的平等,是把奴隸變成人,把人變成公民,把公民變成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曾提出了土地國有的綱領,但卻從未提出其他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憲章運動后期的主要領導人瓊斯(Jones)在1856年曾說過:“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我說財產分配得太不均了,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分配。我不主張平均享有財產,也不相信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這樣主張,但我不懂為什么財產的創造者卻一點財產也沒有。”瑏瑡潘恩雖然對英國的憲政體制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和徹底的否定,但他并不支持經濟上的平均化。在他的著作中,并沒有對富人的財產權和自由放任學說提出挑戰,他認為在經濟社會中,每個人必須保留雇主和雇員的身份,國家不應該對一個人的資本或另一個人的工資加以干涉。潘恩痛恨等級特權,因為它侵犯了應該根據成績和努力工作來賺取報酬的原則,但他認為高度的經濟平等是不可能的:“那種財產的不平等是一定的。勤勞、優越的天資、細致的管理、極端吝嗇、幸運的機會,都將產生那種效果,而這些都不會招致粗劣的貪婪和壓迫之惡名……財產所要求的是誠實地獲得,而不是通過違法的行徑使用。”瑏瑢總體上潘恩的思想并沒有超出自由主義的范圍。潘恩在社會改革和經濟方面的思想對19世紀的工人激進主義,包括工會運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無論工會成員如何艱苦地與其雇主進行斗爭,工業資本仍被認為是事業的成果,不受政治干預。直到19世紀80年代,工人階級激進主義仍基本局限于這個體系內。
馬克思曾講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瑏瑣英國工人階級在創造自己歷史的時候也必然地要受到時代的限制,它在形成自己獨立的階級意識的同時,也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本民族的傳統思想和文化。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表現出鮮明的憲政主義特色,和英國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分不開的。1.悠久深厚的法治傳統西方學者阿蘭在談到英國憲政的法律基礎時曾說:“在英國,由于缺乏一部以成文法宣示的、被尊為唯一法律源泉的高級‘憲法法’,所以法治在英國發揮著憲法的作用。正是在這一基本意義上英國擁有一個普通法憲法:構成法治的那些觀念和價值均體現和蘊涵在了平常的普通法之中。”瑏瑤普通法所采用的陪審制在培育了英國人民的法治精神和憲政主義傳統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采用陪審制意味著將司法裁判權一分為二,由法官和陪審團共同行使,這種分權機制有助于克服因司法權集中于法官之手而導致個人專斷,防止法律蛻變為少數人壓迫人民的專制工具。我們知道,通過分權以達致權力制衡進而消除和防止專制是憲政的根本目的,陪審制顯然是與這一憲政要求相一致的。陪審制使普通民眾得以直接參與司法活動,成為社會成員參與國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托克維爾在評價陪審制時指出:“陪審制度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應當把它看成是人民主權的一種形式。……猶如議會是國家的負責立法的機構一樣,陪審團是國家的負責執法的機構。”“主持刑事審判的人,才真正是社會的主人。實行陪審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質上就是陪審制度把領導社會的權利置于人民或這一部分公民之手。”
在工人階級與政府的斗爭中,陪審制度的確提供了許多有效的保護,使得工人階級可以在憲法許可的范圍內與統治階級公然對抗。在1794年10月托利黨政府組織的對倫敦通訊會社領導人的政治大審判中,雖然政府使用了各種手段,但一向具有激進主義傳統的倫敦陪審團最終仍是宣判哈迪等人無罪釋放。這樣的例子在以后的工人運動中也時有發生,在激烈的階級對抗中,陪審制度事實上起到了一個仲裁的作用,得以使雙方避免訴諸最后的暴力手段,就如托克維爾所說:“事實上拯救了英國的自由的,正是民事陪審制度。”瑏瑦其次,陪審制有提高國民法律素質和道德水準的功能,可從文化層面上促進憲政傳統的成長。陪審團制度教育人們做事公道,教導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沒有這種氣魄,任何政治道德都無從談起。陪審制度,特別是民事陪審制度,還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維習慣進入所有公民的頭腦。而這種思維習慣,正是人民為使自己自由而要養成的習慣。這種制度教導所有的階級要尊重判決的事實,養成權利觀念。否則,人們對自由的愛好就只能是一種破壞性的激情。陪審制度賦予每個公民以一種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對社會負有責任和參加了自己的政府。陪審制度以迫使人們去做與己無關的其他事情的辦法去克服個人的自私自利,增強國民的社會責任感。所以,托克維爾把陪審制稱為“一所常設的免費學校”,他說:“我把陪審團視為社會能夠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勛爵曾這樣評價陪審制度:陪審是這樣一種工作,它為一般人上了有關公民權的最有用的一課。它是一門在以前800年間代代相傳的課程。被任命為陪審團的英國人在主持正義方面確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的同胞有罪還是無罪,總是最后由他們來決定。我相信,參加這種司法活動對于培養英國人的守法習慣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其他任何活動。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曾把它說成是“有利于國家和平發展和進步的一種最強大的力量”。
陪審制培育了人民守法紀、負責任、重寬容、尚妥協等社會美德,而這些美德又是憲政制度賴以建立和運行的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礎。在憲章運動中因為策劃和領導新港起義而被判處流放的約翰•弗羅斯特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到:“毫無疑問,雖然政府反對我的政見,但是如果不經過合法的定罪手續,它也不會堅持要給我懲處的。法律是英國人能夠引以為豪的惟一保障;我要指望重返祖國,也只有指望法律給予保障并付諸實施。”瑏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英國決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全體英國人民的共識,這個共識是英國能夠實現和平變革的最有力的保障。2.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英國的憲政是一種自由主義憲政,個人權利理論構成了英國憲政的理論基礎,它體現了以英國為開端的西方憲政的核心觀念:“人類的個體具有最高的價值,他應當免受其他統治者的干預,無論這一統治者為君王、政黨還是大多數公眾。”瑏瑩當我們研究為什么英國能走出一條和平變革之路時,不能忽視的一個事實就是,19世紀時英國憲政制度的建設和人權水平,即使是以現在的標準來衡量,都是很先進的。18世紀著名法學家布萊克斯通在其名著《英國法釋義》一書中指出:“英國法與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現代憲法不同,與羅馬法的精神也不符,因為后兩者基本上只是那些國家的王室或某些國家的大公為了實施專制霸權控制他們治下的臣民而指定的。而自由的精神已經深深植入我們的憲法,甚至在我們的國土上牢牢生根。”“英國憲法可能是世上惟一一部僅以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為管轄對象并以實現這種自由為終極目標的憲法。這種自由的主要特點,確切地說,應當是一種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做任何事的權利。”瑐瑠在書中布萊克斯通列舉了三種“英國人的絕對權力”,即“人身安全權”、“人身自由權”和“私有財產權”,而當這些權利受到侵犯時,每個英國公民都可以通過要求正規的司法程序、向國王和議會請愿,乃至擁有及使用武器進行自衛等方法捍衛自己的權利,“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除了我國法律對其進行的必要的約束外,我們可以充分行使這些權利。”
在19世紀以前,雖然英國仍是一個等級社會,但“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英國人的權利”這些概念卻是整個社會的共識。倫敦通訊會社在1793年的一份演說詞中指出了英國平民和革命前法國平民的地位差別:“我們的人受法律保護,而他們的生命掌握在所有擁有官爵頭銜的個人手中。……我們是人,而他們是奴。”瑐瑢在憲章運動中的一次集會上,一位曼徹斯特的代表宣稱:“他們(蘭開夏的人民)讀了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律評論集》后,了解人民有請愿權;請愿無效的話,有抗議權;再無效的話,還有武裝自己來保衛他們的自由的權利。……蘭開夏的人民做事,沒有不公開的,也沒有不符合憲法和法律的。”瑐瑣通過和歐洲大陸上那些專制主義國家的比較,廣大英國人民更加深了對本國憲政體制的肯定。其次,在英國,自由主義的理念更多地意味著一種消極自由的含義,盧梭式的、“強迫人自由的”公意理論在英國從來就沒有被真正接受。白芝浩在《英國憲法》一書中曾這樣總結:“英國人的自然沖動就是對權威的反抗。……英國人與生俱來的不屈從的天性可能戰勝了那種非常現代的對完美和平與秩序的熱愛。”“英國人最為奇特的特性是,他們討厭掌握著行政權的治人者。”瑐瑤英國人這種對權威的反抗不僅表現在對國王、議會和政府的敵視和權力限制上,也表現在工人運動中工人階級自身的組織原則上。從倫敦通訊會到憲章運動,歷次工人運動在組織上總是民主有余,權威不足,缺少堅強的領導核心。這種現象與其用深厚的民主傳統來形容,倒不如用深厚的自由傳統來形容更確切些。因為,在工人階級的組織活動中,并不存在少數一定要按照多數的決議去執行的傳統,少數始終保持著自己行動的自由和退出的自由。憲章運動之所以衰落,一個很重要的內在因素就是一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作風不民主。由于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傳統對廣大群眾的深遠影響,使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企圖都很難在英國存在下去。憲章運動中一些群眾領袖如奧康諾、瓊斯等人獨斷專行的領導作風,和群眾中出現的一些盲目的個人崇拜現象引起了工人階級中許多有識之士的警覺和反思,意識到工人階級自身的許多局限性和缺點,加深了對現有憲政體制的認同,從早期單純的強調工人階級通過政治斗爭取得政權,逐漸過渡到在肯定現有社會制度的情況下,既有斗爭也有合作的新策略。3.寬松、寬容的社會環境與法國相比,英國也存在階級斗爭,但不存在像法國那樣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不存在一個階級企圖將另一個階級徹底消滅的行為。這和歐洲大陸上的許多國家,乃至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首先,雖然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的政權始終掌握在貴族地主階級的手中,但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英國的貴族階級并沒有享受太多的特權。克拉潘曾指出:“英格蘭從來就沒有為貴族制定過一種法律而為市民階級制定過另一種法律,如歐洲大陸上某些國家所做的那樣。”瑐瑥托克維爾在將英法兩國的貴族體制加以比較后指出:“18世紀在英國享有捐稅特權的是窮人;在法國則是富人。在英國,貴族承擔最沉重的賦稅負擔,以便獲準進行統治。”
財產的所有者,不僅享受不到賦稅豁免權,還必須向教區內貧窮失業的人提供幫助。濟貧法不僅很大程度上保護社會避免了饑荒的侵襲,也提高了統治階級的威望,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憲章運動興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企圖對濟貧法的修改。在許多人看來,這不僅是對窮人的迫害,也是對傳統的違背。歷史學家哈孟德夫婦通過三個不同人物對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進行了描述,一個英國學生,一個在1835年到訪的德國教授,和一個在1845年游覽英國的法國人,他們一致同意,英國的窮人比大陸上生活的窮人條件要優越些,英國的工人和技工在吃喝,還有服裝上都要優于其他的國家,他們的妻子和孩子穿的也更好,更便宜。而且有許多廉價的出版物可看。其次,對彼此權利的尊重使斗爭中對立的雙方一般都能將行動控制在理性的范圍內。在憲章運動時期,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拉塞爾勛爵(Lor-dRussell)曾就工人階級的集會發表了這樣的意見:“他提到了當時正在全國舉行的公眾集會。也許有人想要取締這些集會;但這不是他本人的主張,也不是他們參與的政府的主張。他認為人民有集會的權力。如果他們沒有冤苦可訴,那么他們憑自己的常識就能糾正過來,停止舉行這些集會。政府應當害怕的,不是自由言論,不是無約束地發表輿論。可怕的是,人們在壓力的逼迫下秘密結合。這才是可怕之處,這才是危險所在,而不是自由討論。”瑐瑨英國人崇尚自由,但自由對他們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從來就不是無政府主義。英國人在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也尊重他人的合法權利。應該承認,雖然英國統治階級手中也掌握著警察、軍隊等暴力機器,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它的軍事官僚機器要薄弱的多,而且一般情況下較少濫用這些權力,從而也贏得了勞動人民對憲法應有的尊重。當時遍布各地的可以表達憲章派要求的公共手段,如報紙、小冊子、尤其是公共集會,給下層階級提供了發泄不滿的途徑,使其不致轉而采取秘密的暴烈的行動。講壇“為本來會以更加激烈的災難性的形式表露出來的大量罪惡情愫提供一條較為無害的宣泄的渠道;它向當局和統治階級表達人民在想些什么,從而在國家的命運面臨為難和危機時提供無價的幫助以保證國家的和平和安樂。”瑐瑩1833年托克維爾游覽英國時就發現:“你不難聽到某個英國人抱怨貴族特權的膨脹,且咬牙切齒地談及那些剝削他們的人。可當你告訴他去摧毀貴族制,變革繼承法時,他轉身就走。”瑑瑠在工人階級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有許多地主貴族、上層知識分子,也包括一些工廠主出身的中產階級能夠站出來維護工人的利益。事實上正是他們的不懈努力,促成了許多有利于廣大群眾的社會改革,在客觀上緩和了工人階級對國家政權的仇恨,緩解了階級仇恨。與同時代歐洲大陸的國家比較,英國是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開放社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礙把一個社會成員固定在一個不變的社會位置上,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期望經由經濟成功躋身上層社會。這就使得階級融合成為可能,也為階級合作奠定了基礎。英國人民是一個尊重歷史,注重實踐,善于吸取經驗教訓的民族。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和17世紀的英國內戰從正反兩方面給英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經驗和教訓,信仰和階級利益上的不寬容導致的只能是苦難。正是伊麗莎白女王的宗教寬容政策使英國人民團結起來,從而走向世界強國的地位,而克倫威爾的所謂共和國卻成為了英國歷史上最為專制的一個時期。光榮革命后,宗教寬容和混合政府的理念幾乎成為了英國全民族的共識,宗教寬容延伸出思想寬容,政治寬容又以思想寬容為基礎,到19世紀英國成為了世界上最為寬容和思想自由的國家。寬容成為了一種政治文化和政治傳統,甚至成為了英語民族的一種民族性格,從而使憲政主義在英國有了一個穩固的思想和文化基礎。而混合政府的理念則意味著對君主、貴族、平民三個階級共同參加國家治理的認可,本質上就是一種階級合作的思想。雖然對選民資格仍有諸多限制,但作為一個階級,工人階級是國家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個要素也是全社會的共識。三一個國家發展道路的形成,歸根結底要取決于廣大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素質水平。只有將憲政文化滲入到廣大人民的生活之中,憲政主義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美國法學家拉塞爾•柯克(RussellCoke)曾這樣評論美國憲法:“憲法不是寫在羊皮紙上的條條。如果一部憲法持久存在,而其他絕大多數成文憲法卻沒有存在許久,那就說明這一文件的成功來自長期確立起來的種種習慣、信念、制定法和利益,并且反映了人們中的優秀分子業已承認、至少是默認的一種政治秩序。簡而言之,憲法并不是創造出來的;它們是逐漸形成的。美國憲法之所以至今已存在兩個世紀,是因為它是從一個多世紀的殖民經驗和若干世紀的英國經驗的健壯根系中生長出來的。”
英國保守主義的鼻祖埃德蒙•伯克堅持認為英國不需要一部(成文)憲法,在他看來,盡管法國的權利宣言寫得很漂亮,但是英國人有自由,法國人卻沒有,因為“沒有(憲政)傳統的支持,一部成文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而有了那種傳統,一部成文憲法就沒有必要。”所以一部成功的憲法首先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可,其次還必須有傳統作為基礎,而憲政傳統的建立則依賴于群眾對司法和政治活動的廣泛參與。因此,可以說能否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是一部憲法能夠成功的關鍵。英國19世紀著名作家斯邁爾斯(SamuelSmiles)在其名著《自助》一書中指出:“一個國家的政府本身通常不過是組成它的社會個體性格的復制品而已。一個高于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必將被拉回到與它的人民素質水平相同的層次,而一個低于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遲早要被提升到與人民素質水平相同的檔次。……一個國家的價值和力量絕非依靠它的制度的形式,而是依靠它的人民的素質水平。”瑑瑢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世界上沒一種政體、一部憲法會是完美無缺的,都需要不斷地改革和進步,但這種進步只能建立在廣大人民自覺遵守和愛護法律的基礎上,否則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樓閣。在近代劇烈的社會轉型中,英國之所以能走出一條和平漸進的改革道路,其議會制度之所以能夠與時俱進、長盛不衰,和英國工人階級的憲政主義傳統是密不可分的。作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英國遇到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問題,工業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平衡,英國的社會和政治體制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一度面臨著解體的危險,但許多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就像一道道的堤壩一樣阻滯了新生事物對傳統社會結構的沖擊,從而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使得國家和社會制度得以作出調整,適應新的社會形勢,保證了社會的平穩過渡。
作者:宋曉東單位:石河子大學歷史系
- 上一篇:破產別除權的權利論文范文
- 下一篇:傳統模式的憲政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