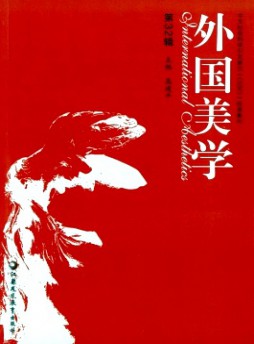美學理論教育的危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美學理論教育的危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哲學與美學辯論”是作者對那些試圖重新闡釋當代藝術的理論進行的分析和討論,主要包括維茨的“開放的藝術概念”、丹托和迪基關于的“藝術界”的理論。在梅吉內斯看來,上述理論嘗試依然沒能解決關于當代藝術解釋的難題,因為即使是丹托的理論,也僅僅是“建立在將美國價值觀引領到最高層面的波普藝術上”②,而對于那些如:偶發藝術、新現實主義、激浪派等遠比波普藝術更加極端的作品則閉口不談,因此他們的理論依然帶有“略顯局限的、簡單化的藝術史視野”。
所以,由丹托這些美學家所代表的英美藝術分析哲學在面對當代藝術的時候同樣也走到了絕路。在梅吉內斯的論辯過程中,關于當代藝術闡釋的難題同樣也隱含著歐陸與英美的差異與對抗,這不僅僅是關于當代藝術形態的差異和對抗(比如波普藝術與新現實主義),同樣也是藝術思想領域的對抗,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暗示的“英美學者和歐陸學者之間的敵意與警惕”,也是造成關于當代藝術論爭中實現真正對話和討論的一個障礙。在本書的最后一部分“藝術、社會、政治”中,作者并沒有直接給出解決當代藝術美學闡釋難題的答案,而是通過描述當代藝術所出現的新趨勢(以1990年代的部分當代藝術創作為例),探討重建當代藝術美學的可能途徑,盡管,至此作者也認為藝術哲學已經不得不放棄那種試圖涵蓋和把握當代藝術創作的“整體性美學理論”,但是可能的藝術美學途徑卻依然是模糊的。面對1990年代以來當代藝術越來越貼近社會和政治的特點,梅吉內斯稱之為“藝術的偏離”,這一點雖然說明作者依然執迷于阿多諾所堅持的藝術本體的思想,但在隨后的論述中他也看到了這種趨勢所具有的打破精英主義、體制壟斷和開辟文化多元主義所帶來的積極意義。
應該說,梅吉內斯的《當代藝術之爭》事實上討論的問題是美學理論在試圖把握當下藝術創作時所面臨的危機,所謂的“當代藝術的危機”也是美學理論所面臨的當代闡釋危機,盡管作者在這本書中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但卻將這個問題的邏輯脈絡進行了清晰的呈現,讓我們在看待和理解當代藝術的時候有更為清醒的認識。關于當代藝術的爭論是否真的可能解決對于當代藝術理解的難題呢?在梅吉內斯所列舉的那些當代藝術的論爭者中,無論其身份是文化學者、哲學家還是美學家,其實大部分都不是專業的當代藝術研究者。盡管他們可能對當代藝術的現象和事件有自己直觀的了解,但從事實上來說由于缺乏藝術史和藝術理論的專業基礎,對于當代藝術的發展邏輯是缺乏認識的,所以其觀點或態度的合法性是令人懷疑的。且不說大部分反對者的思想中都包含著對于過去美學的懷舊和保守,即使是那些支持當代藝術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從當代藝術邏輯出發展開的對于當代藝術的闡釋,所以,梅吉內斯理想中的從藝術本體內部展開的對話和討論從一開始就是難以實現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本書中圍繞當代藝術展開爭論的那些理論和觀點其實都不是“當代的”,而是依然處于利奧塔所說的“現代主義宏大敘事”的邏輯之中,這種“宏大敘事”恰恰是他們在探討和思考當代藝術問題的時候揮之不去的美學情結。對于作者而言,盡管他已經意識到了拋棄這種美學情結的必要性,但在論述的過程中卻始終沒能擺脫他的美學視角。正是這一點,導致了作者在本書中的視野僅僅局限在英美學者與歐陸學者在美學領域中的對抗性關系,雖然他盡可能清晰地概述了兩派關于當代藝術思考的差異,但卻始終停留在對當代藝術表象的描述之上,而沒能真正地進入關于當代藝術的思考,或者按照作者自己的話說:形成從藝術本體出發展開的清理和討論。因為從一開始,他所挑選的對象就僅僅只是從美學立場出發試圖對當代藝術進行闡釋的美學家,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延續著宏大敘事的邏輯踐行著對當代藝術進行系統性整合的嘗試。而那些在實際上處于當代藝術生態之中,對當代藝術進行研究和推進的美術史家和專業藝術批評家卻并沒有真正進入作者的視野。比如,對于像格林伯格這樣的對1960年代美國當代藝術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藝術理論家,作者僅僅是將其作為“近乎教條的形式主義”一筆帶過,卻令人懷疑地沒有分析和探討他在藝術理論上的邏輯情境及其對當代藝術的直接影響,又如何能夠真正從藝術本體來理解極少主義的產生呢?除此之外,像邁克爾•弗雷德在1960年代對于極少主義藝術的闡釋、T.J.克拉克關于極少主義的論辯,以及像羅莎琳•克勞斯、列奧•斯坦伯格等這一批藝術理論家在1970、80年代對于當代藝術的闡述和理論分析等等作者都只字未提,這些都不能不說是探討當代藝術的理論缺失。
無論如何,梅吉內斯的《當代藝術之爭》在探討關于當代藝術的美學闡釋危機的同時,也將當代藝術所面臨的諸多問題展示了出來,其中既有當代藝術自身的問題,也有人們在面對新的藝術形態之時始終存在的理解問題,這些都為我們理解當代藝術提供了思考的途徑。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當代藝術,如同不斷涌向沙灘的波浪,有些在沙灘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或多或少地塑造著沙灘的形狀,而更多的波浪則轉瞬即逝,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對于當代藝術,已經不需要宏大敘事的美學執念,因為當代是一團迷霧,迷霧中的人們很難將歷史的謎題猜透,但卻可以建立起關于當下藝術的基本認知和理解,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雖然不能欣賞每一朵浪花,但也應保持看潮漲潮落的胸懷。
作者:趙炎 單位:中央美術學院美術研究雜志社
- 上一篇:生態哲學背景下的美學理論教育范文
- 下一篇:美學理論教育視角下的大學英語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