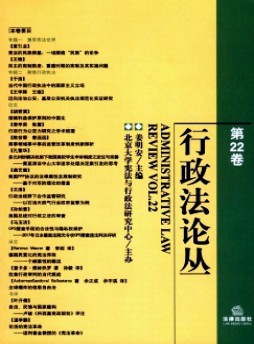從行政法角度審視免職制度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從行政法角度審視免職制度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免職的概念
在國家公務員制度中,公務員的任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免職是公務員任免制度的重要內容。公務員職務任免制度,是指有關國家公務員職務的任用方式,任免機關和任免權限,任免的情形和程序等方面的規定和規范。職務任免是人事管理的重要環節,依法對國家公務員的職務及時進行任免,能實現國家公務員職務任免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對發揮國家公務員才能,保證國家行政機關各職其人,人職相宜,結構合理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
免職是指依法享有任免權的機關或個人根據有關的法律規定,通過法定程序和手續,免除公務員所擔任的一定的職務。免職包括程序性免職和單純性免職,前者是指在委任或聘任公務員擔任新職務之前或同時,免去其原來所擔任的職務。這種免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任用公務員擔任新職務時必經的法定程序,以便將其原任的職位空出,另任他人補充。因此,這里免去原職,是任用新職務的前提。如果不及時辦理免職手續,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人員重疊,即某一職務同時有兩人擔任,二是職務重疊,即某個國家公務員同時具有兩個職務。后者是指以免除現任職務為目的,如公務員退職、退休,長期離職學習,或者因健康原因,能力、水平不勝任而不能堅持工作,或因機構精簡、職數減少、職位撤銷等原因而引起的免職。
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有權免職的主體一是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主要是免去選任制公務員的職務,二是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主要免去委任制和聘任制公務員的職務。但要注意的是,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所做出的免職是一種人事任用方式,性質上與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各級政府的免職一樣(這一點和下文所述其撤銷公務員的職務有著明顯的區別)。但二者的免職還是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免職的依據和范圍不同,前者是依據組織法免去選任制公務員的職務,后者是依據公務員法律法規免去委任制和聘任制公務員的職務。
二、免職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1.免職與撤職。公務員的撤職是指任免機關依據法律法規規定,對嚴重違犯紀律的公務員實行撤銷職務的懲戒。在我國,撤職有兩種,一種是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撤銷選任制公務員的職務,這種撤銷職務的處理方式實質上也是一種罷免,只不過它是由地方各級人大的常委會決定作出,而不是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另一種是行政機關對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處分,屬于對公務員的懲戒,《公務員法》對此已有明文規定。
公務員的撤職和免職雖然在結果上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公務員不再擔任原任職務,無權行使原職權,但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首先,二者性質不同。撤職是一種較嚴厲的人事監督或紀律懲戒,尤其是權力機關的撤職,更是具有罷免的性質;而免職僅僅是一種人事任用方式,本身沒有懲戒性,更不是罷免。其次,二者后果不同。被撤職的公務員除原來的級別和職務工資要降低外,在受處分期間還不得晉升職務、級別和工資檔次,免職則沒有相應的規定。最后,二者對象不同。撤職的對象一般是具有領導職務的公務員,而免職則不一定。
2.免職與降職、降級。公務員的降職是指任免機關依據法律法規規定,通過法定程序,使公務員由較高的職務任較低的職務。和免職一樣,降職也是一種任用形式和任用行為,屬于任用范疇而不屬于紀律懲戒范疇。降職是由于公務員因工作能力較弱或定期考核不稱職而不勝任現職而采取的一種任用方式,一般是降低一個職務層次任職,其待遇按照新任職務的標準執行,因此本人的職責和工資、福利待遇等都要縮小和降低,含有一定的警示、鞭策、負面激勵的意義。而公務員的免職則既可能是含有此種意義,也可能是公務員的正常原因而不再擔任現職。有時免職也是晉升職務或降職的一個必經程序,從這個意義上看,免職是一個過渡性的措施,利于公務員履新,否則會出現人員重疊或職務重疊的情況。與此相類似的一個概念是降級。根據《公務員法》第56條的規定,降級是行政處分的種類之一,性質是較為明確的,在此不再贅述。
3.免職與罷免。公務員的罷免是指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撤銷其選舉的公務員的職務。罷免和免職存在明顯的不同。首先,罷免權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特有的權力,其他任何機關,包括各級行政機關均無權行使罷免權,而免職主要是各級政府的權力,特定情況下各級人大常委會也有此權力。其次,罷免的對象是特定的,它只限于由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自己選出的公務員(即選任制公務員),而免職的對象僅僅在個別情況下才針對選任制公務員,更多的是針對委任制公務員和聘任制公務員。最后,罷免具有一定的懲戒性質或貶義色彩,而免職則無此特點。
三、我國公務員免職制度的漸變
1.免職的性質由用人方式擴展到問責形式。我國免職立法規定不多且較為粗疏,實踐中各地更是各行其是。2002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僅列舉應當免去現職的情形,沒有涉及免職的性質。但從字面仍然可以看出,該條例是遵循了免職作為用人方式的思路。2005年《公務員法》僅在第6章中規定了職務任免,免職是和任用相對應的概念,因此從性質上表明將其納入到用人機制的范疇。2008年《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試行規定》)雖然仍然沒有明確免職的性質,但第一條就明確規定,“為完善公務員職務管理,合理任用公務員,規范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工作”,顯然也表明這是一種用人方式。
但從2007年以后,免職作為一種問責方式逐漸開始在地方的問責法規和規章中出現。如2007年的《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問責暫行辦法》第12條規定行政問責的形式第6項就是“建議免職”;2007年《吉林省行政問責暫行辦法》第18條行政問責的種類第5項就是“免職”;2008年《四川省行政機關首問負責制度》第5、6條都規定的行政部門及負責人的責任就包括“免職”;2009年《南京市黨政領導干部問責辦法(試行)》第8條問責的主要方式第6項是“免職”。甚至到了200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第7條也作了這樣的規定:“對黨政領導干部實行問責的方式分為: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201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以下簡稱《追究辦法》)則將“免職”作為針對在領導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的各種違紀行為進行組織處理的方式之一,是領導干部違法違紀任用人員應當承擔的責任,實質上就是一種問責形式。該辦法第10條規定:“有本辦法所列應當追究責任的情形,情節較輕的,給予批評教育或者責令作出書面檢查;情節較重或者群眾反映強烈、造成惡劣影響的,給予組織處理。組織處理的方式包括調離崗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組織處理的情況,應當在一定范圍內通報。”
2.免職的情形逐漸明晰化、具體化。2002年《條例》第55條規定了黨政領導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應當免去現職:(一)達到任職年齡界限或者退休年齡界限的;(二)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中,民主測評不稱職票超過三分之一、經組織考核認定為不稱職的;(三)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應當免去現職的。但該條例主要針對黨政干部,并沒有針對全體公務員,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其后2008年《試行規定》則詳細規定了免職的情形,該規定第14條規定,公務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免職:(一)晉升職務后需要免去原任職務的;(二)降低職務的;(三)轉任的;(四)辭職或者調出機關的;(五)非組織選派,離職學習期限超過一年的;(六)退休的;(七)其他原因需要免職的。明確列舉了六種情形后,還增加了一個兜底條款,有利于能夠囊括實踐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和新問題。除此之外,該規定還首次詳細規定了職務自然免除且不需要辦理免職手續的情形。該規定第16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職務自然免除,可不再辦理免職手續,由所在單位報任免機關備案:(一)受到刑事處罰或者勞動教養的;(二)受到撤職以上處分的;(三)被辭退的;(四)法律、法規及有關章程有其他規定的。”
3.免職后的重新任用機制逐漸獲得重視并開始制度化。公務員被免職后是否可以重新任職以及如何重新任職,是公務員任免制度的一個重要方面。《公務員法》規定的免職僅僅作為一種人事任用制度,并沒有規定處理后重新任職的問題。《條例》僅僅規定了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干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可以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沒有涉及免職干部的重新任用問題。這也為以后各地政府在推行問責制時更多的使用免職這種方式來變相保護被問責官員奠定了制度基礎。
上文已經提到,2007年以后免職作為一種問責方式開始逐漸納入到各地的問責規定中,但由于缺乏免職后重新任職的規范,因此實踐中免職不僅沒有起到問責的效果,反而變相成了被問責官員的一個保護傘。實踐中有很多這樣的事件,引起了民間和法學界的強烈批評。在此試舉一例:山東省濱州市工商局長邵立勇在全國哀悼日期間公款旅游被問責,但其短時間內復出調任威海市工商局黨組副書記,局長。經查閱,最初對其處理決定為“經濱州市紀委、山東省工商局研究決定,分別給予濱州市工商局黨組書記、局長邵立勇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免去其黨組書記、局長職務”。這里免職處理顯然沒有重新任職的限制。同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12條之規定,“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后果僅僅是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于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免去黨組書記”不屬于該條例13條的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免去黨委書記后果也沒有相關的規定,因此只要重新任職不是晉升黨內職務,即使是黨外升職也不違規,更何況是平級調動。對此,山東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可以信心滿滿回應質疑:調任邵立勇不違反規定。但如此一來,免職作為問責的形式,完全沒有起到問責效果。
另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問責規定都規定了免職作為一種問責方式,因此實踐中免職的適用也是相當混亂。部分是出于對現實的回應,2009年的《暫行規定》和2010年《追究辦法》就正式將免職作為一種承擔責任的形式而加以規范化并明確了免職后的重新任職問題,此舉結束了各地問責規定的不一致的問題。《暫行規定》不僅規定了免職作為問責的一種形式,而且也規定了問責的后果及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重新任職的限制,如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在一定期間內不能重新任職等。該規定第10條規定:“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取消當年年度考核評優和評選各類先進的資格。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貫表現、特長等情況,由黨委(黨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權限酌情安排適當崗位或者相應工作任務。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除應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履行審批手續外,還應當征求上一級黨委組織部門的意見。”《追究辦法》更進了一步,除了規定了免職是一種責任形式,而且還作出了比《暫行規定》對重新任職更多的限制。該辦法第16條規定:“受到調離崗位處理的,一年內不得提拔;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免職處理的,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兩年內不得提拔;受到降職處理的,兩年內不得提拔;同時受到紀律處分的,按照影響期長的規定執行。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免職、降職處理的黨政領導干部,應當綜合考慮其一貫表現、資歷、特長等因素,合理安排工作崗位或者相應工作任務,并同時確定相應的職級待遇。受到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影響期滿后擬重新任用的,在作出決定前應當征得上一級組織人事部門同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追究辦法》僅僅是針對由于違反該辦法規定的選拔任用干部而被免職的領導干部,不具有普遍意義,如因其他原因被免職想要任用則不受其約束。
1.關于免職的規定,黨的文件多于法規規章且法的層級較低。有關免職的規定雖然《公務員法》有規定,但過于原則,主要是黨的文件規定的較多,輔之以行政規章,有時二者聯合發文,這也是我國特有的公務員制度所帶來的后果。但這些黨內規范主要針對領導干部而非全體公務員,因此不具有普遍性;行政規章較少且權威性不夠。即使是2008年的《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在適用上具有普遍性,仍然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家人事部聯合發文,層級也僅僅是規章。雖然黨管干部是我國公務員法的基本原則,但還是有必要將公務員的任免以法的形式加以規定。這一點可以借鑒國務院制定《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對公務員的行政處分加以具體化和規范化的經驗,對關于公務員的任免也應有行政法規進行具體化和規范化,這樣才更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
2.免職的法律性質規定不一致。從最初的《公務員暫行條例》到《條例》再到《公務員法》,免職本來就是一種用人方式和用人機制,本身既不是對公務員的紀律懲戒,也不是公務員的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就沒有那么多的負面色彩。只是在2003年之后,隨著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很多地方開始將免職作為一種問責的手段。從立法到實踐,免職的貶義化十分嚴重。但在各問責法規規章將免職作為一種問責的形式的時候,卻沒有規定免職后重新任用的問題。因此,很多被問責官員的迅速復出,重新任職,極大地沖擊了人們對問責的心理預期,以至于現在一提到免職,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該官員肯定犯事了。久而久之,會固化人們對免職的這種心理,從而無法發揮出免職的本來作用。雖然《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明確了免職作為公務員用人方式的性質,但該《試行規定》本身就是一個部門規章,效力和其他的問責規章不相上下,因此在事實上加劇了法規范對免職規定的不一致。在這一點上,《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對此的認識是正確的。該地方政府規章規定實行行政問責制,但第169條規定:“責任追究形式包括行政處理和行政處分。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理分為:責令限期整改、公開道歉、通報批評、取消評比先進的資格等。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政處理分為:告誡、道歉、通報批評、離崗培訓、調離執法崗位、取消執法資格等。”顯然免職不是承擔責任的形式,說明了立法者對免職有著清醒的認識。
3.缺乏免職程序的規定。《公務員法》雖然規定了公務員的任免,但規定的較為原則,沒有相應的程序規定,也沒有其他相應的行政法規、規章加以明確,導致實踐中免職的隨意性較大,如各地“就地免職”的規定和實踐層出不窮。當然,在各種問責法規規章規定了免職作為問責形式之后,免職的程序也隨著問責的程序建立而建立,但有一部分法規規章本身就沒有規定問責的程序,即使在一部分規定了問責程序的法規規章中,程序依然規定得較少,且仍然沒有專門的免職程序規定。2008年《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試行)》也規定了相應的程序,該規定第15條:“公務員免職,按照下列程序進行:(一)提出免職建議;(二)對免職事由進行審核;(三)按照干部管理權限集體討論決定;(四)按照規定履行免職手續。”但該規定仍然顯得較為粗疏,很多最基本的程序問題,如由誰提出免職建議、誰來審核、按照什么規定、整個免職程序是否有期限限制、被免職者在此過程中能否參與等等都沒有規定。
免職本來就應該僅僅是一種用人方式,這在《公務員法》已經規定明確。該法第40條規定了委任制公務員遇有試用期滿考核合格、職務發生變化、不再擔任公務員職務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職務的,應當按照管理權限和規定的程序任免其職務。分析該規定,可以看出這里的免職情形不可能包含承擔責任的因素,即使有“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職務的”這樣的兜底條款,也無法解釋出其他情形包括承擔責任。但現在的立法和實踐卻沒有遵循《公務員法》的規定和立法精神,強加給它更多的內涵,這是免職概念所不能容納得了的,也是免職概念不應該容納的,“免職”已經越來越偏離了它本來的目的和含義。因此嚴格來說,規定免職是承擔責任的一種方式是與《公務員法》相悖的,現在是亟需修改的時候了。即使是國外,免職也主要是一種用人方式而不是一種懲戒方式。[1]
免職是我國公務員制度中重要的用人手段,本身不帶有懲戒性和貶義色彩。但隨著行政問責制度的興起,免職在我國立法和實踐中逐漸成為一種問責的形式。由于缺乏程序和免職后重新任職規定,致使實踐中免職反而成了被問責公務員的保護傘,從而偏離了免職的本來含義。未來的立法中應該糾正這種做法,以《公務員法》為依據,明確免職的性質就是一種用人方式,既不是對公務員的懲戒,也不是承擔責任的方式,不應具有貶義;其與道歉、訓誡、引咎辭職、責令辭職等責任形式并不是屬于同一層次的概念,將他們放在一起使用,混淆了責任形式和責任后果。尤其,問責立法中應當明確免職不應作為一種獨立的問責形式。如果說免職和問責有關系的話,那么免職應該是問責形式的后續程序或后果之一,如引咎辭職后從程序上進行免職。為了保證立法的權威性,應當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出臺免職(任免)規定,或制定統一的問責法規明確免職的性質和作用,各地方、各部門的問責規定據此進行修改,這樣才能結束各個低層級法和政策對免職的混亂使用,還免職概念以本來面目。同時,免職制度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細化程序規定,要明確具體的免職主體、免職的決定程序、免職救濟、免職后的重新任用等。